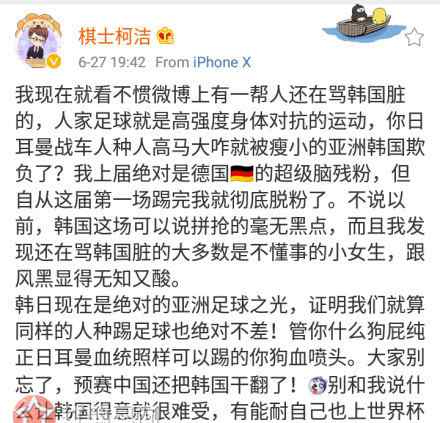牛玉强,北京人,1965年出生。他父母是北京某国企员工,家里有两个姐姐。牛玉强小时候性格内向,老实,害羞。初中毕业,没上高中就呆在家里。当时工厂宿舍大院里有十几个没上学的孩子。他们是黑帮,牛玉强自然“入伙”。在那些孩子中,年龄最大的牛玉江只是一个“弟弟”,一个“死党”。牛的父母认为那些孩子只是在玩。
1983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严打”,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严厉打击危害公共秩序犯罪的运动。同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公共秩序犯罪分子的决定》,大幅增加了6种犯罪行为的量刑幅度,其中流氓罪位居第一。当时全国各地司法机关轰轰烈烈,警察和武警押送罪犯,以示公明。每天都有人被带去参加公断会,“犯罪团伙”每天都被消灭。“严明快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收音机里的高音还在耳边。
刚满18岁的牛玉强偶遇“严打”运动,其团伙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流氓团伙”。牛玉强也被以流氓罪逮捕入狱。不久,牛的家人收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根据判决,1983年5月的一天,牛玉强参加了流氓组织“菜刀队”,当时有8名帮派成员。他参与的犯罪包括:六人殴打刘某某、孙某某,从孙处偷蒙古刀;持枪抢劫一名青年男子和两名同伙,并盗窃一顶军帽;参与砸李家的窗玻璃;聚集三名同伙,威胁并殴打一名名叫徐的年轻人。至于打架对对方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判决书并没有注明。最终,团伙中带头的“首要分子”被判死刑;对牛玉强的判决是:死缓。从此,“流氓”和“严打”成了牛玉强悲剧史上的两个关键词。
1984年,牛玉强等流氓被送到石河子监狱劳动改造。1990年,牛玉强因在狱中表现良好,两次减刑,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然而,经过多年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他患上了严重的海绵状肺结核。同年,在监狱检查下,保外就医,父亲带他回北京老家养病。
1991年,石河子监狱调查组来到牛玉强家。经过评估,我决定续保一年。但是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年...牛玉强等着,检查组一直没来。与此同时,在家休养的牛玉强也逐渐好转。他很少出门,只是呆在家里写思想报告,然后送到派出所、居委会、街道司法所。即使出去几天,牛玉强也会报警。
1996年,牛玉强被介绍给在北京长大的河北姑娘王彩霞。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牛玉强坦白了自己的情况,说自己还是犯人,保外就医。王彩霞认为这并不重要,她只在年轻时打过架,但她对白净英俊的牛玉强一见钟情。1997年,恋爱一年后,他们结婚了。也是在今年,修订后的刑法实施,牛玉强犯的流氓罪被废除。两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给小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增加了很多负担。牛玉强曾经琢磨出去挣钱,但是身体虚弱,没有身份证,找工作无望。这个家庭的收入来自王彩霞的零工,每月花费五六百元。于是牛玉强接手了所有的家务,带孩子。在牛玉强的想法里,2008年只要在家里等到刑期结束,去新疆办理手续,拿到释放证,回来就当个普通人。就这样,一家人过着贫穷和平的生活,但也很甜蜜。
2004年4月的一天,两个“不速之客”打破了平静的一天。他们自称是新疆来的狱警。他们看见牛玉强在家,二话没说就转身走了。那天家里只有牛玉强一个人,他以为只是例行检查。过了两天,两个人又回家了,说要把牛玉强带回来。
牛玉强和王彩霞顿时傻眼了。王彩霞一直在问为什么。狱警回复说,网上通缉牛玉强是因为他没有保外就医,逃跑了。在此之前,监狱多次向北京警方发函,要求牛玉强返回,但没有成功。
“在线通缉?他一直呆在家里,定期汇报!”王彩霞立即去警察局找警察。有了警方的证明,狱警的态度缓和了,说离2008年4月刑满还有4年,应该减刑,两三年就出来了。2004年4月30日,牛玉强被戴上手铐带回新疆。再次回到监狱的牛玉强,对劳动改造充满希望。他只要服完剩下的四年刑期就可以回家,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也能赶上。很快,监狱告诉牛玉强,他10多年的保外就医已经被监狱认定为“在逃未归”,不能算作刑期,所以他还有16年刑期,刑期从2004年推迟到2020年。
截至目前,在石河子监狱,与牛玉强一起入狱的1000多人,要么出狱,要么死亡,剩下的七八人也因未能返回而获得保外就医。自从1997年废除流氓罪以来,十几年过去了,流氓罪的犯人已经很少了。据包括牛玉强在内的近期媒体报道,中国因流氓罪服刑的犯人只有3人,根据刑期,牛玉强将是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牛玉强的“流氓行为”可谓不合时宜。18岁那年,他赶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厉的“严打”,然后被著名的“口袋罪”——流氓罪带上了网。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只是年少无知,参加所谓的“菜刀队”,与阶级斗争,为“帽子”而斗争等等。今天只是治安处罚,最多就是聚众斗殴。
牛玉强的“流氓”帽子让他浪费了半辈子。其中,他的人生有一抹亮色——保外就医让他恢复了健康,找到了爱情,结婚生子,感到幸福。在这短暂而漫长的14年里,他一度有机会摘下这顶可耻的“流氓”帽子,但由于他的无知,他又一次跌入了人生的谷底——他的刑期因为没有保外就医而被推迟到2020年。牛玉强对历史的陌生和荒诞不断地进行解读。从懵懂少年到半岁多,牛玉强还在为一桩早已消失的罪行服刑。他还在为某些权力机关僵化的体制、可笑的错误、呆板的坚持付出代价,他是新中国牺牲青年的“最后一个流氓”。
好人总是基于内心的良知做出常识性的判断。没有犯罪,过了十几年还会继续为此服刑吗?我国已修改刑法,取消流氓罪,然后按原罪名重新收监,继续服刑,直至旧法重刑期满。这样合理合法吗?
为此,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流氓行为。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流氓罪是“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扰乱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规定流氓罪为:“流氓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携带凶器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情节严重,或者流氓犯罪活动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超过刑法规定的最高刑,甚至判处死刑”。此后流氓罪的最高刑罚是死刑,与故意杀人罪相同。
当时,关于流氓行为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目前办理流氓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答复(1984)》指出,流氓行为虽然往往造成公民人身或公私财产的损害,但其本质特征是公然违抗法律和纪律,以残忍、下流的手段破坏公共秩序,包括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社会公共生活。答案详细解释了“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的行为,并规定了刑法“其他情节恶劣的流氓活动构成流氓罪”的六项内容:“1 .利用淫秽物品教唆、引诱青少年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或者经常在社会上传播淫秽物品,造成严重危害的;2.聚众淫乱活动(包括聚众强奸、投宿)、主犯、教唆犯及其他坚持教育的流氓;3.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情节严重的;4.以玩弄女性为目的,采取欺骗等手段强奸众多女性;或者被强奸妇女人数虽少,但已造成严重后果的;5.引诱多名男性青少年,或者引诱外国人与其发生性关系,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6.对幼儿的鸡奸;强行鸡奸少年;或者通过暴力、胁迫等手段。,鸡奸多次,情节严重。”
可见当时流氓行为的适用范围相当广。在实践中,凡是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干扰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都被纳入流氓行为的范围,流氓行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口袋罪”。据媒体报道,“当时流氓行为是口袋犯罪,基本上任何犯罪都可以伪装过去。有人喝多了,在路边撒尿,被判流氓罪;一个年轻人,跟朋友打赌,敢亲女生的嘴,亲了就是流氓行为……”
各地有很多案件从立案到执行,只用了一个星期,可谓是更重更快的案件。但目前没有违法行为,使得当时很多人受到了严惩。人们仍然深深记得那个历史时期为此付出惨痛教训的著名“流氓”。当时,中国出现了两个最著名的“流氓”。一个是著名的电影演员迟志强。1982年,迟志强去南京拍《中秋月圆》时,“几个男孩女孩经常在一起玩,听邓丽君的《甜蜜蜜》,面对面跳舞,看里面的小电影”(迟志强)。当时他们并不在乎这种“超前”的行为是否影响到了其余的邻居,甚至不去想是否引起了邻居的反感。迟志强甚至轻率地和一个女孩发生性关系。结果,当1983年“严打”运动席卷全国时,迟志强和他的几个年轻人在南京的行为被邻居举报为“裸舞”和“男女关系不正当”,并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这件事被媒体披露后,全国一度哗然。江苏省司法厅迅速做出决定:在迟志强案中,涉案人员全部以“流氓罪”处理;迟志强的行为构成流氓罪,被判处四年监禁。
另一个是在三秦引起轰动的秦案。来自Xi的离异单身女性马燕琴性格开朗,善于交际,喜欢跳舞。“严打”前,派出所曾找过马艳琴,问她跳舞的事。马艳琴坦白说,前后几百个男女参加了家庭舞会,也有男的和她发生关系。1983年“严打”后,警方将马燕琴投入监狱,先后逮捕300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陕西日报》在整版的显著位置多次报道此案。因为这个案子太大,很难审结,一直到1984年才逃过“严打”的巅峰。是逃出了巅峰,还是枪毙了以马艳琴为首的三个人,另外三个死缓,两个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就更多了。
今天,男人爱女人是很常见的。迟志强和马燕琴的“流氓行为”恐怕连犯法都不好说,最多是违背道德。如果陈冠希出生在那个时代,他会被枪毙几次。
回头看看这些被打得很惨的“流氓”,让人们重新思考一下我们“严打”的刑事政策。从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确立了“严、严、快”的“严打”政策,到80年代,大规模开展了“严打”运动。一直从事“严打”研究的法律学者秦德良在《严打的刑事政策与历史考察》一文中透露,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犯罪分子102.7万人,检察机关起诉97.5万人,法院判处死刑86.1万人。这是自1950年反叛乱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中袭击。第二次和第三次战斗分别从1984年8月持续到1986年国庆节。三大战役持续了3年5个月。共查获犯罪团伙19.7万个,查处团伙成员87.6万人。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教32.1万人。③
为了达到预设的整顿社会秩序的目标,下级机关或下级行政区域会按照上述要求订立军令(责任书),确定破案抓人指标,或者自上而下下达破案抓人指标,甚至死刑比例。这些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的运动和1983年的“严打”中很常见。毫无疑问,牛玉强就是这种军令中设定的目标。
在那个“流氓”和蚊蝇一样多的特殊时代,说几句下贱的话,唱几句“黄歌”的,是流氓;留长发穿奇装异服者,流氓;亲密过度的男女也是流氓;调戏女人的一定是流氓,打架的也一定是流氓。牛玉强抢别人帽子,砸窗户,和别人打架,被判“流氓罪”。只有今天,回去看看疯癫的历史。因“流氓罪”被错判、重判的错案不在少数。牛玉强只是时代的牺牲品。
尴尬的是,1983年严打的结果,也就是犯罪率下降,只持续了两年,1986年开始上升,一直到1996年。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再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集中的“严打”,而这一次的情况更令人沮丧——刑事案件的发生率在1997年才开始下降,1998年后开始急剧上升,被迫发动第三次“严打”,一直持续到2000年底。1983年、1996年、2001年三次集中统一的大规模政治化、军事化的“严打”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犯罪高峰越来越高,是对这一政策尴尬局面的最好诠释。根据两所高中近二十年工作报告中相关犯罪数据的统计,我国刑事案件总数逐年增加,“严打”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社会秩序。这充分说明,以犯罪分子为敌人、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具有一定阶级斗争形式的中国特色的“严打”,既不能“抓住一切犯罪分子”,也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增长,甚至对防止犯罪过度增长的延缓作用极其有限。
经过三次全国性的行动,法律界逐渐开始反思“严打”行动的初衷、过程和效果。长期致力于宪法研究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佟志伟指出:“法律界对执法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否定或不赞同的较多,这已经是主流认识。人们不赞成严打,主要是因为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治理状态,容易造成普遍的违宪违法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那些照常治国的人治国经验不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后来者看不到这种执法方式对法治的破坏性,看不到它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带来的严重问题,人们就很难一次又一次地理解和接受它。”“平时我们不严格执法,不守法,犯法。如果问题严重,我们将严厉打击。不搞体育不如搞体育,自然很难治理社会。前两次严打运动的特点尤为明显。2001年,除了一些地方,体育特色不明显,是进步。总的来说,运动式打压就像一个不按时吃饭的人。他经常一两顿甚至一两天不吃饭。如果他饿了,他会立刻暴饮暴食。长此以往,这个人的身体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佟志伟教授说,“执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应该是执法机关的正常工作,但严打不是正常工作,与体育执法界限模糊。很容易使用与体育运动难以区分的严厉处罚来执法,导致检察机关和警察在警察的领导下变相合署办公,权力失控的局面。也容易形成纵容刑讯逼供等侵犯被告人及相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况。重刑也是导致量刑过重,冤假错案频发的原因。"
“严打”之后,法律界开始反思流氓行为。其“口袋罪”严重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因此,1997年修订的《刑法》取消了流氓罪,将其分为强制猥亵和侮辱妇女、猥亵儿童、聚众淫乱、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在这些犯罪中,最高刑罚只有有期徒刑。
1.《牛玉强 牛玉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流氓罪反思》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牛玉强 牛玉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流氓罪反思》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fangchan/6721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