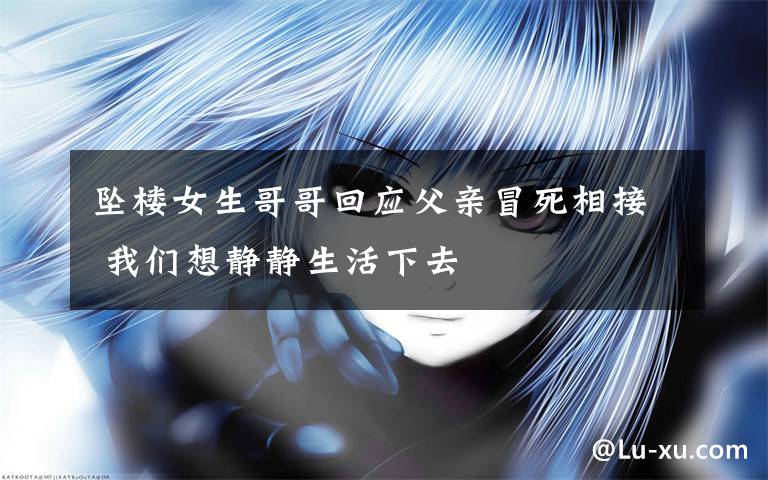图为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尹雪云中篇小说集《我的叔叔李海》
13
我父亲在1997年冬天去世了。他父亲去世的那天是他和母亲结婚50周年纪念日。
我越来越迷信了,从父亲的葬礼开始。古语有云,生不能生,死不能死,但有些人的死亡日期会和人生的一些关键节点重合。这是一种表达。
我父亲不止一次告诉我,他会为他母亲存些钱。他说他妈穷一辈子,但是从来不捡钱借钱,从来不停手,不管大的钱小的钱。
妈妈从来没有因为钱而“泄气”。
父亲的言外之意是,百年之后母亲不应该贫穷。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不这么认为。我不耐烦的说:“养孩子有什么用,不是有我们吗!”
我说这话的时候是90年代中期,李海叔叔出现之后。那时候孩子还小,父母一直住在我家。有一天爸爸出去剃光头,回来摇摇头告诉我他要去窑里当帮工。比方说,一个月要800元。
我一听就急。说你没跟人说过脑出血?你没告诉任何人你因为工作摔断了一条腿吗?你没告诉任何人你腿上有三颗钉子?我给我爸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终于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父亲和孩子低着头坐在沙发上,看上去闷闷不乐。妈妈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说:“他还能听你的。如果我说了,他会带着铺盖卷逃走的。”
我说:“人都七十多了,还能跑到天上去吗?”
换来的是父亲脸上的苦笑,深深的孤独感埋在他脸上的苦笑里。
我上班的时候被告知父亲快死了。我打车冲回家。我的亲戚二娘正走出门槛。她看到我,挥挥手说:“你去看看,二姑娘额头的皱纹都开了。”。
我问二娘怎么办。二娘说,招呼人,给你爸穿衣服。
我父亲平躺在炕上,显然快死了。我把目光集中在他的额头上,皱纹平平,变成了白色的印子。他脸上浮着一层汗,但汗是凉的。父亲闭上眼睛,不管有没有呼吸。我附在他耳边说:“爸爸,我回来了。你能听到我吗?”父亲一点反应都没有。怔了一下,又俯下身说:“爸,要不要通知李海叔叔?”
父亲的眼球突然鼻子底下长了根骨头,然后眼角流出一滴眼泪。父亲的眼泪让我很难受。我把脸贴在父亲的脸上,放声大哭。我妈妈抱着裹尸布从另一个房间走出来,把我拉开。就在这时,父亲把最后一口气留在了嘴里。
事后,我妈说,谁把最后一口气泼在脸上,谁一辈子倒霉。
父亲的葬礼简单明了。当时村里讲究“吹”,唱大丧,穿白的白的。我们只是告别父亲的黑纱。我就不提我和父亲最后的对话了。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没有人想到通知我叔叔,我叔叔上次出现在我家已经五年了。
我偷偷告诉上帝,我父亲一生乐于助人,他不仅养活了叔叔一家。不管谁有困难,他都会尽力去争取。村里那么多家庭,没有一所房子是父亲从未离开过手的。父亲是瓦工或木匠。
如果上天有眼,就送他一场雪吧。
从火葬场回来,雪突然飘上空。雪花稀稀落落,却雄伟壮观。他们走在空里跳舞,好像在表演某种仪式。我把脸贴在窗玻璃上,贪婪地看着远方的荒野。灰色的天空,麦苗蛰伏在冻土里,大雪对它来说是一种温暖。但我相信大雪是为父亲降落的,因为在送我的路上,我一直在祈祷,上帝一定从心底听到了我的声音。
在去墓地的路上,我六岁的女儿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问:“你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吗?”
女儿简单地说:“我知道,死亡是在埋葬坟墓。”
回想几年前,我爸妈看我的眼神很悲伤。他们从不抱怨,但是看着我心里的一些想法就会流露出来。因为我还没结婚,什么都没做成。虽然各种文字总是被发表,但丝毫没有改善我的生活状况。我住的村子越来越诡异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小说被改成了电视剧。导演和县领导谈协议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说这部剧一定会拿飞行奖。整个地点选在离县城不远的山区,但是我一次都没去工作室。我不喜欢电视剧,也不喜欢电视剧。天气突然变冷了,他们可以闹一场,因为他们不能送军装。但是县里的领导都喜欢。他们有负责联系船员的人。戏演完了,我的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其中许多问题包括治疗,甚至婚姻,
我必须用这些来安慰我的父亲,否则,我的父亲会想念他在另一个世界的眼睛。
日子就是过不去,很多年过去了。
14
自从在家里买了车,每年从东到西跑高速就成了习惯。听说京承高速风景不错,就一直在努力看沿途的风景。北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我们乘着闪电路过五环路,一路航向承德。去之前除了旅游真的没想到别的。承德只是我身边的一个城市,和其他城市没什么区别。在离开之前,司机严先生提醒我想一想承德有什么朋友想去看看,并带一份礼物给别人。我在给一件外套缝扣子,有点不耐烦。我说:“只是出去走走。没那么麻烦。”司机严先生是个无故障的人。当然,他还有一个身份,我老公。
我说:“承德对我没有吸引力。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
我有一句口头禅:没去过的地方就要去,没旅行过的地方就要去散步。
站在承德最繁华的大街上,突然有点恍惚。这些场景我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高楼、公园、电影院、小吃店。时光飞逝30多年,它们浮现在我的记忆里。似乎,三十多年前他们一直是这样,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没费多大功夫就知道这种熟悉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这座城市曾经让我梦寐以求,我和很多朋友分享的梦,永远储存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也许他们都忘记了,但作为一个梦想家,我没有忘记。年纪越大,记忆越清晰。
那些梦当然和李海叔叔有关。
当我清楚的知道李海叔叔家在深山里的时候,我告诉朋友,我叔叔家住在一个大城市,高楼大公园,电影院旁边,阿姨在店里卖心脏,家里的零食可以当饭吃……我梦里的城市是承德。目前我在车流人流中,想着很多遥远的往事。我踢毽子,周围好多孩子。他们都对我叔叔和他的家人很好奇...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从小就撒谎,好像天生就有那种虚荣心。我叔叔的家人住在城市或山里。和我或者我的朋友是什么关系?通俗点说,不是一毛钱!
大叔因为住在城里会更受尊重?还是因为舅舅住在市里,我会受到高度重视?是的,我有理由相信,当奶味糖被咬成很多块分发出去时,它来自一个城市或一个山村,给人一种不同的感觉。因为首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一颗来自深谷的糖果在每个人的嘴里味道都会淡很多。时隔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儿时的朋友是很多头两盏灯,我很高兴能得到芝麻那么大的糖果。如果他们知道我把糖果埋了,如果他们把整个糖果都含在嘴里,他们就不会觉得那么甜了。
是的,一定是这样!
但是我的家人欢迎我叔叔,不是因为他来自哪里!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被叔叔领着去花园找我爸爸,他正在掐烟叶。我眼疾开始的时候,发现舅舅身材高大,白白的,眼睛很沉,背很大,一点也不乱。他穿着毛蓝色中山装,完全是干部风格。我的爱无以言表,那时候我对舅舅的背景一无所知。
等等,这些表象都是在说明大叔本人就是他自己的背景?我喜欢的不是大叔,而是大叔的背景?我喜欢背景里的舅舅是因为喜欢他的背景?
故事是在旅行过程中人为添加原材料和底色。我从自己身上想到了父亲。父亲对叔叔的感情,一开始肯定是源于自然,但深入之后又加上了自己的元素就不得而知了。年复一年的等待和欢迎,现在想想,太隆重了,太温暖了。大叔就像一个展品,或者一顿大餐,或者一个牌子,几年来已经成为我们家正月初一的象征。有了这个标志,我们的家庭在邻居中就不一样了,甚至增添了一些荣耀。大叔一定是从这个标志性的身份意识到了什么,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渐渐偏离了自己的渠道。
于是大叔成了我们家的象征,或明或暗。
我突然想到,其实更像是一个阴谋,扭曲变异了一种原本单纯纯粹的情感。时间是经度,故事是纬度,所有经过的人物都随着经纬度的变化而分裂。只是裂变不是我们理想的方向,所以很多想法互相纠结,成为自己心中的一个结。上次舅舅来我家,一直说海棠姐姐一年买五条裙子。潜意识里,除了炫耀,她一定是在纠正自己的身份。当时我们还在讨论大叔有没有带空一个包。事实上,叔叔已经走出了那种情况。他坚持住在我家,不顾父亲冰冷的目光,是不是最大程度的一种表白?甚至,他是不是计划了很久,下定决心要做出最后的样子?
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拍CT,拍CT只是借口?
感觉眼睛突然睁开。
车停在马路对面,严先生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像风一样向我招手。我知道他想让我上车,但此时我另有想法。我拦住一个行人问,你知道保安公司在哪吗?公安局主管的保安公司。这是海棠姐姐的单位,上次舅舅来提,他强调公安局。我不想记得,但我留在了记忆里。我打算问三个人,只有三个人。如果三个人都摇头,我就上车走人。那人刚从一家手机店出来,看着我,转过身,指着身后说,嗯,那不是吗?我说,哪个是?他说,你没看见那个蓝色的大牌子吗?真的看不出来。我不相信事情会这么巧合。我问有多远,他看着我的脚说:“走十步,你就到了。”。我说,是公安局管的吗...那人大概以为我烦了,转身走了。
我打算尝试十个步骤。严先生被招进来,示意他和我一起开车。于是我数着脚步。确实有一个白底蓝字的牌子,大字写着“保安公司垄断”,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写着“承德市公安局”。我走神的时候把脚下的台阶搞砸了,但真的没有十步远。是窄窄的卷首,比起光鲜的左右两边,似乎倒退了20年。门依旧是旧门板,塑料窗帘精致,摸起来冰凉刺手。卷首很寒酸,但他觉得寒酸,很有气势,因为牌子比邻居大。我走进里屋,那是一个更狭窄的世界,两边都是格子房间,灰色的保安服叠得整整齐齐。原来这地方卖衣服。一个女人侧身坐着,脸朝里,用搪瓷罐子喝水。长发,单辫,头顶浓密卷发。听到响声,转头看我,然后站了起来。她的脸上似乎在笑,但笑容羞涩而浅浅,突然就消失了。我忍着心潮澎湃,把胳膊肘撑在柜台上,笑着看着她。她不说我也不说话。她迟疑地喊道:“二姐?”就站在那里。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下来,说道:“我已经打过电话了,进来看看就好...我没想到你会在这里工作。”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有趣。有的寻求突破铁鞋,有的不需要寻求。
我说:“你没怎么变,还是那样。”
海棠终于找到了那句话:“二姐没变。”
我说:“我们多久没见了?”
海棠忙道:“你和大哥一直往我家送麦子...二十年?”
那一刻,我有点感动。她仓促的回复其实是小麦,说明我和大哥之间的古丽玉之行有多沉重。我特别想抓住她,拥抱她,靠近她,就像小时候一样。但在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拒绝我那样做。心中有一种矜持,在脸上,也爬上了身体。我觉得我应该矜持。这个保留是王家对李家的保留。我有权这么做。那一刻,我心中涌起的是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看着海棠,她却没有和我亲密的欲望和打算。这让我很失望,非常失望。既然她没有,我凭什么自作多情?在我心里,一股又酸又涩又毒的液体,轻轻溢出,把我引向了相反的方向。很多年了,她都没有主动给我写信,也没有给我打电话。她是李的家人,她是一个妹妹。无论从哪个角度,她都应该主动...但是现在,站在她面前的是我,除了矜持,我找不到合适的表达。
我说“又不是最后一次送小麦了,那次你带男朋友来我家……”
海棠不好意思,急忙说:“忘了,忘了。是的,那是最后一次。”
我们的对话没有温度,就像天天见面的陌生人。我们是否打招呼并不影响彼此之间的距离。但是我看到她慌了。她冲过去拿手机的时候,打翻了脚下的凳子。电话接通后,她转过身小声说:“爷爷家的二姐来了,你还记得吗?是天津大爷家的二姐...你快通知梅拉和强子……”这个手机应该是她老公的吧,我猜。海棠接着又叫了一声。这一次,声音放开了,爽快地说:“哥哥,爷爷家的二姐来了。我在这里。快来!”
还没有
完成
等待
继续
1.《李海 《李海叔叔》连载来啦!》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李海 《李海叔叔》连载来啦!》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guoji/10197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