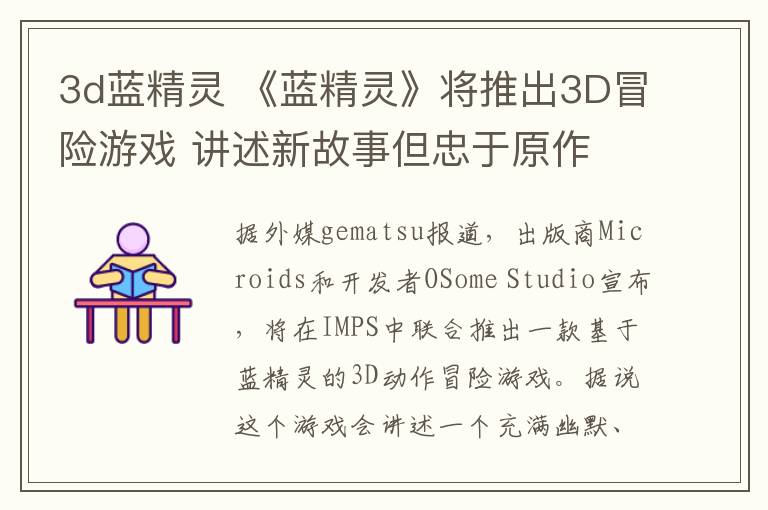我和梅朗第一次见面是因为A姐“陷害”。
梅朗来到岳影馆,只听了阿姐的歌。虽然A姐是一流歌手,但不是大家追捧的头号。但是,梅朗不喜欢盲目跟风。他称赞阿姐声音清亮,像山涧,能冲走人间杂尘。
“故人早出晚归塔,赠我江南春色一梅……”A姐经常给梅朗唱这个词,声音会变得格外柔和。她应该在深情等待他的回答。
可惜梅朗每次都装作没听懂,只用他那温暖而充满爱意的声音回复了另一首诗:“秋浦生凉月,玉沙闪闪。谁不忍心穿越曲塘……”(A姐在亭子里的艺名是《冷月》)
“哦,这些纨绔子弟,在惋惜美女短暂生命的同时,更让美女雪上加霜。”扫地的奶奶把我从窗口拉开:“以后不要像你姐姐那样疯了。”
是的,我听到了窗外阿姨和梅朗的故事。岳影馆是达官贵人的雅座,我不会让我的小女儿打扰我的兴致。阿姨不跟我说这些,但总是爱怜地抚着我的头:“妹妹还小,这些事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他们都跟我姐说,她对我姐很好,但只有我知道,那不是亲情,是莫大的善意。从小失去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妈妈去世前,我让邻居把我送到几百里外的一个远房亲戚家。这是A姐的家。
我的命运怎么会悲惨呢?送我的那天,姐姐的赌(鬼)叔正要把她卖给岳影馆。他马上问来接人的仆人要不要孩子。仆人摇摇头,说孩子很难判断自己未来的长相,岳影馆有钱买更靠谱的。那个赌注。鬼问别人门槛低一点的教学车间,我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这时A姐走过来抓住我的手。“你是我舅舅,你卖我我才能认你。但是这个孩子是我父亲家的亲戚。为什么要卖?我想带着这个孩子。你给她吃饭,也不用给我安排丫鬟。”
“哦,会有用的。”仆人们一起点头,让我和姐姐一起上了马车。
在车厢里,我磕头哭着感谢她救了她的命。她扶我坐起来,苦笑:“之后我们就是姐妹了,一切看命运……”
一开始我不敢直接叫她姐姐,而是跟柜子里其他小丫鬟学的,叫她们“小姐”。
“姐姐,不要记得任何关于救命的事。我把你带在身边是自私的,这样我就不会孤单了。”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真诚地说:“我们相互依赖。”
时间已经流了八年。有了阿姐美丽的容颜和清亮的嗓音,我们在岳影馆的日子并不太难熬。只是,最近O姐有点怪怪的。
那天晚上,将近五次客人散去后,我赶紧帮A姐卸妆,让她赶紧睡。但她戴着一个像墨水一样的头发,怔怔地看着铜镜。
“姐姐,你说我漂亮吗?”A姐已经褪去了脂粉和唇妆,面容略显憔悴,但白皙的脸颊依然像露水打湿的玉兰花,温柔、细腻、清澈。
“你不用问,阿姨最漂亮。”我不是有意讨好她,但在我心里,她是世界上最温柔可爱的女人。
然而,她听了演讲后并没有感到多少宽慰。她反而抬起头来,定定我的脸:“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不能等一个答案...是你,这两年越来越出类拔萃,他们什么都没跟你说?”

我心里忍不住要提一下。仔细想想。这几天阿姨们见到我,会多瞟我一眼。他们以为也能在我身上找到赚钱的方法吗?姐姐早就跟我说,在这个浪漫的地方要想保护好自己,就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我穿了很多年暗淡的旧衣服,从来没有画过眉毛涂过粉,瘦小的身材似乎停留在少女的年纪。但是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我长高了。
虽然我没有回答,但是A姐纠结的心变得清晰起来。她起身走向桌子,打开青瓷熏炉,取了一把香灰,转身放在梳妆台上刻着银粉的盒子里:“你明天把这个抹在脸上,装病几天。”
“可是姐姐,你能不能装病躲过去?”
“我有我自己的办法,听我的就好。”
我顺从地点点头,外面巡逻的女佣提醒我关灯,于是姐姐吹灭了蜡烛,但她眼里的光没有熄灭。一双美丽的眼睛美丽而柔和,在多云的夜晚闪闪发光。
深夜,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被一个熟悉的身影牵着走一条无尽的黑暗之路。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但周围一片黑暗。除了跟在后面,没有别的办法。虽然不是很可怕的噩梦,但是有一种沉重压抑的感觉,让人喘不过气来。
头晕目眩的时候,我挣扎着想要醒来,却听到姐姐幽幽的叹息。
“姐姐,你不要怪我,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选择。你的命是我救的,梅朗是温雅浪漫的儿子。你会喜欢的...所以,给我一个游戏。”
这是什么意思?姐姐想让我做什么?
我在房间里无聊,假装生病了好几天。A姐也说的很实话,甚至伤心地哭着感叹我的命苦。奶奶和丫环给我煎了点偏方,姐姐让我挑点喝,真的让我看起来病怏怏的。
梅朗到来的那天晚上,A姐吩咐我悄悄梳洗打扮,穿上她选的莲色薄纱衬衫和绛红色的淡丝裙,黑发也是第一次撩起来。是A姐亲手梳的一个飞月髻,她还特意从髻上取下一对琉璃月阶,给我发卡。
“姐姐……”我战战兢兢,美若天仙地看着铜镜中的自己。
“你不是一直说要报答我,然后帮我把这个做好,就这一个。”A姐在我耳边低语,但坚定的声音像是在呻吟:“让梅朗喜欢上你,最好是爱上你。”

迎宾女仆邀请梅朗进屋,A姐拂去纱帘,婷婷走了出去。
她今晚的妆容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第一次看到淡紫色的丝绸裙子时,裙子上戴着玉珠,这让一些苍白的脸显得有点悲伤和柔软。郁郁葱葱的岁月里郁郁葱葱的回忆与渐渐远去的惆怅怜惜重叠在一起,她发誓要让梅朗陷入这漫长无边的爱情。
房间里安静而动荡,我能清晰地听到梅朗的呼吸和心跳。A姐虽然笑靥如花,但我知道紧紧抓住最后一颗棋子的心有多难过。
阿姐拿起琵琶,唱着熟悉的曲子,但在梅朗这次回答之前,她先开口了:“清凉的月亮等不到梅花,所以她致力于为梅朗折一朵瑰丽的桃花。”
“嗯?”梅朗不可置信地转过头。透过朦胧的纱帘,我第一次看到了英俊迷人的公子。难怪她内心充满苦涩。
A姐来里面睡,拉着我的手送我去梅朗。“姐姐,这是……我们的梅朗。”
“我们?”梅朗笑得像春风,她的目光从A姐的脸上移到了我的脸上。一双双星的眼睛仿佛被A姐的蓝波浪洗过一样,闪着黑曜石般的光芒。
我哽咽着嘴唇,却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只是低着头给他倒茶。淡淡的香气中,一颗干枯的雄蕊在茶中挣扎摇摆。我想知道它会开花还是死亡。
在云一样的衣袖里,伸出纤纤玉手。我以为他要拿茶盏,没想到他握着我颤抖的手掌,温柔温暖,仿佛在呵护这只柔弱的小鸟。
“多可爱的小女孩啊。难怪你对她这么好,愿意把我给她。”梅朗向A姐翘起嘴唇,笑吟吟地看着我,示意我坐在他椅子旁边的扶手上。“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A姐的爱人。但是,不管他有多帅,多温柔,多温暖,我脑子里只有这个想法,一遍又一遍…
“她是我带来的远房姐姐。多年来,我保护她,拒绝签署岳影馆的合同。今晚是她第一次来。我可以在这个浪漫的地方,我的地位岌岌可危。我能保护她多久?这几天我就让她装病,暂时打消阿姨们的念头。”阿姐抚着琵琶头上的白玉雕,眸中柔光闪闪,滴下一滴寒露:“如果梅朗愿意折我们两朵落寞的花,就给她取个名字。”
花开两朵,愿香一朵。
梅朗是一个浪漫之地的帅哥,但毕竟在花丛中漂泊多年,又不是裸体。现在,A姐向他倾诉,向我们所有的姐妹付出。他权衡了一下痛苦,最后点了点头。
“叫什么?”他的目光映出了A姐忧伤的笑容和我羞惭的侧脸,他们发髻上半弯的琉璃月亮摇摆着,发出了触动心弦的轻柔声音:“有就叫缺月吧。冷月缺月,伴长夜。”
离开岳影馆的那天,梅朗在碧霄仙子厅设宴招待他们的公子哥。A姐弹琵琶唱歌,我点酒...听着大家打趣的“赞”。
"(颜饰)并不有福,这是一个浪漫场上的好故事!"
然而,阿姐那优美的琵琶却压制不住角落里的私语。
“不知道多少钱?”
“好像只要三百两,一个变老,一个不开放,赎回就是一拿一免费,性价比很高。”

如果前一天晚上时间停止了,A姐可能还会开心,因为尽管被人小声说,至少她能叫出“梅朗”。现在,当我们走进梅府后院的小门时,我们知道在岳影亭的八年让我们与这个世界隔离了太多的委屈和尘埃。
“你住在这个房间里。平日里弹琴练琴就好。只有家主宴请,才能给颜色。如果不能赢得客人的好感,养你有什么用!”管事的家仆鄙夷的看了我一眼,我下意识的躲在姐姐身后,却意识到从此我们都成了一家人(怕‘女科’和谐,就用同音字。)
妾室的现实,却没有妾室。
“姐姐,你呢...后悔?”
“与其被所有人玩,不如被自己喜欢的人玩。”A姐拨了拨琵琶弦,声音清亮如溪,却悄悄变得平淡苦涩,因为她知道,以后还会有更悲伤的情况。
在喜欢的人面前被所有人娱乐。
我和姐姐学了琵琶。因为我们的愧疚,她给了我一切,但我没有很认真的学,尤其是唱歌。我不想润色我的声音。我只用自己的母语嗓音唱歌,感情、情怀、委屈都融不进歌声里。最初的悲伤只有一个,歌不合拍,已经很痛了。
“这样下去,我们不是被人遗忘,就是成为梅和魔王历史上的笑柄。”我妹妹很伤心,但也说不出什么可责备的。
你买过唱悲伤歌曲的女生吗?我看着她眉毛之间的细微痕迹。不是时间侵蚀了她的美丽,而是那个浪漫的男人鄙视了她的心。
还好梅朗,其实我不应该这样叫他,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叫过他。那只是我年轻时的第一印象,印象很深。好在居士对我的唱功还算满意,称赞我的声音是绿草上的纯净风,可以扫除灵魂的尘埃。
我和妹妹面面相觑,嘴唇呈浅弧形。
山之泉,草之风,如果勉强能维持依赖,也无妨。
“什么叫纯洁,不是因为年轻。”侍妾嘶嘶低语,妹妹唇上的涟漪立刻恢复了沉默。
“子濯。”女主人进来,在家里的主人旁边坐下。她平静地唤了一声,把这里所有的妃嫔丫鬟都当做碎花花瓣,留给她一朵优雅端庄的牡丹。
两边等候的虞姬后退了一步,妹妹的身体也颤了一下。虽然没什么感觉,但也知道自己的眼睛是蓝色的,低低的,在等待命令。
“小的儿子不是晚点来吗,他们会放音乐陪他吗?”女主人斜睨了一眼A姐:“人们习惯在王宓后门进进出出。你就不怕他觉得我们节俭无趣?”
主人会意,朝姐姐摆了摆手,我垂着头越来越低,低低地伸向姐姐凄凉的背影。
丫鬟们又摆了几个凳子,女主人命几个善歌舞的小妾和贾姬围坐。我不想惹麻烦,就先给角落让路。
“哎,小姑娘,你是不是为姐姐委屈了?”一个虞姬悄悄问我。
“其实她应该感激,因为至少有一个干净的地方太旧了。”
我实在受不了这种轻佻冰冷的语气,我肆无忌惮地回答:“为什么我们这么刻薄,我们都会变老的,不是吗?”
“谁叫她不尽到自己的责任,就认命去死,她还拼命爬高枝。现在她很反感,不能怪别人。”
“不,姐姐,她不是爬高枝,是多愁善感!”
“爱情?开玩笑的。像我们这样的人能说情话吗?”
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此印象深刻,但我非常沮丧,甚至找不到曲调。
我回过神来,发现有人在看我,和居士的温柔和爱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微风轻云的愉快感觉。

他们也意识到萧公子的目光,纷纷盯着我。我低头拨弦,懒得把这个指责放在心上。
“梅哥哥,这丫头从来没玩过音乐。以后大结局该不该用?”萧公子举着酒杯,微笑着将气氛变得温和。
后来才知道他叫琴清,真人如其名。
“小雄自然会同意。”居士应声道,立即示意大家停止弹竖琴和笛子,让我弹琵琶唱歌。
我不得不调整钢琴的声音并拨弦。我只觉得我的眼神五味杂陈,深思,嫉妒,轻蔑...只有纯色如蓝天悠悠云,定住了我的思绪。
即使风很纯,也不是从空开始的,而是因为心底隐藏的痛苦和挣扎的漩涡。我弹的是宴会上经常弹的清欢曲子,但有一首A姐曾经念过的诗传入我耳中。据说是我离开歌姬时的一首感伤的歌。
“当月亮缺花时,花必须以完整的圆圈结束。
怎么做才能把自己的想法卖出去?还有从四川过世的粗壮华人委员会。
婉转地留下一首优美的歌,九原曹纯嫉妒单鹃。
王孙不学多愁善感的客人,自古以来他就失去了青春——”
萧让青听着音乐,时不时和居士碰杯谈心,但总算抽出眼睛来看我。一次又一次,他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位公子少爷,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尊重。伴随着琴声的忧伤,他眼中的轻盈宁静染上了烦恼的色彩。虽然只能低头垂目,但腔的感觉已经映在了内心的湖底,满是起伏和幽幽。
“你叫什么名字?以后想听听你的音乐。”
“奴家缺月,多亏萧公子夸奖。”我的声音很轻,比如我第一次见到我的主人时,但这一次不是恐慌和羞愧,而是一种喜悦和悲伤的矛盾情绪。
因你的赞美而快乐,因我们遥远的距离而悲伤。
从那以后,小让青就经常来吃饭,每次都让我给他唱歌。根据人们的传闻,他以前很难邀请他。
“哦,也许你的运气来了?看来你妹妹给你找的桃花没数过。”家里的女孩子都很不屑的说话。
“我只是不知道这是好运气还是坏运气。肖家是一个大家庭。如果不好,那就比你姐姐还糟糕。像月亮一样黯淡。”
“不如来找你,又凄凉又不完整。”
“哎,缺月,要不要跟那个小公子一起去?”
……
如果余生能被那双清澈愉悦的眼睛看着,我愿意。但是,去不去我说了算?
而我走后的日子,不算。
也许,在一个看不见的角落里静静地枯萎,比在渴望它的人面前枯萎要好得多。至少,不会忘记。
但是既然爱情的根已经深深的扎下,为什么不能说清楚呢?爱情的一句话,我们卑微的宋吉,注定一辈子碰不得?
"纱窗拒绝涂红色粉末,并让萧郎流泪." alt="缱绻悲喜小说 故事:微小说 | 笙歌落尽,心事荼蘼,缱绻爱恋却换来你一盏忘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