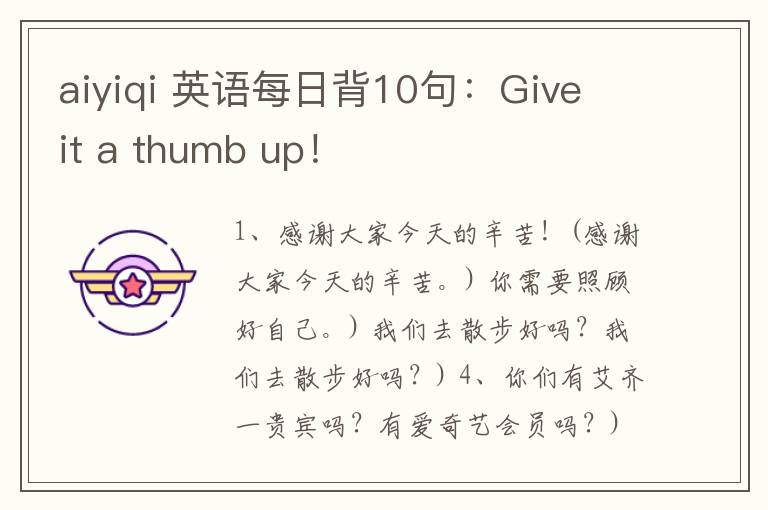最近,以“最美的翻译”为噱头的“古代翻译家”层出不穷。
“世上有千千万万的人,有三种爱。太阳照着,月亮照着,不如你儿子,大海在变。”
我爱这个世界上的三样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永远是你。
“时隔多年,何必以泪洗面,以沉默相贺?”
时隔多年,我该如何问候你?带着沉默和泪水。
是应该把外国文学“驯化”成中国风,还是尽量保持外国语言的魅力?市场上似乎还没有达成共识。
对于读者来说,理清逻辑意义重大——要明白什么是好的翻译,什么是骗人的翻译,可以避免上当受骗,帮助人们买单。好在例子比比皆是,可以用来形象地说明问题。
18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托马斯·格雷的《写在乡村教堂院子里的挽歌》中有一个片段。语法和词汇都不复杂,不构成普通读者的阅读测试。它只需要初中英语水平,同时可以找到很多有代表性的公共中文翻译,是一个优秀的范例材料。
原文是:
宵禁敲响了离别日的丧钟,
哞哞叫的牧群缓缓吹过草原,
农夫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
把世界留给黑暗和我。
丧钟敲响,离别的日子,哞哞叫的羊群,回家的路,扑通……从文字的角度,读者可以看到诗人是如何通过选择文字来创造视觉和听觉形象的,比如看风景,闻声音。
第三版的译本也出自著名艺术家之手:
晚钟敲响,夕阳西下。
一群被称为家的牛沿着草地小道绕行,
农民锄犁,回家累了,
但是我建立了一个荒野,独自面对夜晚。(冯华展译)
晚钟响了,天也没了。
牛羊互相呼唤,绕过草地小路
农夫带着锄头回家,摇摇晃晃
把整个世界留给我和黄昏(郭沫若译)
当晚钟响起时,人们会为这一天哀悼。
牛在草原上迂回,咆哮起伏。
种地的人回家都累了,磕磕碰碰的。
把整个世界给了黄昏和我。(翟译)
著名翻译家丰子恺之子冯华展长期从事英语文学教学和翻译工作。郭沫若尽管人格伟大,却有无可争辩的诗歌和文学才华。卞支林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诗人和翻译家之一。然而,详细解释三种翻译的优缺点涉及许多技术细节,这需要文学专业的翻译课程。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在这里简化问题。
如果说读外国文学作品就相当于品尝外国饭菜,那么卞支林的翻译就有一种外国饭菜的味道。郭沫若的有明显的中国味,所以他等第二;丰富深刻,等待第二次。卞支林的翻译和原文一样生动、形象、富有诗意。母语为汉语的读者阅读了卞的译文,可以满怀信心地与英语读者讨论18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格雷的诗歌《格雷》是一种怎样的天气、意象和诗歌,这种讨论将使英语世界的人们毫无障碍地理解格雷,而不是卞。
然而,冯和郭在翻译中明显地刻意追求汉语的特质和典雅,因此他们舍弃了原文中的许多重要意象,如原文第一行的“敲钟”。这种丢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是致命的问题。第一行往往为全诗定下基调,舍弃了第一行的重要意象,只留下诗的残迹。
更有甚者,冯、郭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美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加入了一些原著所没有的东西。比如两个译本都有“荷锄”的说法,但原文既没有“扛”,也没有“铲”。通过这样的删减和增补,冯、郭对《格雷》的翻译面目全非,至少是“三分之二”,不再是《格雷》,而是冯、郭。仔细阅读冯、郭译本的读者会被误导。
为什么追求“神似”和优雅的译者热衷于删改和添加扭曲的原作?冯先生和郭先生显然没有弄懂“丧钟鸣”这句原话,只是在文学想象面前暂时麻痹了自己的阅读理解。两版不合理的加“锄锄”,说明“锄锄”是中国的套话——两个译者因为套话而无法摆脱。译者的目的不是有意欺骗,而是为了方便写作而表达自己的汉语基本功和诗歌天赋——收集韵脚或音节——而不是表达格雷的诗歌天赋。
译者很聪明,甚至超越了原作者。看来照原文翻译会害了他们心目中的“上帝”,最终陷入耍把戏的烂泥潭。越是难以表达自己,翻译价值就越小。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花刺》中的形象,读者读他们的译文就像在浓雾中看花一样。越是有意识地展示译者的语文功底,就会制造越浓的迷雾,让读者看不到精妙绝伦的原作,充其量也只是对唐诗宋词的不合标准的模仿。
谈到诗歌翻译,可以提到艺术这个词。
在英语世界中,艺术,通常在汉语中被翻译成“艺术”,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艺术,另一部分是欺骗。这样的词义辨析不是文字游戏,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艺术翻译,也就是所谓的艺术翻译,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是艺术的还是隐藏的?20世纪英语世界语言大师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对所谓的诗歌艺术翻译有一个非常尖锐的讽刺——“18%的意思,加上32%的废话,50%的不咸不淡的填料。”
有意或无意的欺骗性翻译给跨文化阅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用古老的方式翻译外国诗歌是用中国传统文学语言来归化外国文学语言的尝试,这注定是徒劳的。然而,如果译者试图炫耀自己的“古文功底”,结果就更可笑了。以汉语为相对文化的读者很容易接近一流的唐诗,那为什么要在“模仿”中寻找“韵味”?而为了押韵工整而“活动在一起”的“古译”本身并不精妙——哪怕只是直观上的,清新别致、生动传神、传神传神的语言也可以称得上是上风。
艺术永远是一场冒险,永远是要冒险的。译者的探索勇气、气度精神和审美追求值得称道。然而,用古代语言翻译外国文学可能只是一个死胡同。比如日本文人曾经投入大量精力写汉诗,但日本汉诗毕竟不算优秀——因为它不是一种生动的文化语言,基于日本现代口语的优秀作品蔚为壮观。
我们今天的情况类似于这样:活泼的、有生命力的、甚至通俗的、口语化的,是动态的文学语言。莎士比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用英语日常词汇写诗,写了他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当时受过教育的英国人都是用拉丁文写的,名著现在都在?为了避免忘祖之嫌,《史记》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司马迁引用古籍时,被翻译成通俗易懂的文字,这可能是《史家绝唱》流传千年的原因之一。淹没在“古韵”中,套用“戴月锄锄”和“让我们走几年”,无疑是陷入了“隔文化”的盲泥。
原发表于2018年第15期《中国青年》杂志
1.《泥淖 “古风翻译家”的泥淖》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泥淖 “古风翻译家”的泥淖》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guonei/10199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