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每晚一张音乐CD
法意导言
卢梭因写作哲学作品而广为人知,不过,在他携《一论》登上欧洲文学舞台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位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了。本文将从卢梭前体系阶段的音乐著作,卢梭的体系与他音乐理论的发展,《论语言的起源》与卢梭的“体系,言语与可完善的激情,怜悯与人类交流的源自激情的起源,从精神性的旋律到物理性的和声六个方面,与大家探讨卢梭的新美学。

个人简介
任崇彬
1984年生,天津静海人,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讲师。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硕士与博士就读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工作期间曾赴美国乔治城大学短期访学。在《复旦政治哲学评论》、《天府新论》、《二十一世纪》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篇。
卢梭的音乐理论与他的哲学是一致的

约翰·T·斯考特 著
任崇彬 译
卢梭因写作哲学作品而广为人知,不过,在他携《一论》登上欧洲文学舞台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位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了。卢梭作为反哲学的哲学家爆得大名之后,继续将音乐作为其首选职业和爱好而终其一生。在《对话录》一书中,卢梭证实,他的音乐作品与他的哲学作品是一致的,他解释说,就像他的所有作品一样,他的音乐著作和创作是被同样的情感和观念所推动的,也就是说,它们同样基于其“体系”的原则,亦即“尽管人们是邪恶的,但人类却是好的。”[1]他的成熟的音乐理论不仅涵括了他有关人之自然与人之发展的哲学,并且通过考察激情在人类共同体中的作用而扩展了这一哲学。卢梭的音乐理论是其哲学中重要但又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卢梭的音乐理论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他的哲学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足够广泛的分析[2]。他唯一一部广为人知的与音乐相关的作品是《论语言的起源》,不过,即使是这部作品通常也未得到完备的分析,因为人们并未根据他的其他音乐著作来解读这部作品。《起源》一书脱胎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中叶的《二论》以及同时代的音乐争论。同时精心构思他的“体系”以及那些接连不断的讨论音乐的作品,是卢梭的成熟音乐理论发展出来的大背景。我将首先解释卢梭前体系阶段的音乐著作并讨论其音乐理论的发展,接着我将转向对《起源》的考察。最后,我将以讨论卢梭的新美学理论及其影响来结束全文。
卢梭前体系阶段的音乐著作
“让-雅克是为音乐而生的。”[3]卢梭的音乐著作或许可以被描绘为他阐明自己与生具来的对音乐之热爱的一种尝试。在《忏悔录》一书中,他谈到了自己几乎从降生时就秉有的“对音乐的爱好甚至是激情”,他说道,在16岁离开日内瓦之后,他去了意大利,正是在意大利,他对音乐的激情才显露出来[4]。虽然在大约17岁时于唱诗班学校所接受的为期6个月的音乐训练,几乎是他接受的唯一正式训练,但是卢梭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越来越沉迷于对音乐的热爱。他得到了拉莫的《论和声》一书,并下大功夫掌握了它,他在一位接受意大利训练的管风琴演奏家那里进行非正规的学习,他回忆起自己如何将他的朋友的“原则”与“我的拉莫”的原则相比较[5]。那么,卢梭至少在回想中注意到了法国音乐与意大利音乐之间的差别,这在接下来导致他与自己的年轻英雄发生了争执。
卢梭不久就干起了音乐教师与乐谱抄写员的行当,在放弃了哲学之后他还会重操这一营生。抄乐谱使他认识到普通的可视的记谱方法所存在的困难,因此他设计出了一套数字方法来记谱。1741年,卢梭带着他的记谱法以及戏剧《纳尔西斯》动身前往巴黎。在科学院,卢梭获得了宣读其论文“新记谱方案”的机会,在获得好评的同时,一个遴选的委员会出具的报告给出结论说,他的方法并非完全新颖,而且在实用方面也不如普通的方法[6]。然而,卢梭确信自己的方法是实用的,并且以《论现代音乐》为题将之发表。这部作品包含了一段讨论音乐表现力的离题话,卢梭在这里解释说,我们并非被声音所感动,而是被存在于声音之中的和谐关系所感动。他提请他的读者阅读拉莫的著作,在那里,音乐表现力的来源得到了“充分的说明”[7]。在其成熟的音乐著作中,卢梭则详述了一种与拉莫的音乐表现力理论明显相反的理论。
在发现他的“体系”之前,接下来的十年中所发生的一些事促成了卢梭与拉莫此后的决裂。首先,1743至1744年间,也就是卢梭作为法国大使的秘书旅居威尼斯期间,他重新认识了意大利音乐。“我从巴黎带来了那个国家对意大利音乐所怀的成见,但是我也从大自然那里秉受了可以破除成见的敏锐感。不久我就对意大利音乐产生了它在知音人心里所引起的那种热爱了。”[8]
其他两件事则牵涉到音乐家自己。从威尼斯回来后,卢梭完成了他的歌剧《风流诗神》,这部剧于1745年9月在拉·波普利尼埃尔家里上演,后者是那好妒忌的拉莫的保护人。拉莫指责卢梭的作品是剽窃得来;卢梭承认自己的作品参差不齐,但他坚持自己就是作者[9]。后来,卢梭将这一作品的缺点归咎于他依然法国式的趣味:“我误把噪音当作和声,误把非凡当作有趣,误把歌曲当作歌剧。”[10]十年之后,他将以同样的措辞来指责法国音乐。最后,大约就在同时,卢梭接手了一项工作,就是改编伏尔泰的一出戏剧以与拉莫的配乐相协。拉莫忙于自己的作品退出了该计划。卢梭并未因在《拉米尔的庆祝会》一剧上所做的工作而受到称赞,同时也未得到相应的补偿。 他与拉莫的关系恶化,而他与伏尔泰的关系也没能撑几年。卢梭在《一论》中对启蒙运动的攻击,在相当程度上无疑要归因于他对他的两位主要榜样的敌意。
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卢梭的音乐趣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法国式的,这不仅为他后来对《风流诗神》所作的评价所证实,而且也为他同时期的一封比较法国歌剧与意大利歌剧的信所证实。他将两者看作是种类上完全不同的音乐,他发觉两者在其各自的类型中都是强有力的,只不过法国音乐通常来说更感人一些。他认为意大利音乐是“普遍的”,因为它并不特别地与意大利语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他谈到了法语与法国音乐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把这当作法国音乐的优点。不过,就在大约十年之后,这却成了他谴责法国音乐的基础[11]。
因而,卢梭前体系时期讨论音乐的著作并未包含其成熟理论的重要要素,甚至可以说是发展了与之相反的论证。他前体系时期的最后一部音乐作品,也就是为《百科全书》撰写的辞条,则比较难以归类。卢梭的朋友狄德罗是在1748年的晚些时候将《百科全书》词条的写作任务交给他的。卢梭在一封信中显露了他的部分灵感:“我试图报复给我以伤害的人,愤怒使我强壮;它甚至给我以智慧和知识。”[12]他似乎是在指涉拉莫,此外,虽然他确实在拉莫的手上经历了屈辱,但卢梭的辞条却大体遵循拉莫的理论并仍尊敬拉莫。不过,辞条的口吻可能要部分归因于达朗贝尔,后者貌似介入其中,从卢梭的手稿中删去了那些透露出恶意的评论[13]。百科全书派急于僭取拉莫的声望以加诸自己;在百科全书计划的“前言”中,达朗贝尔赞美拉莫,说他是一位构造了音乐科学的“艺术哲学家”[14]。
尽管如此,在卢梭礼敬拉莫的外表之下,潜藏着尖锐的批评。比如,在论伴奏的词条中,卢梭赞美音乐家为我们揭示了一门在其中所有事物都显得任意的艺术的真正基础”;但接下来他就批评拉莫的音乐和弦太多,在遵循他自己的原则方面太亦步亦趋[15]。卢梭对拉莫过度“和声的”音乐的批评,指向了他随后就旋律与和声何者优先的问题与拉莫展开的争论。唯一一位对卢梭的《百科全书》辞条做过细致研究的学者认为,论伴奏的辞条是“是对一般而言的法国音乐以及特别是作为法国风格主要倡导者拉莫的隐蔽攻击”,并且得出结论说,卢梭撰写的《百科全书》辞条揭示了其成熟音乐思想的某些重要要素[16]。然而,卢梭的辞条虽然的确预示了其成熟音乐理论的某些关切,但并未包含任何有关语言与旋律之间关系理论的明显迹象,也未包含其成熟音乐著作中的核心观点。《百科全书》辞条在时间上先于卢梭对其“体系”的发现,因而也先于其成熟的音乐理论。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1751年7月,正当《百科全书》的第一卷问世之际,卢梭的思想中爆发了一场革命。在刚刚完成了《百科全书》辞条的写作之后,他偶然看到了那个由第戎科学院发起的有奖征文题目:“一看到这个题目,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17]“范塞纳的启迪”揭示了他有关人之自然善好的“体系”。卢梭之哲学梦幻的首要成果,也就是《一论》,使他名满全欧。达朗贝尔撰写的“前言”,既宣布了卢梭作为音乐辞条的主要贡献者参与了启蒙运动计划,同时也注意到了他针对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所发出的哀叹[18]。卢梭随后对其“体系”所做的详尽阐发揭示了,《一论》并非仅仅是一个巧妙的悖论,它同时还导致了卢梭和启蒙哲学家的决裂。
《一论》刚刚问世不久,卢梭就为当时有关法国音乐与意大利音乐之各自相对优点的激烈争论,亦即“喜歌剧之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而最早发展出了自己成熟的音乐理论。1752年8月1日,伴随着佩尔戈莱西的喜歌剧《女仆情妇》由一班意大利演员成功上演,战斗打响了。喜歌剧演员的持续胜利被当成对法国风格的一种冒犯,并重新开启了五十年前法国歌剧刚刚诞生时就存在的种种争论。一方阵营是意大利风格的拥护者,包括卢梭和启蒙哲学家们,另一方阵营是传统法国歌剧的捍卫者。卢梭将这场战斗描述为显贵和富人与大众及其同盟者之间势不两立的斗争,并且声称,他在介入争论后,所有人都团结起来反对他,从而使国家避免了一场政治革命[19]。
《论法国音乐的信》,也就是卢梭对“喜歌剧之争”的主要贡献,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其音乐理论的发展,而他在《信》之前所发表的其他两部作品则显示出其理论的最早重构。第一部作品是为一场因德图什的抒情悲剧《翁法勒》之重新上演而展开的小册子战争而作,这场斗争就发生在有关民族音乐的争论之前并为之做了铺垫。在其并未署名的《致格里姆的信》中,卢梭推进了由格里姆发起的对法国歌剧的批评,并相应地支持意大利音乐。当卢梭批评拉莫那过度装饰的伴奏以及博学的和声,并且谈到了在音乐作品中戏剧特征与旋律特征的“非常明智且非常可欲的统一”应当占主导地位时,卢梭不仅预见了他将在《论法国音乐的信》中所采取的立场,而且比较明显地暗示了其成熟音乐理论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有关旋律之统一的学说[20]。卢梭通过把对拉莫的批评与一种新的赞成旋律优先的相反学说联系起来,从而迈出了超越《百科全书》辞条的一步。他首先将其有关旋律之统一的学说在他的另一部作品中付诸实践,这部作品在时间上先于《论法国音乐的信》,那就是卢梭那部大获成功的喜歌剧《乡村占卜师》。他在1752年的春天创作了这部作品,该剧的排练是1752年6月在丹白露进行的,接下来八月份在那里的正式演出也非常成功,之后又于1753年3月在巴黎歌剧院上演[21]。在《对话录》一书中,就在卢梭声称他的歌剧所体现的观念和“情感”与他所有作品所体现的完全相同的地方,他将自己歌剧的成功归因于“歌词与音乐之间的完美和谐”,归因于其作品的“隐秘原则”——“旋律的统一”[22]。在《论法国音乐的信》中,卢梭发展了这一“原则”[23]。
1753年11月,当卢梭的《论法国音乐的信》发表之时,“喜歌剧之争”似乎走向了终结。他的《信》以这样的建议开篇:人们不应当考察法国音乐是否优秀,而应该考察是否存在法国音乐。他在《信》中的分析涉及到了音乐和语言的关系。
和声的原则存在于大自然中,它对所有的民族来说都是相同的,即便它有某些变化,这些变化也是由旋律方面的变化导致的;因此,一种民族音乐的独有特性只能源自旋律;更何况由于歌曲特性主要地源自语言,所以歌曲严格说来会受到语言的很大影响。[25]
他设想出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完全不适合旋律优美的歌曲,结果这种语言是法语。为了证明法语不适合音乐,他考察了一段源自吕利之《阿尔米德》的著名宣叙调。就像在卢梭的许多作品中那样,他在开头所提的问题已经预示了他的最终结论:
我相信我已经表明,法国音乐中既不存在节奏也不存在旋律,因为语言不受节奏和旋律的影响;法国歌曲只是一连串持续不断的吠叫,任何毫无准备的耳朵都无法忍受它……由此我得出结论,法国人没有音乐也不可能有任何音乐;要么就是,即使他们有某种音乐,这种音乐对他们来说也是足够糟糕的。[26]
《论法国音乐的信》采取的几乎是完全批评的取向,这就隐藏了卢梭的批评立基于其上的建设性理论。他在后来的作品中才对这一理论进行详细阐发,不过,这一理论在《信》中仍隐约可见,就在卢梭将有关音乐与语言之间关系的论辩与有关“旋律之统一”的离题话联系起来的地方。卢梭采取以下方式暗示了上述联系:他声称,建基于音乐会适应语言的相反假设,他能够推论出真正音乐的所有特质,“它感动、模仿、愉悦心灵,向心灵传递源自和声与歌曲的甜蜜印象。”[27]音乐表现力的来源,乃是由旋律所表达的对激情的模仿,因此,“旋律之统一”是一种确有表现力的音乐的关键。此外,“旋律之统一”的学说还指向卢梭在《信》中对民族音乐进行考察的哲学基础。对卢梭而言,音乐是一个语义体系,是一门为激情所使用的语言,激情通过旋律的变化来传达自己。音乐和语言都是文化现象,不同文化及其所采用的表现形式的差别,源自它们各具特色的需要和激情。换句话说,卢梭对法国音乐的抨击,隐含了他对人之自然与人之发展的分析,稍后他将在其哲学作品中对之进行阐发。
人们对《论法国音乐的信》的反应是迅捷而激烈的。卢梭被禁止进入巴黎歌剧院,该剧院的音乐家们烧掉了他的肖像。他的作品引发了超过三十份的且大多是愤怒的回应,其中最为重要的,乃是拉莫的《论我们的音乐本能及其原则》,该文与卢梭的《二论》是同时出版的。虽然卢梭在他对法国音乐的考察中几乎未提到拉莫,但是它应当被视为对法国最伟大的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的一次攻击。拉莫迅速改写了一本已经着手的著作,他论证说,我们的本能自然地将我们引向源自发声物体之共鸣的和声变化,他主张,这既是其和声理论的核心,也是所有音乐的“原则”[28]。他始终辩称,旋律乃是源自和声,但是在《论我们的音乐本能及其原则》中,他采取一个更为极端的立场来反对卢梭的论证:“只有和声才能唤起激情;旋律只有从和声这个源头才能获得其力量,力量直接从这个源头流淌出来。”[29]卢梭与拉莫的争论直接关乎和声与旋律何者优先的问题,与此同时,它也提出了更为重要的有关音乐表现力之本质的问题,它使得争论由最初的民族音乐之争演变为“一场严肃的有关美学与形而上学的争论。”[30]
拉莫在回应了《论法国音乐的信》之后,继之以对《百科全书》中卢梭所撰若干音乐辞条的尖刻评论。在其《百科全书里有关音乐的错误》中,拉莫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卢梭并未恰切地掌握音乐的和声基础。拉莫将卢梭对其音乐理论和实践的过度“和声的”性质的些微批评,当作他不理解和声这门技艺的可耻证据。例如,卢梭的意见是,拉莫的音乐和弦太多,而且他在遵循自己的原则方面太亦步亦趋。为了回应卢梭,拉莫争辩到,和声“一旦被删节就会违反大自然本身的法则。”[31]
拉莫的反驳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对卢梭在《百科全书》辞条中所言内容的批评,因为他现在是跟《论法国音乐的信》的作者争论,正如我们所见,他在其批评的中间部分转向了后者[32]。他认为,卢梭对旋律的“盲目推崇”和他对意大利音乐的偏爱,暴露了一双未受过正规训练的耳朵。他讥笑卢梭“旋律之统一”的学说为“妄想”——“词语在言说中能够打动双耳,但是在音乐中若无和声的帮助,词语就只有微弱的感染力。”虽然卢梭很想把自己呈现为音乐方面的“立法者”,但他作为一位作曲家以及理论家的失败,透露出他从根本上误解了音乐。“只要是单把旋律当作音乐效果的主要感染力量,那么这门技艺就不会有大的进步了”,拉莫主张,“因此,只有直接地从和声也就是旋律之母那里,我们在音乐中经验到的不同效果才会产生。”[33]对于拉莫而言,音乐是由源自振动物体之共鸣的和声来诠释的。音乐是一门“物理-数学科学”[34],这门科学探究的是一个以和声与比例为其特征的普遍的自然,并且它可以为人类的理性所理解。的确,对拉莫来说,音乐是“众科学之母”[35],在这个学科中,人们可以最好地瞥见,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是有着本质上是和声的或成比例的特性的。
在卢梭眼中,拉莫的音乐理论倾向于还原论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而这恰好是卢梭在其整个哲学中所反对的。正是在他对拉莫的回应中,我们看到他的音乐理论与他的哲学主线汇合了。像拉莫一样,卢梭也把自己音乐理论的根源称作“自然”,但是他的“自然”观念是极为不同的。[36]对拉莫来说,音乐似乎与超出听觉器官的之外的人之自然并无关系,但对卢梭而言,真实的音乐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类现象。卢梭对拉莫的回应,基本上包含了他在《二论》中首次提出的有关人之自然与人之发展的理论。大约在《论法国音乐的信》首次发表的时候,卢梭开始写作《二论》,在他与拉莫的往复争论开始之前,这本书就已经完成了。在《二论》中,卢梭解释了语言和歌曲的激情本质与本源,而这构成了《论法国音乐的信》中所简述之论说的理论基础。拉莫与卢梭之争,实为一场划时代的战斗,在这里,两种美学以及“两位彼此不同的且思虑周祥的音乐哲学家遭遇了。”[37]
拉莫的攻击激发了卢梭去发展《论法国音乐的信》中已经初具轮廓的音乐理论。不过,他对拉莫的直接回应,也就是《考察拉莫提出的两种原则》一文,仍然聚焦于旋律与和声何者优先的争论。卢梭是在1755年写作《考察》的,就在拉莫发表他的《错误》之后;但该作品的最终形式要到大约十年之后才确定下来,那时,卢梭考虑把它作为《音乐词典》的前言发表。就像标题所表明的那样,《考察》是要回应由拉莫在其批评中所提出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和声乃是音乐及其至深效果的唯一基础,由此派生的第二个原则是,伴奏所表现的是发音物体。卢梭把心思放在了第一个“原则”上,他说,这个原则包含了“他们二人就整个音乐技艺的基础问题无法达成一致的关键之点。”[38]拉莫认为,一段配有良好和声序列的音乐“直接与灵魂息息相通”[39],而一段未经修饰的旋律所产生的愉悦“只局限于耳朵”。卢梭却说:
最美的和弦,正如最美的颜色,能够给予感官一种愉悦的感受,此外就再没有其他了。但是声音的调子直达心灵;因为它们是激情的自然表达,它们通过模仿激情来唤起激情。正是由于调子的缘故,音乐才变得雄辩有力、感人至深、善于模仿,它们构成了音乐的语言;正是由于调子的缘故,音乐才将事物描绘给想象,将情感传递到心灵。正是由于歌曲而非和弦的缘故,声音才有了表现力、热情和生命;只有歌曲才能使声音富于精神影响,而从后者产生了音乐的全部能量。总而言之,技艺中单纯物理的部分是少得可怜的,而和声并不能超出此狭小范围。[40]
为了反对拉莫有关和声的“物理”科学,卢梭提出了一种有关旋律之“精神影响”的理论。虽然卢梭承认,简单的和声是自然的,但他主张,“形成和声的情感都是习得的和人为的,虽然其中的大部分都被归于自然”,他以《二论》的风格下结论说,“只能到远方寻找自然,这是一种大城市无法避免的不便。”[41]
卢梭就我们应当去何处寻找人之自然所作的附带评论表明,他能够提供一套有关音乐的旋律本源及其发展的解释。事实上,在这个文本的初稿中,卢梭在一段带有自传性质的离题话中正是这么做的,不过后来他在最终的版本中又把这段拿掉了,最后他把这段合并到了《论语言的起源》中。[42]离题话是以这样的段落开始的,这使我们想起《二论》:
我们对人的自然状态是如此的无知,以至于我们甚至不知道人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某种叫喊;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知道人是种模仿的动物,他能迅速地从其他动物的示范那里学得他能够利用的所有本事。[43]
他接着解释了希腊人那富于表现力的旋律优美的语言,然后是一个衰落过程,衰落以拉莫的现代和声音乐为其顶点。正如杜谢所评论的那样,这段离题话表明了“两类并行的思考的交汇点:一类涉及音乐和语言,另一类涉及社会和语言。”[44]通过将这段离题话并入《论语言的起源》,卢梭完成了一部能够超越他和拉莫之间当下争论并探索他的音乐理论与其哲学之间关系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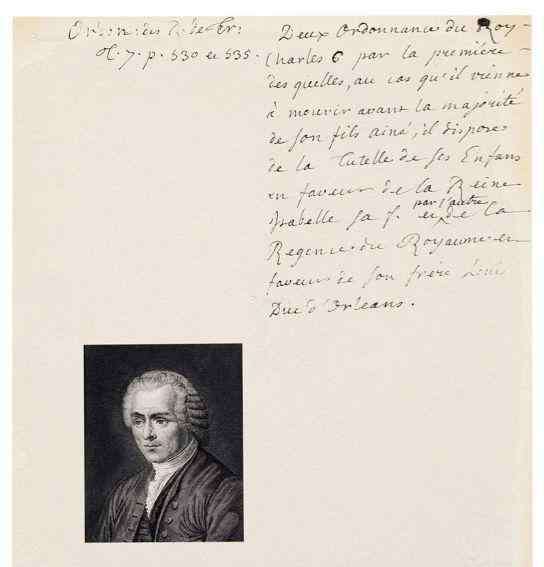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论语言的起源》与卢梭的“体系”
《论语言的起源》是一本宏富的作品,它将卢梭生涯中的两股川流亦即哲学与音乐结合起来了。近些年来,这部作品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最知名的例子就是德里达那本影响广泛的《论文字学》,这本书将卢梭的《起源》描绘为西方形而上学史上一个“决定性”时代的代表作;还有保罗·德曼对德里达的回应以及他的其他著作;然后是斯塔罗宾斯基。[45]上述作品对卢梭的语言学论文所作的解读,并不打算强调其作品中有关音乐的内容,它们也并未在卢梭其他音乐著作的指引下来解读这部作品。卢梭自己说,这部作品发端于《二论》中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因为太长并且不太合适,后来就被他从《二论》里拿掉了。[46]卢梭指的是作品中的哪个部分我们不太好确定;不过,如前所述,我们现在知道《起源》中有个段落是发端于他最初回应拉莫时写的一段离题话,而回应是在他出版《二论》后不久就写成的。卢梭似乎将这两个被删掉的片段整合进一部单一作品当中了。大约1763年左右,这部作品才确定了其最终的形式,在这之前的不到十年中,卢梭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作这部作品。就在1763年,卢梭让《爱弥儿》的读者查阅这部作品以作为以下观点的证据:“精神性的事物会进入与模仿有关的一切。”[47]《起源》是卢梭《二论》中哲学计划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与拉莫之争的一部分,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视角,以考察卢梭的音乐理论与他的整体哲学之间的关联。
言语与可完善的激情
卢梭认为,语言与音乐同样起源于激情的表达,而激情只有当人们进入持续的相互接触后才能得到发展,这种持续的接触会激活人们潜在的激情和能力。他以描述作为人类独有特性的交流能力来开始他的《起源》一书:“言语区分了人与动物;语言区分了不同的民族。”语言上的多样源自当地的物理因素如气候之类。但是,卢梭对物理因素的强调,并未弱化他有关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潜在论证:由于人类的激情和才能是显著可塑的,物理原因才能在人类身上产生可变的影响。一些社会动物如海狸和蚂蚁也具有某种形式的语言,但它们的语言是自然且不变的。“约定的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能够发展,而动物却不能的原因。”[48]
卢梭在使用约定语言的能力与模棱两可的“进步”能力之间建立了联系,这就揭示了语言与他所认为的人类所特有的“自我完善能力”或“可完善化能力”有关。他是这样界定可完善化能力的,“这种能力,借助于环境的影响,继续不断地促进所有其他能力的发展,而且这种能力既存在于个人身上,也存在于整个种类之中。”这种能力之所以存在于整个种类中以及个人身上,乃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持续交往会使得人们需要和激情得到发展,进而激活人类的“可完善化能力”以及“以潜在的方式”为人所具有的其他“能力”[49]。卢梭在《二论》中说,“虽然语言的器官对人来说是自然的,但语言本身对人来说却不是自然的”[50];而他在《起源》中说,用于交流的语言的产生“不是来自于交流所用的器官的功能,而是来自于人的一种特有能力,正是这一能力使人得以运用这些器官服务于交往之目的。”[51]语言是人的潜在能力之一种,而将这种潜在能力实现出来乃是其可完善化能力的一部分。言语是人的官能,只有人才会在个体和种类的层面上不断进步。先前的哲学家们,尤其是亚里士多德,[52]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语言是人类的独有属性。当卢梭说,言语唯独属于人类时,该能力并未起到界定人类的作用,因为言语能力取决于那种真正使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可完善化能力;言语变得能够区分人与其他动物,但是并非以任何必然的或目的论的方式。
对卢梭来说,在源初和本质的意义上,语言和音乐是人用来交流其“精神需要,亦即激情”的。“逼迫人类说出第一个词的不是饥渴,而是爱、憎、怜悯、愤怒。”[53]解释语言与音乐之起源的这同一论证,同样也可以拿来解释它们对人心所施加的力量。言语与歌曲之富于表现力的特性并不像拉莫以为的那样,可以用发声体的和声变化这种“物理原因”来解释,与之不同,只能用能够产生“精神影响”的“精神原因”来解释。[54]卢梭在自然的或“生理的”激情与社会的或“精神的”激情之间所作的区分,对于整部《起源》而言至为关键。生理/精神这对基本区分,构成了贯穿《起源》始终的所有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的基础,[55]它同时也构成了这部作品中诸多二分法的基础:旋律vs.和声,南方vs.北方,古代vs.现代。
《起源》一书中生理的激情与精神的激情的区分,同样也构成了《二论》中有关人之本性与人之发展的核心论证的基础。[56]就其自然而言,人的生理的需要和激情是很容易满足的;但是当人类与其同伴不断接触时,这些需要和激情就发展为社会的或精神的激情。对卢梭来说,这方面的典型激情是爱。卢梭区分了爱情中“精神的”与“生理的”成分:“生理方面的爱是人人所具有的和异性结合的欲望。精神方面的爱,则是把这种欲望确定起来,把它完全固定在唯一对象上。”人类就其自然而言“仅仅局限于生理方面的爱”。[57]爱情的“精神”方面是自然的亦即生理的倾向的某种特定发展,这种发展是与一般而言的激情与才能的发展同时发生的。卢梭在性激情上所作的生理/精神的区分对于其他激情来说也同样适用,尤为显著的是自然的自爱与它的发展了的形式亦即“自尊”之间的区分。
伴随着精神激情的觉醒而来的,是人类与他们的同伴、与那些他们认作同类的人交流的欲望。正在发展中的精神激情的带旋律的声调,赋予了最初的语言以生命;因此,最初的语言是被唱出来,而不是被说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在性质上是诗性的和象征性的。为了阐明最初的语言是象征性的,卢梭给出了一个人遇到另一人的例子。这个人因为害怕,他所遭遇的人在他眼中就显得比那个人实际上更高大、更强壮,于是他称那个人为“巨人”。进一步的经验会使他发觉,那些人其实跟他自己差不多,然后他称那些人为“人”。[58]卢梭在《二论》中给出了有关野蛮人如何看待其“同伴”的类似描述,就在他讨论言语的起源之前:“时间一久,他就会看出在他的同类之间、在他的雌性和他自己之间有许多共同之点,他并能据此推断出另一些尚未被他发现的相似之点;……他便可以推知大家的思想方法和对事物的感觉与他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也是完全相同的。”[59]人类尝试着与那些被他视为同类的人相交流的前提是,他要认识到“另一个人”是与他自己相似的。[60]“一个人一旦将另一个人视为与己类似的、能感知的、能思想的存在,那么,交流感觉与思想的渴望或需要,会促使他寻找交流的方式。”[61]对同伴之人性的觉知,依赖于对共有激情的同情式承认,也就是说,依赖于怜悯。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在《起源》中,卢梭在解释南方气候中言语的源自激情的起源时,先讨论了怜悯。最早的那些散布在地球上的居民没有社会,只有家庭,没有语言,只有手势和某些不甚清晰的声音,因为这时他们缺乏社会的或精神的激情,而只有这些激情才能够导致社会与真正言语的产生。“唯有随着知识的增长,人的社会情感才获得了发展”,卢梭解释到,“怜悯虽于人心为自然,但若无想象的发动,它将永远沉睡不醒。”怜悯要求人出离于自身之外而与他人合一。“倘若对于他人所受之苦难一无所知,倘若对他与我共同具有的一无所知,那么,就算看到他人在受苦,我又怎能有所感受呢?”[62]
虽然卢梭在《起源》中论证说怜悯最初处于休止状态,这看起来与他在《二论》中的说法不一样,但经过仔细的考察后我们发现,这两部作品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矛盾。[63]卢梭在《二论》中的观点,并不是说怜悯最开始就是活跃的,而是说它是自然权利的一项“原则”,而自然权利并不以自然的社会性为前提条件,他在这里强调的是自然权利之前社会的基础。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说过,怜悯就其自然而言就是活跃的:他主张,怜悯是“按照自然顺序第一个触动人心的相对的情感”[64]。卢梭在《二论》中出于雄辩的目的似乎过分地强调了怜悯的作用,以支撑他将自然状态作为和平状态的想法。在《起源》中,卢梭揭示出,怜悯的发展构成了社会的或精神的激情与能力的基础。
人类激情和能力的发展取决于对共性的认识。当人类由于地震或火山喷发等自然事件聚集起来的时候,持续的交往培养了他们的能力和激情。“人们聚集在公共火炉周围,舞蹈,宴饮。亲密而甜美的联系,不知不觉将人类引向其同类。神圣之火在火炉中燃烧,最初的人道的情感在心中萌生。”就像在《二论》中那样,关键的发展出现于不同的家庭开始接触的时刻。南方干旱的气候使得共同的水源地对于那里的游牧民族来说至为重要,正是在这些水井旁边,分散的家庭开始相互接触。“在这里,家庭有了最初的交往;这这里,男女第一次相会……在这里,自童年起便早已司空见惯了的现象,开始多了一份甜蜜。”两性的相会为激情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时激情就超越其起初是习惯性的、本质上是唯我主义的基础:
在古老的橡树下,热情的年轻人渐渐失去了野性而变得温柔。为了使对方理解,他们学会了表达。在这里,第一个节日诞生了。轻捷的足在欢快地跳着,不过,这种热烈的姿态还是难以满足,需要伴之以充满激情的调子;欢愉与欲望合为一体。这里终于成为了民族的真正的摇篮,从晶莹明澈的泉水中迸发出最初的爱的火焰。[65]
作为被唤醒的激情的旋律优美的调子,言语和歌曲就这样诞生了。在《二论》的平行解释中,卢梭给出了自己的圣经堕落版本,他让他的爱人们围绕着一颗大树跳舞:“歌唱和舞蹈——爱情和闲暇的真实产物——变成了悠闲的、成群的男女们的娱乐,甚至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事项。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别人,也愿意别人注意自己……”[66]性激情正由一种生理欲望转变为精神激情,与此同时,自然的自爱激情正在转变为自尊。因此,交流能力的发展实为更为普遍的人性发展的一部分。
激情的发展以及想要传递这些激情的欲望标志了这样一个节点,此时人类变成社会的或精神的存在,并且形成了各个民族。[67]在《起源》中,卢梭比较了南方与北方寒冷地区的语言和音乐的不同起源,前者源于爱情,后者源于贫困。南欧人用“爱我”来表达他们的精神之爱,而北方物质贫乏的民族有着更为刺耳的要求,那就是“帮助我”。[68]气候这种物理因素,导致了人之激情的不同发展,进而导致了交流的不同典型形式。法语作为一种北方语言,带有其起源的印记;它的粗糙的发音以及柔弱的音节,使其无法支持一种响亮的音乐;因此,卢梭提供了一种解释,以说明他在《论法国音乐的信》中就意大利与法国音乐的不同之处所说的话。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在《起源》中,卢梭在讨论了语言的起源之后,转而分析了音乐的特点与发展问题。他以历史的方式呈现了音乐的发展,南方的饱含激情的旋律变成了北方的和声学。南方的旋律优美的语言仍然是语言和音乐的典型本源。他把最初的语言描述为“声调优美的”或“歌唱般的”。激情以抑扬顿挫的带旋律的声调来表达自己:“激情激发了所有的发声器官,竭尽全力修饰声音;于是,诗、歌曲、说话有着同一个源头。”一种语言或音乐的特点取决于带旋律的声调的种类,这种语言或音乐因声调而得到加强,而声调取决于发号施令的“激情的种类”。起初,“音乐不过是旋律,旋律不过是言语的声音变化。”[69]高度清晰的语言出自北方那源自贫乏的激情,反映了言语和歌唱的分离,这同样也是南方的旋律优美的语言所面临的命运。正如《二论》中所言,当人成为精神的和社会的存在时,也是他开始败坏的时刻。现代的欧洲语言,尤其是法语,有着北方起源,它们只是自私需要的刺耳表达,而且它们还代表了音乐与语言的蜕变过程的终点,这一过程同时伴着政治与道德的衰落。
音乐的蜕变在现代和声学那里达到顶点。因此,卢梭回到了他与拉莫就旋律与和声何者优先问题展开的争论,并以历史的方式重述了这一争论,这使得他的语言学论文与《二论》极为相似。他把自己与拉莫的争论重新表述为古今之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把古希腊人的旋律优美的语言和音乐与和声占主导的现代音乐进行比较,前者富于表现力,后者则枯燥无味。拉莫争辩说,古希腊音乐不可能富于表现力,因为它以不充分的和声学为基础。卢梭回应道,古希腊音乐建立在不同于现代和声的“原则”基础上,这些“原则”大体上源自几乎难以想象的旋律优美的语言。[70]在其政治思想中,卢梭指明了古代实践的优先地位,但又将它置于现代自然权利理论的新基础之上。同样地,在其音乐理论中,卢梭诉诸古代音乐和语言的强大感染力,但又尝试着在一种得到恰当修正的现代哲学取向的基础上重新恢复这种感染力,这一新取向认识到人类的交往存在两个层面,一个是自然的或生理的层面,一个是精神的或文化的层面。
若想对音乐表达和语言表达做出恰切的解释,必须首先对人的复杂本性做出解释。
每个人都承认,感觉改变了人,但由于我们没有对各种变化做出区分,于是导致了将原因混为一谈。对于感觉,我们既过于重视,又过于忽视;我们没有认认识到,感觉常常不仅是作为感觉,而是作为符号或意象,在影响我们,我们没有认识到,感觉对精神的影响,也有精神上的原因。[71]
卢梭对音乐表达的分析以《二论》中“生理的”与“精神的”区分为基础。和声的效果是“全然生理性的”,它只能产生一种“愉悦的感受”,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歌曲的完美表现力依赖于旋律,但既然旋律源自使用旋律的人的特有激情,那么,一种音乐的全部效果就会局限在那个特定的音乐-语言共同体中。“在我们看来的最为美丽的歌曲,对那些对它们完全陌生的耳朵来说,也不过尔尔,那是一种必须借助字典才能理解的语言。”[72]
音乐是一个语义系统,它取决于对一个民族的共享激情所做的旋律上的模仿:“旋律的声音之所以能作用于人,不仅仅作为声音,而且也作为爱的符号、情感的符号。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音乐在我们心灵中唤起了它们所表达的情感,我们在音乐中感受到了情感的意象。”[73]如果一种理论只研究音乐的单纯感觉上的效果,那么它就不可能理解其表现力的来源,且只能制作出苍白暗淡的作品。“如果有人想要对感觉的力量进行哲学研究,他必须从区分纯粹的感官印象与思想的、精神的印象入手,后者虽然通过感官来感知,但感觉仅仅是偶然的原因。他要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将一种力量赋予可感知的对象,而这种力量或者它们本来就缺乏,或者来自于呈现于我们的灵魂的情感。”如果音乐是社会的或精神的激情的表达,而这些激情又因民族的不同而相互区别,那么,音乐则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文化现象。[74]音乐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语义系统——甚至于一般而言的文化也应当被理解为一种语义系统。卢梭的理论认为,激情经由富于旋律的调子得到传达。他的这一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之存在的“精神的”层面是如何从当初全然“生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起源》以及卢梭的音乐作品对“生理”和“精神”关系做了最为全面的思考,同时还为我们理解他在《忏悔录》中所描述的那种形而上学理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主义》。[75]卢梭并未完成他的形而上学论文,但他的理论在《起源》一书中表露无遗。这为他在《起源》中讨论音乐的起源和蜕变的段落的最初来源所证实:也就是他从写给拉莫的回应里面所删掉的那段离题话。在那段离题话的结尾,卢梭表达了他反对还原论哲学的巨大野心,而这种哲学在音乐届的代表正是拉莫:
我们不要觉得,音乐对激情的主宰可由比例和数字来解释,因为,人们从中无法发现任何种类的自然与人的关联。原则和规律只是艺术的物质部分;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微妙的形而上学来解释音乐的巨大效果。[76]
在《起源》中,卢梭提供了这种形而上学,他在那里宣称,“在本世纪,人的所有努力都在使灵魂的活动物质化,并从人的情感中夺走一切精神性的东西,倘若新哲学能够证明它不会像毁灭德性那样,毁灭优雅的品位,我将表极大诧异。”[77]卢梭音乐理论的核心,或许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亦即小说《朱莉》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在那部作品中,他用了两封信的篇幅来论述这一主题,将他有关音乐的观点通俗化了。他解释说,音乐并非源于声音之间的物理关系,而是源于人的自然以及“激情和声音之间有力的、隐秘的关联”。[78]卢梭的成熟音乐理论是由相同的精神所激发的,建立在相同的原则之上,并且事关他的整个“体系”。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卢梭相信,他发现了音乐及其表现力的隐秘原则,并且他的音乐理论包含了一种新美学。若抛开卢梭音乐作品的哲学基础不谈,那么我们很难从这些作品中推论出这种新美学。确实,他的音乐创作与音乐理论所产生的效力,无法由它们的直接效果来说明,而应由激发了它们的精神和观念来说明。卢梭在他的音乐著作中表达了一种新美学,我们在他的《音乐辞典》中可以很好地体会到这种新美学的效力。
《辞典》反映了卢梭对其音乐理论所作的文字上的修改,以使其音乐理论与他的哲学更为一致。这本辞典脱胎于卢梭为《百科全书》所撰写的辞条,但是《辞典》中一半以上的辞条都是全新的,并且卢梭对取自《百科全书》的大部分辞条都做了实质性修改。[79]经过十多年的写作,《辞典》最终于1768年出版,并且“迅速取得了必备参考书的地位”。[80]在该书的前言中,卢梭解释说,他尝试着撰写一本理论融贯的辞典,虽然他觉得自己并未成功。不过,《辞典》中的潜在理论已足够明了,可帮助我们理解他那新颖的美学学说。
在《辞典》中,卢梭阐明了他的音乐理论,他认为音乐是人类激情的模仿性表达。模仿的核心地位意味着,卢梭归属于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久远传统。卢梭将音乐理解为对激情的模仿,这样的理解显示出,他的美学理论得益于杜波。杜波认为音乐可以模仿激情,他说“感受性”就是认出这些激情的能力,他甚至还比较了音乐效力的“物理”层面和“精神”层面。不过,杜波似乎又假定了一个不变的、普遍的人之自然,此外他还假定了一种为所有个体所共有的感受性。[81]卢梭的成熟音乐理论,以对人之自然与人之发展的与众不同的理解为基础,这种理解不同于他的前辈所明言或假定的任何理解,因此,他的音乐模仿乃是激情之表达的观点,以及他对激情的表达形式之多样性的坚持,都导向了一种新的美学学说。[82]
我们可以从《辞典》的许多重要词条中,看出卢梭音乐理论所发生的转变。其中,“表达”、“和声”、“模仿”、“旋律”、“旋律的统一”以及其他词条,都直接阐明了音乐乃是激情之表达的理论,这与《起源》中的观点如出一辙,有时还采取了与《起源》中相同的表达方式。其他的辞条则拓展了他有关音乐表达之多样性的理论。在“声调”词条中,卢梭讨论了带旋律的声调的自然基础及其文化上的多样性:“普遍的自然的声调,可从每个人吐字不清的叫喊中推断出来,是一回事;语言的声调,产生了专属某一民族的旋律,是另一回事。”当“激情的共同基础”主宰了所有心灵的时候,在不同的语言和音乐中存在颇为多样的声调表达。[83]在“音乐”辞条中,他着手处理不同的声调表达之间的不同之处,在这里他举了古希腊音乐、中国音乐、土耳其音乐以及其他音乐的例子。他认为,这些音乐种类代表了音乐的独特类型,无法借助据称是普遍的和声理论得到理解。
日内瓦公民所举的一个例子对我们启发尤大。他说,法国禁止演奏阿尔卑斯小调“放牧曲”,因为这会导致他们的瑞士士兵“哭成泪人,逃跑,甚或死去,这调子在他们身上唤起了返乡的强烈欲望。”他还注意到,这一效果在其他外国人身上并未出现。“因此,音乐并非作为音乐而起作用,而是作为记忆的符号而起作用。”[84]音乐天才就是能在他的人民的心中唤起这些意象的创造性源泉:“天才的音乐家能够使整个宇宙听命于他的技艺。他能用声音描绘出每一种画面;他能使沉默自身开口说话;他能用情感表达观念,用调子表达情感;他能在人们的心底唤起他所传递的激情。”[85]卢梭认为,音乐和语言是一个历史民族的表达,而艺术天才则是他们的民族的近乎先知般的声音,他的这些看法影响深远。
人们时常注意到卢梭的哲学与文学作品对他的后继者的影响。类似地,他的自传性著作展现了他有关自然以及人之异化的观点,这吸引了后来的浪漫主义者。他的音乐作品也不例外。我们能够在康德及其后的思想家的美学作品中识别出卢梭有关艺术天才的观念。他与拉莫的争论被认为是一场划时代的战斗,标志着古典美学统治时代的结束,以及新时代的开端。[86]实际上,卢梭的音乐理论直接影响了A. W. 施莱格尔对“浪漫的”这一术语的广泛使用,影响了他在古代的与现代的、“朴素的”与“伤感的”艺术形式之间所作的对比。[87]总之,卢梭的情感和观念使得他的音乐著作成为了其“体系”的一部分,而同样的情感和观念也激发了卢梭的后继者们。

注释:
*本文译自John T. Scott, “The harmony between Rousseau's musical theory and his philosoph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98, 59(2): 287-308.
**约翰·T·斯考特,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政治科学系教授,此文发表时他尚在美国休斯顿大学工作。任崇彬,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
我想在这里对Christopher Kelly教授给出的评论和建议表示感谢。
[1] Rousseau, Rousseau: Judge of Jean-Jacques: Dialogues, The Collected Writings Rousseau(hereafter CW)(5 vol. to date; Hanover, 1990-), I, 22-23. 另参“Letter à Beaumont”, Oeuvres complètes(hereafter OC)(5 vol.; Paris, 1959-95), IV, 933-36.
[2] 参见Robert Wokler, Rousseau on Society, Politics, Music, and Language: 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 Early Writings(London, 1987), chap. IV. 另参Michel O’Dea, Jean-Jacques Rousseau: Music, Illusion, and Desire(New York, 1995).
[3] Rousseau, Dialogues, CW, I, 164.
[4] Rousseau, Confessions, CW, V, 10, 60. 另参Maurice Cranston, Jean-Jacques:The Early Life and Work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54 (New York, 1982), 55-56.
[5] Rousseau, Confessions, CW, V, 98-103, 174-76, 155.
[6] 参见Rousseau, Confessions, CW, V, 227-28, 235-41.
[7] Rousseau, Dissertation sur la musique moderne, OC, V, 206.
[8] Rousseau, Confessions, CW, V, 263-64. [中译注]文中所引卢梭《忏悔录》部分的译文,均出自黎星、范希衡译本,有时略作改动;所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部分的译文,均出自李常山译本,有时略作改动;所引《论语言的起源》部分的译本,均出自洪涛译本,有时略作改动。
[9] Rousseau, Confessions, CW, V, 279-81.
[10] Rousseau,"Avertissement" to Les Muses galantes, OC, II, 1052.
[11] Rousseau, Lettre sur l'opéra italien et français, OC, V, 249-57. 基于内部证据,Pléiade版的编者认为信件写于1744年12月至1745年9月间,这与信件的最早刊印者Albert Jansen所做的推测不同,后者认为信件写于1750年左右(Jean-Jacques Rousseau als Musiker[Berlin, 1884], 455-63)。
[12] Rousseau to Mme de Warens, 27 January 1749, in Correspondance complète(hereafter CC), ed. R.A.Leigh (50 vols.; Geneva,1965-), II, 132-33. 卢梭为《百科全书》所撰写辞条的清单,参见Alfred Richard Oliver, The Encyclopedists as Critics of Music (New York, 1947), Appendix A.
[13] 参见Rousseau to d'Alembert ,26 June 1751, CC, II, 159-62.
[14]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tr. Richard N. Schwab (Indianapolis,1963), 100-101; 另参见Thomas Christensen, Rameau and Musical Thought in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1993), 7-11.
[15] Rousseau,"Accompagnement"(Encyclopedia version), OC, V, 1745, 1749.
[16] O'Dea, Music, Illusion and Desire, 10, 16.
[17] Rousseau, Confessions, CW, V, 294; 另参见Rousseau to M. de Malesherbes, 12 January 1762, CW, V. 575.
[18]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133, 103-4.
[19] See Rousseau, Confessions, CW, V, 322. 关于“喜歌剧之争”的解读,参见Louisette Reichenberg,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Bouffons"(Philadelphia,1937); Oliver, Encyclopedists as Critics of Music, chap. VII; 另参Cranston, Jean-Jacques, 284; Wokler, "Rousseau on Rameau and Revolution," Stud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4 (1978), 251-83.
[20] Rousseau, Lettre à M. Grimm au sujet des remarques ajoutées à sa lettre sur Omphale, OC, V, 273.
[21] 参见Rousseau, Confessions, CW, V, 313-22. 关于戏剧演出的历史, 参见 Cynthia Verba, Music and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Reconstruction of a Dialogue, 1750-1764 (Cambridge, 1993), 11 n; James Miller, Rousseau:Dreamer of Democracy(New Haven,1984), 138; Eve Kisch, "Rameau and Rousseau," Music and Letters, 22 (1941), 97-114.
[22] Rousseau, Dialogues, CW, I, 19-20, 160-63.
[23] 参见Wokler, "Rousseau on Rameau and Revolution," 256, 259-60.
[24] Rousseau, Lettre sur la musique française, OC, V, 289.
[25] Ibid., 292.
[26] Ibid., 328.
[27] Ibid., 296-97.
[28] 关于卢梭与拉莫如何看待吕利的宣叙调的一个更加全面的考察,参见 Verba, Music and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21-30; "The Development of Rameau's Thoughts on Modulation and Chroma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 26 (1973), 72-91.
[29] Rameau, Observations sur notre instinct pour la musique, Préface, Complete Theoretical Writings, V, 264.
[30] Cranston, Jean-Jacques, 279.
[31] Rameau, Erreurs sur la musique dans I'Encyclopedie, Complete Theoretical Writings, V, 208.
[32] See Verba, Music and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4. See also Wokler, "Rousseau on Rameau and Revolution," 261-62.
[33] Rameau, Erreurs, Complete Theoretical Writings, V, 219.
[34] Rameau, Génération harmonique, Complete Theoretical Writings, III, 6.
[35] 参见Rameau, Observations, Préface, Complete Theoretical Writings, V, 264-65.
[36] 关于拉莫与卢梭怎样看待自然与音乐的关系,参见see Kintzler, "Rameau et Rousseau: Le choc de deux esthetiques," Preface to Rousseau, Écrits sur la Musique(Stockholm,1979), xiii-xxiv; Colm Kiernan,"Rousseau and Music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French Studies, 26(1972), 156-65. 关于拉莫音乐理论之科学起源的更全面的讨论,参见Christensen, Rameau and Musical Thought in the Enlightenment.
[37] Cranston, Jean-Jacques, 288.
[38] Rousseau, Examen de deux principes avancés par M. Rameau dans sa Brochure intitulée, Erreurs sur la musique dans l'Encyclopedie, OC, V, 351.
[39] Rameau, Erreurs, Complete Theoretical Writings, V, 221.
[40] Rousseau, Examen, OC, V, 358-59.
[41] Rousseau, Examen, OC, V, 355.
[42] 有两位学者同时且各自独立地刊发了这段离题话: Marie-Élisabeth Duchez, "Principe de la Mélodie et Origine des langues: Un brouillon inédit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sur l'origine de la mélodie," Revue de musicologie, 60(1974), 33-86; 以及 Robert Wokler, "Rameau, Rousseau, and the 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17(1974), 179-238. 另参Wokler, Rousseau on Society, Politics, Music and Language, chap.IV and Appendix.
[43] Rousseau, L'Origine de la mélodie, OC, V, 331. 试比较Second Discourse, CW, III, 25-26, 31.
[44] Duchez,"Principede la mélodie," 48. 另参Cranston, Jean-Jacques, 289; Michèle Duchet and Michel Launay, "Synchronie et diachronie: I'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 et le deuxième Discour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82 (1967), 421-42; Glyn P.Norton, "Retrospective Time and the Musical Experience in Rousseau,"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34(1973),131-45;135.
[45]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1974); idem, "The Linguistic Circle of Geneva," in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Allan Bass(Chicago,1982), 137-53; Jean Starobinski, "Rousseau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in Jean-Jacques Rousseau: Transparency and Obstruction, trans. Arthur Goldhammer(Chicago, 1988); Paul de Man,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NewYork,1971); idem,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New Haven,1979).
[46] 参见Rousseau, 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 Projet de Préface, OC, V, 373.
[47] Rousseau, Emile, 340. 在《爱弥儿》的初版中,卢梭提到的是名为《论旋律的原则》的论文,但后来在1764年时他将之改为《论语言的起源》,参见Duchez,"Principe de la Mélodie et Originedes langues," 49.
[48] Rousseau, Essai, OC, V, 375, 379.
[49] Rousseau, Second Discourse, CW, III, 26-27, 42.
[50] Rousseau,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CW, III, 83.
[51] Rousseau, Essai, OC, V, 379.
[52] 参见Aristotle, Politics 1.2.1253a8-18.
[53] Rousseau, Essai, OC, V, 380.
[54] Rousseau, Essai, OC, V, 412-19.
[55] 参见Duchez and Launay, "Synchronie et diachronie."
[56] 有关卢梭思想中人之存在的“生理”样式与“精神”样式之间关系的一个更为全面的讨论,参见John T. Scott, "The Theodicy of the Second Discourse: The 'Pure State of Nature' and Rousseau's Political Though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1992), 696-711.
[57] Rousseau,Second Discourse, CW, III, 38-39.
[58] Rousseau, Essai, OC, V, 381-82.
[59] Rousseau, Second Discourse, CW, III ,44.
[60] 保罗·德曼讨论了这个片段并且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他强调了卢梭理论中的自恋元素:“典型的语言学模型是由直面自我的实体提出的。”("Theory of Metaphor in Rousseau's Second Discourse," Studies in Romanticism, 38 [1977], 488-95).
[61] Rousseau, Essai, OC, V, 375.
[62] Ibid., 395.
[63] 关于《起源》与卢梭的整体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起源》的写作日期,众说纷纭,对各种立场的讨论可参见Wokler, Rousseau on Society, Politics, Music and Language, 301-24; Charles Porset, "L' 'inquiétante étrangeté’ de l'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Rousseau et ses exégètes,"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54(1976), 1715-54. ; 对卢梭含混不清的怜悯陈述的另一种解读,参见Derrida, Of Grammatology, 165-94.
[64] 参见Rousseau, Second Discourse, CW, III, 14-15, 36-37 (emphasis supplied). 另参Roger D. Master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Rousseau(Princeton,1968), 71-72. [中译注]经核查,此处引文出自卢梭的《爱弥儿》一书。英译文请见:Rousseau, Emile, or On Education, trans.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p.222; 中译文请见: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05页。
[65] Rousseau, Essai, OC, V, 402-6.
[66] Rousseau, Second Discourse, CW, III, 47.
[67] 卢梭如何理解语言发展和政治发展与他有关文化的自然基础和文化多样性的理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个更为全面的讨论,可参见John T. Scott, "Rousseau and the Melodious Language of Freedom," Journal of Politics(forthcoming). 关于音乐与人的社会性的形成,参见Christopher Kelly, " 'To Persuade without Convincing': The Language of Rousseau's Legislator,"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1987), 321-35; 329.
[68] Rousseau, Essai, OC, V, 408.
[69] Ibid., 410.
[70] Ibid., 411-12.
[71] Ibid., 412.
[72] Ibid., 415.
[73] Ibid.,417.
[74]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证实了卢梭对人类学的影响,并且称他为人类科学的建立者("Jean-Jacques Rousseau: fondateur des sciences de l'homme," in Jean-Jacques Rousseau, ed. Marc Eigeldinger[Neuchâtel, 1962], esp. 240).
[75] Rousseau, Confessions, CW, V, 343-44.
[76] Rousseau, L'Originede la mélodie, OC, V, 343.
[77] Rousseau, Essai, OC, V, 419.
[78] Rousseau, Julie, ou la Nouvelle Heloise, 1.48(OC, II, 132). 小说中另一封讨论音乐特别是戏剧的书信是II.23.
[79] Verba, "Radical and Traditional Views," 320; Thomas Webb Hunt, "The Dictionnaire de Musique of Jean-Jacques Rousseau"(PhD.diss., North Texas State University, 1967).
[80] Hunt, "The Dictionnaire de musique,”358-59.
[81] Jean-Baptiste Dubos, 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la peinture,11.3; cited by Kintzler, Poétique de l'opéra, 506.
[82] 参见 Kintzler, Poétique de l'opéra, 492-514, 以及Verba, Music and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36-38. 试比较Georges Snyders, Le Goût musical en Franc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Paris,1968), 121-34.
[83] Rousseau, Dictionary of Music, s. v. Accent, OC, V, 614-15.
[84] Rousseau, Dictionary of Music, s. v. Musique, OC, V, 924. 参见Judith Shklar, Men and Citizens: A Study of Rousseau's Social Theory(Cambridge,1969), 141.
[85] 参见Rousseau, Dictionary of Music, s. v. Genie, OC, V, 837-38. 试比较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46-50. 关于卢梭对康德的更一般影响的出色讨论,参见Richard L. Velkley, Freedom and the End of Reason: On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Chicago,1989).
[86] 参见Kintzler,"Rameau et Rousseau: Le choc d deux esthétiques"; idem, Poétique de l 'opera française de Corneille à Rousseau(Paris, 1991); Cranston, Jean-Jacques, 288-89; idem, The Romantic Movement(London, 1994); 以及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Boston, 1919).
[87] 参见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Lectures on Dramatic Art and Literature, trans.John Black(London,1909), Lecture 1, 17-22.
本文刊于洪涛主编《卢梭的难题: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
1.《斯考特 斯考特 | 卢梭的音乐理论与他的哲学是一致的》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斯考特 斯考特 | 卢梭的音乐理论与他的哲学是一致的》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jiaoyu/421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