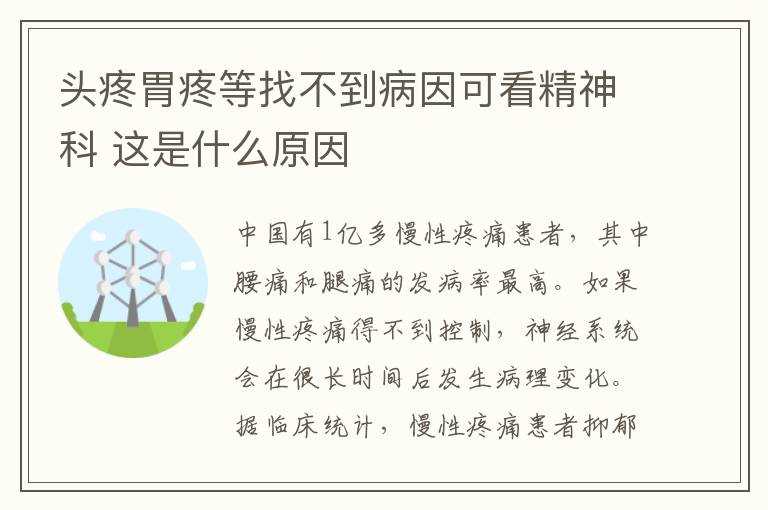在阿莫斯奥兹看来,故事的开头应该仔细阅读,这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契约。于是,他在《故事开始》中挑选了十部小说,尼古拉·果戈理、卡夫卡、契诃夫、卡弗、马尔克斯……如何阅读他们故事的开头,如何区分开头与整个故事的联系。如何履行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约定,如何探讨这些问题,在奥兹的分析下就像一场游戏一样有趣。

《故事开始》,阿莫斯·奥兹著,杨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月
一些尖锐(尖酸刻薄)的文学学者,如特里·伊格尔顿等人,甚至可以从小说开头的分析中读出作者心中的各种小错误,这真是“杀人”也是“照顾人心”。不可否认,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就像DNA隐藏了所有生命体的遗传密码,会奠定整本书的写作基调、叙事风格、语感,甚至一句话就开了一个学校。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最著名的第一句话:
许多年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连诺·布恩迪亚上校会回忆起父亲带他去看冰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句话几乎影响了所有的先锋派作家,我们会读到莫言、余华、马援、格非、孙甘露作品中的各种版本变奏曲。如果所有小说开头都选择“影响因子”最高的那句话,那么马尔克斯的那句话肯定会名列前茅。
上校同志真是个直男,面对行刑队。他想的不是浪漫或者激情爱人,而是冷冰。大概是《百年孤独》有大量的宅男读者,和标题相辅相成,值得孤独百年。女性读者可能更喜欢法国风格,无论是从翻译的美感还是场景的吸引力来看:
我老了。一天,在一个公共大厅里,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自我介绍。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大家都说你漂亮。现在,我在这里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你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还是个年轻的女人。比起你当时的脸,我更爱你那张满目疮痍的脸。”
想问一下哪个女人不怕漂亮的外表褪色,那么哪个女人受得了这样的甜言蜜语?叶芝的《当你老了》为这位写了许多晦涩难懂的诗的伟大诗人赢得了许多“脑粉”,以至于许多女孩眼中的叶芝几乎和徐志摩一样。我相信,没有王小波的赞美,玛格丽特·杜拉斯凭借《情人》的开头,足以吸引大量读者购买——一个写情书的参考。
爱情的确是文学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古希腊,因追求海伦而引发的争议催生了荷马史诗的创作素材。所以,小说一开始,就用一种方便的方式吸引观众去恋爱,去谈婚论嫁:
洛丽塔,我生命的光,我欲望的火。我的罪,我的灵魂。罗里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向下轻轻放在牙齿上:咯咯哒。(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
每个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个老婆,这已经成了举世公认的真理。(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即使是伟大的卡通也未能避免习俗。安娜·卡列宁的开头并不是以史诗般的一句“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开始的,而是编造了一句关于婚姻家庭的广为人知却又纯属偏颇的“金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所有和配偶吵架的文清都能背出图恩的这句名言。椿真的很懂人心,在他对处女座式叙事艺术的追求中,也不忘用QQ签名给读者讲一些好听的笑话。
当然,也有不考虑读者的自命不凡的作家,比如梅尔维尔的《莫比·迪克》的开头:
“叫我以实玛利。”
你要在第一句话里加个长评,取个名字,把圣经典故藏起来,欺负我们不看书?相比之下,查尔斯·狄更斯的装逼要可爱得多,尽管他的形式逻辑课程肯定失败了:
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一起上天堂,一起下地狱。(《双城记》)
在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之初,作者对小说艺术的刻意追求更具象征性。但是,有时候放在一起比较,却往往造成诡异的喜剧效果。比如,它也在睡觉。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的开头就表现了法国贵族的懒惰和优雅:
很长一段时间,我很早就躺下了。
然而,紧张的卡夫卡正在考虑:
一天早上,格里格·萨姆萨从不安分的睡眠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变形记))
不可能平平安安睡觉!
同样是介绍主角。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诚实地以“我来到这个世界”为开头。虽然主角的路还很长,但他还是一个正常人。但是,在20世纪的小说中,主角都不太好说话:如果你说“我是隐形人。”(拉尔夫·埃利森的《隐形人》)是个神话,所以“我是个死人。”(我的名字是奥尔罕·帕慕克的《红色》)是无稽之谈。至于“现在在哪里?现在几点了?现在是谁?”(塞缪尔·贝克特的《无名氏》),醉酒后的胡言乱语而已。
真正聪明的人是马克·吐温和卡尔维诺,他们甚至在第一本书的黄金位置宣传他们的书:
如果你没有读过一本叫《汤姆索亚》的书,你就不会认识我。但是没什么。那本书是马克·吐温先生写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冬夜行者》)
同样是先锋作家,为什么卡尔维诺的书能卖这么好?市场经济的先进经验值得学习!
言归正传,中国当代有很多作家的小说开篇就写得很精彩。中国人好面子。即使小说的结构和结局没有编好,这个“第一枪”也必须开始。它美丽的名字叫“凤头”,所谓:“开本之初,以奇句引人注目,惊一而不敢舍。这个方法也是。”小说的第一叙事通常包含了小说的所有叙事信息。在这里,我们列举几个茅盾文学奖得主的小说开头,看看有哪些“怪句”一看就震惊。你可以在几根管子里看到豹子。
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嘉轩后来成就了一生娶了七个女人的辉煌。
很难想象一部宏大的史诗是这样开始的。在英雄们展示他们高大的形象之前,镜头对准了他的下半身。如果是伪君子,就会遮遮掩掩,恼羞成怒。但是,被读者广泛看到的“英雄”白嘉轩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色彩。这是陈的独特之处,是《白鹿原》无法企及的:它让读者在阅读一部伟大的作品时,有一种读小黄人的感觉(外国文学中只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能与之媲美)。时代写作的气魄贯穿于小说的第一句到最后一句,中间没有一个瞬间是柔和的,真的能“导致壮美”。

《白鹿原》,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
阿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那是一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到窗外有一群野画眉在叫。
妈妈正在铜盆里洗手。她把一双白皙纤细的手泡在温暖的牛奶里,大口喘气。把她的手变漂亮好像很累。她用手指敲着铜盆的边缘。随着一声巨响,盆子里的牛奶泛起细密的涟漪,嗡嗡的回声在房间里飞来飞去。
如果说《白鹿原》的开篇是一个壮士,那么《尘埃落定》的开篇简直就是傅先生的自白。《红楼梦》里的宝二爷“有些呆”,而《尘埃落定》里的二少爷是个“傻子”。一开始他写的是13岁的傻子起床时看到的和想到的,空精神跳跃,洒脱,文笔发光。从小说一开始就不难看出,阿来比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第一章要短。

《尘埃落定》,阿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4月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从最高点看上海,上海的胡同是一个壮观的景象。和城市背景是一回事。上面突出的是街道和建筑,是一些点和线,而它是中国画中一种叫做占卜的笔触,用白色填充空。天黑了,灯亮了,这些点和线都亮了。在那盏灯的背后,是上海的小巷,一片黑暗。黑暗看起来几乎波涛汹涌,几乎推开了几条线的光亮。它有一个体积,但是点和线浮在表面,它的存在是为了划分这个体积,它就像文章中的标点符号一样,断行断句。黑暗就像一个深渊,扔下一座山,静静地沉入谷底。这就像藏了很多石头,如果你不小心,船会翻的。上海的几行光,都叫暗捧,一捧就是几十年。东方巴黎的辉煌是建立在黑暗之上的。一家店就是几十年。现在的一切都显得陈旧,一点一点的展示着原著。
我相信从最高点看垃圾场会是一个壮观的景象。距离可以创造美感,模糊一切肉眼可以看到的污秽。王安忆《长恨歌》中的文字,像她的女主人公王启尧一样,绝对充满了风情,但外表也很模糊。比如这段点、线、光、暗根本看不到巷子,但好像在看“几何图元”。王安忆对上海的城市氛围相当熟悉,但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她只能选择站在最高点看城市,这样才能让自己“眼不见,心不烦”。正如作者自己所说:“面对上海这样的写作素材,我有些遗憾...上海是个历史太短,物质太多的城市,人不够浪漫。”而这恰恰是小说一开始就巧妙地透露给读者的信息。

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11月
贾平凹(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如果你问我,我最喜欢的女人是白雪公主。
清风街喜欢雪的男人很多。都是绿眼睛的狼,所以我一直在偷偷观察。一旦有人送白雪公主一个发夹,一个梨,说太多阿谀奉承的话,或者说路过白雪公主之后说她不在,我就用刀在他的柿子树上割下一圈皮,让树慢慢死去。这些白雪不知道。
如果说《尘埃落定》的叙事是“傻子讲梦”,那么《秦腔》的叙事就是“疯子”。胡建天生矮小,父母也不重要。而贾平凹的本事,就是从短暂琐碎的父母身上,写出人生的悲欢离合,社会的沉浮。疯子的话是对生命毫无意义的隐喻——一段被阉割了的疯狂的爱情。

《秦腔》,贾平凹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4月
莫言(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马洛亚牧师拿着一个黑色瓦罐,走到教堂后面的街上。他一眼就看出,铁匠上官福禄的妻子上官露诗正弯腰拿着扫把扫康,在街上扫土。他的心猛跳,嘴唇颤抖,低声说:“上帝,万能的上帝……”他用僵硬的手指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慢慢退到角落里,默默观察着高大肥胖的上官露诗。她静静地专注地扫去被夜露打湿的浮土,小心翼翼地拣出浮土里的杂物扔掉。
虽然莫言凭借小说《蛙》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正如余华所说:“从文学标准来看,莫言至少可以获得10个茅盾文学奖。”最喜欢的是《大胸肥臀》的开场,和《尤利西斯》的开场挺像的。然而,一会儿,是驴生孩子,是婴儿接生,是魔鬼进村。混沌中洋溢着顽强的生命力,画面变得立体。3D电影的感觉可以用线性词来描述。现代文学有端木蕻良,当代作家有莫言。
《檀香刑》就像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却远比《百年孤独》啰嗦。没有办法。谁让叙述者用了“狗肉美,美,美,美”的说唱,算是艺术真实?
那天早上,我父亲赵佳做梦也没想到他会在七天内死在我手里;宁死也不做忠于职守的老狗。我无法想象一个女人可以用剑杀死她的父亲。我想不到的是,这个半年前仿佛从天而降的公爹,真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莫言小说》,莫言,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
格非(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1956年4月的一天,梅城县县长谭功达开着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水库的煤尘路上。路左边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岸边密密麻麻的芦苇和菖蒲,一群群白鹭在水边飞翔;在公路的右侧,大面积的麦田和棉田像挂毯一样向远处的地平线蔓延。片片芜菁、蚕豆、紫云英点缀着白色、紫色、蓝色的花朵。
谭功达脸色阴沉,忧心忡忡。他的膝盖上放着一张破破烂烂的地图,是梅城县的手绘区域行政规划。他不时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画圈。在地图下面,姚的小腿,这个秘书,有节奏地撞击着他的神经。他忍不住抬头看着她。姚穿着卡其色的布莱宁西装,原来的蓝布已经褪了色。梳着角,脖子上围着一条深红色的围巾。她正和坐在前排的副县长白。她咯咯地笑着,扭动着柔软的腰,不时指着窗外。
“怎么会有这么多鹤?它们飞到哪里去了?”姚佩佩问道。
“傻小子,那不是鹤!那是白鹭和海鸥。”白纠正道。
“那是什么?你怎么还在动?”姚拍了拍白的肩膀,伸手指了指远处。
“哦,那是长江上的一艘帆船。船体被高河堤挡住,只能看到帆尖行走。”(《山河梦》)
格非不仅在小说叙事意义上表现突出,而且是中国作家中不可多得的学者型小说家。学者格非在小说中并不是靠炫目来学习,而是经常用一些没有文字或历史的词来模仿。比如《江南三部曲》第二部开头,就很难不让人想起卡尔维诺的《一子爵分成两半》:
我们和土耳其人打了一场战争。我的叔叔,泰国拉尔巴子爵梅达多,骑着他的马在波希米亚平原上,直接去了基督教的住所。一个名叫库尔西奥的随从跟着他。一大群白鹳在浑浊停滞的空气中低飞空。
“怎么会有这么多白鹳?”梅达多问库尔希奥。“它们飞到哪里去了?”
……
“他们飞往战场,”随从沮丧地说。“他们得全程陪着我们。”
这一定不能算是“抄袭”,因为以格非的知识水平和叙事能力,是有可能避免“英雄所见略同”的尴尬的。我相信这是他的本意。正如一些批评家指出的那样,格非作品中的“中国经验”与西方现代后现代经典文本有着明显的“互文”关系。格非喜欢这种互文关系。这位先锋小说家在小说的开头模仿卡尔维诺或博尔赫斯才是恰当的含义。

《江南三部曲》,格非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
附:余华
1965年,一个孩子开始对夜晚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我回想起那个细雨飘动的夜晚,我睡着的时候,我小得像个玩具一样被放在床上。屋檐下滴落的东西,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我渐渐入睡的,是雨中水滴的渐渐遗忘。应该是在这个时候,我安然平静的去睡觉的时候,它好像呈现出一条安静的道路,树和草依次向旁边移动。一个女人的哭声从远处传来,她沙哑的声音在一开始寂静的夜里突然响起,让我记忆中的童年都在颤抖。
在当代众多有实力的作家中,余华是茅盾文学奖最大的遗产。由于题目的限制,这里的附录把《在细雨中呼喊》的开头放在了我最佩服鼓掌的地方,尤其是“让童年在此刻颤抖”,真是天才的一笔。难怪今天很多读者对余华的作品感到失望。即使后来写的作品还不错,也只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

《在细雨中呼喊》,余华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
1.《小说开头怎么写 故事开始了:茅盾文学奖得主们如何写小说开头》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小说开头怎么写 故事开始了:茅盾文学奖得主们如何写小说开头》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junshi/9985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