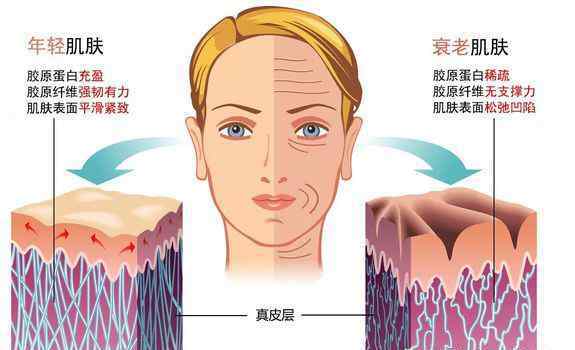“切!”
最后,我看了看眼镜里的头发。当我闭上眼睛时,我对理发师说。“咔嚓”一声,留了4年的齐肩长发不见了。
再过一个月,流产就19岁了。15岁的时候来到广东,在各个工厂区搬来搬去,和朋友一起玩“杀马特”,因为“他买不起别的东西,就玩头发”。但是今年,不要让工厂里留长发的工人。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找到工作了,身上还剩下两百多块钱。
对于“90后”和“80后”来说,2008年至2013年风靡一时的《杀死马特》并不陌生。他们一度被视为社会“异端”:来自乡镇的低学历年轻人,穿着廉价的小摊,模仿日本、韩国明星、动漫人物等夸张怪异、五颜六色的发型...
近日,纪录片导演李一帆拍摄的《杀死马特我爱你》在网上走红,《杀死马特》再次引起公众关注。李一帆说,他讲的实际上是“工人的故事”。
广东东莞石牌镇是影片中“杀马特”聚集的场景。这里有很多工厂。每年春节后,源源不断的工人像候鸟一样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如今,石排里的“杀马特”青年已经逐渐消失。他们为什么离开?你去哪了?
▲根据《杀死马特我爱你》截图
为什么离开
“工厂不再招聘长发工人”
“杀马特”们纷纷离开东莞石牌,而工厂是挑起这一风潮的直接因素。
11月底,红星记者来这里的前一天,石排刚刚留下两个“杀马特”,原因和小月一样:今年工厂招聘减少,对工人的要求更严格——工厂不再招聘长发工人。
罗福兴,25岁,广东梅州人,暂居石牌,自称11岁时“创造”了“杀马特”的概念,并在网上自称“杀马特教父”。在现实生活中,初中第一天辍学后,罗福兴做了一名临时工,学习美发。但在QQ群中,他“杀马特”的追随者越来越多。
记者在石牌粮食研究所附近的出租屋见到了罗福兴。他留着长长的卷发,黑色衬衫,黑色裤子,黑色皮鞋配高跟鞋。“今天‘杀马特’空的生存空间比以前窄了。”罗福兴说,在过去,有许多工厂,而且总是有需要的工厂。赚的少吃的少是大事。但是现在,“有这样的头发,连饭都吃不上”。
罗福兴说,他曾几次试图“复活并杀死马特”,但都失败了。今年10月,“杀马特”线下聚会也在当地取消。
▲罗福兴
一个多月前,江还留着长发。他在罗福兴的一个出租屋住了一个多月,但仍然找不到工作。后来他剪了头发,去了一家工厂,月薪4000元。不久,他退出了由罗福兴组建的“杀死马特”小组。
陈东理发店在石牌街开了8年了。这家理发店的名字里全是“杀马特”——“名人”。
“是‘杀死马特’救了我。”陈东是“杀死马特”的老熟人。他说刚开店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杀马特”的时尚潮流,发了20块钱。一天营业额三四千。“你一开门,屋里都是人,基本上都在做‘杀马特’的发型。”依靠那些年的“杀马特”生意,陈东在家乡买了房子和车,娶了妻子。
现在,“名人”已经成为“杀马特”这条线下唯一的纽带。偶尔,陈东会收到一些“杀死马特”的信。店里每周最多有三五个“杀马特”的客人,“大部分时间都是为了直播”。
东莞石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杀马特”?
在李一帆拍摄时,发现很多来自南方山区的农民工聚集在石排公园。在大型节日,一些人穿着传统服装聚集在石排公园唱歌、摔跤和闲逛。“在这里,没有人会觉得你很怪异。”李一帆表示,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也是《杀死马特》在2013年前后被全国主流网友嘲讽讽刺时得以幸存的原因。
除了落户的工厂,在石排,还有石排公园和溜冰场,是他们为数不多的线下公房空。“杀马特”们做完发型换好衣服后,要么去石筏公园,要么去溜冰场:在溜冰场,10块钱就可以滑冰;在石排公园,“杀马特”们可以闲逛、跳舞、唱歌、自拍。
但是今年年中,溜冰场关闭了。
▲《杀死马特》线下派对地图据受访者称,
新债券
“我知道杀马特,几乎每个人都玩直播。”
旧的聚集地不再是过去的样子,新的纽带正在连接。同样是身份表达的领域,只是这个纽带没有实体。
嘈杂的背景音乐响起,卢晓脱掉拖鞋,随着音乐赤脚在地板上跳舞——两分钟前,卢晓还在客厅和人PK。这种舞蹈是对失败的惩罚。
吕霄,21岁,云南人,留着一头染成金黄色的及肩长发,现在住在罗福兴的一所出租房里。为了直播,今天下午他去理发店摆了个姿势——他的左头发高高的,染满了红色和蓝色。这个型号50元,只能用一天。
吕霄已经直播6年了。他很早就辍学了。15岁那年,他和叔叔在工地上搬砖,挣钱买手机。看到短视频平台上“杀马特”的发型,“觉得很好玩,很好看”,开始尝试做头发,直播。
他不知道怎么操作,直播时间也不固定。“想起来就能打开。”。有时候会得到一些粉丝的奖励。吕霄说,直播的目的是“留下一些回忆”。他会收到一些“粉丝”的私信,这是他每天不断更新视频的动力——内容除了头发就是跳舞。
▲卢晓,谁在直播
当线下公众空空间越来越窄的时候,网络直播就成了“杀死马特”的新链接。“大家聚在一起热身。虽然玩法不同,但核心是一样的。”罗福兴说,在他认识的“杀人马特”中,“几乎每个人都玩直播”。他补充道:“我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有一些流量,可以销售商品。”
罗福兴从年初疫情开始就做了现场直播。当时他因为疫情被困在重庆,“没钱吃饭”。他的朋友建议他做一个现场直播,但他没有想到会成功。从那以后,他一直把头发剪掉。他向记者强调:“就算剃光头,我也会杀了马特。”。我在‘杀马特’,和头发无关。"他明确否认了那些他们认为是对传统美学的抵制的解释。"杀马特基本上是工人,我们没有这个意识。"
除了销售商品,罗福兴的大部分直播都与发型有关。还有一家公司和他合作,有团队,有合伙人,但是合作一个月后就分手了,因为感觉没有什么起色。
罗福兴还承接了一些理发业务——一些来这里找他理发的粉丝,其中一个100元,就在楼下的理发店里。除了场地费,可以赚几十块钱。这样,罗福兴一个月能赚一万元左右,在玩“杀马特”的人里算是“顶流”了。
“你觉得《杀死马特》被消费成直播了吗?”记者问罗福兴。
“消费证明‘杀马特’有价值。如果不消费,那就完全没有价值。这个群体可能真的消失了。”初中辍学的那个人总结说,他不反对“杀马特”被消费,但是他鄙视一些没有“杀马特”的人为了吸引眼球开始直播。对罗福兴来说,他想抓住这个机会,但他不知道如何抓住它。“我想不出我还能做什么。杀死马特的标签已经‘贴’上我了。”
“‘杀马特’大多来自农村社会。城市中的亚文化最终可能成为一个品牌形成商业价值,而‘杀死马特’却没有商业价值,甚至没有资本使用它们。”李一帆说他问过很多人关于“杀死马特”的问题,但是没有人知道谁通过玩“杀死马特”发了财。
那天晚上,吕霄坐在出租屋阳台上的一把椅子上,睡了两个小时——为了让她的发型保持得更长。
矛盾:
夸大网络,封闭排斥现实
除了工厂,是什么让《杀马特》上线?
文化断层是“杀马特”讨论中的一个关键词。李一帆说“杀死马特”爱头发超乎他的想象。他一度认为那些奇怪的发型是对主流文化的反击,但很快他发现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因为信息不平等和文化断层,他们觉得自己是流行文化。”
在四年的拍摄过程中,李一帆发现《杀死马特》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他用五个字概括:留守儿童,文化程度低,工厂流水线小工人,没时间没钱。
事实上,“杀死马特”的大部分生活足以用“苍白”来形容——小月工作的工厂,月薪3000元,工作时间10小时以上,一周工作6天;另一只被采访“杀死马特”的雌鸽,曾经在东莞的两家工厂。她要加班到晚上10点,还要一直值班,会被扣“漏号”。
▲直播中的卢晓
所有被采访的“杀马特”都表示,与之前相比,“杀马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太大变化。在直播过程中,经常有人在直播室尖锐地对罗福兴说:“你过时了”。很多时候他会选择假装没看见,有时候会故意和对方吵架,活跃气氛。
吕霄在广州白云区呆了四个月,才来到石牌找“领导”。起初他想在城市里散步和玩耍,但很快他就放弃了。因为我长头发,路人上街后会自动远离他。“有人觉得我是坏人,有人觉得我是乞丐。”他选择留在住处,几乎不出门。
"“杀死马特”是一个代表自由的不羁的灵魂."《杀死马特》是小鸽子情绪的出口。“这让我觉得我就是我,我会变得非常勇敢,非常强大。”她在网上自称“公主”。这样的“自封”在“杀马特”中并不少见。李一帆对此的解释是:所谓的称谓只是一种关于兄弟姐妹的游戏关系——越穷越喜欢华丽的辞藻。
相对于网络上的极度夸张和喧嚣,“杀马特”的真实世界是封闭的、排外的。李一帆说,他甚至在拍摄前找不到“杀死马特”,他可以通过罗福兴进入这个小组。他们已经联系了六七百个“杀死马特”的人,认识了近200人。很多人中途拒绝面试。最后他们线下采访了67人,通过网络采访了11人。
“杀死马特”的排他性超出了记者的想象——在石排的最后一天,记者和吕霄遇到了一只来到名人理发店做头发的小龙。他是贵州人。他20岁,10岁就出来了。看着吕霄标志性的“杀戮马特”发型,龙啸主动搭讪。吕霄没有理会他,因为“不是一个家庭的人无法分辨这是好是坏”。
▲根据《杀死马特我爱你》截图
今后...
未来?说到这个词,这群年轻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李一帆总结说,虽然很多“杀马特”在广东呆了很多年,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广州或深圳。即使在休息时间也要呆在工厂里。“城市太大了,不能迷路。只有厂区才能让他们觉得舒服。他们很少看城市里的高楼,甚至不敢看。因为我知道我永远买不起。”
根据李一帆的观察,“杀死马特”小组是不断变化的。他把“00后杀马特”归为“新一代杀马特”。比起十几岁小学毕业出去打工的“老杀马特”,他们的教育水平提高了。
对于和杀死马特有类似经历的陈骁来说,尽管他认为石筏可以整合,但他从未将石筏视为作家。石排不是“杀马特”的家——罗福兴在石排才半年,线下租的房子一个月五六百,是“没有任何压力”的,但他并不打算在这里长期待下去。
“你以后想干什么?”当记者问这个问题时,罗福兴停顿了一下。他想了想,说:“我没想那么远。先过好今天和明天吧。如果我想得太远,我就达不到。”
▲来采访的记者、艺术家,有时候会送书。直播的时候,罗福兴经常用来垫手机支架
罗福兴曾经想过攒一笔钱,“至少10万”,在家乡养几百只鸡,养一些猪和牛,建一个池塘,买一辆摩托车。直播对他来说不是长久之计。“以后也有可能开理发店,或者去公园给人理发?”他对自己说。
这只小鸽子计划在年底回到他的家乡。明年,他将回到东莞和罗福兴重振“杀马特”。“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帮助,拍视频。”
不久前,小月在大厂找到了一份工作,月薪近4000元。虽然她一天工作10个小时,经常接触很大的噪音,但在找工作难的时候,这仍然是一份让同龄人嫉妒的好工作。
这家工厂生产的电子元件最终将销往广州和其他城市。"老板说,‘小蛮腰’附近的一家商场正在出售."我是从贵州老家坐车过来的。和工厂里的大多数合伙人一样,虽然离广州只有100公里,但他根本不了解那里的世界——他住在工厂里,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小蛮腰”。
▲晚上10点,罗福兴出租屋楼下的家庭作坊还在赶着上班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李人庆:
《杀死马特》构成了第二代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杀死马特不是所谓的朋克,也不是与传统美学的对抗。他们是一群来自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和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二代农民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李人庆走访了许多杀害马特的年轻人的家乡。他发现两者有很多共性:贫困差距的孩子进入沿海地区的现代领域,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大多处于13~23岁的青春期,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家庭照顾;通过网络互相连接。
李人庆说,与上一代人不同,他们渴望表达自己的自主意识,被认可和理解,但他们缺乏表达的内容,所以他们只能选择玩头发,这是一种低成本、高识别率的方式。“这是一种‘保护机制’,是一种受现代性发展和不均衡发展启发的文化现象。”
李人庆认为,“杀死马特”和痤疮一样,是社会正常而必要的一部分,构成了“第二代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寻求自主的表现。他用李一帆的话总结道:“社会应该给他们说话的机会。”
李人庆发现,李一帆的纪录片《杀死马特,我爱你》也在同代城市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所以他认为,“杀马特”群体反映的问题其实是同代年轻人的通病。
“这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问题。”李人庆说。面对这一群体,有必要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当今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是日益加快的技术社会变革与日益城市化和老龄化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必须从表达权入手。“我们必须给年轻人,特别是弱势的年轻农民工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资源,让他们能够更快地成长。”李人庆说。
1.《杀马特吧 工厂不招长发工人,男子剪掉“杀马特”头发,曾被人当乞丐,如今月工资4000,同伴嫉妒》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杀马特吧 工厂不招长发工人,男子剪掉“杀马特”头发,曾被人当乞丐,如今月工资4000,同伴嫉妒》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keji/7716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