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长沙王司马义掌握朝政时,任命嵇绍为侍中。司马死后,嵇绍被成都王司马颖贬为平民。东海王司马越发兵邺域前,嵇绍官复原职,随惠帝出征。临出发前,同僚侍中秦准好心关照嵇绍说:“此次出征,安危难测,你备有好马吗?”
挟天子以令诸侯
意思是说,如果吃了败仗,你好快点逃跑。嵇绍严肃地回答:“臣下护卫皇帝,生死都得追随,要好马做什么!”嵇绍果然忠心耿耿,他登上辇,用身体护卫着晋惠帝,以防飞来的冷箭。乱兵赶到,举刀要杀嵇绍,晋惠帝大声喊道:“这是忠臣嵇侍中,不能杀!不能杀!”
一个傻皇帝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在大难来临的关键时刻,是最容易分清好人和坏人的。患难之际见真情。可是皇帝的话现在谁还听,有士卒顶撞说:“皇太弟有令,只有皇上一人不得侵犯!”说完,咔嚓一刀,嵇绍人头落地,鲜血溅了晋惠帝一身。晋惠帝顿时吓得掉下车来,昏倒在路边的草丛里,随身携带的玉玺抛落,被石超的兵拾去。石超还算有点天良,喝令部众不得无礼,自己下马相救,叫醒惠帝,扶他上车,拥入本营。问惠帝有无痛楚,惠帝有气无力地说:“痛楚尚可忍耐,只是腹中久饿呀。”

石超命左右拿来秋桃,惠帝吃了数枚,聊充饥渴。石超向司马颖报捷,司马颖派遣卢志将惠帝接回邺城。晋惠帝虽愚钝,却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来到邺城后,有人要惠帝把脏衣服脱下来洗洗,他悲怆地哭道:“这上面有嵇侍中之血,何必浣之!”
傻子的心,远比聪明人纯洁。嵇绍被安葬在荥阳,其高风亮节感动世人,有三十多位故吏门人在他的墓前守哀三年。成都王司马颖意外得到晋惠帝这个宝贝,心中大喜,马上举行了盛大的迎驾仪式。司马颖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砝码。即逼惠帝宣布大赦,改元为建武。这是该年内第三次大放,第二次改元。仅数月之内,晋惠帝连遭变故,几番惊吓,弄得灰头土脸,伤痕累累,有何“武功”可谈?很明显,“建武”是成都王夸耀自己的强盛武力,其称帝之心昭然若揭。
司马颖高兴之余,忽然想起东安王司马繇:这家伙曾劝我投降,真是晦气。于是将司马繇满门抄斩。司马繇的侄子司马闻讯大惊。司马睿时年二十九岁,十五岁时,袭父亲司马觐之爵位,成为第三任琅琊王。司马韬光养晦,恭俭退让,机敏大度,内敛谨慎,做事低调。此前司马容一直在洛阳,荡阴之役后与惠帝一同变为邺城的俘虏。东安王司马繇是司马觐的弟弟,也就是司马的嫡亲叔父。他一死,邺城之内最惊惶不安的就是司马。这时,幕僚王导劝司马容尽快逃出邺城,回琅琊封国去。
然而,要逃出邺城谈何容易。邺城全城戒严,达官显贵出城必须经过司马颖的批准。是夜,司马睿换了一身普通装束,乔装打扮,抱着侥幸心理,打算潜逃出。但邺城防备严密,司马睿无计可施。也许是司马命不该绝,晚上,最初是月明星稀。但到了夜半时分,突然阴云密布,雷雨骤至,守军躲雨不暇,司马容趁机出城。虽然逃出了城,仍未脱离危险。原来成都王为了防止那些被挟持来的朝臣逃,设下关卡,禁止显贵官员通过。当司马睿策马来到河阴渡口时,他被把守的官吏拦了下来,估计人家看出他身上有高贵的气质。

在这千钩一发的时刻,司马睿的随从宋典从后面赶了上来。宋典十分机智,大大咧咧地用鞭子敲敲司马,打趣道:“哟,舍长,有令禁止贵人过河,你怎么也被拦了?哈哈,看不出你还是个大贵人呢。”一听这话,知道来人原来仅仅是个小舍长。把守的官吏疑心顿消,也哈哈一笑,放走了司马。司马睿悄悄来到洛阳城,接上母亲夏侯氏,离开是非之地,赶回自己的封国。琅琊国是一小国,地位低,力量小,只能依附其他司马王族,在政治上根本不敢奢望有什么大的作为。
没想到,司马容这一逃跑,竟然给奄奄一息的司马家族带来了希望。在琅琊国安顿后,司马睿坚定地加入了东海王司马越的阵营,日后被委任管理江南,成为晋朝的中兴之君。如果没有苍天的眷顾和宋典这个小人物的机智,历史上也许就不会有东晋王朝。
害死太子的元凶王浚
司马颖大权在握,沉浸在皇帝之梦中不能自拔,先是在邺城南郊祭过上天,眼下正忙着安排新的文武大臣。刚忙活了几天,忽然有人来报,司马腾和王浚率十几万大军杀邺域来了。司马腾是东海王司马越的亲弟弟,山西并州宁北将军、并州都督,手握方重兵。王浚出身太原王氏,是晋朝开国功臣王沈的儿子。王沈是曹魏时期有名的变节之人。他擅长作文,年轻时深受魏主曹髦宠信,被曹髦尊称为“文籍先生”。当年曹髦密谋袭击司马昭,召来心腹王沈同商议,亲耳听见曹髦那句千古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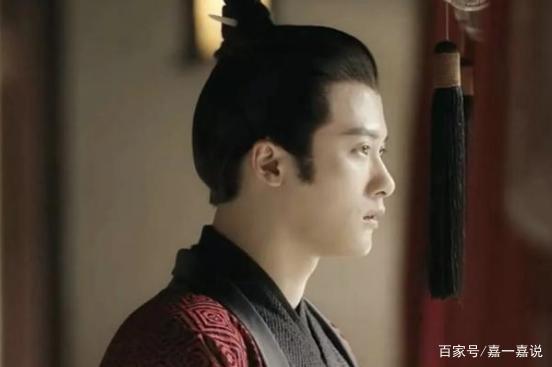
王沈辜负了曹髦的信任,跑去向司马昭通风报信,因此被世人视为不忠。王沈不以为耻,他获得了实惠,从此深得司马氏信任。晋代魏以后,王沈正待飞黄腾达可惜寿命太短,266年就病死了。王浚是王沈唯一的儿子,可王沈对其不屑一顾,没有半点亲情,因王浚是他偷腥的私生子。当年有个赵姓佃户家的妇人出入王沈家,给王家打杂。不知怎么的,王沈就把这个女人的肚子搞大了,生下了王浚。本来这事无人知晓,现在可好,连儿子都有了,不是强奸就是通奸,铁证如山,弄得王沈很没面子,所以他一直都不喜欢这个儿子。
王沈死时,王浚オ十五岁,王氏族人和亲成们共推王浚为嗣子,继承了父亲的博陵县公爵位。贾后专权时期,王浚是害死太子司马遹的元凶之一,因而被升迁为青州刺史、宁北将军,又转徙为宁朔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手握重兵。也因背负上述恶名,此后几年,王浚一直蜗居在东北偏远的幽州蓟城,不敢踏进中原。为了现固自己的地盘,扩充势力,王浚主动与乌桓族和鲜卑族交好,将大女儿嫁给段氏鲜卑族的大头目段务勿尘,将二女儿许配给另一大酋宇文苏恕延,还替段务勿尘讨得了辽西郡公的爵位。
如此一来,段氏鲜卑对王死心塌地。据记载,王没至少有五个女儿,嫁给鲜卑人的这两个是他的妾所生,剩下个女儿都嫁给了名门望族的后代,可见王浚是很注重门第观念的。当时司马家频发内战,依靠谁都有押错宝的危险,王浚找鲜卑人当后盾,那是最好的策略。他明白,只有借助外部的强大力量オ能确保平安,在乱世中オ能左右逢源,把官坐稳。在三王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的时候,天下人云集响应,而王浚采取的策略是保持中立,隔岸观火,严令部下谁也不得参加三王义兵:让他们闹去吧,咱只管用心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王浚坐山观虎斗,让成都王司马颖记恨在心。司马伦死后,中原内战打得乱七八糟,为先稳住王浚,司马颖奏封他为安北将军。随着王浚的实力越来越强大,成都王司马颖对王浚的嫌忌也越来越深。幽、冀两州是成都王的势力范围。幽州就在冀州的背后,背后潜伏着如此强大而又虎视眈眈的敌人,成都王如芒刺在背,必欲拔之而后快。而王浚有染指冀州进军中原的企图,被成都王挡住了去路。因此,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发生争战,已成必然。

司马颖与司马联手灭掉司马义后,司马颖自立为皇太弟。一向深藏不露的王浚居然在背地里为长沙王司马打抱不平,认为司马颖实在是胡闹,他想主持“正义”。此时王浚在塞北经营多年,底气十足。司马颖听说后,决定先下手为强。密令幽州刺史和演寻机杀死王浚,统领幽州兵马。刺杀王浚谈何容易。蓟城是王浚的老巢,他的势力在这里盘根错节,遍布耳目,而且王浚的警惕性颇高,其卫队防守严密,在城里根本无从下手。和演决定寻找帮手。他把目光向了乌桓单于。
和演要结交的乌桓,与鲜卑段部和鲜卑宇文部相比,实力较弱,而这两部都是王浚的儿女亲家,势力大得很,因此乌桓处处得看人家的脸色行事。当时的乌桓单于叫审登,和演投其所好许以重赏,说得审登心花怒放,当即答应与成都王司马颖结盟,共谋王浚。和演与审登密谋定下暗杀之计。和演特邀王浚一起去清泉水观光赏景,审登则带杀手在清泉水设伏。清泉水是蓟城南边约七里远的一条河,河水清澈见底,游鱼可见,岸边茂林郁葱,鸟语花香,景色优美。王浚、和演乃幽州地区军政首脑,对于和演的邀请,王浚自然不便推辞。
无奈天不作美,也是王浚没命不该绝,那天本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突然间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为此王浚不能如约而来,计划泡汤了。一场大雨让和演倒了大霉。审登这人迷信鬼神,心想这么晴朗的天,怎么会突然下起大雨来呢?这王浚定有老天保佑啊!别跟着和演瞎掺和了,说不定会遭到上天的惩罚。赶快坦白自首,忏悔祛祸吧。于是把和演的阴谋向王浚全盘托出。王浚不计前嫌,与审登联兵,合击和演。杀了和演之后,王浚完全掌握了幽州的军政大权。
北方的土皇帝
他当起北方地区的土皇帝,从此也跟成都王司马颖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和演被杀之后,司马颖又生一计,让惠帝下诏召王浚入京为官,这一招根本骗不过王浚。他干脆带着女婿务勿尘、苏恕延等鲜卑部首领,并约请司马腾联手讨伐司马颖。之前,在东海王带着惠帝讨伐成都王的时候,河间王的猛将右将军、冯翊太守张方,见洛阳京城空虚,便征得司马顺的同意,率兵二万趁机欲占洛阳。洛阳是长沙王故将上官已的地盘,他当然不能让张方来接管。

于是,他和另一支军队的将军苗愿联合抗击张方。双方交战,结果是上官已大败。大家知道,上官已虽然在洛阳作威作福,但还是比较讲究策略的,任何事他不出头,表面上让太子司马覃主事。司马覃并非傻瓜,深知这个上官已玩不了多久。再让他打着自己的旗号折腾下去,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因此,趁上官已大败而还时,司马带上自己的卫队,在半夜三更时突然袭击上官已和苗愿。这两个家伙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扶持的人居然会下此狠手,一时哪来得及应付两人夹着尾巴逃之天天。
这两人一走,张方就大摇大摆进了洛阳城。司马在广阳门举行仪式欢迎张方进城。在张方入城时,司马覃“迎方而拜”,把姿态放到最低,张方下车来把他扶住。张方虽然对司马覃客气,但他到底是司马颖一伙的,进洛阳城后,便马上宣布废黜太子司马和羊皇后。羊皇后和司马罩的命也是够差的,还没过几天皇家的幸福生活,就接连被废。王浚带领十多万兵马杀向邺城,此时张方便坐山观虎斗,以图渔人之利。司马颖陷入了困境。他深知双方实力悬殊,对方兵雄将勇,自己根本不是王浚的对手,便召集众臣商议对策。
说战的有,说逃的有,说守的有,就是没有一个敢说“降”字的,因说降的司马繇刚被斩首。正在众臣七嘴八舌的时候,原匈奴左贤王、五部大都督,现为司马颖手下冠军将军的匈奴人刘渊站出来说道:“殿下,今王浚与司马腾合兵十余万,来势汹汹。”“邺城的将士恐怕难以御敌,愚臣有一计,可为殿下解忧。”司马颖忙问有何妙策,刘渊答道:“我曾奉诏为匈奴五部都督,今愿前去说服五部兵马,为殿下效劳,共同对敌。”司马颖沉吟半响,摇头说:“你能保证五部兵马都能调发吗?”

“即使发遣前来,亦未必能抵御鲜卑乌桓凶悍之师。我想还是先护着皇上返回洛阳,以避锋芒,然后再传檄天下讨逆贼,不知将军以为如何?”刘渊思维缜密,从容答道:“殿下为武皇帝亲子,有功皇室,恩威远著,四海之内,何人不愿为殿下效命?况匈奴五部受抚已久,不来?王浚竖子,司马腾匹夫,怎能与殿下争雄抗衡?若殿下一旦走出邺域,这分明是告诉别人,殿下的力量虚弱,恐怕洛阳亦不能到。即使到了洛阳,洛阳已被张方控制,此人骄横无德,亦不会让权于殿下。如此,皇上反落张方之手,到那时殿下则两手空空。”
司马颖听了这番话,心里没了主意。刘渊趁热打铁,进一步说道:“如今唯一可行之策,乃殿下抚勉士众,加紧备战,静镇邺城,待我召入五部兵马,以两部打垮司马腾,以三部摧王浚。如此,斩下此二贼的头颅,指日可待,殿下有什么可虑的?”司马颖听得此言,像是吃了颗定心丸,遂封刘渊为北单于,又加参丞相军事的头衔,命他马上回去召兵。刘渊得令而去。刘渊虽名为晋朝的臣子,实际上是晋朝的人质。从264年起,他就作为担保族人不会反叛的人质,来到洛阳过着受监视的生活。
从晋武帝始,他一直被作为潜在的敌人而提防。刘渊刚走,卢志轻轻对司马颖耳语说,刘渊这小子野心很大,如今您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司马颖两手一雄,意思是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卢志是看明白了,司马颖失察。刘渊后来真的成为西晋的掘墓人。司马颖派大将王斌、石超和王粹迎战。王浚率领的鲜卑和乌桓军队战斗力极强,勇不可当,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击溃成都王的有生力量。邺城是待不住了,文武百官纷纷逃命。司马颖傻眼了。卢志劝成都王带着惠帝撤往洛阳,投河间王的悍将张方。

放眼望去天下之大,而现在只有依靠他人的力量オ能保存自己。昨日还权势熏天,做着皇帝梦,今天却忽如丧家之犬,要仰人鼻息、寄人篱下。司马颖怎么也想不通。世事难料,福祸相倚。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逃命吧!此时,司马颖身边的人已经跑得差不多了,他伤心极了:平日我风光时,你们言必效忠,如今我落魄了,你们就没了踪影,世态炎凉,人心叵测,怎么这么没有人性啊?司马颖的老母亲程太妃,哭天抹泪地不愿意离开长年生活的邺城。卢志说动了司马颖,还得去说服程太妃,但她就是不听。
结语
当时有个道士姓黄,被称为黄圣人,程太妃对他十分信任。卢志没办法,只得把黄道士叫进后宫,这道士故弄玄虚,喝干了两杯酒,把酒杯一扔,扭头就走,意思是说赶快离开此地。这下,程太妃同意了。有时,用愚昧之法治愚昧之人,还真管用。
1.《嘉一嘉说 王浚在乱世中左右逢源,为什么跟司马颖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嘉一嘉说 王浚在乱世中左右逢源,为什么跟司马颖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lishi/18411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