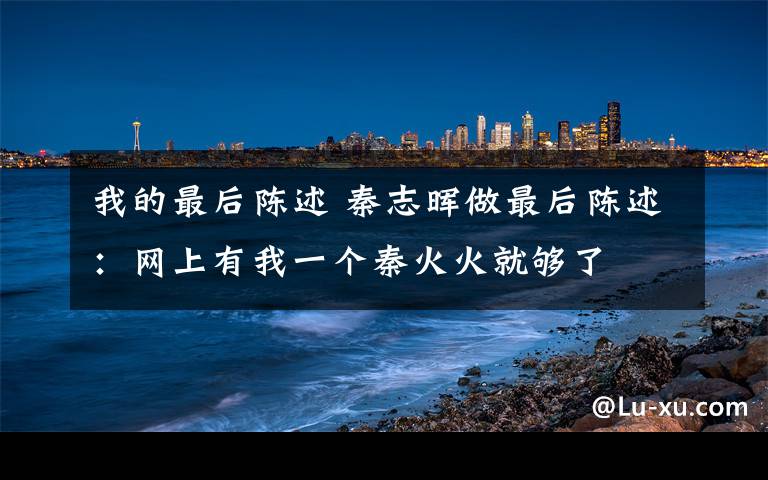增长
抗战胜利还在南京的那一年,住在大方巷仁爱东村,隶属空军户区。在四川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经过多年的苦难,我们突然回到了京都,那里到处都是六朝金粉,到处都是古迹和繁华,帝王的气息让我们的眼睛看起来很美。
一抹绿色
正文/白先勇
出自白先勇短篇小说集《台北人》
画面和配乐取自电视剧《触摸绿色》的小说改编
当时,成卫是第11旅的队长。他指挥的两个小队刚从美国训练回来,他的飞行员很受重视,工作也异常繁忙。遇到紧急差事,往往由他亲自带队。一周三四天,我连他的背影都看不见。每次出差,他总是带着郭驰。郭琦是他最喜欢的学生。郭琦在四川冠县航空学校读书时,他的丰功伟绩经常对我说:郭琦这个年轻人,以后一定会有丰功伟绩。果不其然,不出几年,郭驰就跳起来,爬进了一个留在美国的小队长。
郭驰是空军队的残余。他的父亲是成卫的同学,他很久以前就失去了飞机,他的母亲也生病了。我在航空学校的时候,总是让他放假来我们家吃团圆饭。成卫和我膝下没有孩子。看着郭驰一个人,我们经常照顾他。当时他还剃了个亮头皮,穿了一身卡其布学生装。虽然他的言谈举止处处乖巧,但他的争吵却温柔幼稚,他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后生婴儿。当他从美国回来,跑到我在南京的家,给我行了一个军礼,还叫我老师的妈妈的时候,我真的被他震惊了。郭超穿着美国范·李丁的空军装,上身披着一件带翻领和毛皮的皮夹克,腰间系得很紧,但腰带上系着一个拉夫-班太阳镜盒子。全新高耸军帽的帽檐正对着眉毛;头发也长得很长,乌黑发亮的毛脚紧贴太阳穴。就是一两年,没想到郭超竟然挑英气。
“怎么了,年轻人?这次回来,应该会有一些征兆吧?”我笑着对他说。
“没别的,师娘,不过我在国外存了几百块钱。”郭超说。
“够老婆用!”我笑了。
“是啊,师娘,我在找。”郭超也向我露出牙齿,笑道:
战后,南京成了我们小飞行员的天下。无论你走到哪里,在大街小巷,你总会遇到一个小空军,手里拿着一个穿着衣服的小姐。她在下雨,摇摆不定。爱情——所有单身飞行员都恋爱了。我总是在一个月内收到几份卫城同学的结婚请柬。然而,郭驰从美国回来多年,却一直没有他的好消息。他还带了几个德模小姐来我家吃我的豆瓣鲤鱼。我问他之后,他总是摇摇头,笑着说:
“没什么,师娘,玩玩就好。”
但是有一天,他来告诉我:这次他认清了真相。他爱上了一个在金陵中学读书的女孩,名叫朱庆。
“师娘,”他对我说,“你会喜欢她的,我想带她去看你。师娘,没想到我会对一个女孩子这么认真。”
郭超那个人的性格,我倒是觉得一二。性格极其高尚,年纪小,年纪小,有点自负。平时说起这件事,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要选择一个满意的女孩,才会结婚。他带来见我的女士都是长相不凡的,他不喜欢。我和朱庆度过了我的私人时光,他可能是一个一流的仙女,这让郭超很受诱惑。

当我遇见朱庆时,真是一个大惊喜。那天郭驰带她来看我,在我家吃了午饭。原来朱庆在十八岁或九岁时是一个相当瘦的黄花姑娘。她穿着一件半旧半直的蓝布长袍,翻领里塞着一条白色丝绸手帕,来做客了。头发不烫,抿得整齐地垂在耳后。我穿了一双脚上有绊子的黑色鞋子,一双白色短袜也很干净。我看了她一眼,发现她的身材还没挑出来,略显扁平,皮肤有些青白。但是,她的眉心有一种水秀,让人忘记了习俗。一路低着头看我一路半,绵腼腆害羞,有一种教人感到痛苦和怜悯的胆怯状态。吃完饭,我该怎么逗她开心?她回答不好。她含糊地回答。郭超在一旁忙活,时不时给她挑菜,时不时给她倒茶,叫她跟我聊天。
“她真是个笨拙的人,”郭池不耐烦地指着朱庆说。“她跟我说了一件事,可是遇到了人就哑了。师娘在这里又不是外人,又如此与众不同。”
郭拙诚的话有点暴躁,朱庆羞愧地转过脸去。
“算了,”我看着有点放肆,拦住了郭驰。朱姑娘初来,自然有些拘束。"。别戳她。吃完饭,你们两个应该去逛逛玄武湖,那里荷花盛开。”
郭驰骑着他那辆很招摇的新摩托车来了。晚饭后,他们离开时,郭驰把朱庆扶到后座,帮她系上黑色丝巾,然后跳进车里,轻快地生火,得意洋洋地向我挥手,突然把朱庆带走了。朱庆依偎在郭驰身后,高高地吹着他头上的丝绸。看着郭超对朱庆的微笑,我知道他这次真的认出来了。
有一次,成卫回来了,脸色很难看。他一进门就对我说:
“郭超那家伙越来越不讲理了!我没想到他会是这样的人。”
“怎么了?”我很惊讶。我从没听成卫说过郭驰的坏话。
“你还是问吧!你不知道他在金陵中学追一个学生吗?我想他在谈论爱情的时候已经失去理智了!经常闯进人家学校,不管人家在上课,就把那个女学生逗出来。那就更不用说了,他练机的时候飞到金陵中学空,在那里玩转子,导致所有的女同学都从教室里出来看热闹。人家校长来我们总部了。什么丑闻?一个飞行员这么轻浮,我得重罚他!”
郭超被记下,被免去组长职务。当我看到郭驰时,他向我解释说:
“师娘,我没有故意犯规,惹老师生气,是朱庆把我的心带走了。真的,世娘,我在天上飞,我的心在地上跟着她。朱庆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孩,但她在陌生人面前有点胆小,不能很好地交流。现在学校已经把她开除了,她妈从重庆拍电报逼她回去。她不肯死,和他们闹翻了。她说她跟了我一辈子,现在一个人住在小客栈里。”
“傻瓜,”我摇摇头,叹了口气。没想到聪明人在谈爱情的时候会变得这么迷茫。“你这么傻,我们结婚吧。”
“师娘,我只是想和你讨论这件事。我想请你和老师做我们的婚礼官员。”郭超满面光彩地对我说。
郭驰和朱庆结婚后也住在我们仁爱东村。郭驰有两周的婚假。他和朱庆打算去杭州度蜜月,但他们还没有去。突然爆发了国内战争。成卫的旅被调往东北。临走的前一天早上,天快亮了,郭驰进了我的厨房。我正在生火为成卫做方便米饭。郭超穿着军大衣,头发蓬乱,眼睛里全是红绫,胡子也没刮。他抓住我的手,声音嘶哑地对我说:
“师娘,这次无论如何要讨好你老人家——”
“我明白了,”我打断了他。“如果你不在这里,我会照顾你的妻子。”
“师娘——”吉果仍在唠叨,“朱庆仍不懂事。她不知道我们军队的很多规矩。你要做她自己,多教她。”
“是啊,”我笑道,“你师娘在空部队里跟着你师父十几年了。我还没看到任何东西。不知道有多少人向我学习过。朱庆不傻,你等我慢慢开导她。”
和郭驰走后,我收拾了一下屋子,去朱看她。国家配给郭驰的宿舍是小木屋平房。在他们搬进来之前,郭驰特意请人粉刷了一圈,挂了一些新窗帘和窗户,挺显眼的。当我走进他们的房子时,我看到客厅仍然像新房子一样。桌椅上摆满了红绿绿的礼物,还有一些包裹还没打开。桌子下面,周围有一个花篮。玫瑰剑兰的花蕾很鲜,连凤尾草都是绿色的。墙上那些快乐的不是收藏,而是挂在大厅中央的一个郭驰同学送给他的乌木烫金快乐匾,上面写着“白头偕老”。
朱庆在她的房间里,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她没有听到我。她扑倒在床上,脸埋在被窝里,抽泣着,哭泣着。她还穿着新婚的彩色丝绸旗袍,刚烫过的头发乱七八糟,发尾的枝条僵硬而张开。一床绣着五颜六色鸳鸯的蚕丝被被她揉出了皱纹。在她脸旁的被子上,有一大碗湿痕。听到我的脚步声,她坐起来喊了一声“师娘”,然后就哽咽了。朱庆的脸又青又黄,眼睛又肿又眯,看上去越来越瘦。我走过去抿了抿她的头发,拧了一条热毛巾递给她。朱庆接过来,捂住脸,又哭了起来。屋外有大卡车和吉普车拖着行李,铁链撞击的声音很刺耳。村里的人开始陆续上任。女人有时会尖叫,孩子有时会哭,这让他们很困惑。我等着朱庆哭,然后拍拍她的肩膀说:
“第一次,总是这样——今晚不要开合伙,来我家吃饭,做我的同伴。”
成卫和郭驰一走就不见了。听说他们调到华北去了,我就发了一封信坐飞机去华中。几个月没回家一次。在此期间,朱庆经常和我在一起。有时我教她做饭,有时我教她织毛衣,有时我教她打一些麻将牌。
“这个东西是灵丹妙药,”我笑着对她说。"如果你有什么心事,就坐在桌子上,忘掉一切。"
朱庆结婚后,她变得更加开放,但她仍然害羞和胆小。除了我,她和村子里的其他家庭都没有联系。村里那些人的生活经历我都知道。渐渐的,我挑了一些,让她熟悉一下我们村里那些人的生活。
“别误会这些人,”我对她说。“他们背后都经历过一些经历。像你背后的周太太,结过四次婚。她现在的老公和她前面的三个男人曾经是一个队的。一个死了,一个受托,就这样下来了。她的丈夫以前是好朋友,对她很体贴。你还告诉徐太太,她丈夫是她姐夫,徐的两个兄弟是第十三旅的。哥哥死了,哥哥取而代之。原生子女,既有叔伯,也有父亲,早就不清楚了。”
“但是他们还在说笑。”朱疑惑地看着我。
“我的女孩,”我笑了,“别让他们哭了?想哭就不要等到现在。”

郭驰走后,朱庆拒绝去很远的地方,每天都呆在村子里。有时我们都去孔庙听女孩子唱歌,但是朱庆拒绝和我们一起去。她说,她害怕在总部的电话里错过郭驰的消息。一天晚上,总部发来一封信,说卫城的队伍经过了上海,今天会是个好天气,可能会来南京。朱庆一大早就跳了出来,出去买了两筐蔬菜。下午我路过她家门口,看到她头上戴着蓝布和旧头巾,站在凳子上洗窗户。她个子矮,踮着脚够不到脚,但她手里抓着一块大抹布,来回摆动,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朱庆,上面的灰尘,郭威看不见。”我笑着哭了。
转头看我,红了脸,讪讪的说道:
“不知怎么的,才过了几个月,房子又旧又洗不干净。”
晚上,朱庆过来邀请我在村里放军用电话的门房等消息。总部的人答应六七点给我们打电话。朱庆梳洗完毕,穿上杏黄色的雪纺长袍,头上系着一条苹果绿色的缎带,嘴上涂着口红。它看起来非常新鲜和令人满意。起初,朱庆很开心,和我有说有笑。过了六点,她渐渐紧张起来,脸色紧张,声音沉默。她在织毛衣,但不时抬头看桌上的电话。我们左等右等,直到九点钟电话才响。朱庆突然跳了起来,怀里的毛线球滚到地上,飞快地跑向电话,但当她走到桌边时,她转向我的声音说道:
“师娘——电话来了。”
我接了电话,总部的人说卫城只在上海呆了两个小时,下午五点已经起飞去苏北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朱庆。朱庆的脸色突然变得非常难看。她静静地站了很久,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脸上的肌肉在微微抽搐。
“我们回去吧。”我对她说。
当我们走回村子时,朱庆默默地跟着我。当我来到我家门口时,我对她说:
“别难过,他们的事情很难办。”
朱庆转过身去,用袖子翻了翻白眼。他的喉咙哽住了。
“没别的了,不过今天我又等了一天空-”
我搂着她的肩膀说:
“朱庆,师娘有几句话要告诉你,不知你愿不愿意听。费将军夫人不易为人。24小时,心悬在天,即使你的眼睛从天而降,那一天的人也未必知道。它们像铁鸟,东飞西飞,你抓不到。你嫁给了我们村,朱庆。不要怪我说了实话。你要冷酷无情,才能承担未来的风险。”
朱庆含着模糊的泪水盯着我,点着头。我拉起她的下巴,笑着叹了口气:
“今晚回家早点睡。”

民国三十七年冬,我方战事处处失利,我东村几户人家在北方日益吃紧的情况下,惨遭噩耗。有的家庭天天去庙里求神拜菩萨,算命,摸骨头。我从来不相信这些神,鬼和鬼,当成卫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我写信时,我邀请我隔壁的邻居做了一桌饭,熬了一夜,下定了决心。一天晚上,当我和几个邻居打牌的时候,住在朱庆对面的徐太太跑过来把我拉了出来。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总部刚刚通知我,徐州的郭驰出事了,飞机和人都碎了。我到达了朱庆,那里已经黑了,挤满了人。朱庆扑倒在一把扶手椅上,一个女人抓住她的左右胳膊,紧紧地抱着她。她头上绑着一条白色的毛巾,毛巾是红色的,会说话,是一大块血。我一进去,里面的人就告诉我:朱庆一得到消息,就抱着郭棣的军装往村外跑,边跑边哭,说要找郭棣。有人拦住她,她又踢又打。她一跑出村子,就撞上了一根铁电线杆,碰到了额头上的一个大洞。她只是背了回来,没有声音。
我走向朱庆,从别人那里拿了一碗姜汤,用一把铜勺撬开朱庆的嘴,给她倒了几口。她的脸就像一个切开的鱼肚,一白一红,鲜血淋漓。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但她的眼睛却心不在焉。她没有哭,但那两片蓝色的嘴唇总是开合着,喉咙里不停地发出尖细的声音,就像一只瞎老鼠被踩着发出尖叫声。我灌完那碗姜汤后,她渐渐闭上眼睛,有所觉察。
朱庆长期卧病在床。我把她搬到了我家。没日没夜的抱着她,有时候打牌的时候把她放在我面前。我怕她错过眼睛会自杀。朱庆整天睡在床上。不说话,不吃饭。每天,我强迫她喝一点汤。几个星期后,朱庆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的脸死了,眼睛凹陷成两个大洞。一天喂完她,我坐在她的床边对她说:
“朱庆,如果你说你是为了郭驰,你就不该这样作践自己。就是郭为在地下,知道了也不放心。”
朱庆听了我的话,突然颤抖着挣扎着坐起来,冲着我点了两个头,冷笑道:
“他知道什么?他崩溃了。他能感觉到哪里?他太好了,他走了——我也死了,但我仍然觉得。”
朱庆说,他的脸扭曲得像哭和笑,非常难看。
在朱庆呆了几个月后,我几乎筋疲力尽了。幸好她妈妈是重庆人。她老子见她一句话也没说,她妈却用力啐了一口:
“该啊!是时候了!我希望她不要嫁给空军队。她要是不听话,就这样收场!”
说着,朱庆蓬头垢面地从床上拎下来,用滑板车连铺盖一起拖走了。朱离开几天后,我们也开始出逃,离开了南京。

向下
这些年来,我一直住在长春路。我们家的小区正好叫日奈东村,不过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没关系。里面的人从四面八方搬来,我以前认识的都走了。好在这么多年来日子过得很平静,也很好摆脱,但是我军空的娱乐活动没有南京那么频繁,还有今天的评剧。明天跳舞,节目新鲜的时候,我经常去那些聚会玩。
某年元旦,空军校新生社团举办了一次文娱晚会。有人说连这一次都是历史上最大的。有人送了我两张票,所以我带着隔壁李佳念中学的女儿去了。当我们到达新生社时,聚会已经开始很久了。有些人挤在一起抢彩票,但音乐和舞蹈开始在大一大厅。整个新生俱乐部都挤得不能动。大多数男女都是年轻人。大家笑啊笑啊,兴奋的不得了。大厅里满是红、绿、绿三色的气球,几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小空部队拿着烟头,把气球烧得砰砰响,于是一些妇女试图尖叫。夹在那些杂七杂八,吵吵嚷嚷的男青年中间,我头都晕了,终于和李的女儿挤进了大一礼堂。我们靠在大厅的柱子上,看着那些人跳舞。那天晚上,他们在军队里组建了一支20人的大乐队。乐队里也有不少歌手,一个个上来,穿衣服穿浪漫歌曲,唱几首流行歌曲,却下到舞池和熟人跳舞。正当乐队里的那些人都在拼命地敲打的时候,一个穿得特别妖艳的女人走了过来。当她站起来的时候,下面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她的风头似乎与众不同。那个女人站在舞台上,毫无羞耻地微笑着,慢慢地调整麦克风,回到乐队,唱了起来。
“秦予言,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李的女儿问,她不像我一样擅长流行歌曲。我的收音机总是早上打开,睡觉时关掉。
“东山淡淡的绿色。”我回答。
这首歌我很熟悉,经常在收音机上拿到充满白光的唱片,但那个女人很难唱出白光的慵懒懒散。她一只手拿起话筒,另一只手却不停地拨弄着头发,头发就像一个大鸟巢。她翘着下巴,一字不差地唱着:
东山,淡淡的绿色。
西山,淡淡的绿色。
郎有心来找姐姐,
郎,我们可以好好结婚——
她的身体微微向后倾斜,晃了晃,晃了过去,然后突然一咕噜,像是从心里迸出来似的唱道:
嘿,嘿,嘿,
郎,我们可以好好结婚——
当她唱歌到门口时,她放下麦克风,走过去,从一个音乐家的手里拿了一对像锤子一样的门环,发出吱吱的敲门声,同时踩在舞台上的伦巴舞步上,上下颠倒,扭曲得很厉害。她穿着一件带有透明紫色薄纱和金块的旗袍。一双高跟鞋有三英寸高。当她扭动时,全身的金锁闪闪发光。一首歌唱完,欢呼声听了半个小时,她就随意再唱了一首,才下台。立刻,一群小空部队迎接她,把她带走了。我还想站着听几首歌,但李的女儿吵着要去另一个大厅抽奖。就在我们把人挤出舞池的时候,突然有人在我身后抓住我的胳膊,叫了一声:
“师娘!”
我回头一看,看到那个叫我的人,就是刚才在台上唱《东山一把草》的那个女人。来到台北后,再也没有人叫我“石娘”。大家都叫我秦夫人。很久没听过这个名字了。突然,很奇怪。
“师娘,我是朱庆。”那女人笑吟吟的看着我说道。
我上下打量了她半天,还没来得及回话,一群小空部队跑过来,嚷嚷着要背她跳舞。她把它们打开,放在我耳边说:
“你给我地址,石娘。过两天我来接你去我家打牌,现在我的牌已经改进了。”
她转过身,笑吟吟的对我耳语道:
“师娘,我早就认你老人家了。”
从前,我看京剧的时候,伍子胥在昭关过了一夜,头发变白了。那时候我只在歌剧里这么做,人往哪里看都变得那么厉害。那天晚上回家洗完脸,看着镜子突然意识到自己洒了一层霜。难怪连朱庆都认不出我了。从前我逃亡的时候只想逃命,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天已经黑了。当我们撤退到海南岛时,成卫病了。可笑的是他一生都在天上飞。他坐在船上突然死去。他感染了痢疾,船上有很多病人,所以没有足够的药。我看着他患了痢疾,脸色变黑。他一死,船上的水手就把他包在一个麻包里,和其他几个病人一起扔到海里。只听砰的一声,人都走了。自从我和成卫结婚的那天起,我就已经想好了将来如何收集他的骨头。我知道像成卫和其他人一样的人无法在我面前生存。没想到最后他的骨头被没收了。来到台湾省,每天忙着生活,大陆的事情也渐渐淡忘。老实说,如果我没有在新生社再见到朱庆,我就不会想到她了。

两天后,朱庆派了一辆出租车带着一张纸条来接我去吃晚饭。朱庆原来住在新沂路4号,另一个空军属区。那天晚上,她还有其他的客人,三个空军佬,周末从桃园基地来台北度假。他们还沿着朱庆向我师娘尖叫。朱庆指着一个肥胖的面包状侏儒对我说:
“这是刘骚包,石娘。你回头看他打牌,就知道那块疯骨头的样子了。”
那姓刘的便凑到朱庆跟前嬉皮笑脸的叫道:
“姐,难道我今天又打你了?我还没说好话呢。”
朱庆只是吃着笑着,没有理会他。他指着另一个瘦瘦的黑人说道:
“他是儿科医院的,师娘就叫他王儿科。他跟我们打了这么久的麻将,没打出像样的牌。他是这里有名的鸡王。”
那个叫王的歪着嘴笑了笑,说道:
“关于大姐的话什么都不要说。我回到桌旁。我和老刘抱起大姐姐,看着大姐姐又开始赌钱。”
朱庆抬起脸,冷笑道:
“别说你是一对宝,换两个更厉害的。我也有同样的能力,教你丢了裤子就离开这里。”
朱庆肩上背着一个布袋和一件红色毛衣。袖子在摆动,但两臂露在外面。她的腰变得异常圆润,肤色细致多了,脸型很时尚,天生一双水汪汪的眼睛。这时环顾四周,风情万种。然后朱庆给我介绍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叫小顾。小顾比前两个多才多艺,身材魁梧,浓眉高鼻,人又粗,没有那两个圆滑。朱庆迎接客人的时候,小顾一路跟着她,给她搬桌椅,听她的指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很快,我们进入了餐桌,朱庆端上了第一道菜。那是一锅蒸好的整鸡,一个大大的琥珀瓷碗里盛着一只热气腾腾的肥母鸡。一放下碗,姓刘的跳起来,走到小顾身后,把他推得直叫道:
“小顾,多吃点,你大姐会炖鸡给你补。”
又笑与姓王,怪叫。小顾也跟着笑了起来,但是脸上很尴尬。抓起茶几上的一顶船形军帽,往刘的口袋里砸去。刘抱着头,绕着桌子疾走。姓王的拿起勺子舀了一勺鸡汤到嘴里,然后舔了舔嘴唇,叹了口气:
“小顾来了,最后不一样了,大姐姐的鸡汤是蜂蜜炖的。”
丢了帽子,笑弯了腰,指着刘、王,咬牙切齿,恨恨道:
“那两把小刀子把大姐的鸡汤砸了,居然吃了大姐的豆腐!”
“大姐的豆腐自然留给我们吃。”刘和王异口同声地笑了。
“今天要不是娘师太在,我就说点好听的。”朱庆走到我面前,笑着用一只手搭着我的肩膀说:“师娘,别把你老人家当回事。我本来叫这群小兄弟去伺候你老人家八圈。我不知道有几个孩子平日被我惯坏了,嘴里也没混上混下的。”
朱庆永戳了一下姓刘的额头,说道:
“最讨厌的是你!”
他走进厨房。小顾跟着进去帮朱青端上饭菜。那顿饭我们吃了多久,那些姓刘的和姓王的跟谈了多久。

从那以后,每隔一两周,朱庆总是来接我,然后去她家。然而,当我看到她时,她一句关于过去的话也没说。见面的时候总是忙着打麻将。朱庆告诉我,小顾除了这些照片什么也不喜欢。他一从桃园来台北度假,就到处为他搭顺风车,甚至经常有一品香的老板娘在她胡同口的杂货店拉她的脚。当小顾和我们打牌时,朱庆没有参加比赛。她总是拿了一把椅子,挨着小顾坐下,点了张子给小顾。她把胳膊肘放在小顾的肩膀上,双脚交叉,嘴里却一直哼着歌。什么是《叹十》什么是《夜深人静》,唱着各种花样。有时候,当我们长时间打牌时,朱庆会唱很长时间的歌。
"朱庆,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好的?"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我记得以前她说话的时候,怕提高嗓门。
“我不是刚到台湾省,什么都找不到。在空军娱队学了这么多年。”朱答道。
“秦太太,你还不知道,”一品香太太笑着说。"我们这里都叫朱小姐‘赛白光’。"
“老板娘又让我馋了,”朱庆说。“快点用心打牌。等你回头输了,就轮到你熬通宵了。”
我认识朱庆才三四个月。有一天在新沂路东门市场买了卤菜,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处理货物的香老板娘。她一看到我,就抓住我的胳膊哭了:
“秦的女人,你听到了吗?上周六朱老师的小朋友出事了!他们说在桃园机场,起飞几分钟就摔了。”
“不知道。”我说。
一品香的老板娘叫了一辆三轮车和我一起去朱看她。一路上,老板娘一品香说她已经在路上半天了:
“这个怎么说?一个好人突然消失了。那点小心思,恐怕已经在朱小姐家进进出出两年多了。一开始朱老师说小顾是她弟弟,但是两个人眉来眼去,长得不像。我们巷子里的人都说朱老师爱吃‘鸡’,喜欢部队里的空男生。谁能怪她?一个有着小顾这样性格的男人,对朱老师真的是百依百顺。在哪里可以找到?我觉得对不起朱老师!”

到了朱的时候,我们按了半天门铃,没有人来开门。不一会儿,我们听到朱庆透过窗户对我们喊:
“师娘,夫人,进来,门没闩上。”
我们推开门走进她的客厅,却发现朱正坐在窗台上,穿着粉红色的丝绸睡衣,舀起裤腿的脚,在脚趾甲上画着,一张发纸也没脱。她见我们抬头大笑。
“我早就看见你们两个了,我的指甲油没干,我没法穿鞋出去开门,我叫你等着——你来得正是时候。中午炖了一大锅糖醋蹄子,担心没人来吃。回去给余奶奶退织针,我们四个就凑了一桌麻将。”
正在这时,余奶奶进来了。连忙从窗台上跳下来,拿过指甲油,对老板娘一品香说:
“老板娘,麻烦你给我摆摆桌子,我去厨房上菜。今天女士们都快了,饭后至少有二十四圈要搓。”
朱庆走进厨房,我跟着他去帮忙。朱庆倒出锅里的糖醋蹄子,一味地在架子上炒豆腐。我站在她旁边,端着一个盘子等着给她上菜。
“小顾出事了,石娘该不该听?”朱庆做饭,也没回头,便对我说。
“一品香老板娘刚才告诉我的。”我说。
“小顾没有亲戚。我和他的几个同学算出了他的遭遇。昨天下午,我把他的骨灰运到碧潭公墓安葬了。”
我站在朱庆身后,看着她,没有说话。朱庆没有在脸上搽粉,但她看起来仍然出奇的年轻和酷,她看起来不像一个30多岁的女人。她两颊丰腴,皮肤紧绷,岁月似乎没有在脸上留下痕迹。我觉得虽然我比朱庆大,但我找不到任何东西来启发她。朱摔了一跤,把豆腐翻了两遍,然后拿了一瓢送到我嘴里。他笑着说:
“师娘尝我的‘麻婆豆婆’,可是好吃吗?”
我们吃完后,朱庆放下麻将桌,拿出她用来招待客人的苏州竹牌。我们一坐下,第一道菜后,朱庆就掉了一双大三元。
“朱小姐,”一品香太太叫道,“你真幸运,该买一张‘爱国彩票’了!”
“试试看,”朱庆笑着说。“今天,我的风头又来了。”
八圈以上,就成了三合一的局面,朱庆面前的筹码堆积在鼻尖上。朱庆不停地笑着,嘴里哼着她经常喜欢唱的歌曲《东山再起》。过了一会儿,她哼了两句:
嘿,嘿,嘿,
郎,现在摘花还早——
-结束-

台北人
白先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电话号码:I247.7/160(4)=2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部复杂的作品。这本书由十四篇短篇小说组成,每篇都有不同的写作技巧和不同的篇幅,每篇都可以独立存在,堪称一流短篇小说。但如果把这十四篇文章聚合在一起,串联起来,效果会大幅度增加:不仅小说的广度会变得更宽,让我们看到社会上的“众生”,更重要的是,因为其中一个主题是重复的,相互补充的,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作品的意义,窥见作者隐藏在作品中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欧阳子的白先勇小说世界

过去的文章
也许你仍然对这些活动感兴趣...
1.《一把青小说 白先勇:一把青 │ 周末选读》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一把青小说 白先勇:一把青 │ 周末选读》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shehui/15114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