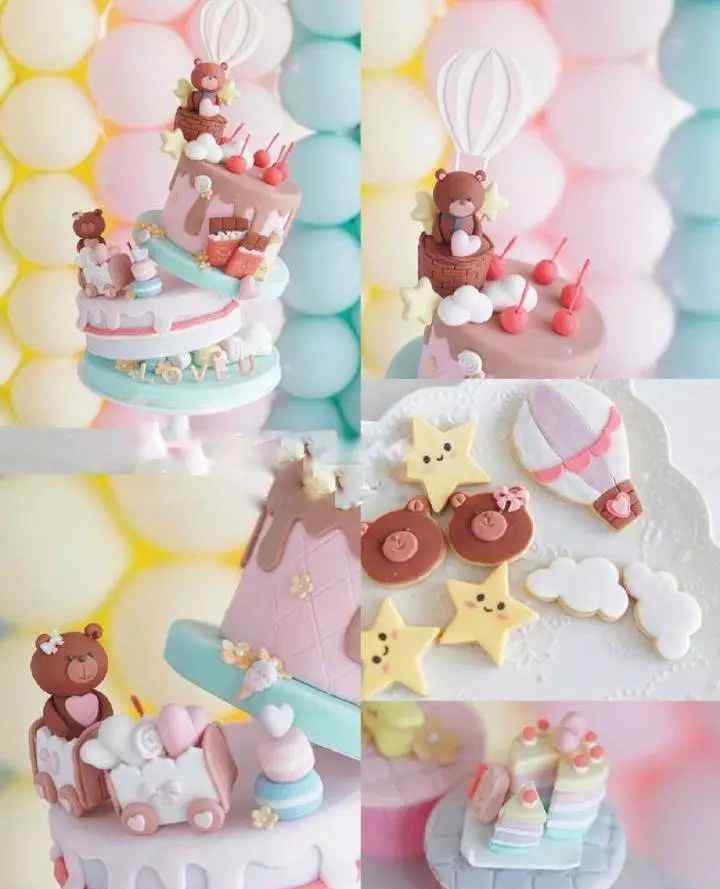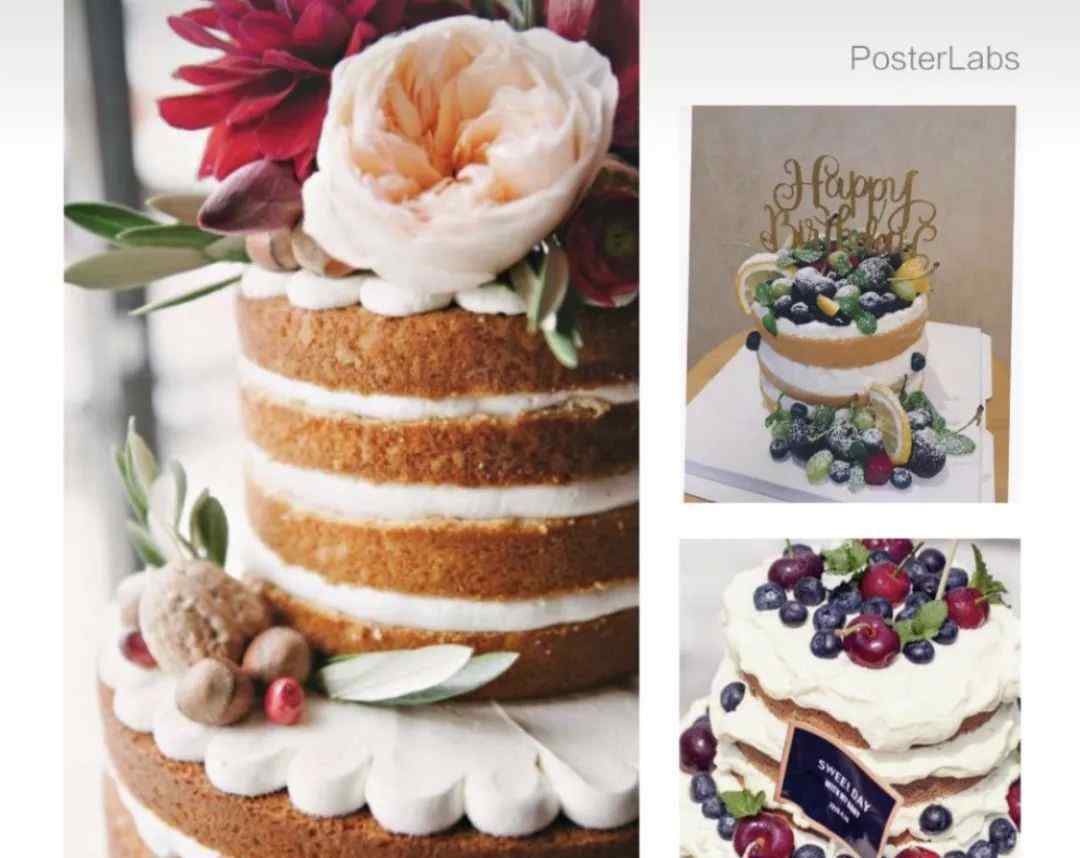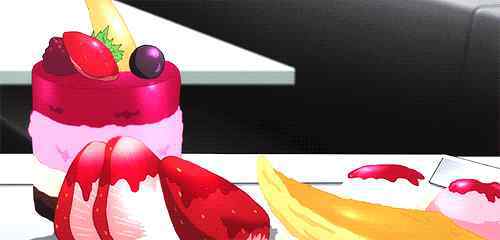∞《新京报》2016年3月5日
书评周刊文学
六个半部分
2007年,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就像一头困兽。他身高1.9米,金发碧眼,长相英俊,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人),住在瑞典的海边小镇马尔默。他三十九岁了。确切地说,他是一位挪威作家兼小说家。他出版了两部广受好评的小说:《走出世界》(挪威文学评论奖)和《万物有时》(北欧文学奖)。他正在写第三本书——这是他困境的根源:他写不出来。他写了六年(从妻子怀第一个孩子到第三个孩子出生)。他知道自己想写什么(父亲中年离家,父亲去世,少年时第一次喝醉)。他对自己的才华和才华充满信心,但是——他就是写不出来。一片空是白色的。写作瓶颈。他卡住了。

马丁·林格曼
阻碍他进步的清单包括:尿布、睡眠不足、洗碗、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抽烟、喝酒、老婆、孩子、幼儿园、邻居、朋友、嫉妒、虚荣、焦虑……一切。或者说,生命本身。生活本身阻止他继续写作——确切地说,阻止他继续化妆。他发现自己似乎已经失去了编故事的能力。
因为如果“虚构”是一道光,那么现实生活就像一个黑洞。一切都被吸进去了,什么都逃不过。与坚不可摧的现实相比,小说是可怜的,可笑的,甚至可耻的。但是小说——即使是没有故事的小说——难道不是小说家最基本的责任吗?更不幸的是(或者应该说,幸运的是)我们这位来自Knaus的高先生,无论是作为儿子、父亲、丈夫还是小说家,都有着一种高度的、近乎自我毁灭的责任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那么痛苦,焦虑,迷茫,执着,绝望,最后开悟。
当我坐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才知道,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能隐约分辨出我的脸在对着我的窗玻璃上的影像。除了一只眼睛,它闪烁不定,紧接着它下面的部分微弱地反射出一点光,整个左脸都在阴影里。两道深深的皱纹划破了我的额头,每一个脸颊上都有一道深深的皱纹。这些皱纹似乎充满了黑暗。再加上严肃的目光和微微下垂的嘴角,很难不觉得这是一张阴沉的脸。
什么刻了我的脸?
今天是2月27日。时间是晚上11:43。我,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出生于1968年,当我写这些话的时候,我39岁。我有三个孩子——维加、海蒂和约翰——这是我的第二次婚姻,我的妻子是琳达·博斯默·克纳斯·高。他们四个人睡在我周围的房间里。这是马尔默的一套公寓,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半。
2007年2月27日,晚上11:43。在高克纳斯的第三部小说《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这是一个类似于BIGBANG的奇点时间,共六卷(近四百万字)。一切都开始了(其实我们会在第二卷看到,虽然这一段不是真正小说的开头,但确实是他为这部巨作写的第一段)。一切都以此轴向外辐射、扩散、旋转。

我的奋斗,2018
1.父亲的葬礼侯麟翻译
2.恋爱中的男人被慷慨地翻译
就是在这一刻,当他凝视着窗外自己幽灵般的脸,当他写下“我,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时候,他顿悟了:既然生活让我无法弥补,我愿意写下这让我无法弥补的生活。
自从尿布,睡眠不足,洗碗,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抽烟,喝酒,老婆,孩子,幼儿园,邻居,朋友,嫉妒,虚荣,焦虑...一切都让我无法写作,我会写关于尿布、睡眠不足、洗碗、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抽烟、喝酒、妻子。
于是就变成了超级盯着自己。正如这个顿悟场景所暗示的,他久久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的脸:“是什么刻了我的脸?”这等于问:是什么刻了我的人生(让我无法弥补人生)?这六卷3600页是他的答案:死亡(第一卷:父亲的葬礼)、爱情(第二卷:恋爱中的男人)、童年(第三卷:男孩的岛)、工作(第四卷:在黑暗中跳舞)、梦想(第五卷:雨会落下)、思考(第六卷:结束)

贝奥武夫·希恩的《克努斯》
我们很容易想到费里尼的著名电影《八岁半》。两者的主角都是深陷中年困境的艺术家(一个是导演,一个是小说家),他们的危机都来自于自己的创作(《八岁半》的导演吉多——他可以被认为是费里尼的翻版——正准备拍一部科幻大片,而高克纳斯则口口声声说——听起来像咒语——他想写一部莫比·迪克。圭多在片中的名言是:“我无话可说...但我还是想说出来”,他接着说,“我想把所有东西都拍进去”。这些话也适用于克努斯高:我没有故事可写...但是我还是想写——我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无”和“一切”之间有逻辑关系吗?
D.A .米勒曾在他的精彩著作《八岁半》中写道:“如果你不能拍出一切,那么没有什么是真正完美的。但如果你不能像圭多一样什么都不选,那么一切都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似乎已经从消极的混乱变成了积极的混乱,从缺乏思想变成了取之不尽的个人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