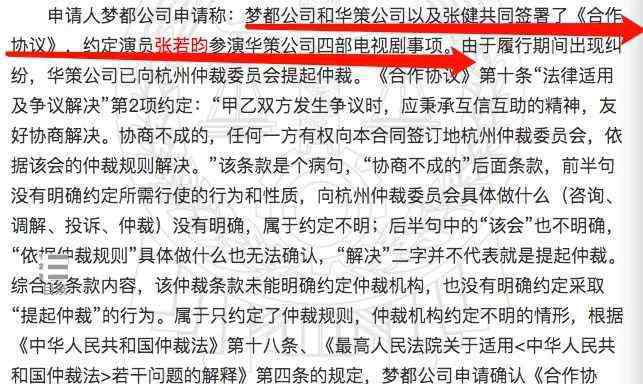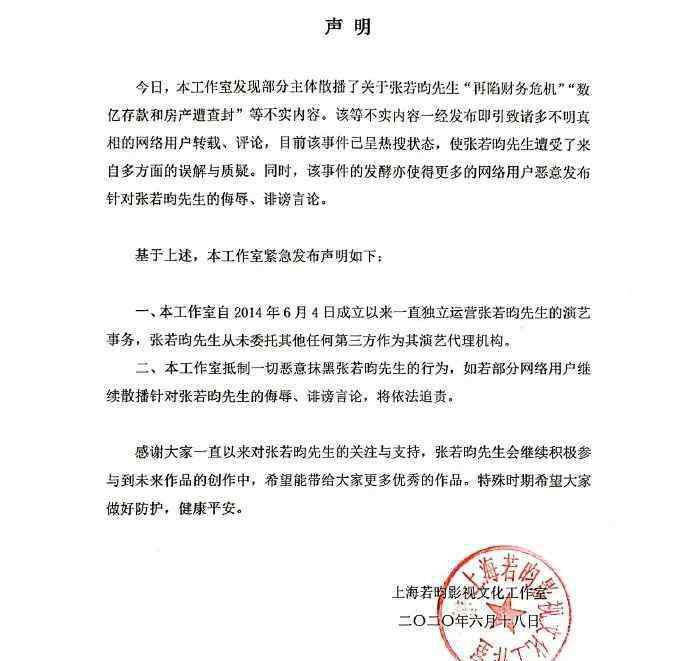□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著名作家刘亮程端坐在村中木垒书院,通过网络直播给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创作大会讲课。镜头里的刘亮程朴实、安然,如同原野上一株庄稼,说起话来却诗情漫溢。他的身前放着书,身后也是一排长长的书架,书架上方挂一块牌匾,上书“三山两盆”4个苍茫恣肆的大字——这四个字说的乃是新疆的地形:“三山”是指北部的阿尔泰山,中部的天山和南部的昆仑山;“两盆”则是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和北部的准噶尔盆地。
刘亮程已经在菜籽沟村生活了7年。“在这个村子里,房子被风吹旧,太阳将人晒老,所有树木都按自然的意志生叶展枝。”而梦,“梦把天空顶高,让土地更加辽阔。”对于以《一个人的村庄》而名满天下,并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的刘亮程而言,人和万物一样,只有向时间敞开自己的心灵,才能找到精神的永恒故乡。
为所有人去迎接朝阳,送走落日
刘亮程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沙湾县的一个小村庄里,长大后种过地、放过羊,当过十几年乡农机管理员。那时候,乡农机管理员刘亮程同时也是诗人刘亮程,二十几岁,骑着自行车、摩托车,游走乡村,工作轻松,心高气傲,因为“太喜欢诗歌了”,所以“只写诗”,“觉得诗真是太奇妙了,每写一行诗都像是在往上爬升一步,一行一行诗写下来,仿佛是在为自己造一架天梯”。
30岁,刘亮程辞去了乡农机管理员的工作,孤身一人到乌鲁木齐打工。写诗生涯瞬间中断,“再也写不出一首诗”。而《一个人的村庄》的写作,却也正是在诗歌创作中断之时萌发。在乌鲁木齐打工时,有一天黄昏,刘亮程行走在庞大的城市,看到硕大的落日,越过城市的楼房,慢慢地向西边落去,心中突然感慨万千,“我的家乡正是在乌鲁木齐的西边,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我家乡的每一样事物都将被这辉煌的落日照亮,那一张张村人的脸庞,那一声声母亲对孩子的呼唤,那一切的一切都将被照亮。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我的村庄,看到了我从小在那儿长大又被我扔在天边的村庄”。
只有远走他乡,才能在不经意间回头看见家乡。在乌鲁木齐街头那个“看见家乡”的瞬间,让刘亮程决定提笔写下自己的村庄。
刘亮程的家乡,和几乎所有的农村一样,一年四季没有多少故事,“三年一丰收,五年一灾荒“,那些坑坑洼洼的土路,那些成群的牛羊,和那些贫穷的人,刘亮程没有像流行的散文一样写春种秋收,写村落文化,他返视内心,想看看一个远离家乡的人,在回望那个“被自己扔掉的村庄时,真正想写的究竟是什么”。彼时刘亮程刚过而立之年,早已不是对生活浑然不觉的少年,他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一颗长大的心灵,已经可以理解曾经的村庄和生活,已经“可以带着苦涩的微笑,可以忍住眼泪去写自己的村庄了”。
“我”于是成了《一个人的村庄》的主角,“我”有时候是幼年,有时候又是青年、是老年,“我”白天在村里游手好闲,夜深人静到一户户人家的窗口去听人家说梦话。那是一个沙地边的村庄,刮大风的时候,黄沙漫天,当风刮过村庄,“我”会觉得这个村庄如此小、如此封闭,又如此宽广、如此阔大,“风刮过整个世界,当它来到村庄时,村庄就是世界的中心”。“我”还会一个人站在村口,以孤独的方式迎接日出、目送落日,“此时此刻,天地间一件伟大的事情就要发生,总要有一个人为所有人去迎接太阳、目送落日”。
至今刘亮程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村庄》最成功的地方,是创造了“我”这个“闲人”,“他放下忙碌之事,只关心天地大事,当一个农民抬起头来时,他的疾苦就不在脚下而在天上。村庄的时间于是被看见。这目光把时间留给村庄的痕迹变重了,把村庄经历的那些经济运动、政治运动变轻了。一个时间里的村庄,被一颗孩子的心,一颗永不衰老的心,从尘埃中找了出来”。
每个生命都承先启后,连天接地
《一个人的村庄》写完,刘亮程觉得该写写自己最想写而又一直没写的父亲了。父亲37岁去世,那时刘亮程只有8岁,当自己37岁一过,“就觉得一天天都比父亲在世时的年龄更大了。生命突然有了一种即将老去的空茫感,就很羡慕那些有老父亲的家庭:一个老父亲可以让儿子知道50岁、60岁、70岁的男人会活成什么样,可以让儿子在父亲的葬礼中知道生命究竟是什么”。
刘亮程的父亲是一个旧式中国文人,“琴棋书画医都会”,失去父亲让一家人的生活变得更为艰难、心酸,刘亮程也常常觉得孤独、忧伤,但从未绝望。然而,多年以后,当他想提笔写写父亲的时候,连父亲的样子都想不起来了,“一个已经去世又被遗忘的父亲,真正想要落笔,笔下又一片空茫”。
直到有一年跟随母亲回了一趟甘肃老家,刘亮程才找到了写父亲的感觉。父亲是逃荒到的新疆,多年未曾回过甘肃老家,所以刘亮程一直认为新疆是自己的故乡,只隐约听过父母也有自己的故乡,“那一次回甘肃,我的堂叔带着我上祖坟,老家的祖坟都迁到叔叔家的田地里,那时候暖暖的阳光从坟地落向村庄,与炊烟离得那么近,那时候我一点也不恐惧,一点也不绝望,觉得地下的先人和地上的后人是一体的。我就想:用什么方式才能听到地下的声音呢?”
从祖坟回来,堂叔又带刘亮程去敬堂屋里祖先的灵位,给刘亮程看他父亲早年用毛笔小楷写在一整块布上的刘氏家谱,“一代一代的祖先就像扎向大地深处的大树之根,地面上的参天大树就是还活在世上的后人,在生命的长河中,祖先没有离去,他们铸就了我们的故乡和家园。”刘亮程说,“那一刻我明白了,在漫长的时间链条上,生命是无限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承先启后、连天接地。每个人的此生都连接着前世和来世。土地就是故乡,祖先就是故乡。我要用笔写出精神和宗教层面的故乡,写出生命和时间的面孔。”写作就是一场时间中的等待
从一开始写作时,刘亮程就从内心排斥文体的概念,“文学就是文学,散文也可以是小说”。不过当真正写起小说来,他还是退让了,决定还是应该遵循一些小说的基本规律。但《虚土》和《凿空》两部小说,依然有着散文的强大引力,故事讲的也是村庄的生存之状、人事与自然。比较起来,刘亮程更喜欢《虚土》,“一个不到5岁的孩子突然睁开眼睛看外面的世界,写作时有一种作为一个诗人天马行空的愉悦”。到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捎话》,刘亮程从散文中彻底走出,进入了纯粹的虚构。其所构筑的世界已非读者熟悉的他的那个世界,故事背景发生在了古代,两个国家,毗沙和黑勒,因信仰不同而开启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两国间书信断绝,无法沟通,捎话人应运而生。这是“语言之难“,也是“生死之思”。
刘亮程说,《捎话》中的问题其实自己关注了很多年,“故事看起来很神秘,其实写的都是我的感觉”。对于刘亮程而言,《捎话》写得异常艰难,整整写了7年,“如果写得快一点,也许4年就够了。但我不想太赶,写作就是一场时间中的等待。书是时光之子,我们应该等待一本书在时光中被完成”。
如今生活在菜籽沟,坐在由一个废弃学校改建的木垒书院中,刘亮程觉得自己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了时光,并且“早早看见了自己的老年”,“一个人的童年和老年都是他的家,唯独中间是无尽的漂泊和流浪”。在菜籽沟,木门被风吹响,声音像老人沙哑的嗓音,在菜籽沟,早晨看着阳光照过来,一寸一寸移过土墙、树叶、天空,黄昏时再从另一个方向移过来。在这里,“万物老于一处”,而这,正是一个作家安顿自己老年岁月的最好场所,“在时光中,一棵现实中的树会在心里长出来,成为一棵精神之树”。
8月1日,刘亮程发了一条朋友圈:“待疫情过去,我们哪都不去,依旧过封闭在菜籽沟木垒书院的日子。”一段小视频是他亲自拍摄的菜籽沟的原野,视频下还有一段题为《菜籽沟早晨》的文字:“我要在一山沟的鸡鸣声里,再睡一觉。布谷鸟、雀子、邻家往小河对岸的大声喊叫,都吵不醒;满坡喳喳疯长的花豆草、野油菜、麦苗和葵花吵不醒。山梁呼噜噜长个子,在我傍着她的均匀鼾声里,有一匹马和小半群绵羊,枕边走过,行到半坡拐弯处,一只羊突然回头,对着我半开的窗户,咩咩咩地叫,仿佛叫她前年走失的羔子。我就在那时睁开眼睛。看见在我被一只羊叫醒的另一世里,我跟着她翻过了山坡。”孙婷婷 绘
1.《刘亮程 刘亮程:向时间敞开心灵》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刘亮程 刘亮程:向时间敞开心灵》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tiyu/4291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