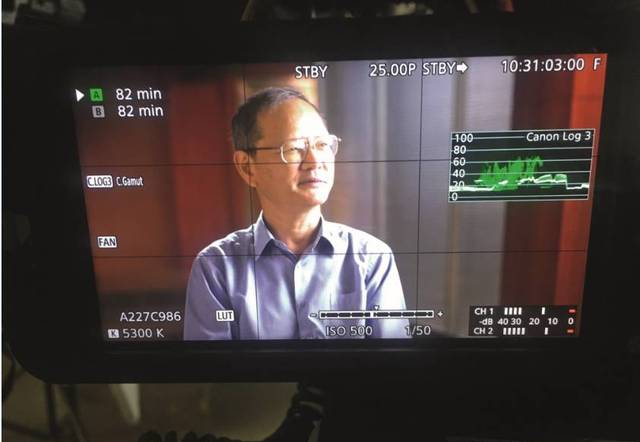
回忆上海证券交易所往事,他说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当他在浦江饭店敲响那一声中国股市开市之锣时,或许从未想到,从一家老饭店大厅启程的中国资本市场,短短27年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他首推电子交易、无纸化交易、创办上海证券报、力主市场扩容、推出国债期货,画出一条跌宕起伏的股市进化曲线图。
他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1990年冬天,35岁的他被摆到了中国资本市场坐标系的原点;2017年秋天,笔者来到上海滩,黄浦江畔,风轻云淡,与他面对面,还原中国证券交易所诞生始末。
由尉文渊来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偶然中的必然。尉文渊出身于军人家庭,15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去新疆伊犁当兵,住地窝子,在冰天雪地中经受了艰苦的锻炼。恢复高考后,他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他婉拒了母校的挽留,到正在组建中的国家审计署工作,不久便当上副处长,32岁时,又被提拔为审计署人教司处长。
虽然仕途顺利,但他老想做一点竞争性、挑战性更强的工作。他的老师、原上海财大副院长、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对他十分赏识,于是,在1989年的11月他被调到人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当了正处级的副处长。
1990年初,中国政府宣布将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6月,在海外访问的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向全世界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年内开业。这一只有半年的时间表,让筹备交易所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措手不及。这时候,刚调来不久的尉文渊,主动请缨筹办交易所。就这样,国家大局与个人处境微妙地联结在一起,不经意间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当时只知道交易所是搞证券交易的,没想过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影响。‘少不更事’,一切都是零,大家都是股盲。”尉文渊笑着回忆。
“可以说浦东的开放是中国股市的催产师!”那时,资本市场的初级形态已经形成,在北京,王波明、高西庆、李青原等创办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积极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在深圳,已有10个股票交易柜台,并且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已经开始受理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转让业务。
“浦东大开发如何解决资金筹措问题,需要资本市场,需要交易所。而民间和市场的力量,恰好和浦东金融中心重大的战略结合起来,慢慢上升为政府的战略决策,中国金融发展史新的一页就此翻开。”尉文渊总结说。

中国股市第一声锣
如何筹建证券交易所?是个难题!解放前的上海曾经是远东的金融中心,为了学习和了解什么是证券交易所,尉文渊找来几位曾参与旧上海证券市场的老人座谈。但由于在战乱中,旧上海的证券市场也没有很好地运作,且这些老人只是一般参与者或工作人员,虽然热情很高,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调研了一圈,他仍一头雾水。
“意识形态在当时仍是绊脚石。使我在筹备交易所时特别注意,避免政治风险,做了很多设计。例如名称,开始有两个,一个是上海股票交易所,一个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选择后者,就是为了淡化股票交易的色彩,避开《子夜》中描述资本家的谈股色变。早期的宣传口径,都是以国债交易为主。交易所在设立的时候,名称、职能,都在回避敏感区域。”
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从哪儿来?今天的股民已很难想像“老八股”是一帮矮子里拔将军的公司。譬如,真空电子是上海郊区第一家发行股票的企业;而上海豫园前身是老城隍庙商场,是一家集体企业;爱使电子小到只有40万股。初上市时,发行规模小得可怜,8只股票的发行总量按面值计算仅2.6亿元,流通股总额不足7000万元。
“外地的浙江凤凰是第八家,流通股只有510万股,但意义重大,那个时候,我就想打破上海为主的地域,交易所面向全国。包括一开始就面向外地证券公司,外地信托公司。而无纸化交易更是一次关键的选择。”尉文渊自豪地说。
有了股票,该如何交易呢?尉文渊从一些资料中了解到,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交易所主要是口头竞价交易。中国人熟悉的《子夜》里描述的就是口头竞价,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听说像新加坡、台湾等新兴市场正在推行计算机电子撮合交易。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方式的选择,很多人都赞成口头竞价模式,因为当时就那么几只股票,交易会很冷清,口头竞价能够满足需要,还能造点气氛。但尉文渊觉得,现在高科技发展那么快,难道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交易所,还要重复那种古老的方法吗?
“我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挤出100万,决定搞计算机交易系统。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口头竞价交易方式的准备,还请在美国华尔街工作过的‘海归’来帮助设计口头竞价的方式。搞了一段时间,那些手势根本来不及学会,只能全部押在电子交易上。”
“可以说,这是一种极其大胆的、跨越式的发展,一下子就进入电子交易领域,谁也不敢保证此事能够成功。难度可想而知,因为当时我们连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是怎么样的都搞不太清楚,要在这个基础上编写电脑软件和程序,确实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
“当时负责电脑交易系统开发的谢玮,是我从上海财经大学请来的工程师,他问我:‘设计的需求量要多大?’我心里根本没底,就说:‘3000笔。’因为当时以为这已经是很大的交易量了,谁想到现在的股票交易量会有数千万笔。记得临开业前一天的晚上,我们还在赶最后几个电脑交易页面,系统连测试都没来得及就开业交易了。”尉文渊感慨道。
证券交易所的场地呢?尉文渊在一本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一张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他找过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的旧址,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旧仓库,看了北京东路的火车站售票大厅和金陵东路的船票售票大厅,都失望而归。有人说北外滩的浦江饭店有个大厅,这个饭店是一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以前叫理查饭店,尉文渊顶着正午的烈日,步行来到浦江饭店,看到这里的孔雀厅很有模样,于是便敲定成为交易大厅。
交易大厅的装修布置、交易规则的制定、具体到交易大厅的色调、交易柜台的位置、显示屏的安装等,尉文渊都是事必躬亲。交易大厅里著名的红黄马甲和开市铜锣的由来,也都有故事。
“当时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厅的色彩为冷色调,如果交易人员穿红色,那么整个市场的色彩比较鲜艳,气氛就显得比较有活力。结果负责服装的同志去买布做马甲的时候,看黄颜色比红颜色好,就自己擅自决定买了黄布。我认为原来是因为颜色太淡才用红的,这么一改,不整个把事搞反了吗?结果重新买了红布做马甲。交易所开业时,因为已经做了几件黄马甲,临时决定管理人员穿黄马甲。于是全世界的证券交易所里,只有中国有红黄马甲之分。”
“我看电视报道,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市敲钟很有仪式感,于是定下来上交所用敲锣来开市,就满上海地找。一开始找来是锣鼓队用的那种锣,脸盆那么大、又很单薄,敲上去的声音龇牙咧嘴的,都没法听。后来,在城隍庙花600元找到的那个铜锣直径七八十公分、中间的部分鼓出来很大一个疙瘩,往上一敲声音嗡嗡的、挺浑厚的,它就成为中国股市第一锣了。”尉文渊在开市那天便敲响了它。
推行无纸化交易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尉文渊回忆:“19日一早,我发高烧,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只好向人借了一双大号鞋,一瘸一拐地在现场做最后的布置,然后倚着墙迎接贵宾。”按照原定程序,上午11点正式开始交易,由交易所的理事长李祥瑞授权尉文渊鸣锣开市。11点整,兴奋的来宾们还在议论参观着,未能全部进入仪式现场,而显示屏已经开始显示交易数据。“如果我不发布指令,电脑就会全部乱掉。情急之下,我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
放下锣锤,尉文渊艰难地走进电脑房,看到谢玮他们兴奋地抱在一起。交易成功了!送走来宾后,他就一头倒在床上。此时他高烧已达40度左右,当晚被送进医院。他在医院修养了一个月,才被允许出院。
上交所从开业的第一笔交易开始就跨入了电子交易时代,这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讲,没有电子交易的技术基础,中国证券市场不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扩张,也无法支持从上海到西藏的大中国、上亿投资人参与、万亿元的成交规模。在电子交易的基础上,尉文渊解决了股票无纸化交易的问题,在当时,这又是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意义的创举,推动和支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为了防止投机倒把,一开始交易所采用严格的涨跌停板控制,股票价格每天涨一点点,加之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结果滋生场外交易,黑市交易。于是,交易所出台了一个过户规定,凡未经场内交易的股票,不能过户。未经合法过户的股票,不能再进场交易,即使拿了股票实物,也不承认。就是说,我们不光认股票,还要认过户记录。”
这一招果然见效,由此尉文渊突发奇想,既然只认场内成交记录,有没有那张股票也就无所谓了。就这样,从1991年5月开始,上交所向股民回收手中的股票,正式实施无纸化交易系统试运行,几个月后,便建起了全世界最先进的交易系统。
“当时,推行无纸化的最大压力来自市场。投资者不愿交出股票,收老八股的实物券整整用了6个月还没有完全收齐。后来上交所再出规定,不交出实物股票,不能交易。到了老八股之后的第一只股票,也就是兴业房产新股发行时,印制了30%的实物股票,全部被封存于上交所,此后发行新股再也没有印制过实物股票,上交所才真正进入了无纸化时代。”尉文渊说。
因为无纸化,使交收期大大缩短。上交所开业的时候,规定是“T+4”,也就是说今天成交,第4天才完成交收。按照不允许买空卖空的规定,必须拿到钱和股票,才能再进行买卖,市场效率比较低。无纸化以后,缩短交收期就简单了,有了之后的“T+1”,甚至“T+0”。

创办中国第一张证券报
除了无纸化,激荡的岁月里还有尉文渊创办全中国第一张证券报纸的故事。上海证券报的一位老同志说,“尉总,你有媒体情结。”现在看来倒不是个人喜好使然,而是股票交易靠的就是信息,而信息必得借助媒体平台。1990年初夏,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在筹建之时,刚刚接手筹建工作千头万绪的尉文渊却先去了一趟上海《新闻报》的办公室,提出想尽快办一份证券报。然而,那时候若想要办报纸,取得新刊号很难,更不用说是敏感的证券类报纸了。因此,当时《新闻报》的采访部主任贺宛男建议尉文渊,先在现有的报纸上开辟证券专栏。
就这样,当年7月,国内第一个证券专栏在上海《新闻报》诞生了,专栏虽然已经启动,对尉文渊来说,这远远不够,交易所必须有自己的报纸。刚刚起步的中国证券市场十分需要一部专业性质的证券类报纸加以引导和知识普及。经过一年的筹备,1991年4月,上交所终于创办了内刊《上海证券》,也就是《上海证券报》的前身。
那时候《上海证券》是每周一期的对开大报,首期印了5000份,结果星期六清晨一出版,就被股民们一扫而光,短短几个月后发行量就超过了十万份。
“当时有媒体报道说,曾有个在万国证券公司黄埔营业部门口卖茶叶蛋的老太太,看到卖《上海证券》报比卖茶叶蛋生意还好,于是就改卖报纸了,在报纸的熏陶下,这位老太太不久之后也开始购买上海的股票认购证,成了股民。”
股民们最看重的是《上海证券》的头版头条,和第四版的《市场一周专栏》,编辑们通常是在每周五股市收市后,开始讨论头版文章的内容,而最终的题目,大都是由尉文渊亲自拍板决定的,由此,股民们就能透过报纸获悉交易所一线管理层的声音。“当时很多人每天都看头版的言论,都说这是我写的。”至今回忆起来,尉文渊还颇有得意之感。
而对于仅有千字篇幅的市场一周,股民们也是仔细地研读,还会用红蓝笔在上面作出各种记号。《上海证券》的巨大影响力,使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交易所信息披露和市场管理者调节稳定市场的重要工具。
洛阳纸贵,内刊被抢疯了,甚至出现了黄牛,杭州、宁波、南京都是拿火车来载报纸回去。于是,尉文渊就跟新华社合办了《上海证券报》,当时,每天早上空运200份报纸去西藏,让西藏投资者也能第一时间看到这份报纸。
从专刊一直到公开出版的上海证券报,尉文渊始终担任总编辑,重要的文章一定要送他审阅,直至他1995年离开交易所。他说,在黄浦路门口一边卖报,一边听股民读者发发议论,是他一早上班最喜欢做的事情。
也就是在这段期间,他成了大众传媒中的名人,市场开始揣摩他的一篇文章,一句话,甚至一个表情。不过,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成熟,这一点逐渐发生变化。1995年尉文渊曾经感慨道:“过去我在报纸上讲话,行情可以变化个100点,现在一点都上不去,这是件好事情,说明市场大了,成熟了。”
市场创新与扩容
“1992年2月,我在美国考察了1个月,美国市场给我很大触动。我觉得一个市场发展,必须解决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市场开放,第二自由竞争。假如我们能有这样的机制,市场也能快速发展。”
为此,在“春天的故事”下,尉文渊迈开步子,进行了多项尝试和改革。比如,市场扩容。到1992年底,上市公司数量从最初的“老八股”扩大到近60家。比如,扩大交易席位。交易所的会员已经从16家扩大到100多家,交易席位由最初的50个扩大到上千个,到1993年更是达到了6000个。
另外,他还推出一项极其大胆而有远见的金融工具创新:国债期货。国债期货以及国债回购交易工具的推出,大大活跃了国债市场,提高了金边债券的声誉,极大地促进了当时让政府揪心的国债发行难问题的解决,也是资本市场深化发展的一次勇敢探索。但也正是三年后的“3·27”国债期货事件,让尉文渊因负“监管责任”而离开了他一手创建起来的交易所。
邓小平在南巡中对股市的经典之语,在当时乃至现在,尉文渊都能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大浪淘沙,时间证明,正是尉文渊这一代践行者们,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为中国资本市场敲响了“第一锣”,打开了一扇大门。
1.《尉文渊:上交所的激荡岁月》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尉文渊:上交所的激荡岁月》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yule/117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