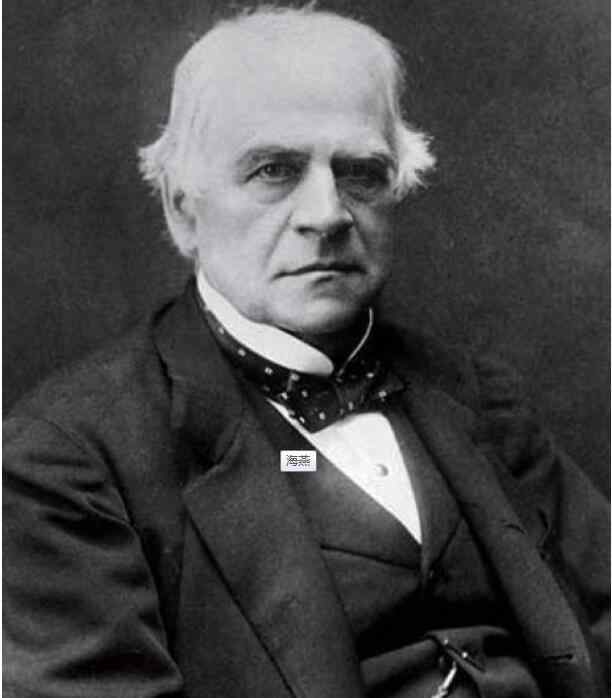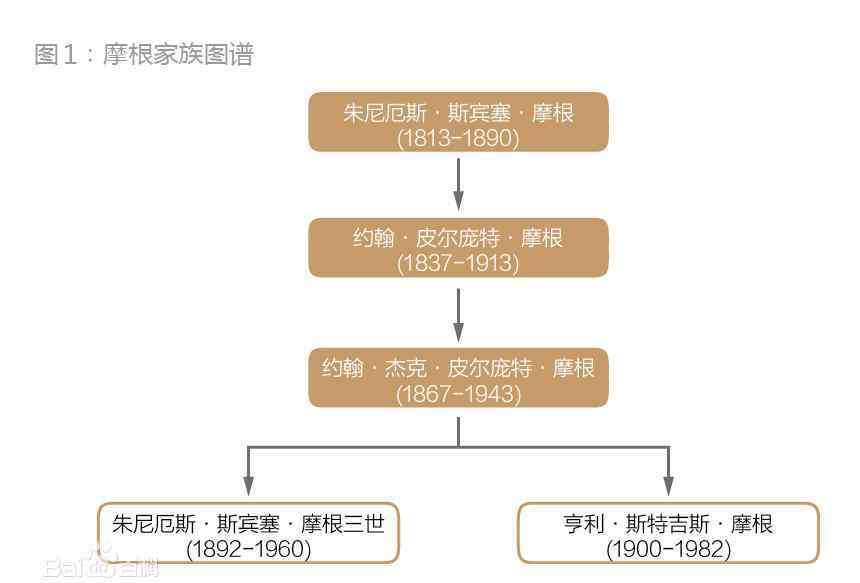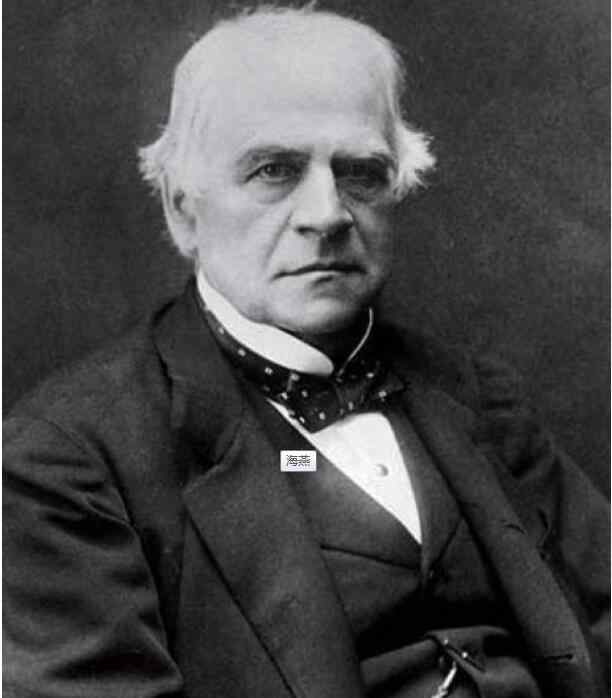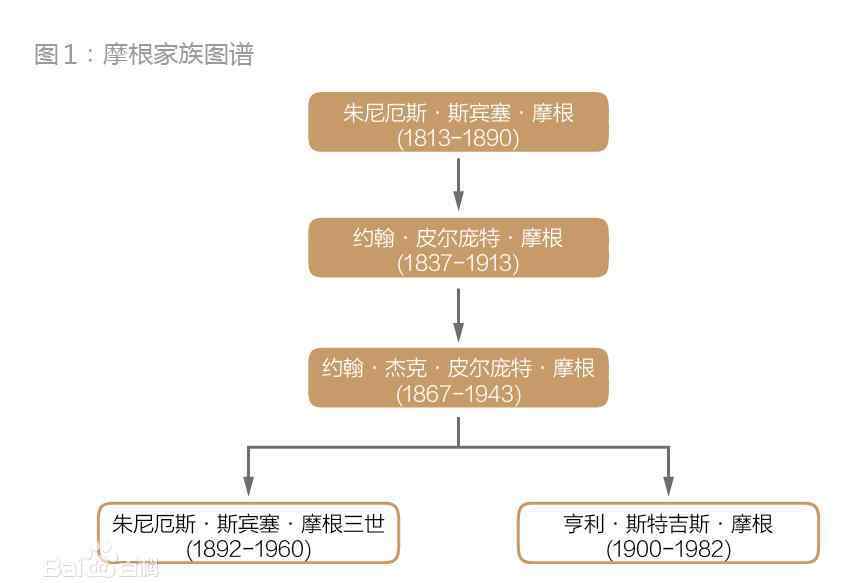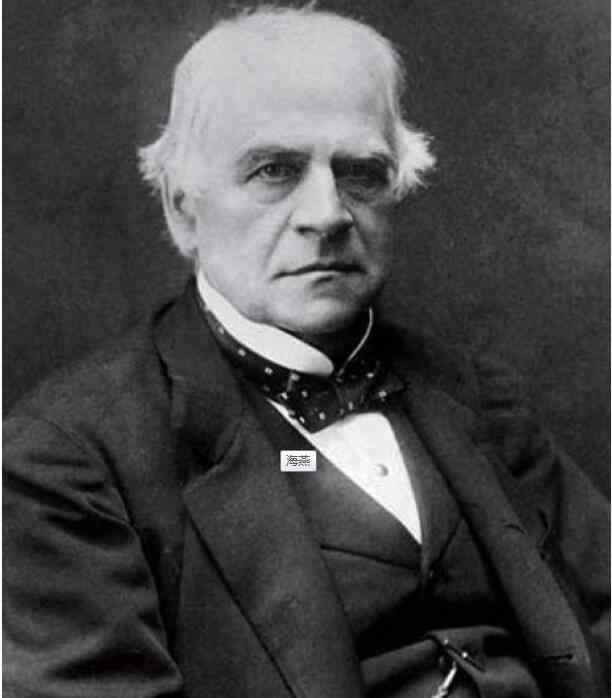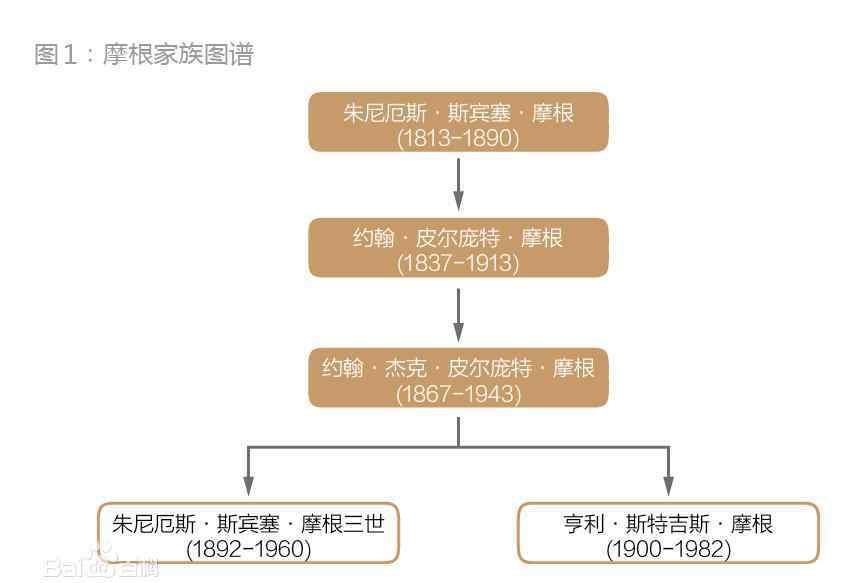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35)
内容介绍:
《红高粱家族》虽然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但是描写的是战争题材。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过去以抗战为主题的小说给人以正义与邪恶的强烈反差,塑造了近乎完美的正义爱国英雄。但《红高粱家族》中塑造的一些抗日英雄,却是正义与邪恶的化身。他们是一群属于《红高粱》的独特英雄,有着鲜活的生命和人性。
高粱葬礼3
五恼站在拴马的柳树下,从怀里摸出一只黄铜哨子。GGG吹了三次风,铁板社的五十名成员从离拴马的柳树不远的棚子里跑出来,各奔东西。马兴奋地吼叫着,蜿蜒的柳树被它们啃得露出一片片白色的树干。铁板社的这50多名成员都是精瘦的,武器轻巧精良:一把精致的马刀和一把肩上扛着大背的日本马枪。五扰四高的男人不带马枪,但是脖子上挂着一把俄罗斯老花镜机枪。他们跳上马,过了一会儿,他们变得拥挤起来,排成大致整齐的双向纵队。马儿轻快地调转蹄子,疯狂地小跑,向村外直接通向墨河桥的土路走去。马蹄上五颜六色的毛发在晨风中飘动,明亮的蹄子反射着柔和的银色光芒。铁板俱乐部的成员们在磨光的黑色明亮的马鞍上有节奏地跳舞。五扰骑着一匹精瘦的小马跑在前面。一阵沉闷的响声过后,父亲看到骑兵像一朵厚厚的乌云一样飘在平坦的黑土地上。
老师站在一个高凳上,身穿长袍和中山装,高喊:“吹手队——”
一群戴着黑色和红色帽子的小号手似乎从地上走了出来,奔向路边的小号手大楼。建筑由木板和芦苇垫组成,大约有五七米高。街上的人就像蚁群,小号手挤过人的缝隙,踩在一级木板上,握手爬到自己的高处。
石大师叫了一声:“起来——”
小号和唢呐齐鸣。看着人群拼命往前挤,脖子被拉长到最长,试图看清圈子。后面的人群像潮水般涌了上来,弱弱的号手楼子拥挤不堪,吱吱嘎嘎,摇摇欲坠。号手们吓得纷纷做鬼叫,拴在路边树上的牛驴也很挤。
爷爷谦虚地说:“老黑,我该怎么办?”
黑眼睛大声喊:“第三,把队伍拉出来!”
铁人俱乐部50多名荷枪实弹的成员也像从地下出来一样出现在人们的圈子里。他们挥舞着大枪,用枪托和枪托刺伤被推进去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有几万人挤在村里看葬礼,50个铁板成员累得口吐白沫阻止不了人群上来。
黑眼拿出一把箱枪,对着天空开了一枪空;把枪放在乌鸦的头上;铁板的成员也疯狂地向天空射击空。枪声一响,挤到前面的人转过身来,返身向后一推。后面往前推的人很迷茫,往前推。中间的人突然站了起来,就像一把黑色的尺子弓起的背在运动。被踩在地上的孩子尖叫起来,两个小号手慢慢倒下。小号手里的小号手擦着蹄子,兜圈子,掉进人群里。小号手的尖叫和被砸者的尖叫成为喧嚣春潮中最尖锐的吼声。一头驴被困在一个人的缝隙里,就像被困在沼泽里,它的脖子被抬起来,头被抬起来,它鸡蛋大小的眼睛像两个铃铛一样伸出来,发出微弱的蓝光。在这次暴乱中,至少有十几名老弱病残被踩死。几个月后,几头驴和牛的尸体躺在这里散发气味,吸引苍白的绳子。
在铁血成员的压力下,人群终于平静下来。几个女人在人群外的叫喊声中,把又一次爬上大楼的慌乱的小号手演奏的垂死音乐中的精华带了出来。知道自己挤不进核心的人,有一大半退到村外,站在通往奶奶坟前的路边,等待大葬礼的仪式仪式。在那里,年轻美丽的五烦恼正驾着他的骑兵来回穿梭。
受惊的老师再次站在高凳上,喊道:“小兜帽——”
两个没有腰的铁板俱乐部成员会掀起一个小小的天蓝色罩子。小兜帽有一米多高,方形,脊状,有龙头一样的角,帽顶上有一个红色的琉璃顶子。
石大师大叫:“请取主题——”
我妈跟我说,主题是一种精神立场。后来我简单考证了一下。题材不是祭祀的精神阵地,而是专门用来证明丧葬时棺材的身份。正确的名字是“上帝之主”,与仪式仪式前面的名单进行补充和交叉证明。奶奶的主题在帐篷里的火里被烧掉了,主题的墨水也没干,就请了两个面容姣好的铁板社成员出来。主题上写着:清光绪32年5月5日出生,2008年8月9日中午去世。民国高密东北乡游击队司令龚玉,占领奥园,戴上自己的姓氏,三十二岁时,每一个神都葬在白马山阳的墨水河阴下。

奶奶的神披着三尺长的白色紫菱,看上去优雅;铁血成员小心翼翼地把上帝放在一个小兜帽里,然后退到两边,垂下双手站立。
石大师大叫:“大兜帽——”
在小号手的倡导下,铁板俱乐部的六十四名成员抬着深红色、西瓜般蓝顶的大罩子。封面前有一个铁板社小头目,手持锣,打出鲜明的节奏。六十四个人踩着锣走路。人群中原本的叽叽喳喳声停止了,只有小号手吹着笛子和笛子,被踩死的女人绝望地哭喊着,锣声尖叫着,所有人都盯着像寺庙一样缓缓移动的大罩子,人群中弥漫着一股严肃的空气息/[/k0/。
爷爷受伤的胳膊周围总有一只极其讨厌的马蝇,它总想落在爷爷伤口渗出的黑血上。爷爷挥了挥手,炸开了它,它惊喜地飞了起来,愤怒地围着爷爷的头打转,发出如此强烈的吼声。爷爷恨不得一巴掌拍成肉酱,但是打不过,反而像针一样打伤了胳膊。
大兜帽颤抖着,锚定在奶奶的棺材前。红帮和蓝顶子的和谐色彩,以及锣声,唤起了爷爷对转瞬即逝的前世的挥之不去的记忆。
爷爷杀和尚的时候十八岁。他逃离家乡,四处流浪,直到21岁。他回到高密东北乡,去“婚丧服务公司”吃了一顿大餐。那时候他已经经历过人间疾苦,被穿红黑裤扫街侮辱过,具备了大土匪的基本素质。他知道吃粗棒饭不容易,但他并不害怕。爷爷忘不了1920年在交县齐翰林家被扇耳光的耻辱。爷爷忘记了打扰他的马蝇。他盯着机会咬了一口爷爷胳膊上血淋淋的白布,从嘴里吐出来,又红又咸的血吸进嘴里。在没有倾斜的号手楼里,几道炽热的金色光芒像球一样照在号手的脸颊上,汗水从他们的脸上流到脖子上。在喇叭和唢呐口的下缘,小号手的口水从弯弯曲曲的铜铁管里流了下来。看丧礼人踮起脚尖,成千上万只眼睛发出的光,像焦灼的月光,古老灿烂的文化,反动落后的思想,笼罩着圈子里的活人和纸人。我的父亲全身都暴露在邪恶眼睛的美丽光芒下。起初,他的心像一颗紫葡萄一样愤怒,然后是一系列五彩缤纷的彩虹般的痛苦。父亲穿着一件厚及膝的白布孝衫,腰间系着一条灰白色的亚麻辫子。一顶方形孝顺帽遮住了他剃过的头。人群中的汗水和奶奶棺材上的焦油味变成了恶臭,让父亲站不稳。他浑身是汗,但他的心却不断地变得阴暗。从小号手口中乐器刺耳的唧唧声和尖利的金线,从沉闷的盘子到送葬的人群,从圆圆的眼睛,从父亲脊背上过敏的白绢络,都有三月霜般的轻微而冰冷的信号。奶奶的棺材当时狰狞,麻脸板脸,前高后低的俯卧姿势,刀切、急剧倾斜的棺材头,都让它有了某种野兽的隐隐性格。父亲总觉得它会突然打着哈欠站起来,扑向啼啼的人群。黑色的棺材在父亲的意识中膨胀得像一朵云,被厚厚的盘子和红砖粉包围着的奶奶的遗体清晰地展现在父亲的眼前。那天早上,在墨河边,爷爷用铁锹头挖着绿草芽的奶奶的坟,把泡得很厉害的高粱秆扯出来,露出了奶奶鲜活的身体。这一幕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父亲的眼前,父亲无法忘记奶奶那张从土坑里突出来的脸,就像他无法忘记奶奶抬头看着红高粱死去的时候一样。这张崭新而梦幻的脸突然融入了温暖的春风。父亲在执行孝子繁琐礼仪的同时,一直在思考着这些辉煌的人生片段。被太阳晒得不好意思的师傅大声吼道:“打棺材——”暂时给搬运工装上的铁板社六十四名成员蜂拥到巨大的棺材前大喊,但棺材一动也不动,搬运工像一群蚂蚁围着猪的尸体一样围着棺材。爷爷把苍蝇轰走,鄙夷地看着对大棺材束手无策的同事,挥手叫了小头目,对他说:“你去拿几根棉布来,不然天亮了都进不了兜帽!”小头目困惑地盯着爷爷的眼睛,爷爷却把目光移开,仿佛看到了黑土平原对面的墨河大堤…
交县齐家前有两个水桶旗杆。这块老朽木象征着齐家家族的荣耀。晚清老翰林去世,追随天下享富贵的老人儿女,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葬礼的日期太晚了,无法宣布。在齐家的深院,棺材停在最后一排房子里;要把棺材拿到街上,你必须先穿过七个窄门。看到棺材和地形后,十几家“婚礼和殡葬服务公司”的经理们都低下头离开了,尽管齐家支付的价格令人吃惊。
消息传到了高密东北乡的“婚丧服务公司”。玩棺材可以得到500元的白银和海洋的高额奖励,像诱惑诱饵一样诱惑着我爷爷和他那一班粗棍男。似乎一个渴望爱情的年轻女子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天才,向她眨眨眼,扔出一个金钩。爷爷,他们去找乡长曹二,发誓要讨回高密东北乡的威风,在阴阳赚500块钱。曹二的师傅稳如磐石,坐在太师椅上,连屁都不放。爷爷,他们只能看到他冷冷的眼珠子,那是聪明的转动。我听到他手里水烟的砰砰声。爷爷他们兴高采烈的吵了一会:二爷,不是钱的问题!人长生不老,不蒸馒头打架!别让他们小看我们,别让他们觉得高密东北乡无能!当时曹二的师傅不欠屁股,慢慢放了个屁。他说,回去休息吧,让他有个三长两短,碾压人事,丢高密东北乡的脸,毁了我的生意。你缺钱,二爷赏你求饶。曹二爷说完,就闭上眼睛,粗棍丈夫们被他们的心揪着,齐声叫好。二爷,不要破坏自己的野心!二爷说,不要吞镰刀钩刀没有弯肚子。你以为这500块钱的大洋这么好赚?齐家有七道门,沉重的棺材里装满了水银!水星!水星!你用你的狗的大脑来计算这个棺材应该有多重。曹二主骂完之后,冷冷地斜眼看着自己的粗棍丈夫。他们彼此观望了一会儿,脸上有一片不舍得却又恐惧的浊云。曹二爷见此,从鼻孔里喷出两个喷嚏,道:“回去等着看英雄,挣大钱!哎,你们这些小人打个小分,320就赚了,给穷人家抬个薄棺材就好了!”
曹二主的话,像一剂猛药,刺激着粗棍们的心。爷爷上前一步,带头喊了一句:“曹二爷,跟你这种窝囊的班长共事,真他妈的吃紧。一兵一将结一窝!我不干!”

年轻力壮的理发师齐声叫唤,二老爷站起来,步履艰难地走到爷爷面前,用力拍了拍爷爷的肩膀,诚恳地说:“占领敖!是个好人!是高密东北乡的一种。家里奖励标准高的事实就是欺负我们吃粗杠的兄弟。如果兄弟们能齐心协力打棺材,那一定能让我们东北乡出名,也很难买到几分荣耀。不过这个家族是清朝的翰林家族,规矩很严。玩这个棺材一点都不容易。兄弟俩晚上睡不着,琢磨着怎么把七重门赶出去。”好像是事先约定好的,理发师在说话。两个冠冕堂皇的人从外面进来,自称是乔翰林家的管事,来找东北乡的理发师挣大钱。
齐家的管事说明来意,曹大师懒洋洋地问:“多少钱?”
“现在五百大洋!管班,这是世界罕见的价格!”齐家的乡长说。
曹二爷把银水烟扔在桌上,冷冷一笑。说:“我们的生意不缺买卖,不缺钱,不缺钱。请另请高明!”
祁家的管事潇洒地笑了笑,说:“班长,我们都是长期做生意的人!”
曹二爷道:“是,是。这么高的奖励,总有人抢着去抬。”
曹二爷闭上了眼睛。
两个管事交换了一下眼神,第一个说:别拐弯抹角了,求个价吧!
曹二爷道:“为了几个银两,丢几条人命,我可承受不起!”
管事说:“六百!六百块现在在海里!”
曹二爷坐得像个化石。:
“七百!七百块钱,班长!做生意要讲良心!”
曹二爷撇了撇嘴角。
“八百八,多一个都不行!”
曹二爷睁开眼一饮而尽:“一千块!”
管事牙疼似的鼓起腮帮子,瞪着曹二冷酷的脸。
“小队...那我们不能做决定……”
“回去告诉你的师傅,一千块,别少做什么。”
“好吧,那么,等着听。”
第二天早上,管家骑着一匹来自交县的紫马,给棺材定了日期,先付了500大洋,棺材做好之后再付500块。那匹紫色的马在昌跑得又热又汗,它的角上覆盖着白色的泡沫。
出殡那天,六十四个烧烤的丈夫半夜起来,点起火来煮饭,吃饱了,收拾好自己的家当,穿过满天星光,奔向交县。曹二的师傅骑着黑驴跟在杠铃后面。
爷爷清楚的记得那天早上,天高露水冷的时候,藏在腰间的铁钩重重的打在胯骨上。到了交县,日出之初就打开了,看了看街旁的送葬人群名单,把街道缩小了。爷爷,他们走在街上听着人们叽叽喳喳的低语,高昂着头,竭力表现英雄风范,心里却如坐针毡,沉重的心事像石头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