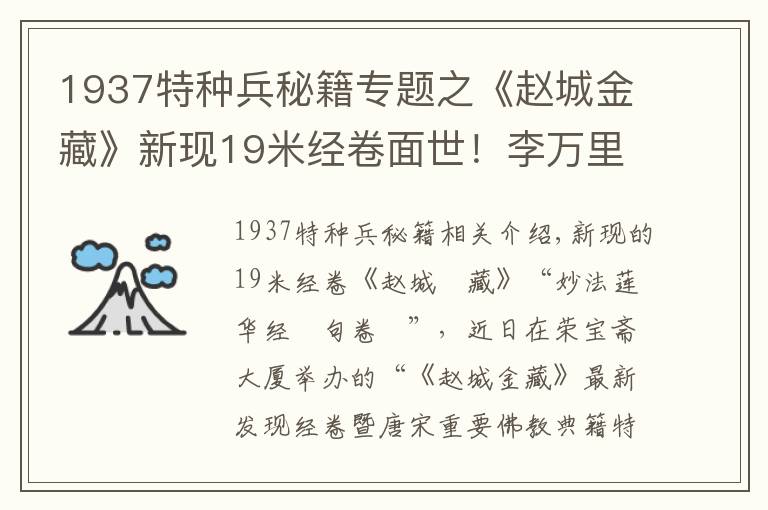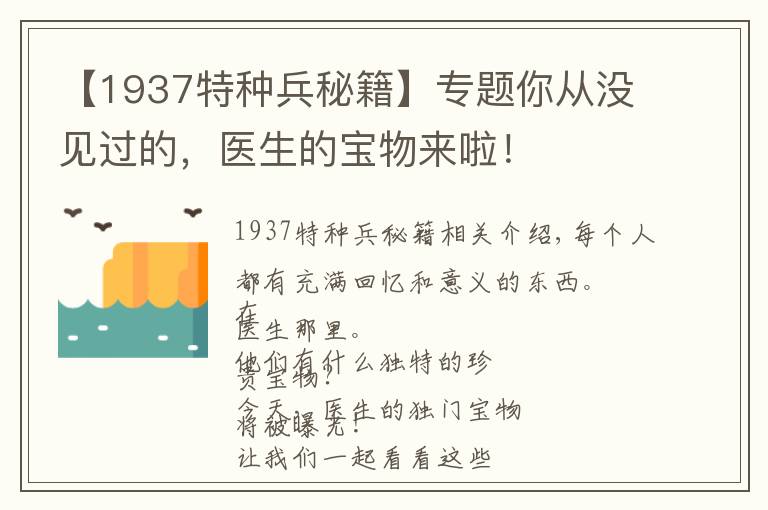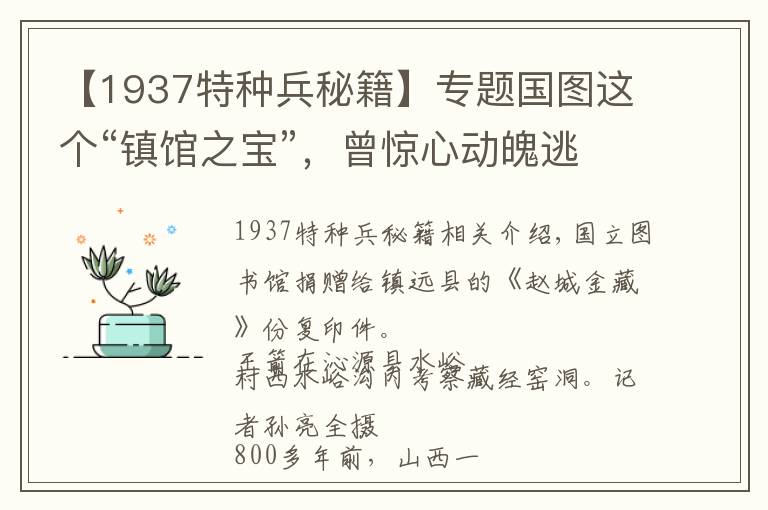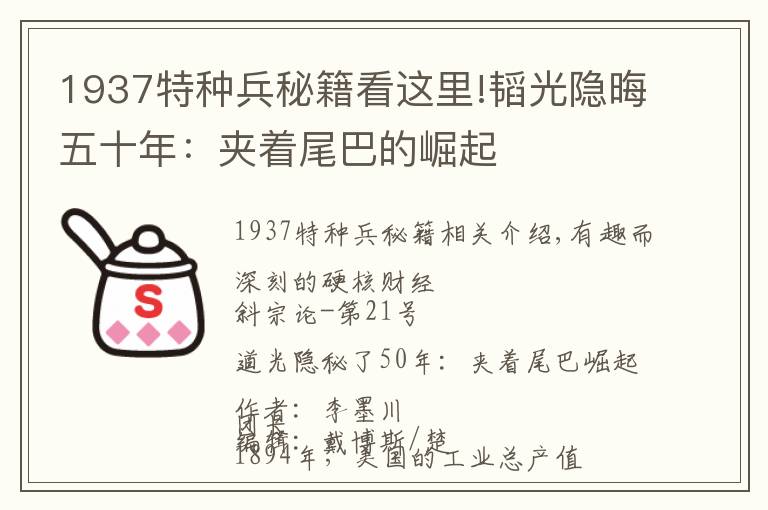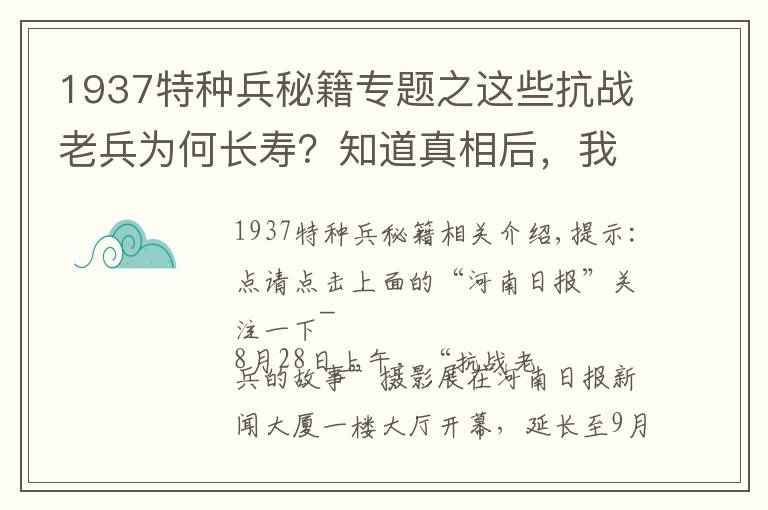马明谦
施哲村收集西方书籍的方法
根据《施蛰存老师编年事录》 《上海摩登》 《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和上海新书业》 《上海出版志》和其他数据,可以推断出市休眠老师获得西方文件的几个主要途径。
一、 外国人开办的西文书店。
据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资料,上世纪年代的上海,中外书商先后注册登记经营外文书的有近百家,外国人开办的别发书店(Kelly & Walsh)、中美图书公司、伊文思书局,这三家规模较大,并称为当时沪上三大西文书店。
别发书店创办最早,1870年由英商开办,地点在南京路12号,靠近惠罗公司和沙逊大厦,发售的主要是英文教学用书、外语工具书及学校用品;此后不单经销原版书,还出版英文图书,曾大量印发了汉学家如翟里斯、理雅各、卫礼贤等的著作;1935年8月起,由法学家吴经熊向孙科提议,别发负责出版发行英文月刊《天下》(T'ien Hsia Monthly),另邀林语堂、温源宁等人联合创办。陈子善先生在《闲话别发印书馆》中,曾记述施先生亲口告诉的订阅T. S·艾略特1935年版《诗集》一事,当时施先生通过别发预订,得到了珍贵的签名本。另外,1929年1月,施先生的小说集《追》列入“今日文库”由水沫书店出版印行。他在《我的创作生活之经历》曾记述:“其时,第一本新俄短篇的英译本‘Flying Osip’在这当儿运来中国了。我从别发书店里买了来,看了大半本。于是我又想摹仿一下了。《追》就是在这种不纯的动机下产生的。”这段文字记录了施蛰存先生作为一个文学新手从购书、阅读到受启发而创作的完整过程,殊为难得。
中美图书公司在南京路78号,后改南京东路160号,主要业务是经营进口欧美图书杂志、教科书、参考书的发行,也经营出版业务。
伊文思书局起先在虹口北四川路30号,后迁九江路200号,早期专营西文原版教科书,供各教会学校使用,以后增销原版图书并进口欧美期刊杂志、仪器文具等。1935年由华商沈芝泉等集资十万元接手,改称伊文思书局,1937年迁南京路220号。
在这些西文书店可以直接从国外购买书籍,并订购如Vanity Fair、Harper's、The Dial、The Bookman、Living Age、London Times、Lettre Francais和Le Monde等国外报刊。
此外还有内山完造的内山书店,1929年后迁至施高塔路11号(现编为四川北路2048号),主要经营普通汉、日文书籍,还可货到付款。外国人开办的外文书店还有派立贡书店、凯利书店 、俄人的舰队书店、金星堂、至诚堂、乐善堂书局、璧恒公司等。1932年创办的龙门书局也翻印原版书。
二、国人开办的售卖西文书的书店。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这两家都进口外国书刊,在书店门市发售。商务印书馆也兼带发行英文书。除此,国人开办的销售外文书刊的书店还有大华杂志公司、中外书局、东亚书局、世界书局、中外科学书社。
三、上海本埠的西文书旧书店。
1928年,施蛰存与戴望舒、杜衡和冯雪峰四人共居松江家中小厢楼,俨然一个文学工场,施先生晚年有一篇《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曾讲到众人去书店搜买书籍的情形:“这期间,雪峰和望舒经常到上海去,大约每二星期,总有一个人去上海,一般都是当天来回。去上海的目的任务是买书或‘销货’。雪峰一到上海,就去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和设在海宁路及吴淞路一带的日本旧书店;望舒到上海,就去环龙路(今南昌路)的红鸟书店买法文新书;我到上海,先去看几家英文旧书店,其次才到南京路上的中美图书公司和别发书店。英美出版的新书价高,而卖英文书的旧书店多,故我买的绝大部分是旧书。所谓‘销货’,就是把著译稿带到上海去找出版家。”之所以多买旧书,实在是有着经济考虑上的原因。
西文旧书店,当然不止上文《列奥帕迪散文、对话和随想录》英译本一条提到的“中西旧书商店”。
施先生自己在文章里曾多次谈到逛旧书店的经历。如1932年12月25日刊于《申报·自由谈》的《买旧书》一文就描述甚详:“在中日沪战以前,靶子路虬江路一带很有几家旧书店,虽然他们是属于卖教科书的,但是也颇有些文学艺术方面的书。我的一部英译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便是从虬江路买来的……西文旧书店老板大概都不是版本专家,所以他的书都杂乱地堆置着,不加区分,你必须一本一本的翻,像淘金一样。有时你会得在许多无聊的小说里翻出一本你所悦意的书。我的一本第三版杜拉克插绘本《鲁拜集》,就是从许多会计学书堆里发掘出来的。但有时,你也许会翻得双手乌黑而了无所得。可是你不必抱怨,这正也是一种乐趣。”
《鲁拜集》参考书影,Garden City豪华版(1937,New York)
《鲁拜集》参考书影,Hodder & Stoughton版(1911,London)
还有“蓬路口的添福书庄”:“老板是一个曾经在外国兵轮上当过庖丁的广东人,他对于书不很懂得。所以他不会讨出很贵的价钱来。我的朋友戴望舒曾经从他那里以十元的代价买到一部三色插绘本魏尔仑诗集,皮装精印五巨册,实在是便宜的交易。”
此外,施先生还提到一个自称是爱普罗影戏院经理的人,此人爱书如痴,后来在愚园路开了一家旧书铺:“文学方面的书很多,你假如高兴去参观参观,他一定可以请你看许多作家亲笔签字本,初版本,限定本的名贵的书籍的。他的定价也很便宜,一本初版的曼殊斐儿小说集‘Something Childish’只卖十五元,大是值得。因为这本书当时只印二百五十部,在英国书籍市场中,已经算是罕本书了。”曼殊斐儿即英国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另,1933年5月,施先生在复戴望舒信中曾提及译有《蔓殊菲儿小品集》——但凭此尚不能推知英文版的书名。
Something Childish的参考书影
施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到了一本爱德华·李亚的《无意思之书》。据他另一篇文字回忆,是“偶然在蓬莱路一家旧书店中得到了此书,真是喜出望外的事”。
《无意思之书》的参考书影
在与李欧梵的访谈中,施先生也提到他有一次很幸运地在一家旧书店买到了波德莱尔的诗全集。
1933年,年轻的诗人徐迟走出故乡南浔,来到上海拜访时任《现代》主编的施蛰存,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江南小镇》中,曾动情回忆当年施蛰存先生带他逛上海书店的经历:路线是先去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之后上南京路别发书店和大中华旧书店,过后就去喝下午茶。喝了茶,再去逛了中文书店和南京路附近的其他西文书店。
此外,施先生在《读书》1992年第六期有一篇文章《我的爱读书》,也提到了他收藏爱读的西文书:“现在是在‘读’的范围之内,找寻几种可以说是我所爱的,先从诗说起。Loeb Classical Library洛布经典丛书里的《希腊诗选》,Palgrave(帕尔格雷夫)的《英诗金库》和Harriet Monroe and Alice Corbin Henderson合编的The New Poetry:An Anthology 《新诗选》(NEW YORK: MACMILLAN, 1917),这三本都是好书,可以说是我所喜欢的,也是随时翻读的。”
《英诗金库》参考书影
《《希腊诗选》参考书影
《新诗选》参考书影
之前买来的外文书弄丢了,施先生还会再买一本。如《〈丈夫与情人〉初版引言》中所记:“我在一本美国出版的‘繁华市’月刊(Vanity Fair)上读到匈牙利现代戏剧家弗朗茨莫尔那(Franz Molnar)的一个对话,题名曰‘雏’。我很喜欢它的幽默与机智,当时即译出来刊载在自己办的《新文艺》月刊上……不久,在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本崭新的书,在封面上题着‘丈夫与情人,对话十九篇。弗朗茨莫尔那著,英译者彭及敏·格拉才’。是莫尔那那本书的英译本。此书后来丢失。后来无意中又在一家旧书店里找到了另一本旧的。我把它从头再看过一遍,插上了书架。一直到抗战开始,它与我的其他许多洋书一起损失在兵燹里了。”
也有因价格不菲而放弃的时候。1935年2月,施先生译成意大利迦桑诺伐的《宝玲小姐忆语》,在《译者附记》里他坦白说:“《迦桑诺伐回忆录》的全本我没有钱买,我所常常耽读着的只是‘近代丛书’本的英译本。但虽然已删节得干干净净,虽然经过了转译,这十八世纪的恋爱艺术家的感伤气氛还是洋溢乎字里行间。现在为《文饭小品》选译一节,不过是尝鼎一脔罢了。”这里的迦桑诺伐即意大利情圣作家卡萨诺瓦。
四、委托友人代购或友人相赠。
这是施先生收藏西文书的另一个渠道。好友戴望舒留法期间,施先生与他通信时,便时常提及购书之事。如1932年11月18日函:“书店跑过否?珍书秘籍的市场已研究过否?均迫切欲知之。”12月27日函又追问道:“卖奇书的书店去跑过否?能否快给我找一个目录来?”1933年1月12日函:“英文的大大主义宣言及超现实主义宣言如有,也请设法。”1933年4月28日复戴望舒信中谈得更详细了:“你说的德国本,定价18Frs的《Lady Chatterley's Lover》是英文呢法文?如是英文,我要的,等你钱宽的时候给我买一本。Herbert Read,David Gamett,Feliot,Kay Boyli这些英文书都不必买,因我都在向‘丸善’等处买了。Breton的超现实主义宣言法文本我也买了。以后我只要杂志(英文的)及新派别法国作品之英译本。”
戴望舒1935年自法国返回时,据说带回了几千册的法文和西班牙文的书回来(数量实在惊人,有待核实),施先生必定也受赠了不少的法文原版书。
另外,他的好友邵洵美经常与圈子里的作家朋友随意分享自己的西文书收藏,施先生或许曾获赠书也未可知。至于他的另一文学同道刘呐鸥,因我尚未购得台南县文化局出版的上下卷《刘呐鸥全集·日记集》,目前没有可掌握的资料。
“李欧梵书库”这批施先生藏书中,也有可以确定为友人所赠,如上面提到的那本叶赛宁诗集《安魂弥撒》就是诗人艾青游学法国时购买,此后转赠了施蛰存先生。
以上只是概略介绍了施蛰存先生经眼、过手的部分西书。我还有一个思路,就是从先生的译作来反推他的藏书。根据沈建中先生的《施蛰存编年事录》,我将施先生1926年至1937年的译介工作梳理了一遍,又发现了不少资料。不过,这篇文章的篇幅已太长,故而只能省略。今年年初,听闻《施蛰存全集》重新整理后,将分为作品和译作两大部分再次推出,目前已初步制作了译作编年目录并进行整理校勘,已搜集到的单行本和散篇译作就有两百余种,这部分将定名为《施蛰存译文全集》先期出版。从中当可充分了解施蛰存先生在文学译介方面筚路蓝缕的功业轨迹,也能更完整地探知他的西文藏书全貌。
不得已的离舍
施先生大部分中西文的藏书此前都存放在松江家中,书斋名之曰“无相庵”。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件,抗战全面爆发。7月下旬,熊庆来出任云南大学校长后抵上海,因了朱自清先生的推荐,邀请施蛰存赴云南大学任教,承诺预支路费两百元。随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先生辗转避难。9月初,“遂决计从公路行,藉以一看内地景色”,踏上了赴滇旅程。
日后,施先生在《浮生杂咏》组诗中曾做过这样的心迹剖陈:“我以朱自清先生之推毂,受熊公聘。熊公回滇,而沪战起。我至八月尾始得成行,从此结束文学生活,漂泊西南矣。”
1937年11月2日晚11时,施先生接大妹施绛年由上海拍来的电报,得知松江家屋被日寇飞机炸毁,无相庵书斋中的旧物全数化为齑粉,包括历年所购的中西文书刊、手稿、文物、字画、尺牍等,其中就有很可珍贵的鲁迅来函与郁达夫书联。
11月3日,先生赋七律《得家报知敝庐已毁于兵火》,先有小序记事:“11月2日接家报,悉松江舍下已为日机投弹炸毀,翌日感赋。”诗句如下:
去乡万里艰消息,忽接音书意转烦。
闻道王师回澲上,却叫倭冦逼云间。
室庐真已雀生角,妻子都成鹤在樊。
忍下新亭闲涕泪,夕阳明处乱鸦翻。
隔年的1938年4月5日,施先生在香港《大风》旬刊第四期发表《我的家屋》,自述得知故园被毁消息后的怅然:“我读了电文后,不禁有些感怆,而平生第一次地怀念起我的家屋来了。这二十年来长于斯歌于斯的屋子,现在竟遭受了敌人的暴虐,我们一家人在这屋子里的生活,到如今终于结束了。”
施先生如此深情地忆想自己书斋里的故物:“我们在这屋子里舒服地住了二十余年。在这间屋子里,与我关系最密切的,自然是客室左边的那间书斋了……这一间书斋的陈设是很简单的,统共只有一桌书椅,和十二只旧式书箱……十余年来,我已养成了一个爱书之癖,每有余资,辄以买书,在新陈代谢之余,那十二只书箱的内容,已经成为比较的齐整了,虽然说不上是藏书家,但在我已是全副家产了……”
而在家屋书斋被炸毁之前的6月,施先生还刚刚添置了新书架:“我因为历年来买的西文书多得没有地方安顿。遂又制备了四只西式书橱,放在书斋中,以庋藏西书及一部新买的《四部丛刊》。这些书橱陈列不到一个月,上海战事就发生了,不及两个月,我就离舍了它们,只身走天南了。”
由藏书所折射的文化环境
在距今百年以前的中国,书籍等出版品的引入、译介和转化,实在是很值得考察探究的一个角度。这篇小文从施蛰存先生的藏书入手,借由西文书这扇小窗,期望能够窥见当时作家购书、阅读、译介和创作的实况的一斑。
翻检过往的历史资料就可以发现,上海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通商口岸,西方文化的输入并不仅限于一般日用商品或时装、电影、咖啡馆等消费形态的建立,它进而还扩展到了更高层的文化:音乐、绘画、雕塑与文学。书店业繁荣所带来的书籍的流动,作品的阅读所带来的思维刺激、交流与分享,赋予了像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叶灵凤及稍晚一辈的路易士(纪弦)和徐迟这样的文化工作者以从所未有的开阔视野。这个文化环境,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习俗处在了一个有机的交织渗透中,而正是这样的多元丰富的文化环境,熏陶并塑造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审美鉴赏力,继而赋予了他们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传播的不竭动力。
施蛰存钟爱着爱伦·坡、奥雷维尔、叶芝、麦克里奥德、勒法努、弗雷泽、德昆西和萨德侯爵,也喜爱研读弗洛伊德、蔼理斯的学术著作,特别是从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获得了重要的创作思想的启发;而戴望舒服膺于法国诗人魏尔伦,弗朗西斯·耶麦、保罗·福尔,德·戈尔蒙、西班牙诗人洛尔加、乌纳穆诺和阿左林,开启了自己的诗创作。邵洵美和叶灵凤都共同热爱了波德莱尔、史文朋、王尔德和比亚兹莱的创作,而叶灵凤还关注到了当时的新进美国小说家海明威和福克纳。他们的文学关注的频谱如此宽阔,可以说覆盖了当时欧美所有一线的作家和作品。
他们几个人在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和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呼应了时代的风气,还投入很大的智力、精力、甚至财力(如刘呐鸥、邵洵美),或开设书店,或创办文学杂志。施先生先与戴望舒等同道友人合编过《文学工场》《无轨列车》《新文艺》月刊,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时声名鹊起,其后又主编过了随笔刊物《文饭小品》。戴望舒在《现代》杂志之后,又创刊了《新诗》;叶灵凤编辑过好几种杂志,包括《现代小说》和《文艺画报》;邵洵美自己拥有出版社,独立运营了好几种杂志如《金屋》月刊。施蛰存和他的文学同道,在过往那个时代成为文化领域的领风气之先者,会同上海、北京和各地的作家、诗人、出版家、教育家,由此构筑起现代中国活泼泼的文化生态。今天,从更长时段的文化史角度来观察,我们已深知一个开放、宽容的社会环境的重要,须有健全肥沃的土壤,文化才会迎来欣荣勃发的生机。文学的活力必渊源于此,也只能渊源于此。
李欧梵在八九十年代曾前后为施先生做了三次访谈,他发现施先生对欧洲的现代主义谈得头头是道。从以上介绍内容可知,这绝不是单一的偶然现象。在当时的上海,以施蛰存为代表的文化人士,在思想、创作、活动等诸多方面,是与当时的世界波潮同步的。施先生所完成的文学事功,尤其是他特异出色的小说创作,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才得以孕育成形并成熟起来。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言:“仅仅举出以上这些人就足以展示当时上海的现代主义者的全貌,其光彩与技巧在中国直至今日还从未再次被达到过。”
而施蛰存先生,正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案。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栾梦
1.《关于1937特种兵秘籍我想说马鸣谦︱施蛰存外文藏书摭谈(下)》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关于1937特种兵秘籍我想说马鸣谦︱施蛰存外文藏书摭谈(下)》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gl/20823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