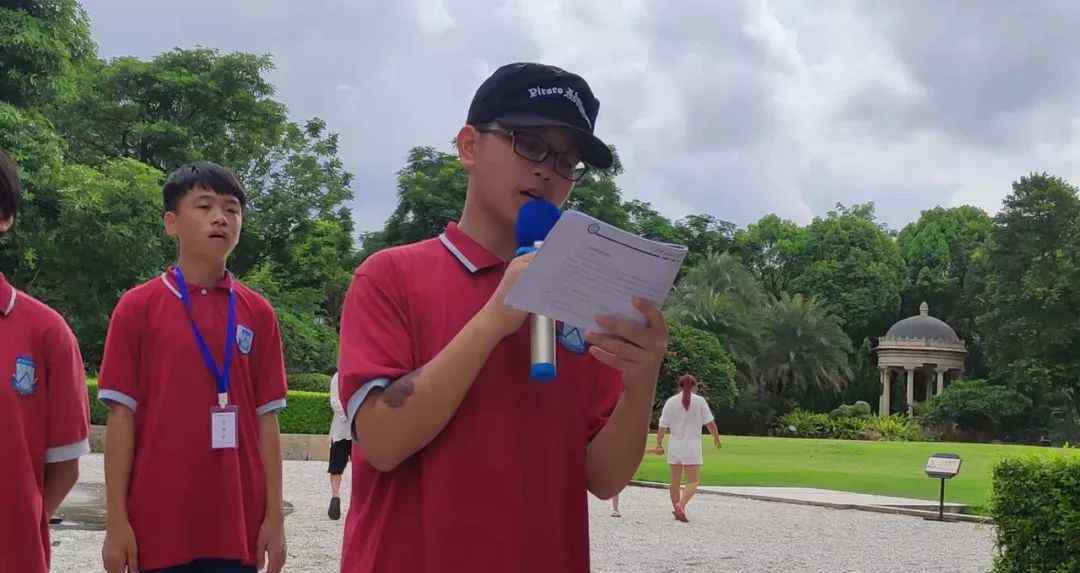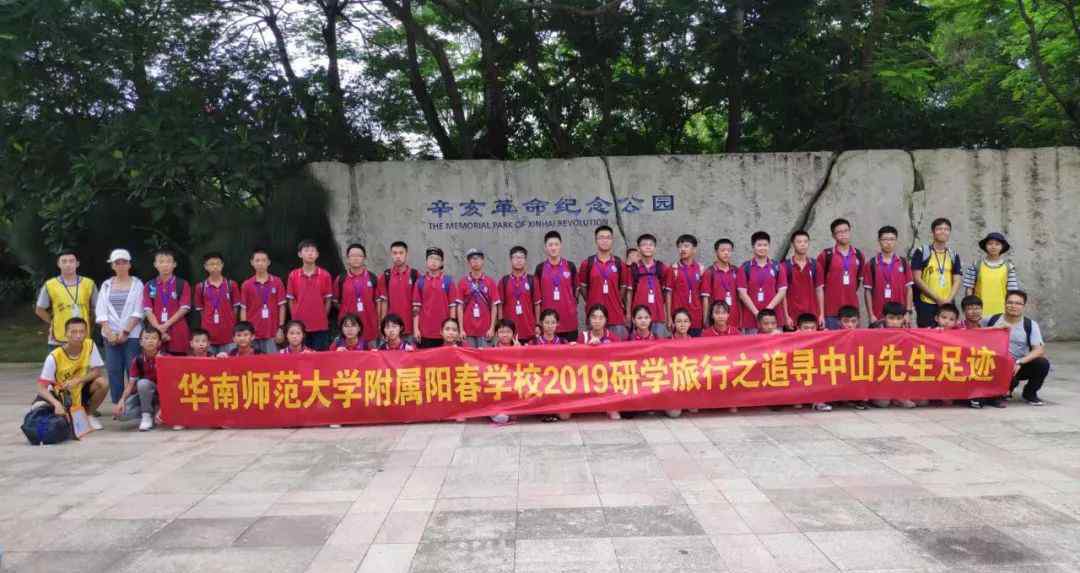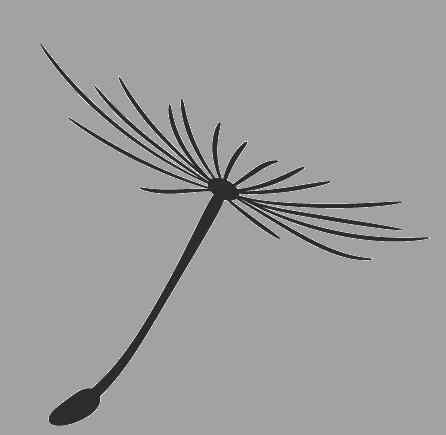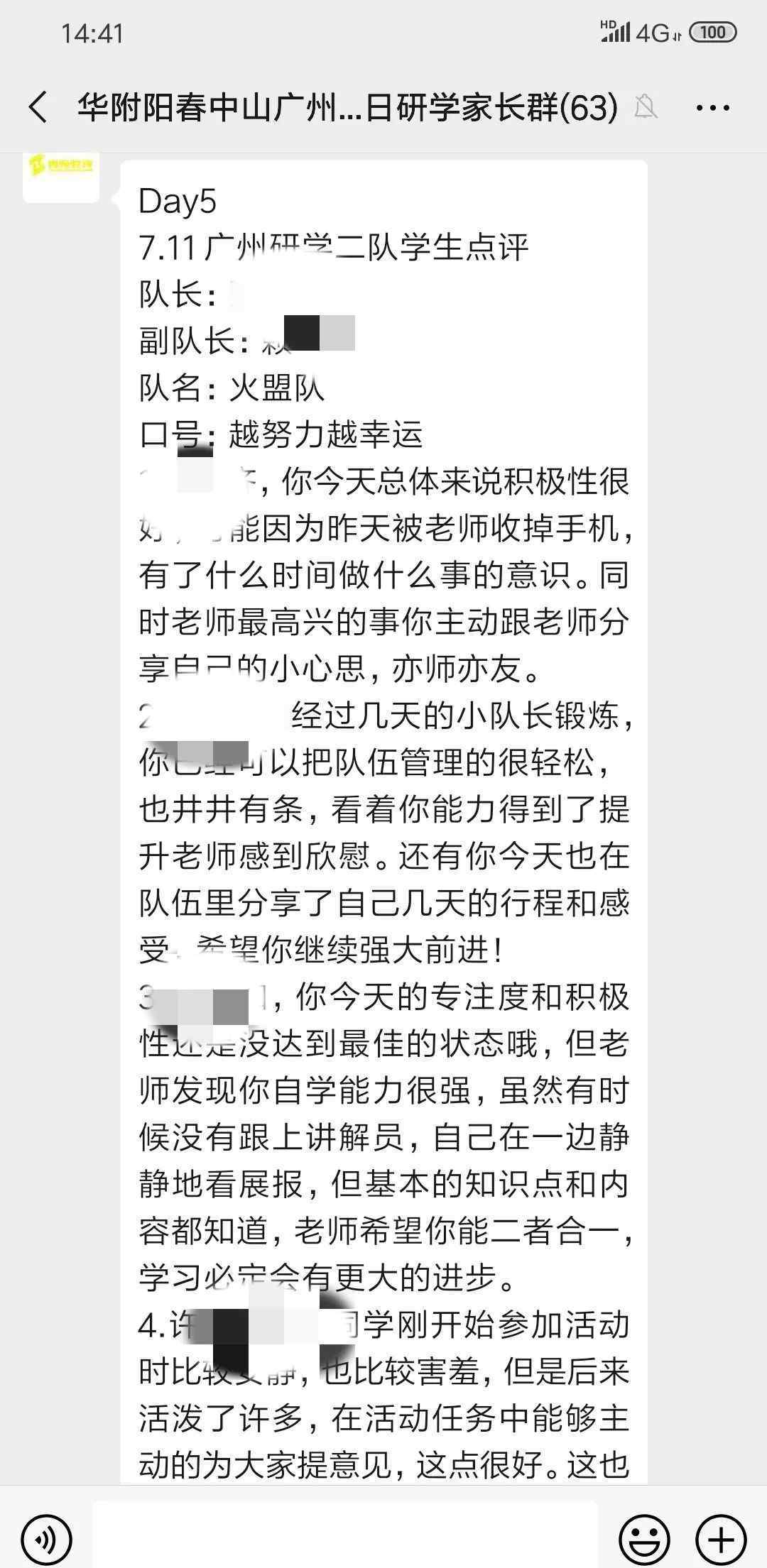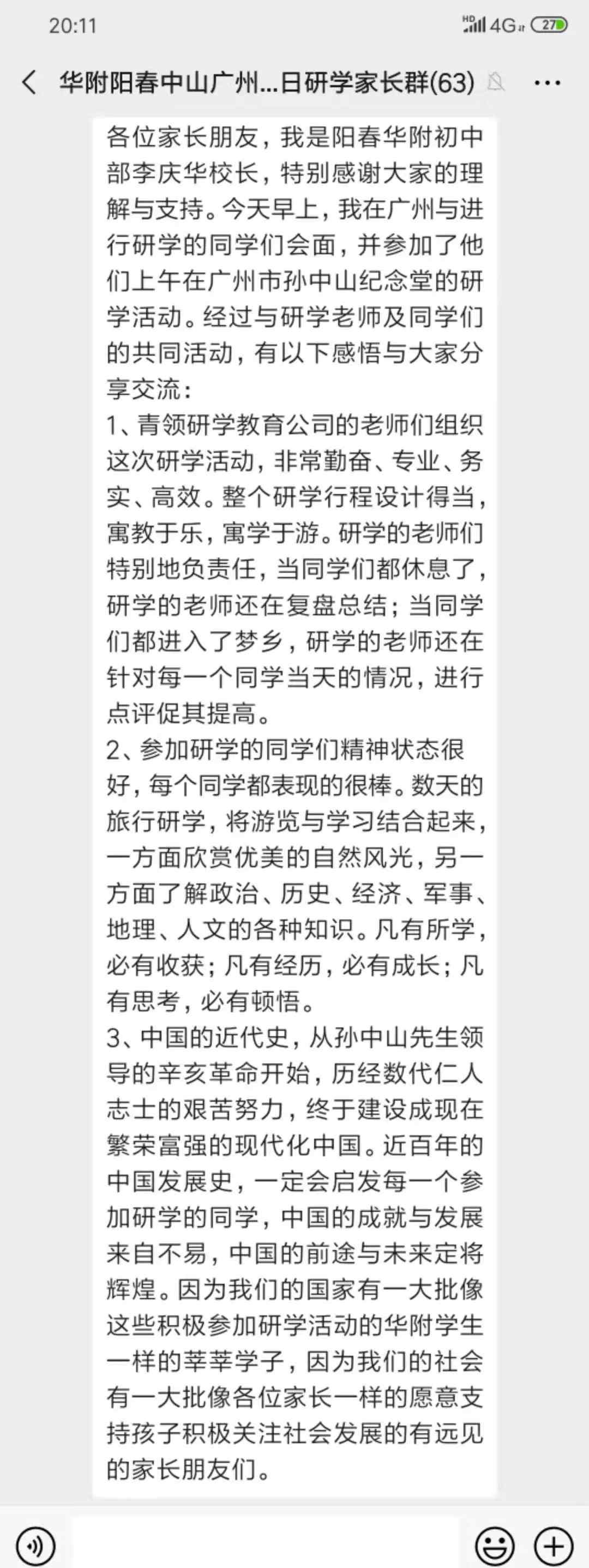导语:中国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专家吴宁坤,于2019年8月10日在美国逝世,享年99岁。在学者余世存的心里,他欠了吴先生一笔债。他觉得,当吴先生的文字、思想、人格还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有义务代表自己去宣传,去照耀潜在的美德之光。如果吴宁坤等人的介绍在大陆华人世界缺失,不仅对我们不公平,也是我们华人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缺失和失落。
在看来,40年来的中国文学具有伤痕、控诉、粗暴、怨恨、狂怒的特征,但像吴先生这样有节制、高尚、愤懑而不愤懑的作品却很少见,他涓涓细流的声音中,有着难得的勇气和不屈的人性之心。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进入了中老年状态,即使有的流下了眼泪,也远远没有到融入泪海的程度。因此,吴先生以百年生命为代价在法庭上作证的“眼泪”更是弥足珍贵。
天下弱于水,强攻强能胜。
—01—
听到吴宁坤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很惊讶。
我欠宁坤先生一笔债。自从几年前看了他的《一滴泪》,我就认定我欠了他一笔债。我也请人去海外买他的书,希望能欣赏他的字和美。后来从孔那里买了一本《接龙》。当然,这只是一份拷贝,但已经足够了。我从他的话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也印证了一些东西。够了。
其实还不够。从高尔泰先生开始,我就向所有同时成就人格的前辈、同行和后人致敬。当他们的言语、思想、性格还处于保密状态,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为了传播潜在美德之光,我觉得有义务去宣传。王鼎钧先生和齐邦远先生的作品流传甚广,没有我这个谋士他们不会有任何损失;但是,如果说高尔泰、吴宁坤等人的引入在中国大陆的世界里是缺失的,那对我们是不公平的,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缺失和失落。
大概几年前,我开始在“万能”网站上寻找关于宁坤先生的消息。我想告诉他,他的一个读者对他感恩戴德,愧疚不已。可惜我在微博、微信、博客上搜了很多次,都很难找到联系他的方法。我看了一些关于宁坤先生的书评,他的学生回忆了他的文章,但是没有线索可以联系到他。年轻的时候,我有一句诗——“整个大而活泼的世界都在等着我的死亡。”汉语世界对宁坤先生等人的态度是一样的。
在我这些年搜集资料的印象中,只有外地人何伟先生是最近认真采访过宁坤先生的少数人之一。何伟在书中写道:“我去吴宁坤的住处时,他回忆说自己曾被监禁,直到1980年才再次见到赵洛瑞。吴宁坤小声说,我们连陈蒙家的名字都没提。那是我最难说的话——说出来会很难受。我知道我说什么都不重要。她没有哭。“她意志坚强,”吴宁坤跟我说,他在监狱的那几年,经常靠背诗发力。“我总是想起杜甫、莎士比亚和迪伦·托马斯,”他说。你知道迪伦·托马斯在他父亲去世时写了什么诗吗?有一句话叫“在断头台上挣扎”,出自“死无葬身之地”。你知道,我曾经在芝加哥听过迪伦·托马斯背诵他自己的诗。“非常感人,”我问吴宁坤有没有和托马斯谈过。吴宁坤说,不,我只是个观众。况且他已经半醉了。他吃了很多苦——我认为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02—
诚然,我不是宁坤先生的普通读者。我和他还是有些缘分的。

穆旦、周郁莨和他的妻子
将近30年前,我刚大学毕业不久,还是穆旦诗歌的读者(今天应该称得上是穆旦最早的粉丝之一)。我和几个好朋友联系了木丹的亲戚朋友。我带着学生去了万安公墓的牡丹园,去了天津南开大学的牡丹园周夫人和梁先生的家。周老师给了我几本牡丹诗集,我还多次去拜访袁可佳先生和杜先生...今天二十出头,在老先生们中间乞讨福利。
在与穆旦的亲友接触中,我其实是去了宁坤先生的家里,当时宁坤先生在国际关系学院的家里。宁坤先生不在家,只有他的妻子李奕锴先生招待我们——李奕锴先生是穆旦的学生。李先生让我在她的留言簿上签上他的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李先生是NTU的高材生,也是宁坤先生的妻子,但在我当时的眼里,她是一个脾气很好,话很多的中年妇女。请她谈谈木丹。她好像说话很猥琐,只是说穆旦是怎么帮他们的,给他们送了一斤蛋糕,半斤糖,粮票。.....许多年以后,听到吴、李在国关的待遇,读到李先生在极端岁月里的坎坷与坚忍,心中曾经无比痛苦。
我也和郭保卫先生有联系,他是穆旦被遗忘的朋友之一。和先生、先生失去联系后(他们都相继出国),我和郭先生之间断断续续地互通邮件。记得郭先生两次问我和宁坤先生有没有联系,有没有需要他介绍的。但是很快,在Google退出大陆之前,我的Google邮箱死了,我和郭先生失去了联系,我和很多朋友的信息凭空而来。

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九夜派诗人冯至
当然,热爱诗歌,聆听历史的好处之一,还是可以无意中遇到历史的碎片,甚至创造历史的瞬间。在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之际,我有幸与孙长江先生和他的女儿孙梅在福建玩耍。我听孙梅说她和穆旦的女儿查媛是好朋友,我想去见见亲戚。我一次又一次地让孙梅向查元老师问好。还有一个场景,我在北京新街口汽车站遇到先生的女儿,我说我是穆旦的读者,郑的女儿问我喜欢哪一句。结果我们都背诵了:我才知道,我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完成我平凡的人生。
—03—
我欠宁坤先生一笔债。除了汉语本身,我也有这些生活原因。当然,“北京当代中国贡献奖”也应该颁给宁坤先生。
在无法表达愧疚的时候,我在朋友间和微信讨论中多次推荐宁坤先生。我甚至跟很多自称在中国文学方面有成就的人说,我应该读读宁坤先生,他对中国文学确实有贡献。40年来的中国文学具有伤痕、指责、粗暴、怨恨、狂怒的特征。但是宁坤先生很少能做到有节制、高尚、生气而不抱怨。我还在一篇官方文章的编者按中说:“吴宁坤先生的作品被中国知识分子所忽视或回避。有人认为他的写作是近百年来中西文学的结晶,给中国文学以新的东西,高于楚辞的哀怨而不伤人不怨。他的节制有杜甫的东西,更有西方的成分。”
去年秋初前后,我开始解读文心国公的《宋正琦》。我的《新宋正琦》里有这样一句话:“帝王之路,应是一宿一。穷的时候可以一个一个看。尔太高有空,宁坤亡泪,而英语时间是一百万以上……”我赌吴、余词条解释,“吴宁坤,江苏扬州人,1920年生,译者,见《一滴泪》,其文融汇中西脉络,但不切,怒而不怨,疑而真。”“余英时,祖籍安徽潜山,1930年出生。他是思想史家。他也是直来直去,不骄不躁,但不出彩。”
—04—
这样介绍宁坤先生,让我觉得需要联系宁坤先生。郭保卫先生失去了联系,我不能指望了。我问过美国的胡晓东先生,他不认识宁坤先生。这让我放弃了。我隔一段时间就在微博微信上搜一下宁坤先生。结果去年10月底,我真的在纽约一个华人老年社区的官方号上发现了宁坤先生生日的消息。原来宁坤先生和李先生住的是旧房,但是宁坤先生已经快100岁了。我赶紧给这个读者很少的公众账号留言,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得到宁坤先生的联系方式。很快,官方号编辑回复说会问老年公寓的牟某先生;很快,官方编辑回复说联系到他了。李奕锴先生说他记得我快30年了。她还记得我,留了他们的电话,让我给他们打电话。
我没有打这个国际电话。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又害怕了,同时也和北大同学有了联系。在微信上和校友李聊天的时候,聊到了宁坤先生。李其实认识宁坤先生的女儿吴。她迅速把茅毅先生的微信推给我,我几乎同时和宁坤先生取得了联系。
说起来,我和毛毅老师曾经是同事,没想到会有这个线索。联系了毛毅老师后,我问候了她的父母的情况。她说她爸爸像个孩子,给我发了她父母的视频,让我放心了很多。我们也聊了很多话题。我问了宁坤先生的生日,并为此献出了生命给毛毅先生。可惜我的微信也死了,我的即时通讯沉入海底。我觉得打捞太难了。直到今天,我仍然和毛毅老师没有联系。
我的债感,我对宁坤先生的寻找,在某些人看来很可笑,但对我来说,永远是真的。正如龚自珍在纪海年间感叹的那样,言语近乎骨肉。正如一位英国网友所说,这是因为我们可以体验到最深层次的共同生活感。
—05—
当我意识到宁坤先生已经100岁了,我知道我无法和他进行实质性的交流。他一生经历的很多事情,我其实都想和他东山再起。例如,李毅杰先生的二哥在他快要饿死的时候给他食物。他拿了吃的,又搜了一遍二哥的口袋,回来的路上拿了二哥的口粮。而他的母亲,多年不见的母亲,最后默默死去...历史巨变时代的个人命运,总是让人说出来写出来就觉得很紧,让人感到无名的悲痛和愤怒和心愿。还有,幽默自嘲的毛卢晓教授,“教授原来是个草包”,难道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hip-hop,有没有和他交心的时刻;另外,他只给冯志先生和卞支林先生写了几笔。他能写更多吗?还有陈先生、、赵先生、、沈从文先生、汪曾祺先生、、钱钟书先生等。,他的老师和朋友,能不能多拓展一下?

吴宁坤、沈从文和张兆和

吴宁坤和汪曾祺
我也想和宁坤老师探讨一下命理学。我在微信里关注了宁坤先生的生日。这些材料都丢了,不过没关系。宁坤先生的名字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他的名字反过来就是中国后宫的住所的名字。坤宁是希望,但事实是坤不安分。坤瓜虽“直大而无弊”,但“龙争虎斗,血变黄”就更悲剧了。宁坤先生一定意识到了。只是他有中西文化中最高尚的精神,他有上帝赋予的精神维度,他不纠结于个人的苦与乐。
我在收集穆旦先生的资料时,就知道宁坤先生的经历。宁坤先生劝穆旦回国,李政道不太同意。穆旦回来是右派,宁坤先生回来是右派。他在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里奋斗,但李政道先生在职业和社会方面取得了成功,没有浪费。宁坤先生对自己的总结是:“我回报,我受苦,我生存。”(我来了,我受苦了,我活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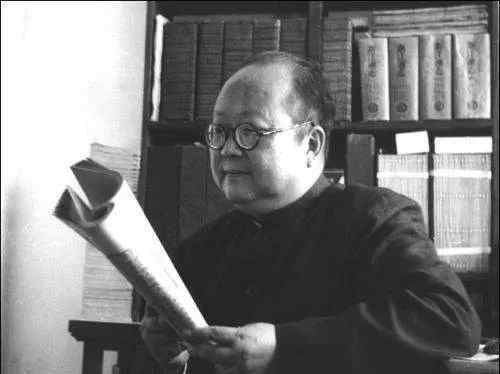
潘光旦,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
宁坤先生的总结和民国学者潘光旦先生的总结差不多。潘光旦对自己的总结是:投降,屈服,生存,屈服。有和宁坤先生一样的话,但有异同。比如潘先生总结的没有自我,而宁坤先生借助凯撒大帝的名言翻新,其中有一个必然的“自我”。同样的,不管他们有没有我,他们都已经远离了一段业力历史,或者说他们已经超越了这段历史。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绝大多数现当代人都在自己的历史中奋斗。有的人甚至以打架为乐,但潘先生和宁坤先生坚守自我,与黑暗的历史割裂开来。
余英时先生说,宁坤先生的《一滴泪》是中国数百万知识分子中的“一滴泪”。但这部《一滴泪》也忠实地反映了“泪之海”的整体情况,也可以说是具体而细微。然而,余英时先生关于《一滴眼泪》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宁坤先生的作品几乎是屈指可数的特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沉了下来。经过屈辱和摧残,他们进入了中老年状态,不是变老就是变老,不是油腻就是温柔。余先生自己说:“从1978年起,我认识了许多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包括过去在哲学、历史和文学方面杰出的知识分子。短暂的交谈后,我发现他们在精神世界已经到了无所适从的状态。.....这让我不得不佩服宁坤先生伟大而顽强的精神反抗,能经得起几十年铺天盖地的废话。”
—06—
宁坤先生真的很特别。他躁动不安,而这位熟悉西方文学的译者,似乎注定不仅要为我们贡献华丽的翻译作品,还要孕育出东西方文学的奇妙结合。然而草造于天而不安份,辇如辇,马如纲,血泪如涟。这个奇妙的儿子的诞生,充满了痛苦、煎熬和泪水。
宁坤先生不会屈服于这种煎熬。当几乎所有人都真诚地或方便地谈论和解与建设时,只有少数人,如宁坤先生,有异议。如果有网友评论,“吴宁坤最著名的译本大概就是迪伦·托马斯的译本了,尴尬,不屈,愤怒。像一把锤子,一把锤子把迪伦的诗钉进中国读者的心里。”宁坤先生的翻译其实是钉在了中国世界的心脏。他翻译道:“不要轻轻进入那个良夜,老人应该在夕阳下燃烧咆哮;愤怒,对光消失的愤怒。”

韦君宜的《伤逝》,周一良的《毕竟是读书人》,季羡林的《牛棚杂记》
宁坤先生的《一滴泪》比起《痛苦思想的记录》《毕竟是个学者》《牛棚里的杂记》等许多知识分子值得称道的作品来说,还是很特别的。余英时先生认为我们知识分子有眼泪,这给了我们太多的荣誉。即使有一些知识分子流泪,他们也远远没有融入泪的海洋。
宁坤先生的“一滴眼泪”是如此珍贵,它是一个纯真孩子的眼泪,是现代个人在上帝面前的控诉和诉求。不管它的社区多么招摇,多么招摇,不管某些知识同行多么光鲜时尚,这个“眼泪”的分量甚至比社区的汪洋大海还要重要。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和警告的那样,用一个婴儿的眼泪换取天堂的门票是不可接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问,如果无辜的孩子需要为和平、我们的幸福、永恒的和谐和他们坚实的基础流泪,我们能找到一个好的理由吗?陀自己的回答是:这一滴眼泪,不能宣告任何进步,任何革命,甚至战争的无罪。它们永远不值得一滴眼泪。只是一滴眼泪...
现在,宁坤先生已经在法庭上,以一百年的生命为代价,为这“眼泪”作证。他像水一样虚弱,但他有能力通过石头解决棘手的问题。天下弱于水,强攻强能胜。是的,宁坤先生涓涓细流的声音里有着难得的勇气和不屈的心。这就是水的意义。这对你有好处。
余英时先生注意到并同意宁坤先生对何伟说的话。如果没有那段时间,我可能会成为一名更成功的学者,也许我会写几部关于英美文学的专著。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关于这方面的专门书籍已经很多了。《一滴泪》可能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
这是弱水的救赎,对于苦难的人生,对于文学的人生,都是一件高尚的事情。愿宁坤先生回到祖国大陆的山川,在天堂里享受和平。
【作者简介】诗人、学者、作家余世存被誉为“当代中国思想影响最大、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最强的思想家之一”。
版权声明:《洞察》是凤凰文化的原创栏目。所有手稿都是独家授权的,未经允许不得复制。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1.《一百滴眼泪 巫宁坤走了,上帝落下了一滴眼泪|洞见》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一百滴眼泪 巫宁坤走了,上帝落下了一滴眼泪|洞见》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guoji/10766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