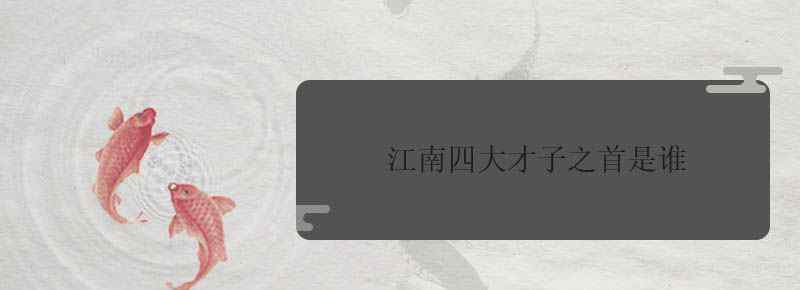柴龙
思明搬到张孝友,从童年记忆中画了一幅“南翔旧梦图”的轴线:面向街上的祖屋,住在枕河边;梅月门巷,酒楼交错;邻水楼台,花云;年轻的邻居,竹马爱好者,篷船,石桥,社戏,马头墙,图书馆建筑,等等。
所有的江南印记,所有的江南风光,所有的江南味道,所有的江南风华,在宁波都可以成对的数出来。如果你来这里,你可以理解。
从《南翔旧梦》的一个轴上,瞥见了黄梅田的小品《下午的梅雨和梅花》,让人想起了宁波的“黄美姬”和“糟糕的日子”。
江南多雨,“黄梅雨”更具特色。在《千首诗》中,我读过赵师秀、戴复古和几首描写黄梅雨的诗。说“黄梅季家家下雨”,戴说“熟梅半阴半阳”,曾云说“梅黄即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年纪大了就懂一二了。梅雨因其出现的早晚、持续时间和降雨量的不同,可分为早梅、晚梅、空梅和丰梅。三人的梅雨诗呈现多角度,但并不矛盾。
“自由飞花轻如梦,无边丝雨薄如愁”,这是古人的悲哀;“少年听雨唱楼上,红烛昏厥”是雨季的情感。黄梅时节,是江南一首悠长而阴郁的韵文。下了几天雨,苔藓沿着床脚长了起来,令人担忧,眉头打结,却又无可奈何。
雨多了,空气就湿了。总是懒得打理的器皿悄然生出霉味。红枣、黑木耳、蘑菇、柜子里的衣服、被子、书架上的书都会发霉。黄梅田,日日潮,夜愁夜愁,密密麻麻的雨网笼罩着宁波人,似乎有一种黏糊糊的说不出的压抑。
只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来到门口,梅雨似乎要破了,这就是在雨中停留的节奏。在饭的附近,还好罐子里有咸雪里蕻,草窝里有一些家鸡蛋。炒一碟咸菜鸡蛋,熬一碗咸薯汤,蒸点腊肉香肠,去农堂口熟食店剁半只三黄鸡,舀半碗糯米酒,就成了不错的家宴。风雨过后,风平浪静,告辞感谢,主客友谊加深。
有趣的是,下雨天,宁波人见面打招呼不再是“老王,吃饭了吗?”而是“梅花什么时候出来?你知道怎么切吗?”
梅花一出,阳光高照,接近炎夏时节。家家户户,老少都开始晒霉,带着过年的兴奋:支起晒杆,晒衣服,晒鞋子;铺开竹匾和晒干的黄花菜、红枣、桂圆;小文人纷纷干书干书画...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清云的喜悦。众所周知,未来会有桑拿日等着他们。想到这里,又觉得梅雨真的让人留恋。
黄梅田当然不是一味的恶。黄梅天的雨时密时疏。雨点冲刷天地,打在蓝瓦上,发出清脆的叮咚声;雨从屋檐下落下来,整夜哗哗淌着,就像一首田园诗般的交响曲,在我年轻的时候常常伴我入眠。
那些甜美的雨滴屋檐声,不撩拨烟亭清风,不触云桥醉态,如梦如幻,在下一个舞台前,点点滴滴直到天明。
心情好的话,还可以放雨香蕉当背景音乐。窝在家里,看书,把雨季变成雨中的休闲歌。
以前看过周作人的《苦雨》。据我猜测,一定是江南梅雨。虽然书名以“Ku”为前缀,但它是浙东黄梅季节的独特趣味。周在文章中提到“卧篷船,听雨声”,雨滴落在篷顶,落在河上,夹杂着青蛙和橹子,难以言喻。
搬进大楼后,城市里的小巷越来越少,老房子一天天地消失,雨滴和屋檐的声音久久听不见。搬进高楼,我们的生活悬浮在离地面很远的空里。别说下雨,就是霉变的现场,好多年没见了。
唉,那些普通的老巷子,下雨的小巷,我们身边还剩下多少?
1.《梅子黄时 梅子黄时家家雨》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梅子黄时 梅子黄时家家雨》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guoji/1216590.html

 三、2019届研究生招生人数
三、2019届研究生招生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