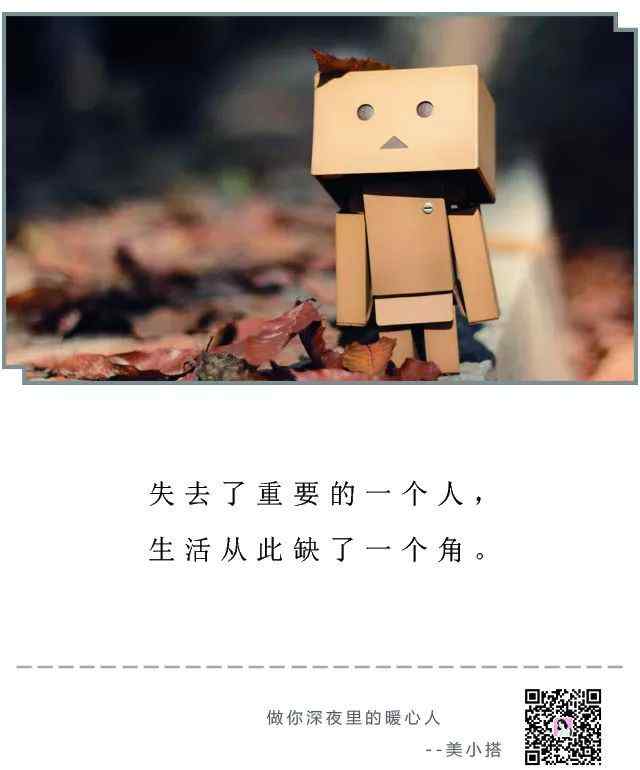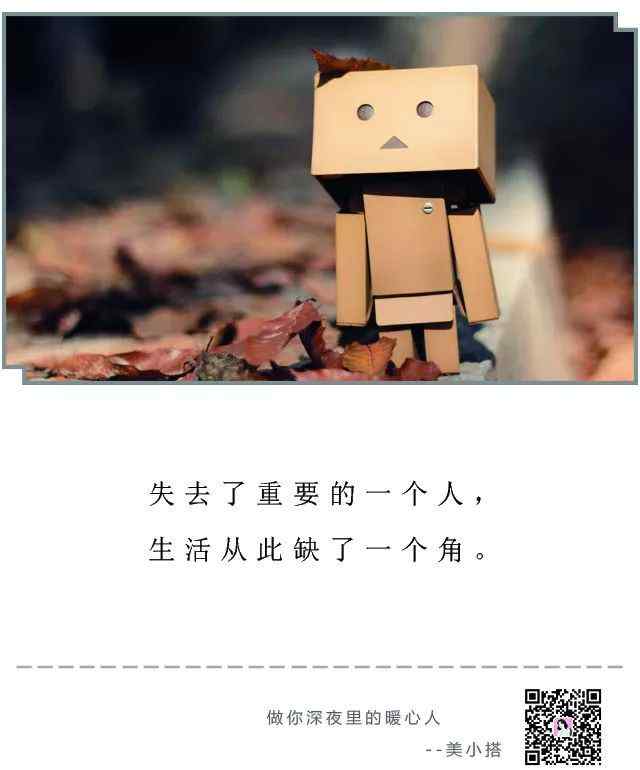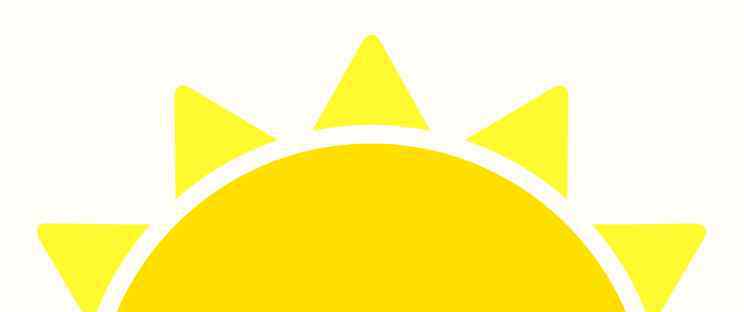关注我,过上有文学相伴的生活
黑暗中的爱与光
一个
一个
我少年时代的所有黑暗都来自死亡。
1992年夏天,我39岁的父亲死于车祸。我十二岁,我妹妹九岁。20多年来,我对父亲的死只字未提。我没有勇气去反思那个黑暗的时代,我也不想承认这个命运拟定的不公平条约。很久以来,我觉得我的心被死亡的恶作剧戳了一个大洞,生命的温暖从那个洞里流走了。直到今天,当我成为另一个人的父亲,当我的命运渐渐解脱的时候,我才敢用言语去触碰92年的夏天。
生活突然暗淡,黑夜来临,一盏又长又亮的灯永远熄灭,我们的家突然陷入黑暗。父亲这个角色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对我们来说似乎更重要。他几乎是全家人唯一的依靠。我们衣食的来源,我们童年时家庭的优越感,我们得到的尊重和礼遇,大部分来自父亲。早在四年前,父亲就把我们从深山里的村子带走,在这个偏僻城市的郊区开了一家小诊所。就像新移植的植物,我们在移动手脚,在新的地方生根。如果他父亲的剑走偏了,他在自学中学会了各种疗法,并试图将中草药和西药结合起来解决各种疑难杂症,这几乎成了一个传说。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那一刻,死亡暴力地将他带离了这个世界。
这场灾难将平静的生命之舟吹向命运的惊涛骇浪。妈妈不会读书,也不会工作,但什么都要一个人扛。她不顾身心的痛苦,一边哭一边继续“生火做饭”,让余烬里像火星一样的一点点温暖延续下去。当时,她的母亲也是车祸受害者之一。她和父亲一起坐三轮小货车到了市汽车站,换了一辆长途汽车。她回到家乡处理她哥哥不幸的婚姻。在黎明的昏黄灯光下,一辆大卡车像一部大片一样昏昏沉沉地从内室出来,撞上了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坐在中间的三轮小货车。母亲在车祸中打掉了三颗牙,面部肌肉严重受损。然而,她自己离开了医院,照顾她父亲的事情。过几天她就去村里的草席厂打工,在漫天的灰尘里挣点生活费,帮我们熬过漫长的时光。
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没有自己的房子和亲人。亲戚都在另一个城市,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叔叔叔叔...相距甚远。最多过年前后他们会来看我们,然后各自奔回自己的生活。他们一走,我和姐姐就不笑了。我知道我今天用的“笑”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92年夏天是一个很重的分割线,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什么笑声。如果我们在开玩笑,我们笑得很谦虚,大多数人脸上都有一点笑的迹象。在一个微笑能够充分发光和发出声音之前,我们很可能会有“父亲走了”的想法在我们心中升起,我们会匆忙停止笑。我们的心绷得紧紧的,悲伤以一种铺天盖地的方式占据着生活,仿佛想到幸福就可耻。
我妈随时随地都会哭。别人提到我父亲的名字,都说徐医生太坏了。如果他还在,我孩子的病就不会这么折腾了,我妈也抹不掉眼泪了;当草席厂仓库负责人指责她一次拿三捆灯心草,而别人一次拿一捆的时候,想多干点活的妈妈忍不住哭了;每年除夕,妈妈都会郑重的准备一桌快餐,安慰在另一个世界的爸爸。我妈蹲在门边烧纸钱,喃喃地唤起她爸的名字。当她转过身时,她又开始哭了...我开始产生一种长久的错觉,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它呈现出深灰色的基调,里面阴冷潮湿,包裹着哭声、泪水和无尽的悲伤。
我妈在家哭的时候,我和妹妹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她的哭声像冷风一样撕心裂肺。我妈在外面哭,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痛苦,还有那种痛苦中的很多尴尬。很多年后,生活一再告诉我们,自尊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不相关的人掩饰伤疤,擦去眼泪,显示尊严。妈妈可能不懂这个道理。也许失去丈夫的痛苦比失去父亲的痛苦更严重。她的哭声很难控制。
那几年最怕两个节日,春节和清明节。大年三十,我妈的眼泪比别人的笑都多。我们在我妈的眼泪里吃着简单的年夜饭。屋外的鞭炮声在噼啪作响,夜晚的烟花在绽放空,但这一切的激动在我们看来都显得格外的寒冷和孤独空,仿佛总在提醒我们生活中有多么巨大的瑕疵。除夕那天,我和姐姐想放烟花,但是妈妈不让我们把钱花在没用的东西上。有一次因为买了几个烟花,和我妈大吵了一架。记得大年三十下班,买了一大堆鞭炮烟花,我和姐姐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一个个点着了空,仿佛在为过去漫长时光的孤独而愤怒。那时候清明节,别说多凄凉多痛苦了,我们去父亲的坟前,母亲还要扶着碑哭,她的哭声在墓地里盘旋空,传到很远的地方,引来其他扫墓的人侧目。在大众眼中,一种强烈的羞耻感正在蔓延,无休止地笼罩着我。
二
一排局促的人去了老小平家,过了塔诺贝的马路。有几个搁置村委会杂物的,一个是村里的小诊所,一个是住人的。这是我们一家三口,我们就像三只飞来这里寄居的燕子。父亲去世后,村委会允许我们住在原小诊所旁边的闲置空房子里。
小平的房子不到20平米,小到只有一门一窗,小到只能装三个人的尸体,装不下更多蓬松的期待。有一张漆成蓝色的铁床,一张木床,还有一个低矮的柜子。这些从郊区拆的老房子里淘汰下来的旧家居用品,一次次被妈妈冲走,变成了我们的家具。乍一看,燃气灶是靠在两堆灰砖上,算是厨房。还有一台21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张从跳蚤市场买来的圆形木桌,桌面很多地方开裂,像是被洪水冲刷出来的坑坑洼洼的地面。再加上四个方凳,一个小板凳,两个老家带的大木箱,一个塑料衣柜。这是所有的家当,被别人用来进入我们的生活,支撑着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就好像我们家是从别人过时的生活中借来的一样。
我的青春就是从这个小房间开始的。进入初中后,除了上学,几乎剩下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贫穷、不幸、人情差、不安全感强,形成多变的季风,随时会侵袭小平家。我成了树荫下的一棵小树,变得孤独、寂寞、沉默。
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拿着一本薄薄的毕业生登记表,久久地看着“爸爸”这一栏。后来班主任让我帮他整理填写全班学生登记卡。看到学生登记卡上“父亲”一栏里老师写的“死了”两个字,我拿着橡皮擦悄悄擦掉这两个字,制造出父亲还存在的假象。我不想让中学老师和同学发现这个由来已久的事实。
与此同时,青春期像漫长的雨季一样,以黑暗、暴躁、不可预测的方式溢出了我。我越来越为自己粗声粗气的嗓音,嘴唇上翘起的胡须,家庭的境遇感到羞愧。但是小平楼就站在路边,我很多同学进城上学都要骑着穿过去。
门窗打开,房间里的一切,哪怕是匆匆骑着自行车,也能一目了然。这不是我的猜想,这是我在一个空荡的晚上,铺开一辆自行车,反复模拟路过我家门口时测试出来的。所以门总是半开半关,唯一一扇面向马路的窗户也被一个淡浅色的小碎花窗帘紧紧的遮住,微弱的光线透过小窗帘。让我担心的是,我开门的时候撞到了班里漂亮的女生撞门,或者回家的时候几个女同学就在我身后叽叽喳喳看着我推着自行车进了这个简陋的家。有时候在我家附近,感觉身后有熟悉的人,就故意放慢骑行的步伐,等他们的自行车开走了,我才偷偷进门。就像一个偷偷摸摸的小偷一样。
青春期临近期间,放学后,除了在田野的暮色中漫无目的的游荡,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躲起来。房间里开着一盏20瓦的灯,我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一个略高的小方凳成了写字的“书桌”。没有被那么多人看着,我的心在胸前牢牢地停了下来。
三
必须有光、雨和露水,以及从体内生长出来的救赎力量。挣脱藩篱,生出翅膀,飞越无尽的寒冷与阴霾。
十三岁暑假的一天,在小屋不远处的一个老教师家的床下,发现了一本旧书。确切地说,它不是一本书,封面掉了,内页不见了,几乎剩下一半。如果有一个人对应这本书,他只能是一个被抛弃的流浪汉,蓬头垢面,一丝不挂。光秃秃的书页是黑色的,上面覆盖着丝,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灰。
我把书拿到太阳底下打了一顿,这些年灰尘都飞走了,仿佛是为了打扰附着在上面的过去。幸运的是,文本仍然清晰地留在发黄的纸上。我已经忘了读哪一页,第一句话是怎么进入我的眼睛的。就像生活中遇到的一些贵人,他们已经忘记了初次见面时的样子和样子。但正是这本半旧的书触动了青少年冰冷的心。旧纸上的黑色汉字有着炽烈的体温,像是一团小炭火,让包裹在灵魂里的冰悄悄松开。
我看到火车上飞着一群游击队,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这群人脉很广的游击队给人生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似乎落在了湖面上,脑海里闪过一个细细的倒影。但当一个故事进入阴暗卑微的日常生活,就会产生看不见的涟漪。几乎是默默的,这几个页间的人仿佛向我走来,站在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孤独队列里。我好像一下子有了一群亲戚。我的叔叔阿姨们都有很厉害的臂膀,都无所畏惧。我把这半本书放在怀里,当我走到可怕的地方时,我应该特别带着它,这样它才能让我振作起来。我妈带我去法院要求对我爸的死进行赔偿。司机对事故负有全部责任,但我得不到任何可怜的赔偿。黑暗的办公室里,法庭上一个胖胖的执行院长拍着办公桌喊道:“滚,滚!”他的声音在走廊里盘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把他妈妈推向门口。我抬头瞥了他居高临下的脸一眼,一个巨大的影子抓住了我,我浑身发抖,怕他一巴掌拍下去。我真的很想帮妈妈跑步,但是后来我的指尖碰到了这本旧书的这一半。我攥紧拳头让自己冷静下来,对着法官喊了句:“叔叔,这是人民法院。我们不是坏人。我们在这里寻求帮助。法院是为人民服务的。”喊完那句话我忘了法官的表情。但是那天和妈妈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我没有哭,也没有更多的恐惧跟着。我怀里抱着一本书,心里有一群英雄故事,所以我不害怕。
这样,这本书还是有宿命感的。好像是上天精心准备的礼物。上帝可能在一次野蛮而傲慢的攻击后感到了同情。只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他伤害了你,给你准备了药。无论如何,这本半旧的书不经意间就来了,让我恍惚中意识到,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物质存在——课本之外的书。
纸上写的字就像一群充满灵性的萤火虫。它们在浓密黑暗的丛林中漂流和汇聚,闪烁着无尽的光芒。挣扎的人们顺着这一线光,一步一步向前走,绕过一个山谷,走过一片沼泽,停在一个开阔的悬崖上。抬头望去,深夜里空布满了明亮的星星。你要相信,只有上帝的旨意,你才能走到这空旷的地方,看到最明亮的星光。一些赎回伴随着书籍和文字。神说:这是一个漫长的疗伤过程,必须经历一生。
四
但是不会有很多书可以看。就像踮着脚在裂缝里接触到一缕阳光,或者在沙漠里挖一口清泉,因为稀缺而更有价值。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去的最远的地方大概是七八公里外的一个小镇。当时,在一个小镇的商店里有一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几本书。每当我走过这个小玻璃柜时,我的脚步就被钩住了。除非你想买,否则书是不允许提前拿出来预览的。柜台后面的售货员黑着脸,不屑地看着顾客。即便如此,我还是忍不住看了看柜台,对着里面稀稀拉拉的书投去了一个饥渴的眼神。它看起来一定像一个饥饿的人在看面包店新烤的面包。
第一次走进城市里的一家大书店,站在一排排书架之间,光线并不明亮,书架形成的影子落在地上,书在半明半暗中散发出一种安静迷人的气息。我瞬间就被书的宏大、厚重、无处不在的宁静和庄重吸引住了。像一个常年生活在热带的人一样,他第一次来到了雪原,惊呆了,追不上雪。
去书店,去书店,成了少年心中朝圣般的心愿。每当我有机会进城,我的脚就想去有书的地方。但是书店很远。我不知道怎么去那里。我自己还没能踏上从农村到城市的道路。每次走进书店,我似乎都有些好运。远方的亲戚来看我们,把我们带到城市的街道上。我们走着走着,来到了老城区的旧书店。我们照例一头扎进去,不肯退出。我知道进书店不代表能买到称心如意的书。书是除了食物和冷衣服以外的东西。我妈想让我们读好书,但是她认的书都是课本。她认为“读书”的全部意义在于“读课本”。这样,去书店只能是一种内心的仪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然看到一个少年在书架间徘徊。他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翻开一页,静静地读了几行,合上书,用手摩挲着书的封面,然后把书拿在手里,反复掂量了一遍,又翻了一遍,羞涩地看了一眼封底的价格。他把书放回书架,在书前站了很久,像一个好朋友一样告别了书架上的书。然后,他转向另一个书架,简单地取下一本较厚的书,这是一本镀金封面的藏书家的书,手里很重,木质很深。当他打开书时,他听到自己的心怦怦直跳。他闭上眼睛,把书放在胸前,贴在心口。然后,他没有把书翻过来看封底的价格,而是迅速地把它推回到书架上的空书桌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书店的门。
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他奢侈的买了一大摞书。上了中学之后,才有人把一个男人介绍给他妈。起初,这个少年无法接受另一个人来代替他的父亲。经过长时间的冲突,母亲也因为儿子的情绪拒绝了几个人。后来,这个人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他看起来很诚实,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人,但只有他的诚实和单纯大概消除了那么多不好的感情。认识母亲一段时间后,他主动提出带全家逛逛这座城市。小伙子很自然地踱进书店,他说想买什么书就挑什么书,妈妈站在旁边,没有反对的意思。他扑到书架上,鼓起勇气,从书架上拿出他从来不敢期待的书。一套四列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本厚如墙砖的《泰戈尔小说选集》,还有一本平装本《安娜·卡列宁》...总之都是很重的书,一共八九本,真的是童年最丰富的购书经历。
他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书店,每次都在标有“文学”的巨大区域里徘徊。那些精彩的故事和淡淡的诗句,建造了一个梦幻的庭院。他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走着,在每个转弯处都藏着惊喜。他看到了古老的圆柱和美丽的窗户。他在黑檐下透过身体听着几千年前的雨声。他继续往前走,站在院子里。一天,美丽的夕阳铺展开来。是傍晚夕阳织成的锦缎。
九月,我十四岁的时候,遇到了第一个文学老师。在语文课上,他讲了魏晋文人的故事,[/k0/]。他用优雅的行书把李白和苏轼的诗“泼”在黑板上。他还深情地读了李清照、舒婷、朱自清的《匆匆》和余光中的《听冷雨》。一开始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举动,但当我们回望时间之岸,这个简单的举动是最不寻常的,又是一次上帝动了恻隐之心。在那些汉语课上,古代汉字散发出迷人的香味。十四岁那年,我被附着在文字上的永恒之美俘获,蹑手蹑脚地离开了魂宫的另一扇沉重的门。在那之后,书籍以一种更加坚定和不可抗拒的诱惑向我敞开了大门。那时的书已经不是书了,而是地球上打开的窗户。
语文老师在家里藏了一个大书架。他开始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借给我。书从老师的书房到我简陋的家。他们是我家最尊贵的客人。
五
我渐渐变了,我们家也渐渐变了。随着书的到来,我并不觉得这个不到20平米的地方只有可怜和悲哀。还放了其他的内容,比如很多高尚的灵魂,比如很多轻松的诗,比如一些光明蓬松的愿望。小平家不再黑白分明,不再只是哭泣和悲伤。小平的房子开始有了颜色,天空的瓦蓝空,向日葵地的金黄,地平线上延伸出新绿。即使在更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似乎也有办法应对,因为有一个人能读书,他的心就像云彩和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轻,他能轻松战胜沉重的现实。
一年夏天,一场台风带来了大雨。村子里的河水泛滥,道路和田地都被淹没了。我们在家里的床垫上放了三块砖。不到半个小时,水就爬过了三块砖头和我们的小腿,几乎到了膝盖,大雨也停了。我们涉入水中,在床上坐下。床脚已经被淹没了。坐在床上就像坐在小驳船上。但我们并不难过。我拿着从老师那里借来的普希金的诗,翻到《如果生活欺骗了你》这一页。我给妹妹念了一首诗:“如果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不要生气/不满足的时候克制一下自己/相信吧,快乐的一天就要来了……”当我读这首诗时,我似乎真的看到了快乐的一天,那是胖乎乎的
我渐渐变了。因为读的书,我变得自信了。好像很少觉得一个人的魅力是由家庭背景决定的。我有了新的认识:一个人的魅力是由他读过的书决定的。当我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女同学听的时候,看到她们笑起来那么友好,笑容里也没有偏见,就开始抬起头,平静的对着女生笑。当我在语文课上大声朗读一篇感人的文章时,听到老师如此真诚的赞美,心里充满了自豪。当我把老师的名著装在书包里带回我那小小简陋的家时,我仿佛带回了一个沉默而忠实的朋友。他们从不说话,但房间里有明显的温暖迹象。一部托尔斯泰的书,一部雨果的书,或者一部海明威的书,这些留着很多胡子的老人都是严肃可爱的,他们的书都被搁置在破旧开裂的旧餐桌上。这间昏暗的空房间很不寻常,即使在深冬,似乎也有小火在跳动。
我渐渐的变了,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再是一团婆娑的雨云。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书里的字有这么动人的力量,但是汉字真的像药丸。我把泰戈尔的句子写在纸上,贴在床头。每天早上醒来,泰戈尔都会在晨光中在我耳边重复那句话:“错过太阳就哭,错过星星就哭。”你无法知道这句话默默的提出了多少勇气和力量。我反复咀嚼,几乎每次咀嚼都能止住悲伤。
因为书,小平的房子变得宽敞了,我的心胸也变得开阔了。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重新审视了母亲,才发现母亲带给我们的只是伤心的屈辱。她带来了那么多无微不至的保护。那些作家一遍又一遍写出来的她的爱情,不就是一股甜甜的味道吗?她的爱情比他们写的爱情更具体,更真实,更不平凡!经过这个发现,我才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人,不仅是我遇到的旧书前半部分的人和我站在一起,还有那么多老师,那么多充满美好想法的人,还有更多其他书的人和我站在一起。我的队列越来越大,我总能从小平家排到很远的地方。
书带来了那么多无声的变化,我每天踮起脚尖迎接。
六
无意中来的书,都像匆匆相遇的路人。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离开我的世界,重新回到老师的书房。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我的失望不仅仅是因为书,更是因为书中精妙的笔法和句子,以及那些句子带给灵魂的悸动。就像舍不得离开一个远方的亲人,比如姨妈,每次来看我们,她走了,我们都会偷偷难过几天。那种不情愿是小而具体的。我的不情愿,是姨妈的询问的话语,是她的微笑,还是她用手摸我脸时的温柔温暖。我的失望点从书到书的里面,到书里的人,到书里流淌的温暖和光。
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为什么不把书的内容摘录一部分呢?这就留下了另一种形式的书。刚开始只是把作品节选抄在软面上,挑了一本之后就出现了新的想法:要选一本好一点的书,然后再对内容进行细分分类。就这样,我爱上了买笔记本,在每周十二块钱的午餐费里省下三块钱,一个月买一个漂亮的笔记本。当我得到一些笔记本时,我让每个笔记本负责存储一个内容。把小说片段放进一个绿色封面的大本子里。这个笔记本的内页是蓝条和横格。我以谨慎的态度挑出伟大作家写的句子。就像那些秋天过后在田里捡稻穗的人一样,笔记本有稻香。把古典诗词放进一个狭长的蓝灰色笔记本里,那些挂在很久很久的树枝上的诗句,就像古老的种子,被重新采摘,埋在一张新的写着恭敬汉字的纸上,意味着春风又来了。普希金、拜伦、雪莱、阿赫马托娃和中国的戴望舒、朱湘、顾城都在昏暗的灯光下行走。他们抒情而通透的短诗句,如草间满露,让少年看到了爱情的美好与忧伤,也看到了汉语长短句跳跃的微妙节奏。
最初的笔记很快演变成抄写书籍。当泰戈尔的《鸟》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很激动。挑一句,又觉得错过一句可惜。我想出了简单地抄下全部诗集的主意。好在《飞鸟》不长。它的短诗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像轻鸟在孩子的窗前盘旋。鸟儿带来了春天的消息。
然后我转录了泰戈尔的《渡口》和《吉檀迦利》,然后转录了《园丁》、《新月》、《随想》、《又来了》和《上周》...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坐在那张小板凳上,成为了最敬业的抄写员。忘了时间是怎么流动的,忘了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悄悄变化的。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除了学校生活和学业成绩,剩下的就只有一直背单词的项目了。
春天,小平家外的田野里,大面积的油菜花开了,金花的潮水一般向远方的天空奔涌空。我在小平房间昏暗的灯光下抄书,页间的诗词文章在一片明亮的行军中点亮。夏天,太阳烤焦了大地,小平的房间闷热难当。一个小盒子风扇吹着信纸,汗水从他的额头渗出。秋天,夕阳跳跃在芦苇的白穗上,晚稻的香气透门而入。我把自己埋在小方凳里,纸上的果实在秋风中成熟了。我想象自己是一个采摘水果的农民。冬天,寒风在村口呜咽了一夜,像一个悲伤的人。一点温暖的光围绕着小公寓。我缩着脖子,用冰冷的手指捡起汉字。这件事贯穿了一个少年的全部日常生活,贯穿了一年的全部时间。
收纳工作越来越复杂,我成了一个占有欲无限的男人,像国王对江山的迷恋,商人对金币的迷恋。我对所有出现的单词都很着迷。它们可能是豪放的,优雅的,像沙漠中的沙子一样广阔的,也可能是像江南的烟雨一样模糊的...每一种角色都在吸引着我,治愈着我。
当一个人被这样一个广阔的世界所吸引时,他就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局促而寒冷的生活了,蜗牛壳大小的小平屋也不再是一个尴尬的避难洞穴了。因为一本书接一本书,潮湿的小平屋渐渐亮起来,也因为一本书接一本书,那些风风雨雨的岁月被各种形式的文字吸收。他的身体生活在一个狭窄潮湿的地方,而他的灵魂生活在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他在那个世界徘徊了很久,书上的字是用来读的,书上的字也是食物,小麦,大米,高粱,土豆,也是用来吃的。
他贪婪地咀嚼着这些汉字,仿佛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在吞食谷物。他吞下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食物,吞下了作家们用心良苦准备的各种味道,尝到了人间的苦与苦……这些食物进入了他的胃,进入了他的血液,进入了他的骨骼。这些看不见的食物正在逐渐改变脆弱的心灵,它们提供各种营养,它们提供美丽和勇气,它们提供梦想所需的物质,它们提供一种抵抗病毒的力量。
年轻人内心的粗糙,愤怒,对命运的憎恨,对贫穷的无奈...不再像以前那么大,也不再大到足以把他的整个灵魂带进去。他的灵魂开始得到光明,水蒸气逐渐蒸发,它摆脱了臃肿和沉重,从寒冷和黑暗的现实的尴尬中跳了出来,他得到了安慰。
七
如果没有书,命运会把一个不幸的少年吞没在怎样的荒谬之中?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的胸口充满了沉重,充满了痛苦。我找不到出口来散发世界的恶意。我怎么可能走到一条光明的路?怎样才能拥有生活的轻灵?因为书,灵魂的殿堂里有爱和光,有包容和接纳。在阳光下,霜和雪融化了,新的草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在文字的帮助下,那么多宽广的心灵拥抱了我这个少年,也用亲吻安慰了我的灵魂。
我让妈妈腾出一张旧床头柜。在那里,我把每天买的书一本本的放进去。三四年,十几本书,小柜子都满了。摸着这些书,第一次感到满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并不穷。
这是命运最深刻的暗示吗?从现在开始,书一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伴随着我。他们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参与命运的奇妙曲折。在医院艰难的病房里,在尘封的旅途中,在很多痛苦的选择中,书以一种无法言说的方式存在着。
我必须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说:你的痛苦需要文字治疗一辈子。
原发表于《青年文学》2018年第5期
实习编辑:孙佳怡
转载自青年文学官方微信
1.《黑暗里的光 《青年文学》 | 徐海蛟:黑暗里的暗与光(散文)》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黑暗里的光 《青年文学》 | 徐海蛟:黑暗里的暗与光(散文)》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guoji/12380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