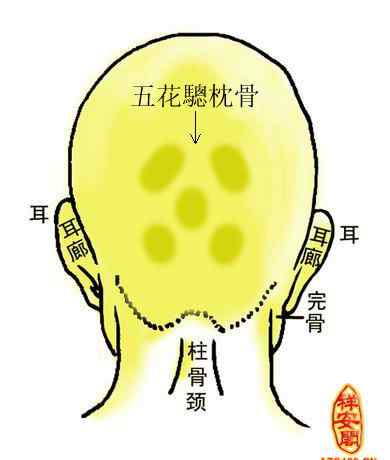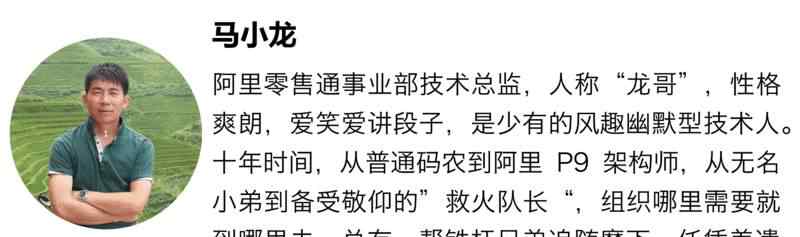张《锁林胶囊》
44岁的张是个谜。她不说教,不讨好,但在歌剧市场极度低迷的时候,她却有着巨大的票房。
作为的亲密弟子,张是京剧青衣派的第三代传人。她不化妆看起来更瘦。头发醒目,衣服大多是黑色的,不是人群中带头的那种。
化着妆,张是另外一个人。她就是《索林囊》中的薛香玲,《荒山之泪》中的张朱晖。她矜持、正直、举止严谨、擅长穿袖子。舞姿的调度和萌动是符合标准的,她从不眨眼,有一种庄重的风格。
上午9点,张与乐手第五次愉快地交谈。胡琴、三弦、大阮和秦越在中国戏曲学院影视中心排练厅的位置上。张比音乐人来得早。为了让声音回声空和声音接近舞台效果,她特意在这里设置了排练空间。
时间还早,乐手正在调整音色。不一会儿,牙牙学语起来,张和开始说话。
这是程派的名剧《荒山之泪》。没有麦克风和扩音器,所以你能清楚地听到张的真实声音和每一句话的吐字。
程拍与梅拍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发音完整而清晰。同一个唱段,梅派唱3分钟,程派唱5分钟。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充分发展。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戏剧学家傅晋说,张总是小心翼翼地唱好每一个小腔。
张在排练厅里没有化妆也没有穿演出服。她坐在椅子上,声音很低,表情很克制,全身的肢体语言都很收敛,偶尔会做一些手部动作,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眼神和姿势。
她唱“看焦怕风侵睡”这句话的时候,停下来对乐师说:“开头的节奏有点仓促。”
顾玉洁是镜湖的一名钢琴演奏家,与张相识已有20多年。很多时候,她觉得音乐人已经很有活力了。然而,在《荒山之泪》第四次排练的时候,一个慢板连着原来的板,练了三四次腔后,张还是说:“风口不太舒服。”“我赶不上人物。”
在《荒山之泪》说话的两个小时里,她好几次几乎没有停止咳嗽,但还是唱了起来。
张在西皮水上很安静。她呆在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也只有她能到达的地方。
在这个时候,张显得单纯、刻苦、专业。

青衣是京剧最重要的部分,蓝色的褶裥,沉重的唱腔,内敛的风格。南有郑丹,北有青衣。是抽象的女性角色,是女性中的女性。
在各种流派中,青衣Xi成派的人很少,整个戏剧学院只有六个人。这所学校从程先生开始,讲究气韵,温柔敦厚。在眼神、身法、步法、指法、衣袖等方面都不同于其他流派,不容易学,更难有技巧。
即使在京剧不景气的时候,张的表演也从来不需要赞助。同事们表示,在向张推销演出时,没有必要像一些剧团领导那样,与演出公司的老板们“在桌子底下喝酒”。
2014年,张演出四年归来,在长安大戏院演唱《朱良》两夜,演唱成派代表作《锁林胶囊》。开票第一天,“锁林胶囊”就卖光了;第二天,《朱良》卖完了;第三天680元的座位涨到了2200元,很快就卖光了。
歌剧界不乏商人和机构的表演,但张的每一张票都卖完了。
和张学戏剧已经十年了。之前她有转行的想法,准备放开程派青衣的时候,在舞台上看到了张。后来,她在张当了学生。10年来,很多同事都放弃了,转行了。原因很简单:京剧不景气,没人看,歌手赚不到钱。一部剧能拿两三百块还不错,观众只有30%在长安大剧院。
但是很奇怪。只要你看着张还在台上,做着她的身段,甩着袖子,一句话不说,不笑,吐字,动着眼睛,唱着她的程派青衣,说,她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继续在这块地毯上练习。
这是一种奇怪的力量,可以让人做出决定。
戏剧评论家朱看到张在《山野之泪》中的表演,感到非常惊讶。“她手里提着篮子走出来,走得非常非常安静,非常非常漂亮。一点一点的,先是手出来,然后篮子出来,然后下面的裙子踢出来,就像清水溢出来一样。不知道她练了多少次这个样子才达到这样的效果。真是令人震惊的样子。”
但是她对自己的力量或者神奇的魅力并不敏感,很少被自己感动。
在舞台上,眼睛和步法,水一样的身材和袖子并没有影响她的性格。在舞台下,她没有那么多情绪,直到现在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她缺乏江湖精神,从不谈论自己的理想。
朱后来问张为什么这个样子这么好看。张丁火说:“这是老师教的。”
有人夸她:“你连提篮子都和别人不一样。”张问:“有什么不同?”
张也对“她有青衣应该有的样子”的评价感到不解:“我从来没想过青衣应该有的样子。”
她话不多,但很有礼貌,很温柔,但相当直接。她是一个天真果断的人。
学生张柏(音译)表示,张丁火身上有一种不开放、不天真的特质。她从来不会想太多,也不会设定长期目标。事情从她在做的事情开始,一件事做不完,她就永远不会开始下一件事。
她对为什么能坚持做这行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很简洁:“没想过。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这个行业的其他事情,也没想过别的。”

李文敏快80岁了。她是张在北京的第一位老师。她还记得19岁时张第一次在她面前开口。
当时的京剧团,一个战友,只有三个角,一个死了,一个没了,少了一个青衣。剧团团长王喜欢程派。由于哥哥张火钱在剧团里工作,他说他会打电话给张试试。
这一天,在戏剧学校宿舍,一个同事带来消息:“政委王说,团里有个学生,请出示一下。如果你能训练,你就做不到。”
这是第一次见到张。
不是特别显眼的孩子。很瘦,两条辫子齐腰长。“性格乍一看很孤僻,我一句话都不说。”
那一天,张开始唱两段,一段《春秋搭配》,一段《春秋亭》。李文敏仔细听着。《春秋搭配》比较好。《春秋亭》全是程派的错。”她回忆道。
然而,她注意到孩子的声音很大。她虽然实力不够,戏也不多,唱歌也没有什么基础,但是很素净,没有修饰自己。
经过仔细询问,这名学生来自吉林省白城市。他父亲在家唱平西,没有京剧基础。10岁开始报考省戏剧学校京剧系,每年都被刷下来。自费到天津戏剧学校做转学生。
有了内心的,立刻意识到张并没有在戏剧学校学到什么真东西。这个男孩虽然缺乏歌唱技巧,但气质并不俗气。脸上没有戏份,羞耻和快乐都是含蓄的。“京剧里有句行话叫‘脸朝下玩’,这是最重要的,但丁火不是这样的。”
李文敏以一副好嗓子和干净的面孔接受了她。
张和战友们一起留在了京剧团,被当成了编制里的一名战士。
作为学生,张太老了。每天早上9点到12点,她准时去李文敏家学戏剧。
战友京剧团位于北京香山。张从住处到家需要3个小时。那是1990年,地铁1号线只有一段,两头都要坐公交。张从不迟到,9点前到,12点才走。
冬天太冷了,李文敏看上去很沮丧。他和戏剧学校的校长商量了一下,租了一个宿舍。于是张就住在老师家附近。
回忆说,当时的张虽然不会说话,但很渴望练琴唱歌,说是想追到当时红极一时的青海燕。
她学的不快,但每次回去上课,说的话总能消化,该背的练的都能做。剧团里有一句话:如果训练室只剩下一个人,不要猜,一定是张。
三个月后,专门开了一次教学会,请来了刚学了三个月弹钢琴的张。
这是19岁的张第一次上台演唱《雪中六记》。奇怪的是,观众不仅鼓掌,还听其他东西。但这时候,张只学会了这一段,“没有别的”。
政委看了觉得不错,想“重点培养”她。
但是张却是倔强的。她声音很宽,但声调不高,不适应的戏不安排也不礼貌拒绝。她只是说“我不会唱歌”,她不是那种会来上班的人。船长不太喜欢她。
几年后,王退休,战友京剧团解散,张调到中国京剧院。
当年轻的张第一次在京剧院演唱时,她不知所措。她对李文敏说,老师,你能帮我把它关在后台吗?
那是张出名的时候。
那时候她不太懂戏。著名粤剧艺术家仙奴红非常欣赏她,给了她2.5万元和一盘60分钟的磁带,让她录下一整盘磁带,自己保存。当时张的旧戏社还不足以录一盘磁带。

与哥哥张火倩

一个有才华的人难免会被自己的才华所束缚,但张不在其中,她也不太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2007年1月,媒体与张协调能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独奏会,并要求举行两小时的独奏会。张对很是放心不下,怕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人。
“一定要做,”当时央视戏剧节目主持人白燕升告诉她,“在人民大会堂唱京剧是前后最后一件事。”
演出结束后,效果非常好,张成为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梨园演出的人。媒体问张他有什么感受。张丁火说得太坦白:“我不喜欢唱歌的形式。我觉得戏曲演员不仅要唱歌,还要表演。如果只是站在那里唱歌,我会觉得很尴尬。我都不知道放哪了。”
身边的人都说张没有那个野心,想抓住自己的某个机会或某个阶段去成就什么。
2008年,“张京剧艺术工作室”声誉很高,但张因为“压力太大”而拒绝做。之后她被调到中国戏曲学院当老师,不久怀孕生了一个女儿。她四年没有掌权。
那时候,张37岁,正值壮年,突然放手4年,这可不是小事。
旁边的人都为她着急。当时工作室已经是第四年了,势头极好。每年最多一百多场演出,在一个城市持续两三天,在另一个城市继续。
傅晋解释说,高强度、高频率的表演是对演员的优秀训练。张早年的老师也说过,程和梅艳芳两位大师,和剧团这样唱过,演过一个世界。他们希望张会走老派的老路。
做一个独立的戏曲工作室,在梨园也不是没有先例。早年,王佩瑜尝试过这条路,但以失败告终。以张当时工作室的势头,独立于京剧院也不是不可能的。
当时,虽然片场的名字叫张,但她只是主角。工作室以京剧剧院为名,没有完全的自主权。
但是,张拒绝了,并不想独立做这件事。原因很传统:“我没有那个能力,必须靠组织。”
她说她过来这么多年了,从战友京剧团到中国京剧剧院,剧院或者学院给她什么她都一直在做。
这使得她在很多问题上的判断极其简单明了。比如玩了这么久,真的能承受表演机会少吗?“是的,当然。”张说:“如果我不能忍受,我就不离开剧团来戏曲学院。这么多年在团里很累。戏曲学院一给我发邀请,我立马就答应了。”
至于生孩子会不会影响艺术和私生活,她的回答是“如果影响你,你就得生”。
李文敏谈到了过去的梨园之旅。表演者需要组建一个剧团。如果他们一天不唱歌,一个队里的每个人都不能吃东西。所以,在残酷的生存法则下走出来的,都是身体健康,有足够信心,能承受高强度表演的人。
张的体力没有那么强。她一直吃素,身体比较虚弱。由于体力不足,中场休息时经常在后台吃饼干。年纪大了以后,声音和力气就更容易跟上了。
张对年龄和身体的变化并不小心。她用一种过于豪爽和坦诚的态度说:“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能和过去相比了,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玩了。”
给她讲这部剧的万老师经常对她说:,你太直了
她做事的方式一直有点顺势,被动。“我从来不想扩展什么,它会很用心的。”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她正在为王家卫制作自己的纪录片。


很少有人知道充满魅力和自由的张其实很焦虑。
傅晋曾看到张等着表演。她提前3个小时到达现场,默默弹奏,并在脑海中读出具体的唱法、台词和身段。有条件的话,她会尽量让自己一个人呆在更衣室,开场前十分钟就不说话了。
“每个压力都不小。”张对说道。上任后,她总有一段时间嗓子不好,“唱一会儿再定下来”。
在受欢迎的京剧演员中,王佩瑜,一个来自豫派的老学生,不介意被邀请在晚餐时唱几句。但在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她晚上不做那种唱歌,让她觉得角色没头没尾,“我会很紧张”。
她宁愿拒绝那些短短的一段话:“上去之后,我紧张的心情还没说完。我下去了。”她要化好妆,慢慢进入角色,唱,读,玩,全部演完。
她一度怀疑这种紧张超过正常,于是问老师:“我怎么这么紧张?”老师告诉她:“你激动了。”她非常犹豫。
到现在,张一直保持着每周3-4天的时间,9点准时“绕场跑”,也就是绕着训练室走一圈,一次走一两百圈,走路的时候穿上宽腿裤,以便在镜子前修正膝盖的动作幅度。
此外,钢琴家虞照将被邀请每周在家悬挂他的声音。在这些地方,张对是很守旧和执着的。她认同老规矩:老一辈人愿意努力,冬天在地上扔一层冰在舞台上走,在冰上轻而稳地走,让舞台上的台阶像流水一样。
学生顾玉洁(音)记得,张第一次上课不怎么说话,但没过多久,下面的人就安静下来了。“她能吸引人冷静下来。”
还说张对不严格,但她一说起戏就说:“你听好了,我这次就在这个地方说。”语气没有特别提升,但人已经紧张了。
起初,张对并不适应。戏曲学院的孩子还小,有时候起晚了不来,就给张发短信:“老师,我有事,不去上课了。呵呵。”
张丁火问张柏:“她不上课,为什么还跟我说‘呵呵’”
在课堂上,学生们没有做好。张问:“你练过吗?”学生平静地回答:“我忘了。”
张也愣住了。对她来说,这不是那种可以“忘记”的事情。
张也慢慢的生气了。她不会拍桌子。她愣了一下,想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挺失望的。”
和张在一起很久了,知道这种“失望”比愤怒更糟糕。但是孩子们不在乎。
她的学生李莉说,虽然老师不生气,但她很专业,这让你感到害怕。第一讲,张丁火看着李丽说:“不要怕高,要支持。不要缩,台上丑,得按身材比例走。”
“她审美很好。”李丽后来说。
从小,就不怕跟张一起去上课,但他很紧张。上课前他不得不在镜子前扎头发,怕自己邋遢。
有一次在一首慢板里,李丽问老师:“你唱这个词的时候在想什么?”
张被问到:“我什么都没想,就是想把这个词唱好。”
在李丽平凡的课堂体验中,人物只有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深刻的内在动机后才有言行和动作。张对说:“你想多了。”
她告诉李丽自己的标准,“别那么大声,话没了。拼写要清晰,发音可以圆润。记住你是男的,无论唱多高,面部表情都要好看。”
当谈到张的时候,同学们都很激动。这种兴奋也出现在张的朋友和合作者的脸上。他们愿意对她进行思考和反思。
说张丁火身上有一种让人紧张又依恋的东西。当他们靠近时,他们会感觉到,但他们不能说。

像所有来自小城镇的女孩一样,一旦有了很大的成就,远在东北的爸爸妈妈哥哥奶奶都来找她。
父亲从老家出来,在廊坊工作了一段时间,母亲没有工作,身体一直不好。哥哥生意不好,人也老于世故。整个家庭的压力都压在她身上。
张自己的气质和她家的气质很不一样。她从小就出来了,老戏滋养着她,她活在干净的戏里。
成名之后,哥哥成了张的经纪人。老戏迷发现张火钱很堵观众。在媒体、观众、合作者面前,他几乎是不屑的。有很多人情突破了他。在一些重大决策和计划中,张火乾的操作多少阻碍了张丁火。但是她的家庭价值观太重,她从来没有把事业和家庭完全分开。
这些都与张在舞台上的。
2015年9月,张在林肯中心演出,这是业界的一件大事。但是因为她没出过国,不会说英语,所以吃饭的时候太紧张了,背不了剧。
她不习惯吃沙拉。她只吃蔬菜、奶油冻、蘑菇、鳄梨和苏打饼干。李莉每顿饭都需要给她补充一些蛋白质,否则体力跟不上。
文艺剧在国外不流行是因为看不懂,外国人更喜欢看武侠。可有武侠《白蛇传》不擅长张的,这回她硬生生的把它啃了下来。
演出的前一天晚上,张吃了安眠药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当张起床时,李丽战战兢兢地告诉她,饰演的签证有问题,不能来了。
张丁火听了,面无表情,只说:“哦。”
李丽并不十分惊讶。张对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反应不太大。她脑子里总是只有一件事。
当晚临时替补演出《白蛇传》后,全队转移到加拿大演出。保安一走,所有人都进去了,张和被拦住了。因为她只带了一本公共护照,没有加拿大通行证。整个党人心惶惶。
张终于着急了。她慢慢地说:“我真的很着急。”然后她开始给家人打电话:“我不知道。没人叫我带这个。”
所以通行证必须由家人空运到美国。

林肯中心演出结束后,张为谢幕六次。世界顶级舞台上布满了张的大剧照。她从19岁到现在用了25年。
傅晋说,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张与同时代人的横向比较很突出,纵向上可以与前代大师相比,并不是很好;不过她在北京,年龄合适,言谈举止坚持戏曲应有的范式,天性既聪明又腼腆,很有价值。
她早年封闭而简朴的训练给她留下了一些痕迹。她言简意赅,自律,极度克制,很少应酬。你很难在专业之外找到和她共同的话题。
这给了她某种品质。张在舞台上是庄重而内敛的,即使把妆从舞台上卸下来,一些懵懂、缓慢而又远离当代的东西依然留在她身上。
她的这些品质吸引了一群人。
张有很多戏迷,比如、、白,他们都是主流行业,有独立的审美,有话语权。他们内心执着,必要时老练,而张则保留着他们留下的一些东西。
在一次晚宴上,谈到了他对张的欣赏。现场的一个朋友马上说:“我跟张很熟,可以马上给她打电话。”张立宪阻止了他:“她不是一个很戏剧化的人,我不想那样做。”
直到合拍《张论青衣》一书,他才真正在舞台下认识了张。
首先是她的服装。黑匣子一个个搬了进来,上面写着“中国京剧院”“张歌剧院”。
京剧行头厚重,服装复杂,盛夏不演是梨园的老规矩。况且京剧妆饰很重,长时间化妆对演员的外貌伤害很大。
和往常一样,张的话很少,几乎没有和摄影师直接交流。她只演戏,其余的都是哥哥张火倩照顾。
那是仲夏,五天之内,她开始每天早上化妆三四个小时,从下午到晚上,每一个动作和歌声都重复三遍以上。太热了,我化了很久的妆。张头上的膜让他额头流血。
演员勒死头后不能吃固体食物,大家都在中间吃。张不会卸妆,只喝酸奶充饥。
时隔六年,仍然记得张在拍摄第一天上台的那一刻。
下午两点,舞台安装完毕,调好灯后,先黑了,再亮。薛香玲蜷在背景墙边唱道:“恐怕春天流水就没了。”。
张立宪坐在舞台下面,几乎要哭了。
早年,张曾在舞台上哭过。当时她在各个县级、地级市巡回演出,还在枣塘子唱歌。听完剧,一群男人去洗澡,环境很糟糕。
有一次他在唱歌,凉风灌进敞开的舞台,张在唱到一半就开始咳嗽,几乎停不下来,一个长长的歌喉就咳了出来。
学生在侧屏看到张勉强唱完最后一句。当他背对着观众时,他的肩膀开始颤抖。他下台后,靠着梳妆台哭,背上全是汗,无法呼吸。
张柏拍拍她的背,周围有许多人。只好让人群稍微开一点,让张喘口气,然后上台谢幕。
那一次,她哭着告诉观众,她的事业从来没有犯过这么大的错误,那么她还能再唱一遍吗?
玩耍是唯一让她张扬、舒适、充满控制力的东西,也是让她脆弱的东西。

1.《张火丁老公 最不像京剧演员的演员——程派青衣张火丁》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张火丁老公 最不像京剧演员的演员——程派青衣张火丁》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guoji/16204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