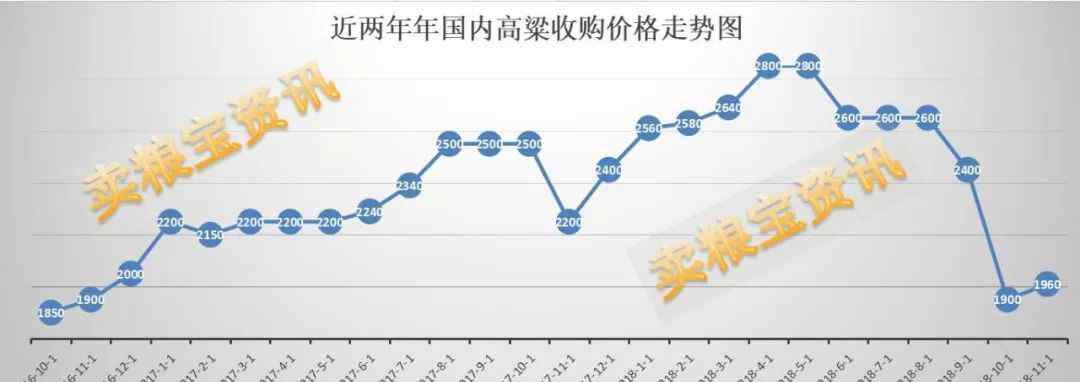随着电影《红高粱》还原版的上映,与这部电影的过去重新浮出水面。
在这里贴一篇莫言的老文,反思拍摄中的波折和趣事。
我一度怀疑张艺谋已经看不见它了
莫言
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既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要改编他们的作品,我要忠于原著,喜欢改编莫言的作品就改编。
如果你想让“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试验原子弹,跟我没关系。不仅无关,还想为你的好勇气喝彩。在张艺谋拍得好是你的荣幸,拍得不好也不是我的耻辱。
当时国家规定小说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钱。一开始不想参加改编,但是张艺谋想让我参加编剧,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些民俗之类的东西。有三个作家,一个是陈建宇,一个是朱伟,一个是我。手稿是福建电影制片厂当时的导演陈建宇写的。
1987年我在高密的时候,张艺谋给我看了他的最终版本,和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一样。张艺谋其实做了很多精简。看到它我很惊讶。几件事,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才知道,电影不需要太多。比如《跳脚》的一个场景,剧本里的几个字在电影里被“跳脚”了5分钟。
1987年6、7月,张艺谋给我发来电报,希望我能回高密帮他们找到县领导,得到帮助,说高粱不能长了。说实话,他们在高密选址的时候,我是反对的。
第一,高密东北乡变化很大。我描述的高粱地在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就有了,我以前也没见过。盛开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也是我的梦想。他们要去高密东北乡拍红高粱。他们拍什么?当然可以种。其次,我在很久以前的小说里写过,高密东北乡是英雄和混蛋最多的地方。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对农村经济生活的无情入侵,原始的淳朴、诚实、讲义气、英雄主义的祖传礼仪就像用旧铜币,剥去灿烂的青铜色,加上绿锈。
一切都需要钱。你有多少钱?但是张艺谋坚持高密度拍摄。
1987年春天,他第一次派助理导演杨凤良到高密,和普通人签了合同,种了两株高粱。
我接到张艺谋的电报就回去了。到了孙家口,真的好想哭。高粱都是半死不活的,不到一米高,只有几英尺低。叶子都卷了,叶子的茎上长满了蚜虫,甚至蚜虫都被晒伤了。太干了!第二天,我遇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的负责同志,批准了5吨化肥。县领导还把种高粱的乡镇领导叫到县委开会,要求他们把高粱的管理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举动感动了。
拍戏结束,想邀请所有剧组成员来我家。当时不叫“红高粱”剧组,叫“九九星沙口”剧组。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家人时,他们非常兴奋。父亲提着锄头悄悄走到地上。父亲一直劝我要谨慎,不要自高自大,否则我会作恶,我也尽力而为。一大早,妈妈和阿姨忙着擀蛋糕,最后一集媳妇忙着逛街。十点左右,一辆画着几个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的麦田里,张艺谋、副局长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伟等下了车。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很一般。她在高密招待所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穿着不伦不类的衣服,脸上带着担忧的表情。
感觉和自己的“奶奶”形象相去甚远。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朵眼睛明亮、水分充足的刺玫瑰。那时候的巩俐更像是一个没什么人间经历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错过了她的眼睛,担心戏会落到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片子拍完,看到样片,真的很震撼。完全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红高粱》是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在视觉和色彩运用上都营造了如此浓厚的氛围。
电影的影响力确实比小说大很多。小说写出来之后,除了文学界没人知道。
但是当我1988年春节后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听到很多人在半夜走在路上唱着“姐姐,大胆前进”。这部电影真的很棒。很幸运遇到了张艺谋这样的导演。
1.《红高粱巩俐 电影《红高粱》重映,莫言忆旧:我曾担心巩俐演砸了》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红高粱巩俐 电影《红高粱》重映,莫言忆旧:我曾担心巩俐演砸了》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guoji/7959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