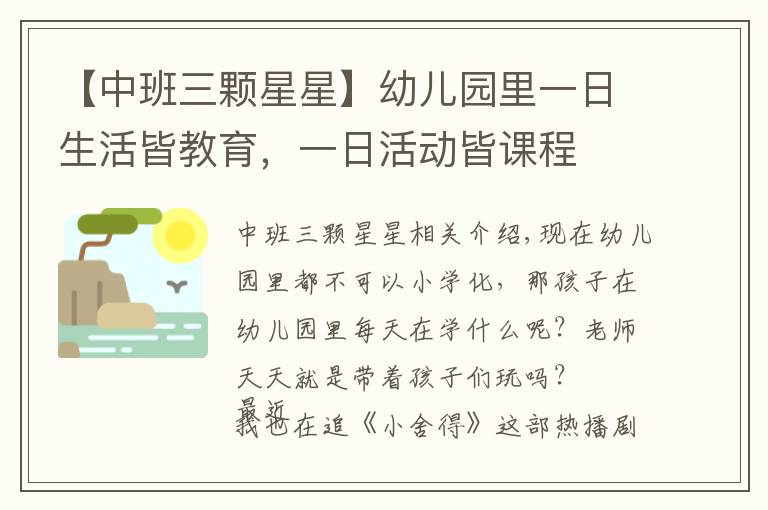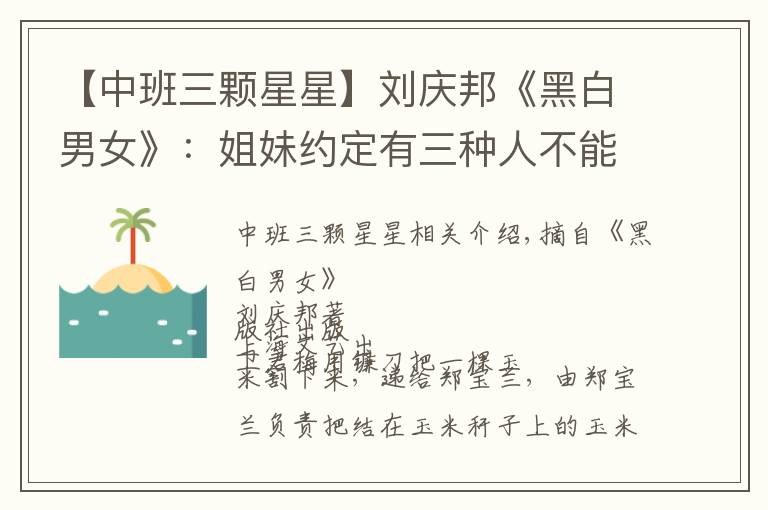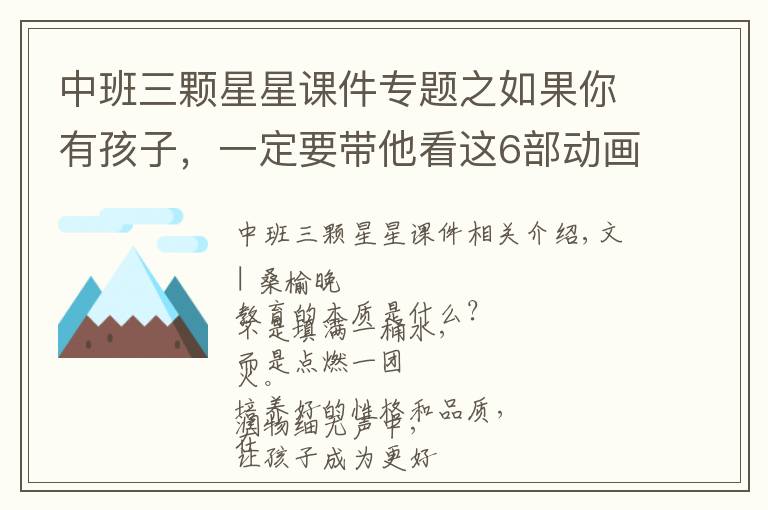摘自《黑白男女》
刘庆邦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卫君梅用镰刀把一棵玉米割下来,递给郑宝兰,由郑宝兰负责把结在玉米秆子上的玉米棒子掰下来,放在旁边的荆条筐里。这里收获玉米一般采用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玉米棵子还长在地里时,人钻进玉米棵子丛中,逐棵逐个把结在玉米秆子上的玉米棒子掰下来;还有一种办法是,直接把玉米棵子放倒,再掰下上面的玉米棒子。卫君梅不愿采取前一种办法收玉米。因玉米种得比较密,玉米叶子锯齿样的边缘又很锋利,人钻在玉米棵子丛中,暴露出的皮肤很容易被玉米叶子划伤。而采用后一种办法收玉米,人的皮肤被玉米叶子划伤的情况就可以避免。太阳已经西斜,小鸟叫着飞走了,田里弥漫着被砍倒的玉米棵子甜丝丝的气息。卫君梅对郑宝兰说:宝兰,我怎能忍心让你帮我干活呢!
郑宝兰说:君梅姐,我在家里心里空得慌,出来手里抓挠点儿东西,心里好受些。她手里抓到的是玉米棒子。这棵玉米只结了一个棒子,所有的养分大概都集中到棒子上去了,棒子又粗又长,顶端金色的玉米子儿都胀破了包皮,从包皮里露了出来。她一手抓着玉米秆,一手握住棒子,往下一掰,又一拧,才把一个沉甸甸的大棒子取下来。当她的手转着圈儿拧棒子时,棒子吱哇叫了一声,似乎并不情愿,仿佛在说:你的手轻一点儿好不好,你都把我拧疼了。郑宝兰把玉米棒子取下来后,并没有剥去青色的包皮,就把棒子扔进筐里去了。此时的玉米棒子还会从层层包皮里继续吸取营养,直到把包皮吸得发黄发干,人们才会把包皮剥下来。
在地里干活儿的还有卫君梅的两个孩子,女孩子慧灵,男孩子慧生。慧灵是姐姐,慧生是弟弟。姐姐上小学二年级,弟弟还不满五周岁。姐弟两个在向地边运送掰过棒子的玉米棵子。他们的办法是把带着叶子的玉米棵子扛在肩膀上,一趟一趟往地边扛,扛到地边堆起来。玉米收完之后,这块地要马上翻起来,种冬小麦,所以要及时把玉米棵子收拾出来。姐姐一次扛三棵玉米,弟弟还小,肩膀还嫩,一次只能扛一棵玉米。弟弟扛了几趟就不想扛了,他觉得扛玉米一点儿都不好玩儿,不如逮蛤蟆好玩儿,也不如捉蜻蜓好玩儿。看到一棵植物上结有紫色的浆果,他想去摘浆果。看到脚前飞起一只绿色的蚂蚱,他把蚂蚱指给姐姐看,说蚂蚱,蚂蚱!姐姐不让他去摘浆果,对蚂蚱似乎也不感兴趣。姐姐像是要给弟弟做一个榜样,又像是一个监工,希望弟弟能够专心干活儿。她不能吵弟弟,要是吵了弟弟,她担心弟弟会产生逆反情绪,跟她撂挑子。她的办法是不断表扬弟弟,用表扬把弟弟套牢。她说:慧生最能干了,最热爱劳动了。慧生这么小就帮助妈妈干活儿,真不简单!等慧生干完了活儿,姐姐就给你讲故事,讲好多好多故事。慧生想听什么故事,姐姐就给你讲什么故事。
慧生受到姐姐的表扬和引导,果然把摘浆果和捉蚂蚱的事忘记了,好像把肩膀上扛着的玉米棵子也忘记了,他说:我想听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故事。
那好吧。你是想当乌龟呢?还是想当兔子呢?
慧生皱起小眉头,像是想了一下,说:我想当乌龟。
你当乌龟,我就当兔子,来,咱俩赛跑。一二三,开始!
当乌龟的应该爬行,慧生却跑了起来。他的脚绊到了一棵露出地面的玉米茬子,摔了一个大马趴。玉米棒棵子还在他的身上压着,像压着一棵小树。这样一来,慧生四肢着地,真的像是在模仿乌龟的动作。这可不是慧生所需要的动作,如果“乌龟”这样爬,就赛不过“兔子”了。慧生欲哭,他满脸通红,眼里已经含了泪。
姐姐没让他哭出来,姐姐说:慧生勇敢,慧生坚强,好了,起来吧!她拿开压在弟弟身上的玉米棵子,拉住弟弟的一只胳膊,把弟弟拉得站立起来。弟弟站起来后,姐姐把玉米棵子重新放回弟弟肩上,姐弟俩一块儿向地边走去。
慧生没哭出来,看到这一切的郑宝兰,眼里却泪花花的,她对卫君梅说:别让两个孩子干了,孩子这么小,让人看着心里还不够难受的。
卫君梅说:不干咋办呢,他们的爸爸不在了,我从小就得培养他们,让他们学会自强,自立。她抓住一棵玉米,用月牙镰刀钩住玉米的根部,贴着地皮一拉,便把一棵玉米割了下来。这棵玉米棵子上结有两个玉米棒子,一个棒子大一些,一个棒子小一些。她割玉米割得快,郑宝兰掰玉米棒子掰得慢,再割下玉米后,她没有把玉米棵子直接递到郑宝兰手里,而是放到了地上。
郑宝兰问:他们的爸爸不在了,两个孩子都知道了吗?
卫君梅拐起胳膊,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走到郑宝兰身边,小声对郑宝兰说:两个孩子都知道了,不过都不是我告诉他们的。慧灵是在学校里听她同学说的,回来跟我哭了一大场。慧生呢,是今年清明节的时候,慧灵背着我,领着她弟弟到他们爸爸的坟前去了,姐弟俩跪在坟前,给他们的爸爸磕了头。
小来他爸爸不在的事,我至今还瞒着小来。他爷爷奶奶都不让我跟孩子说实话,老是说启帆到外国学习去了。这样瞒着孩子,瞒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儿呢!
这个你不用着急,也不用发愁。爷爷奶奶都是好心,你也是好心,你们是在保护孩子,免得孩子幼小的心灵过早受到伤害。我也想瞒着孩子,可慧灵已经懂事了,这孩子像他爸爸,灵透得很,我想瞒也瞒不住她。爸爸是罩在孩子头上的一把伞,伞没有了,雨点儿迟早会落在孩子头上,没有大雨点儿,也有小雨点儿。我们想为孩子遮风挡雨,但终究不能代替他们的爸爸。等孩子一找再找找不到爸爸,迟早会明白过来,原来爸爸已经不在了。当孩子知道爸爸不在的时候,他们跟别的孩子就不一样了,离他们长大就不远了。你看我的这两个孩子,我不用怎么说他们,也不用吵他们,他们就变得这样乖。是他们的爸爸的离去使他们变乖的。就算他们有时候做了错事,我也不骂他们,不打他们,只瞪他们一眼,就把他们吓得眼泪八叉的。
君梅姐,你这样做,你不觉得对孩子太狠心了吗?
不是我狠心,是老天爷狠心。是老天爷对咱们太狠心了。过去我常听人说老天爷有眼,老天爷最公正。自从你龙民哥出事后,我再不相信老天爷了,再也不去给老天爷烧香了。我就是要看看,老天爷对咱们还能怎样!
郑宝兰仰脸朝天上看了看,似乎要找一找老天爷在哪里。天很高,云彩很淡,一只孤鸟从天空飞过,她没找到老天爷在哪里。她摇了摇头,并轻轻叹了一口气。
卫君梅把沾在郑宝兰衣服上的一缕玉米缨子替郑宝兰拈去,有些怜惜地说:说来说去还是怨我,当初我要是不给你介绍对象就好了!
你不能这样说,千不怨,万不怨,还是怨我自己的命不好。
卫君梅和郑宝兰是初中同学,也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在学校里,女同学的表现与男同学不同些。男同学常常独来独往,有没有要好的伙伴都无所谓。而女同学总愿意找另一个女同学结成伙伴,或结成同盟,以显示自己有人缘,不孤单,并显示出“团结”的力量。当时,卫君梅和郑宝兰是“梅兰团结如一人,誓看全校谁能敌”的架势,二人上学一路走,放学一路回,下雨共打一把伞,一枚杏子分开吃。有一个男同学悄悄给郑宝兰递纸条,郑宝兰还没有完全看清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就马上把纸条拿给卫君梅看。来到男同学所指定的约会地点,是卫君梅和郑宝兰同时出现在男同学面前。那位男同学见他给郑宝兰写的纸条拿在卫君梅手里,什么话都没敢说,转身就走了。卫君梅命他站住,站住,他走得更快些。
草要发芽,树要开花,二人难免会谈到将来找对象的事。她们先是说不找对象,一辈子都不找。对象是夹板子,一找对象,就被夹板子夹住了。对象是个鬼,找到了对象,就得跟着鬼走,就没有了自己。她们不想被夹板子夹住,也不想跟鬼在一起,所以还是不找对象好一些。后来她们听说,不找对象不行,好比只有肉没有骨头不行,只有骨头没有血液也不行,肉要和骨头在一起,血要和肉在一起。她们的口气稍稍松了一点,说找对象也不是不可以,定的标准要高一些。至于高到哪里,她们你看我,我看你,一时都拿不出具体标准。她们只好采取否定的态度,商量来商量去,认为有三种人不能作为她们将来要找的对象。一种是身体有病的人。凡是有病的人,不能长期支撑门户不说,身上都有一种气味儿,难闻得很。一种是当警察的人。郑宝兰说道,她有一个表姑,嫁了一个男人是警察。警察在外边抓坏人抓惯了,看谁都是怀疑的目光,好像每一个人都跟坏人沾边。警察一回到家,不跟老婆说话,先往门后找,到卫生间搜,还掀起床单往床下瞅,看看家里藏的是不是有别的男人。半夜里,表姑当警察的男人会突然起身,把枪口对着表姑,要表姑老实交代,以前是不是跟别的男人好过,表姑胆敢不说实话,他就崩了表姑。表姑成天担惊受怕,久而久之,好像自己真的变成了一个坏人,常在睡梦中被自己的噩梦惊醒。还有一种是煤矿工人。她们这里地底下蕴藏的煤多,开的煤矿就多,大煤矿小煤窑都有。因为离煤矿比较近,对煤矿工人的情况,她们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挖煤的人成天在煤窝里滚,他们的脸是黑的,手是黑的,全身上下都是黑的。拿一块白布投进盛满黑颜料的大染缸里染,再把布拿出来,整块布就变成黑的,黑得到边到沿。同样的,拿一个人放进煤井里染呢,人也会被染成黑的,进去是一个人,出来就变成一块人形的煤。卫君梅对郑宝兰说过,千万不要跟煤矿工人握手,你的手本来是白的,跟煤矿工人的手一接触,就会变成黑手。卫君梅还对郑宝兰说过悄悄话,说千万不要跟煤矿工人接吻,你的嘴唇本来是红的,牙齿本来是白的,倘若被煤矿工人吻到了呢,嘴唇就会变成黑的,白牙也会变成黑牙。卫君梅在郑宝兰耳边说悄悄话时你你的,把郑宝兰的脸都说红了,好像她和煤矿工人已经有了某种联系似的。她说:你说话别老你你的,你才是你呢!卫君梅笑了,说我只是打个比方,又没有真的说你,你脸红什么!郑宝兰不承认自己脸红,说你的脸才红了呢!卫君梅抬手把自己的脸摸了摸,问是吗,它要是敢红,我就打它!说着,真的在自己的腮帮子上摩擦似地拍了两下,说:我叫你红,我叫你红!后来她们还共同说到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使她们不和煤矿工人谈对象的决心更加坚定。煤矿事故多,井下容易死人,如果和煤矿工人谈对象,并嫁给煤矿工人,就有可能当寡妇。当时她们还是中学生,并不知道当寡妇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更没有把寡妇与自身联系起来,只隐隐约约知道,当寡妇是一种不幸的遭遇,寡妇的日子不好过。说到寡妇时,她们有些惊诧,甚至有点儿夸张,好像看到电视剧中一个惊险的镜头一样。就这样,姐妹两个在将来找对象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约定。在约定中,煤矿工人是被排除在外的,是免谈的。
首先打破约定的是卫君梅。不仅她自己打破了和郑宝兰的约定,自己嫁给了煤矿工人,她给郑宝兰介绍了一个对象,竟然也是煤矿工人。卫君梅结婚早,生孩子早。给郑宝兰介绍对象时,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女儿。那个时段的卫君梅,气色红通通的,脸上笑盈盈的,浑身都充满着热情,洋溢着幸福。她像是一股春风,吹到哪里,哪里春暖花开。她好像是一支火把,照到哪里,哪里就一片光明。一花独秀不是春,有福是需要与别人分享的。于是,她想到了自己中学时的好友郑宝兰,就把周启帆介绍给了郑宝兰。周启帆与她丈夫陈龙民是工友,两个人在同一个采煤队上班。卫君梅给郑宝兰介绍周启帆时,提供的周启帆的情况不是很多,只说周启帆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的老矿工,周启帆家在矿上的家属院里有三间房子,家庭条件不错。她的话题有些跑偏,说到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丈夫陈龙民。她说陈龙民这人太好了,百能百巧百样好,没有一样不好。陈龙民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有时正看着她,眼里突然就泪汪汪的。她问陈龙民为何这样?陈龙民说:因为你是我的恩人。提起陈龙民对她的好,她的眼里几乎也含了泪水,她说,她不但这一辈子给陈龙民当老婆,下一辈子还要给陈龙民当老婆。
听着卫君梅的话,郑宝兰没有插言,只是抿着嘴儿笑。卫君梅见郑宝兰对她的话反应平平,回想起了她当年和郑宝兰的约定,她说:那时我们年龄还小,并不是真正了解煤矿工人。自从我嫁给了你哥陈龙民,当了煤矿工人的家属,我才渐渐对煤矿工人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就是因为他们在井下常年见不到女人,他们对自己的妻子才特别稀罕,特别亲切。就是因为他们的作业环境艰苦,时常面对凶险,他们才有自觉的生命意识和紧迫的危机感。他们每一次下井,都像是和妻子经历一次离别;每天从井下出来回到家,都是和妻子重逢。不管是离别还是重逢,他们都对自己的妻子特别珍爱,也特别珍惜。
郑宝兰说:你把陈龙民说得这么好,是要推销他吗?
我倒是想推销他呢,恐怕再怎么推销也推销不了,他说了,他这辈子只跟我一个人好。
郑宝兰让卫君梅把双手伸开,给她看。卫君梅把双手伸在郑宝兰面前,郑宝兰把卫君梅两个手心打了一下,说:我看你的手不黑呀!郑宝兰又让卫君梅张开嘴,把嘴唇和牙齿给她看。卫君梅明白了郑宝兰的意思,她张开嘴,露出牙,故意凑近郑宝兰的脸,似乎要咬郑宝兰一口。郑宝兰说:我看你的嘴唇和牙也不黑呀!
好你个臭丫头,原来你是笑话你姐呢!反正我把周启帆介绍给你了,一块好煤摆在那里,采不采你自己决定。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要是错过了周启帆,可别怨姐有好事儿不想着你。矿上到处都写着安全第一,卫君梅也跟郑宝兰说到了安全的事。她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打保票。谁都不敢在这个事情上打保票。她只是对郑宝兰转达了陈龙民的一些说法。陈龙民说过,现在矿上上上下下对安全生产都非常重视,全矿已经连续好几年没发生过大的工亡事故了。
卫君梅带着郑宝兰到矿上的女澡堂洗过澡,下进汤池里,卫君梅在前面走,郑宝兰在后面跟;卫君梅往身上撩水,她也往身上撩水。郑宝兰试出来了,池子里的水热乎乎的,一点儿都不深。郑宝兰看见卫君梅的身体又白又丰满,通体闪耀着迷人的亮光。相比之下,她显得有些瘦,有些平常,似乎缺少应有的光彩。
郑宝兰嫁给周启帆了,成了周启帆的新娘。新娘备了礼品,到卫君梅家看姐,也是谢媒人。卫君梅问他:哎,怎么样?
郑宝兰的脸顿时红透,说烦人,他天天都要,要起来没够儿。
你就烧包吧你,他要是不要,你就该着急了。
由陈龙民请客,两家人在矿街上的一家酒馆里吃了一顿饭。陈龙民和周启帆以兄弟相称,卫君梅和郑宝兰以姐妹相称,他们你敬我,我敬你,都喝了不少酒。两兄弟把酒杯碰得轻轻的,没怎么闹酒。两姐妹却喝得满面春风,流光溢彩,手舞足蹈,不亦乐乎!卫君梅以郑宝兰的娘家姐自居,指着周启帆说:你要是敢欺负我们家宝兰,我可不依你。
周启帆嘿嘿笑着,一句话都不敢说,比一个大闺女还腼腆。
卫君梅要周启帆说话,不许装憨。
陈龙民打圆场,说喝酒喝酒。
卫君梅态度严肃,说不行,要周启帆必须表态。
周启帆只好说:我哪敢欺负她呀,她欺负我还差不多。
我不信,她怎么欺负你了,你说。你要是说得不对,我罚你喝酒!
郑宝兰说:姐,他拙嘴笨腮的,别让他说了,我替他喝酒还不行吗!
噢,宝兰心疼女婿喽,宝兰心疼她的周郞喽!
有一个词,卫君梅和郑宝兰在学校都学过,一开始是不会读,后来会读了,又忘了怎么写。这个词的名字叫戛然而止。之所以记不住这个词,是觉得这个词有些生僻,跟她们的生活没有关系,可能一辈子都用不着这个词。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这样,当你觉得井水不犯河水时,当你觉得遥不可及时,你不会感兴趣,也不会往心里去。而某样东西一旦降落在你面前,并拦住你的去路,你才不得不重新审视它,以看清他本来面目。在卫君梅和郑宝兰看来,戛然而止这个词是大逆不道的,面目是狰狞的,是让人深恶痛绝的。天哪,原来什么词都有所指,什么词都是有用的。一把琴弹得好好的,琴弦嘣地一下断掉了。一只鸟在天上飞,随着一声枪响,那只鸟一头栽了下来。不,戛然而止的不是琴声,也不是飞鸟,是他们丈夫的生命。井下积聚的瓦斯,以爆炸性的灾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降临到众多矿工头上,瞬间造成了大面积的死亡。这种灾难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管青红皂白的毁灭性,不管你年龄大,还是年龄小;不管体力强壮,还是身单力薄;不管你的性格活泼外向,还是沉默寡言,它不由分说,照单全收。卫君梅的丈夫陈龙民,郑宝兰的丈夫周启帆,是众多被夺去生命的其中二人。在卫君梅和郑宝兰的体会中,她们丈夫的生命不仅属于丈夫个人,她们的生命与丈夫的生命紧紧相连,她的生活与丈夫的生活不可分离,她们的世界与丈夫的世界是一个整体。丈夫的生命终止了,她们的生命随之被撕裂,她们的幸福生活随之被打破,她们的世界犹如一下子跌进万丈深渊,眼前一片黑暗。
问题在于:丈夫死了,她们还活着;丈夫的生活结束了,她们的生活还得继续下去;丈夫的世界消失了,她们得重建一个世界。也就是说,一个阶段的终止,同时也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按道理讲,她们牺牲了丈夫,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今后的生活应当得到补偿,应当得到上苍的怜悯和眷顾,日子起码应当风平浪静一些。是呀,还有什么比年纪轻轻突然丧失相亲相爱的丈夫更惨痛呢!除了幼年丧父,老来丧子,恐怕没有比青年丧夫更悲哀了。惨痛复惨痛,悲哀复悲哀,让人难以接受的现实正在这里,因一个年轻矿工的失去,这三种人生悲剧会在一个家庭同时上演。拿郑宝兰来说,她失去了丈夫,小来失去了爸爸,公爹失去了儿子。卫君梅也是如此,是卫君梅失去了丈夫,慧灵慧生失去了爸爸,婆婆失去了儿子。难就难在,上苍似乎并没有怜悯和眷顾她们,她们的日子也没有平静下来,相反,荒漠连连,雄关漫道,她们的挣扎好像刚刚开始,磨难也好像刚刚开始。
陈龙民家住陈家湾,家里有房子,还有土地。他生前没在矿上买房子,没到家属院里去住,带着妻子儿女,还是住在自家的老房子里。他到矿上挖煤,妻子卫君梅在村里种地。他挖煤挣的是工资,卫君梅种地挣的是粮食,他们家钱和粮都不缺。陈龙民去世后,矿上为了照顾他们家的生活,给卫君梅安排了一份工作,在矿上的职工食堂当保洁员,也就是打扫卫生。一个月干下来,卫君梅也能挣七八百块钱。虽说有了一份工作,卫君梅还是舍弃不了她的土地。她的观点是,煤有挖完的那一天,煤矿也有关闭的那一天,而土地呢,只要地面不沉陷,只要不变成湖泊,就一直可以种庄稼,可以打粮食。说到底土地才是最可信赖的。井下是三班倒,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干活儿。食堂的炊事员呢,也是三班倒,啥时候到食堂都可以买到饭。相应的,食堂餐厅里的保洁员也分早班、中班、晚班,每班都有两个保洁员值班。因为三种班轮着上,卫君梅可以做到两兼顾,两不误。比如上中班,下午4点才上班,在4点之前的多半个白天,她就可以去种地。也许有人会说她这么干太辛苦了,卫君梅不这么认为。辛苦听来文绉绉的,像是一个书面用语,那是给别人预备的。她肚子里没有辛苦的想法,嘴里也从来不说辛苦。一个靠劳动吃饭的人,说什么辛苦不辛苦。除了让人家笑话。
这一片玉米,三天两天收不完。卫君梅刚要对郑宝兰说,今天就干到这儿吧,这时玉米地里又进来一个人,来人身穿印有龙陌煤矿字样的工作服,手持一把镰刀,径直向站立着的玉米走去。来人不看卫君梅,也不看郑宝兰,像是直奔玉米而来,眼里的目标只有玉米。这本是卫君梅家的玉米地,来人却像走进自家的玉米地一样,连跟卫君梅打个招呼都不打,直接跟玉米说上了话。他说话的办法,一个是砍,一个是杀,说话不及,他已经把结有棒子的玉米放倒了好几棵。
来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卫君梅和郑宝兰看在眼里,她们都认识这个青年男子。青年男子二话不说的举动像是把她们吓着了,二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她们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青年男子一步一步走进玉米地,一棵一棵把玉米放倒,竟像傻子一般,一点作为都没有。好像她们受到了一场奔袭,还未做出反应,就当了人家的俘虏。卫君梅又看了郑宝兰一眼,郑宝兰又看了卫君梅一眼,她们还是不知道怎样应对才好。女人就是这样,不管她们平时如何口齿伶俐,说话如何五马长枪,一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她们总是有些发蒙,脑子总是有些不够使。
慧灵喊了一声妈,卫君梅激灵一下,总算清醒过来,对青年男子大声喊道:蒋志方,这是我们家的玉米地,你干什么?
蒋志方所答非卫君梅所问,他说:我下班后又办了一点事,来晚了。
谁让你来的,没人请你来。我们家的玉米,我们自己会收,你走吧!卫君梅的口气是冷淡的,也是拒人的。
蒋志方没有走,也没有作任何解释,他只叫了一声嫂子,只管接着割玉米。他叫嫂子的声音有些低沉,还有些伤怀,仿佛千言万语都在里面。他毕竟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割玉米像割小麦一样,速度比卫君梅快多了。
1.《刘庆邦《黑白男女》:姐妹约定有三种人不能成为对象》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刘庆邦《黑白男女》:姐妹约定有三种人不能成为对象》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jiaoyu/21858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