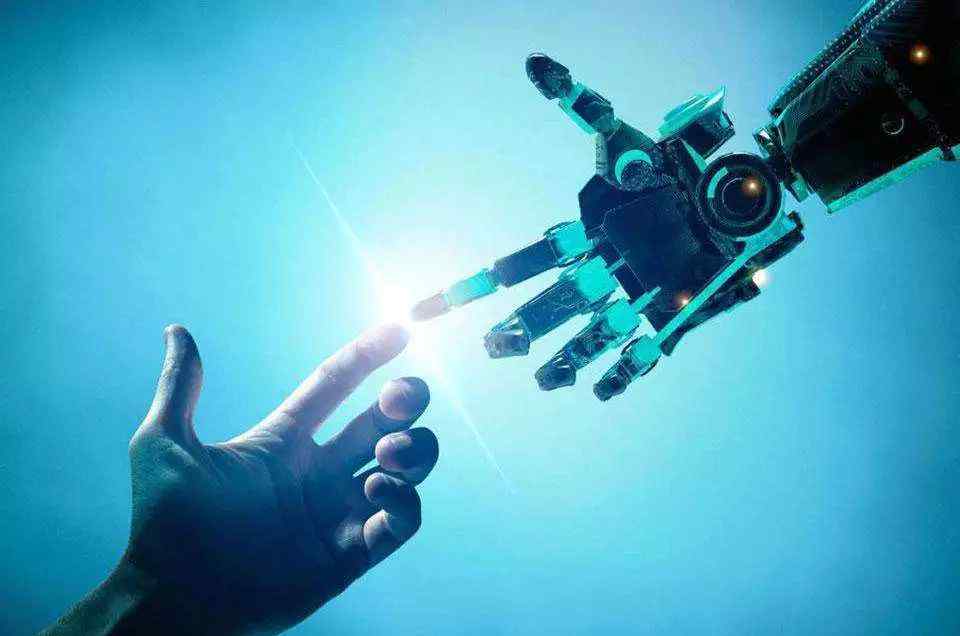奥井恩威佐(1963-2019)
翻译/郭娟
2019年夏季

Okui Enweizo,Kassel,2002;照片:Rysard Kasiewicz。
严肃的人从不使用最高级的修辞——至少我们受过这样的教育。但任何对Okwui Enwezor的认真评价,都必须依靠最高层次的形式。作为过去二十五年最具影响力的策展人,恩威佐认识到殖民主义对艺术史的暴力扭曲,他知道重塑一个“正典”话语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无畏的野心。他开始探索新的历史,构思一个新的当代,在这个时代里,他的视野和能力都是惊人的,可以在阅读中吸收——他的写作和他的展览一样重要。
当这位周游世界的尼日利亚馆长在3月15日因癌症去世时,我们无法马上意识到我们失去了什么。他的成就不胜枚举。很多人都会想起他在2002年策划的传奇的第11届卡塞尔文学展,或者是他在1994年与奇卡·奥凯-阿古鲁(Chika Okeke-Agulu)、萨拉赫·哈桑(Salah M. Hassan)和奥卢·奥吉贝(Olu Oguibe)共同创办的史无前例的杂志《Nka Journal of当代非洲艺术》。1996年,他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组织了划时代的“In/Sight:非洲摄影1940年至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成为了1997年约翰内斯堡双年展(和奥克塔维奥·扎亚一起)和2008年光明展的主要策展人。他一生中计划的最后一个展览,“埃尔·阿纳特苏:胜利的规模”,将在慕尼黑艺术博物馆展出,直到7月28日。
《艺术论坛》杂志邀请了一些朋友和同事写一篇纪念欧奎的文章,开始了另一个庞大的项目:试图梳理恩威佐遗产的规模。
阿德里安·派珀|阿德里安·派珀

Nka当代非洲艺术杂志封面,2011年秋季。
回想起来,他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必要的、不言而喻的,但对于那些在他之前缺乏机会和勇气去做这些事情的人来说,他的自由很容易被解释为一种轻蔑的姿态。但我知道这不是他的本意;他刚意识到需要做什么,就去做了:他看到没有平台可以吸引人们对后殖民时代非洲艺术家作品的关注,于是创办了这样一份艺术杂志;他看到所谓的国际展,无非是欧美“白”弟子的狂妄浮夸的展示,于是策划了一个又一个创新的、真正的国际展,更不用说他对审美创新的新的、急需的贡献了。他探索了以前从未探索过的领域,包括非裔美国人。
当然,他树敌很多。他无意中暴露了敌人的无知和庸俗。但就连他们也为他丰富而原始的自我表达所震惊,这种表达将艺术带出绝望,是创作灵感最深刻、最可靠的来源。他们害怕他看似神奇的力量,仿佛他可以挥舞魔杖,背诵咒语,然后,“啪”!突然,无形的另一方创造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艺术作品一件接一件地出现了。这些作品是如此的强大、精准、复杂,似乎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直到比赛结束,他们才因为害怕而压制住了自己的贬损攻击。此时的欧奎已经打破了艺术界许多根深蒂固的规则,他带来的危险已经无法控制。
太晚了。他重新定义了艺术杂志、收藏品、卡塞尔文学展、威尼斯双年展等的目标。没有回头路。在他之后,任何一个炫耀自己对当代非裔美国艺术的无知,或者对南美艺术、非洲艺术、印度艺术、中东艺术、中国艺术的无知的人,都不再是时髦的精英姿态,而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表现。愚蠢庸俗的人对此不高兴。他们所立足的地壳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所熟悉的人,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患有多发性骨髓瘤。每当我想起欧奎或者为他祈祷——我经常为他祈祷——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除了这种致命的疾病之外,我无法想象他为什么不能长寿,不能享受他所获得的声望——当他的成就的历史重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享受本应归于他的赞美和桂冠。他值得休息和享受,至少与他的名声和赞美相称。然而,人们不断试图诋毁和推翻他的成就,使他没有时间休息和享受。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名望和赞誉,但病情却越来越严重,尝试也越来越多。最后,这些挣扎耗尽了他的精力,这正是他们的意图;他所处的充满敌意和无处不在的环境让他只能选择离开,过早地从另一个出口离开,这是他自己的意图——在一个完全不同但未被探索过的领域里寻找休息和享受,那里不会有愚蠢和庸俗的人在后面追赶他。
他死得太早,他的死只是邪恶和不公。但我无法像他拯救我那样去拯救他。我谢过他,却无法报答他。我从远处观察,我担心他正被疾病一步步卷走,而对他重要成就的系统性抹除和诋毁却在加速,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媒体。我保持隐性的鼓励和支持是不够的,怕破坏他的隐私。我想不出什么话来说他处在致命的威胁中,而我却处在失去他的致命威胁中。我不能向他承认。我以他的名义在媒体上的反击太晚了,没有用。我愿意相信,他知道自己是被爱和被尊重的,他把这些爱和尊重带到了新的归宿。
阿德里安·派珀是居住在柏林的艺术家和哲学家。她的大型回顾展去年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幕,并参观了洛杉矶的哈默尔艺术博物馆。展览的最后一站原计划是慕尼黑艺术之家美术馆,但在去年12月奥库·恩威佐(Okui Enweizo)辞去馆长职务后,美术馆商业总监伯恩哈德·斯皮斯(Bernhard Spies)决定取消展览。
蒂姆·格里芬|蒂姆·格里芬

艾萨克·伊萨克·朱利恩和马克·纳什的《资本论清唱剧》,2015年;表演现场,竞技场,威尼斯,5月8日,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照片:安德里亚·阿威佐。
对我来说,艺术界没有什么比和欧奎聊天更有趣的了。无论我们的谈话开始时多么温和,最终都会变成——就像他曾经突然笑着评论的那样——“拼命寻找底部”。我相信这种快乐很大程度上来自编辑和作者之间的良好关系。十年内,我们与《艺术论坛》和其他出版物上的许多文章进行了合作。奥奎展览的魅力在于他们要一扫一切的野心——不管他在2002年讨论他在过去十年双年展文化余晖中策划的卡塞尔文献展时说什么,“打破全球话语的核心”;或者我们应该超越西方视角的限制,扩大我们对战后艺术的理解——但这种野心相当于他在任何日常谈话中的激情。
现在看看2015年欧奎策划的威尼斯双年展,或许对他的展览画册的设计有更好的了解。在专辑的开头,我们用了那么多篇幅摘录卢梭的《论社会契约论》以及相应的手稿。即使是最抽象、最雄心勃勃的对文化及其可能的社会组织结构的理想化想象(无论在欧奎的构想中是多么迫切的需要重新发明),也仍然只是手写的文字和个人笔记。这个大型展览围绕着个体主体的重要性展开,他的策展实践始终是针对对象的。其实,欧奎策展的意图——这是他自己的背景——也许可以用他在讨论自己策划的威尼斯双年展时的一个基本观察来概括:“生产艺术就是生产意义”,而对于大型展览的组织,“全世界不仅渴望了解人类处境的矛盾,也渴望意义”。欧奎作为策展人和个人的出色表现,一部分在于他的视野不局限于艺术领域,如果他的目标是扩大艺术的意义,那么他的视野将延伸到它的生产条件——科技、经济和政治——正如他在世界各地完成的许多项目中多次观察到的那样,通过这种方法扩大展览生产的规模,并通过超越传统模式迫使观众做出反应,让观众没有回避的余地。在欧奎的实践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联系:无论他在每一个个体观众中创造了什么意义和权重,这些都成为了共同经验的基础,供大众讨论。在奥尔基的地图上,艺术可以提供——如果有强烈的欲望——一个公共领域迫切需要的港湾。
然而,正是在这种公共语境下,欧奎几十年的作品始终蕴含着紧迫感的种子。在他最早的写作中,传达了一种极其不稳定的氛围:一切都是“变化的”、“未完成的”、“未实现的”。当然,世界总是这样。然而,欧奎的独特重要性体现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预见并捕捉到了全球化和世界重组的最初曙光——种族隔离的结束、冷战铁幕的落下、生产方式和及时性的变化——并指出全球展览生产不断面临回归旧模式的危险,从而失去了对这些变化的激进和微妙的感知。回顾我们的交流,我对欧奎早在2002年提出的警告感到震惊。他指出,全球策展实践中最具创造性和社会参与性的方面一直在下降,因为人们通常讨厌在社会图景中提出更大的艺术问题。在艺术中创造意义的机会一直处于危机之中。
这样一个高度意识到这种不稳定性的人——并善于将艺术置于更大的社会语言学结构中——无疑应该是一个诗人。他应该用céolite的文学理论框架来描述一种“身份模式的不断改写”,就像他在描述自己的策略时暗示的那样,这不是“反对,而是……全球文化的公开辩论”。语言及其社会结构可以成为讨论的主题,包括无数的意义和路径。但是让我们再回到这个人身上。有时候我觉得O 'Que可以想那么多未来,因为毕竟他有那么多过去:尼日利亚,新泽西,纽约波多黎各社区,纽约,等等。克里奥尔语在这样的人身上应该有独特的回响,因为他有那么多的过去,同时,他也为我们打开了那么多的战线。
蒂姆·格里芬是纽约厨房艺术室的执行董事兼首席策展人,也是《艺术论坛》的特约编辑。
史蒂夫·麦昆|史蒂夫·麦奎因

史蒂夫·麦昆,《加勒比海的飞跃/西部深处》,2002年,超8 mm和35 mm三频数字视频,颜色,声音,28分53秒;12分6秒;24分12秒。《加勒比海的飞跃》,来自第11届卡塞尔文学展。
1999年,欧奎打电话给我,说他被提名为第十一届卡塞尔文学展的策展人。这是一个很长的电话。我们谈到了各自的女儿,当时她们才一岁,这个展览将如何改变她们的未来。
确实如此。
欧奎去世前两周,我坐在慕尼黑一家医院的病床旁。他很虚弱。他开始大声朗读诗歌。这种读书体验就像吃了最美味的水果。咬了一口,汁水流到下巴,他一边仔细品尝每个单词的发音。
他最后读了奥克塔维奥·帕斯的《皮德拉·德·索尔》(1957),摘录和编辑如下:
我想继续前进,走得更远,但我不能:
这个时刻一次又一次地滑向其他时刻,[……]
一棵晶莹的垂柳,一棵水汪汪的黑杨,
一个高高的喷泉在风中漂浮,
一棵直树在跳舞,
蜿蜒的河流
向前,向后,迂回,总是到达
去哪里;
星星还是春天
平静的脚步并不匆忙
河水闭上了眼睛
预言流传了一整夜,
在波浪中聚在一起
一波又一波,
直到它被掩盖,
绿色的主人永远不会变黄
就像天空华丽的翅膀空,
在未来密集的岁月里
和不幸的荣耀
像鸟一样跋涉
在朦胧的枝头歌唱,
伴随着歌声和不稳定的幸福
痴呆树
预兆从手掌中逃脱
鸟儿在晨光下啄食
一个形象就像突然唱歌,
风在火中歌唱
眼睛挂在空
看看这个世界及其山脉和海洋,
像一团被玛瑙过滤的光,
大腿轻,腹部轻,海湾轻,
太阳的岩石,多彩的身体,
快速跳跃日的颜色,
闪烁和物理时间,
因为你的物质世界变得有形,
因为你晶莹的世界变得明亮,
我沿着你的腰走
就像沿着一条河,
我沿着你的身体行走
就像在森林里散步一样,
我顺着你敏锐的头脑走
像一条通向深渊的山路,
我的影子在你白皙额头的出口处
我摔成碎片,我拾起碎片。
没有身体继续摸索寻找,[……]
你像一朵云,你像一棵树,
你们都是鸟和星星,
你就像一把剑的边缘
刽子手的血杯,
就像推动灵魂前进,纠缠着它
让它和自己的常春藤一样,[……]
我想继续前进,走得更远,但我不能:
这个时刻一次又一次地滑向其他时刻,
我曾经有一个梦,梦见一块我做梦也想不到的石头,
结果却像石头一样
听到他被囚禁的血的歌声,
大海随着光的声音歌唱,
城墙互相让步,
所有的门都被摧毁了,
太阳开始从我的额头上消失,
睁开我紧闭的眼睑,
剥去我生活的包装,
让我离开我,离开我自己
千年沉睡之石的幻境
当他镜子的幻象重现时,
一棵晶莹的垂柳,一棵水汪汪的黑杨,
一个高高的喷泉在风中漂浮,
一棵直树在跳舞,
蜿蜒的河流
向前,向后,迂回,总是到达
去哪里。[1]
评论:
1.奥克塔维奥·帕斯,《太阳石》,1957年;《太阳石》中译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赵振江译。
史蒂夫·麦昆是居住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艺术家、电影导演和剧作家。
ARTFORUM.COM.CN
1.《恩维 奥奎·恩维佐(1963–2019)| ARTFORUM杂志》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恩维 奥奎·恩维佐(1963–2019)| ARTFORUM杂志》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junshi/15653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