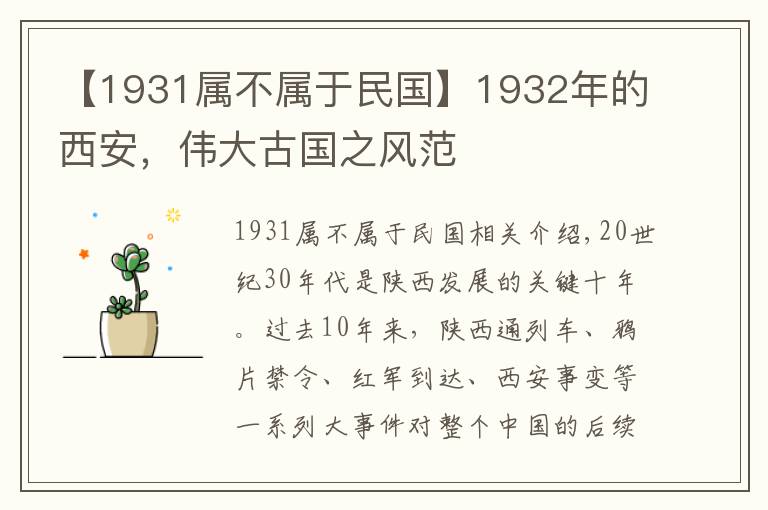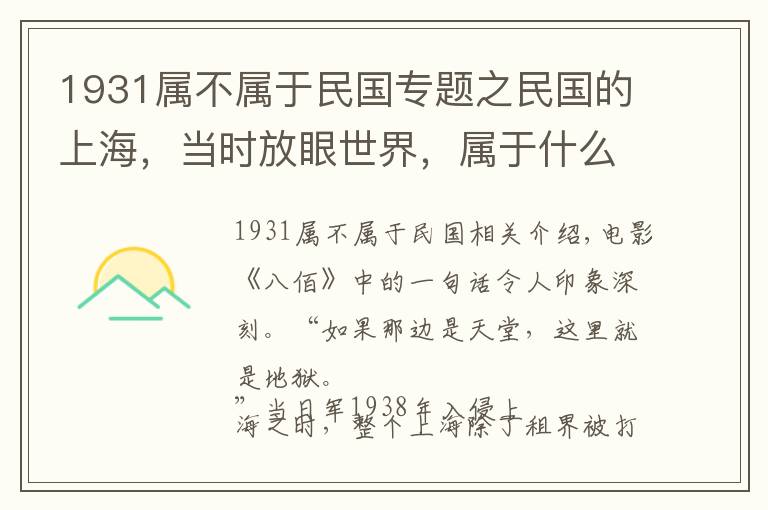1931年江淮特大水灾,5270万人受灾,60万人死亡。
(最大的估算为受灾1亿人,360万人死亡)三分之二国土上的百姓流离失所。
此灾造成25亿经济损失,是当年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3.7倍。
这般数字,代表的是那一代中国人,几乎每人都遭遇了相当的苦难。
家破人亡、卖儿鬻女、妻离子散的个体悲剧,发生了上千万次。
1931年8月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书中疾呼:“此次灾情之广,几亘全国,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被难人数,至少在五千万以上……今日中华民族,实已濒九死之绝境。”
实际上从当年5月后,全国各地的集中性降水已经不容乐观,长江流域全月平均雨量达到361mm,是历年同期的2倍以上。
7月26日,武汉市区岌岌可危,1日后一处决堤,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8月2日,武汉市区被江水吞没,除日租区外成一片汪洋。
8月13日,武昌“沦陷”。
8月15日,日租区“沦陷”。
8月17日,汉阳“沦陷”。
8月19日,汉口水位达到江汉关建关以来最高纪录:53尺6寸。
直到9月初,积水才退却。
武汉市区
武汉三镇化为一片泽国,水最深处可达3米,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月有余。
对于此时生活在武汉市内的市民而言,这是无穷的悲剧。近80万灾民中,16.3万户被淹,4.5万户住房损失,无家可归;2500人被淹死;20万饥民无工可做;每天上千人死于饥饿。
而这般灾情放大到全国三分之二的国土之上,则是同时发生的更多的个体悲剧。
这场水灾的灾情遍布苏、浙、皖、湘、鄂、赣、豫七省,一些县全县90%人口受灾。
汉江难民集中地
金陵大学抽样调查显示,七省农村40%人逃难,这其中20%的人行乞,60%为男性。
若估算经济损失平摊到个人,则每个灾民损失457元,是当时西人估算中国家庭生活贫困线的4倍左右,真可谓人人倾家荡产。经济的损失后,却是物价的普遍上涨,甚至就连棺木也是一应难求,一些商贩为了生存甚至把其他死人从棺材里人扔走,给新的死者使用。而受灾更为严重的灾区,既无土可葬,亦无棺可安。无奈的人们只能将大批尸骨挂在树杈上,痛苦的看着亲人一点点的腐烂。
疫病盛行、灾荒遍地,这地狱般的人间即便是活下来的人也难保健康,来年的生存又何以谈起。
人们开始不理智,冲进田地里哄抢麦苗、秧苗,只为活过今日。
如此绝望之际,灾民急需政府和其他地区人民的援助。但如今看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慈善团体的援助,都难以解决这千万的苦难,只因那世道时局,短期内无人能救。
1931年9月18日,武汉城区的积水已然退去,人们走上街头舔舐着灾难刚刚过去的伤口,东北三省却突发骤变,数万日寇犯边。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进犯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却只能签下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东北沦陷,上海被攻。
民国政府顿失两臂,一个是工业基础雄厚、未曾受军阀混战荼毒太深的东北;一个是民间商业活跃,外贸发达的上海。此等状态,对五千二百七十万灾民来讲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民间捐款集中的上海损失了十分之四的市政收入,原本不堪的捐款来源更加岌岌可危,上海甚至都需要外来的援助,度过难关。
正如《申报》1932年1月的一篇社论所言:“际此全国百业凋枯之时,国人助赈能力,至为有限……惟自暴日入寇以来,举国沸腾,国人急谋对外,对于内灾渐渐不见其注重,此诚五千万灾黎之重厄也!”
而此时国内的战争仍然在继续。
刚刚在1930年结束的中原大战,是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的。双方在中原大地上投入了近百万的兵力,死伤三十万人。战场所及,兵燹不断,百姓极苦,痛不欲生。
1931年8月4日,武汉市区被水“侵略”的第二天后,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蔡和森在广州被捕牺牲,年仅36岁。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南昌督战,对工农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8月17日,蒋介石飞往上海,为宋美龄的母亲执绋。
9月1日,蒋介石发表电文《呼吁弥乱救灾》,称:“中正为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
再加之,放眼国际,1929年以来爆发的经济危机正在持续,中国遭到了巨大的冲击。时人推断中国受此影响,损失超10亿元。
时局已然如此,此时生活的中国人,又有谁不痛苦,又有谁没有在经历人生的悲剧。
他们被时代的车巨轮压过,只留下尺寸的血肉,和卑微的呼喊声。
时人痛骂:“一批当国的人,没有哪年不用兵打仗,政府的心目之中,只有伟人、有政客、有武夫,并没有看见百姓!”
事实也正如他所言那般,民国的政府的种种举措,很难说他是一个以百姓为本的革命政府。
首先是财政开支。据杨荫薄的《民国财政史》可知,民国政府财政第一大开支是军费开支,平均占年支出的45.82%,最高一年达87%,最低的1935年也达到了27.1%;第二大开支是债务开支,约为39%。1931年当年的财政支出中,债务开支加上军费开支合计为财政支出的79.4%,次年两项支出为76%。
剩下20%上下的财政支出,要摊给教育、摊给科技、摊给政府雇员、摊给水利等等,以至于这些领域的工作人员欠薪情况严重。北大等4所北京地区的大学5个月未曾发过一分钱的工资;外交部4个月没发薪水,连煤炭的钱都不知道上哪儿弄。东南富省江苏省也不堪重负,数百万的财政窟窿不知道上哪儿填,省长叶楚伧干脆撂挑子不干了。
其次是官员的贪腐和无能。这点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印象,但请看以下这些具体的案例:
1933年8月28日,《申报》揭发湖北省早先用于修筑堤坝的款项被贪污挪用,数量大概在350万元上下。当时的人们估算,如果在7月份武汉暴雨之际投入33万元加固堤坝,就可以防止武汉三镇被淹1个多月的悲剧。而这钱本已经备好,却被腐败的官员上下其手,贪了个干干净净。
实际上这笔堤防款高达2000多万元,湖北上的全体官员只拿了“小头”,而大头则被大官僚大地主大买办资产家拿走。1930年中原大战,宋子文挪用了1000万元充作军费,还将这笔钱的余款打到川江龙公司做鸦片生意,结果血本无归。
江苏省水利经费常年被挪用贪污,共计77.7万元的巨款在数年内“花的”只剩下1.1367万元。民间民谣称:“黄河决口,黄金万斗”、“导淮好心肠,县长盖楼房,乡长盖瓦房,保长喜洋洋,甲长两头忙,百姓泪汪汪。”
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一个官员想要贪这笔钱可不要太简单。此次大水,江苏一工务所所长李仲强借口账册被毁,12万工款用作何处无人晓得,而堤坝却不见修起,民众咬牙切齿也无可奈何;淮安水利局长夏防费“开价”33万元,实际所用仅数万。
河工人员既贪腐又无能,对所辖事务可谓“一问三不知”。时人言:“河工人员对于最大决口,迄今不但未定堵塞计划,甚至尚未实地测量。若问每一决口宽度若干,深度若干,河工人员亦瞠目不知所答。”至于预防性的水利工程、植树工作,虽然见到了计划和拨款,但实际上用“几乎未做“来形容,并不过分。
所以,这般天灾中亦有无穷无尽的人祸,民国百姓难以用“不满意”来形容政府的行为,而应当是用“绝望”来形容,哪儿天政府突然做了好事,倒是破了天荒。
但灾情发生后,并非人人昏聩,人人熟视无睹。种种灾民的惨状通过方兴未艾的大众传媒渲染后进入千家万户,一名记者发文题为:《汉口是何世界:人居危蝼蚁鼠争栖,水面头颅呼售馒头;数千万灾民,生无安身之所,死无葬身之地,鹄待赈济,岂容观望?》
慈善界人士奔走疾呼,四处筹款。中国红十字会发乞赈词,号召“节省一元之费可救一人之命,百元之费可救一村之命,聚沙作塔,集腋成裘。”上海筹募会发乞赈词“伏望父老昆弟,本己饥己溺之宏怀,大慈大悲之愿,迅解仁囊”。
《大公报》甚至专开板块,欢迎普通读者为政府建言献策、亦有不好听的痛斥时政之语。工赈、农赈、医疗卫生、标本皆赈……种种意见都在救灾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即便是微小的个体,也参与到了赈灾过程中。
小学生高书海撰文《小朋友快助阵》呼吁小朋友“愿将自己的钱财积蓄起来,救济那些受灾的同胞吧!!”
一位“避居深山”的老者听闻灾情汹涌,他“心潮起伏、坐立不安”,于是扶杖下山,卖掉自己的房产,捐出20万元的巨款。
一名军人读《大公报》后同情灾民,便和同事凑齐28.77元捐赠给大公报;连长刘震芳同全连士兵,捐款10.46元。
一名供职于洋货铺的商铺学徒月薪不足1元,却捐了足足1元;报贩刘一鸣每天只能挣一二百文,却决定将三天收入连本带利共大洋1元、小洋4角、铜元26枚捐给灾区;一名女仆省下了看病的钱,将20多日的工钱共5元悉数捐赠;天津租借一车夫每日收入132铜元,他“搜索腰囊及床头席底”,捐助1.6元,自己只剩下了六角;乞丐老于把五天才能讨来的一角钱捐到了报馆;天津残疾院的残疾人剩下70.744元捐给灾区。
朱庆澜
而国际社会,也多有慷慨之举。
日本以天皇名义捐赠10万日元;罗马教皇捐赠25万里拉,意大利政府也统一将庚子赔款中20万美元还给中国;美国贷给中国45万吨美麦。
辛亥元老朱庆澜此时出任救灾会灾区工作主任一职,作为民国的慈善先驱,百姓对他极为信任,于是便把大批捐款捐到他的手中。朱庆澜亲赴灾区一线,并聘用上海的著名会计师撰写审计报告,在报纸上进行公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称他“其慈祥恺悌之人格性情,真足以生死人而肉白骨。”
国民党决定全体公职人员捐献3个月工资中的5%~20%,也出了相当的一份力。
政界、商界、宗教界、海外的同胞华侨甚至是上海滩的娱乐界都被动员了起来,参与到赈灾当中去。
影星胡蝶也参与了慈善义演
国府主张官民通力合作,于是绕开了常设的赈委会,新成立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聘用中外、民间人士加入到救灾的中枢。这一方面有动员力量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有绕开腐败的地方政府的想法。
从实践上看也是如此,国府救灾会成立了自己直接领导的地方组织,而地方官员只充当辅助作用。江北赈务委员会起草的“规程草案三则”中,甚至赤裸裸的规定查放急赈“不得假手县长及区长、村长、以符本会自查自放之本意。”朱庆澜甚至直接说“从前官赈假手地方管理,流弊滋多,此次均应痛加革除!”
正是在救灾委员会的运转之下,仅有的赈灾款才被更好的利用了起来。除了办收容所、办粥厂,为灾民提供免费的饮食和医疗物资、生活物资之外,这次救灾还体现了“标本皆治”的思维,即用以工代赈、以农代赈来进行“积极救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如此这般声嘶力竭,振臂疾呼,最终集中了多少赈款呢?
救济委员会到灾情结束,总计支出7000余万元;民间筹集的国内外捐款共计770余万元。
而金陵大学的调查报告显示,如果要让灾区彻底恢复生产,则需要15亿元;据国府赈务委员会估算,需要维持灾民生存的粮食总计8.4亿元。
即便动员了整个社会,也只能帮到灾区分毫。这便是1931年江淮水灾最大的悲哀。
朱庆澜发表《为被水灾民最后求救书》中,无奈的指出这样的援助“岂只杯水车薪,直如沧海一粟!”社会各项物资若平均到灾民,按照江苏赈委会的统计为春赈平均每户3.14元,冬赈平均每户麦54.79磅、衣服0.65件、面粉0.06袋、红粮0.8袋。金陵大学的调查报告估算全国情况,灾民每户所得赈款为“大洋六角”。
如果是遇到这般情况,你会选择每个人都给一些少有的资源,还是把资源集中的给一些灾民呢?
这就是一个极端情况下的伦理道德难题,无论选择如何都是悲剧,而国府当时选择将赈款平摊,让尽可能多的人拿到赈款。
让我们来看江西的一角。
灾情发生后,国府救灾会成立的江西收容所收置灾民20249人,不到三月死亡2476人,一年后近半数的灾民死亡,除了疫病困扰外,大都被活活饿死。
此时湖北省立医院共有医生10人,护士和助手30人,而他们面对的是2万人名感染疾病的病患,和20万武昌、汉阳灾民。此情此景,他们只能哀叹:“事实困人,徒深浩叹。”
上海筹赈会的宏伞法师广施粥厂,灾民纷至沓来。但他看到的是许多人挤到桥下淹死、拥挤踩踏而死。有一些远在乡村的灾民听说他在施粥,拖儿带女空着肚子跑到县城,结果一碗都没有喝到,“沿途倒毙,在在皆有,情状至惨。”
当年的收获只有往年一成,而明年的耕种更是毫无办法开展。农具被毁、青壮年劳动力流离失所,导致了严重的春荒。
1933黄河决口、1934东南特旱、1935水旱交替、1937日寇全面侵华……
盘在那个年代,普通的中国人心中的总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到底怎样,我才能够活下去?”
外有强寇犯边,杀我同胞。
内有饿殍遍野,天灾无情。
政坛党争不断,国内战争不断。
这就是1931年,中华民族面临的血淋淋的现实。
时至今日,在这片“饥荒的国度”中,我们已经基本根除了饥饿和贫穷。
但中华民族始终没有摆脱灾难,人类亦如此。
1931年这般苦难的记忆镌刻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
即便今日的人们有了许多的快乐与满足,
但那场洪水却时常被人们被人们提起。
树杈上腐烂的尸体、夺食麦苗的饥民;
卖掉财产捐款的老人、欲救世却暂时无可奈何的卑微个体;
内斗的军阀,吸血的官僚;
上海滩的阔太阔少、江西收容所活活饿死的灾民;
这两极背反的众生相总能给人深刻的印象和反思。
如今我们在巨大的尸山血海之上,走过了苦难的近代史。
我在今日提起这般往事,只是希望大家能回忆起那份“恐惧”。
“恐惧”能带给人勇气,亦能带来智慧。
参考资料: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救治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的考察》
《1931年江淮流域水灾及其救济研究》
《民国财政史》
《申报》
《大公报》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
1.《【1931属不属于民国】1931江淮大水:5270万人、三分之二国土受灾,救灾时逢九一八事变》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1931属不属于民国】1931江淮大水:5270万人、三分之二国土受灾,救灾时逢九一八事变》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lishi/20661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