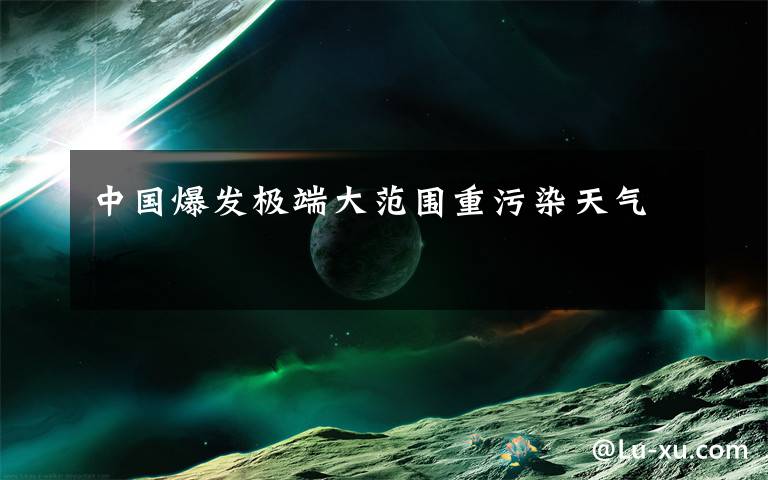▲“波斯字母”
第二册见于《地理》第二卷,内容与第二册相同,但文字略有不同。据考证,这份笔记写于1734年至1738年之间,因此可以推定这是第二次编辑的手稿。这时,孟德斯鸠正准备写《论法的精神》。如果不是巧合,孟德斯鸠在二十多年后又整理出这张纸条,恐怕是为了写《论法的精神》。
与黄交谈是孟德斯鸠第一次与中国人直接接触,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1713年11月15日,孟德斯鸠的父亲去世。他回到波尔多哀悼了八年,直到写完给波斯人的信才去巴黎。黄因肺结核于1716年在外国去世。
孟德斯鸠在意大利旅行时遇到了传教士芙凯。法国人傅圣泽,1699年在中国传教,在江西福建生活了二十年。1720年被教会送回欧洲,1729年在罗马与孟德斯鸠相遇。孟德斯鸠在罗马逗留期间,多次见到傅胜泽。根据他的《意大利游记》,傅圣泽是他在罗马遇到最多的人之一。随笔记录了他们在1729年2月1日的一次谈话,其中涉及到中国历史和伦理道德。
1737年6月2日,孟德斯鸠在巴黎会见了传教士阿塞马尼。此人是法国派往叙利亚的耶稣会士,曾到过中国。在这次谈话中,他向在华传教士介绍了孟德斯鸠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议。

▲德美朗
法国皇家科学院书记德·麦兰是孟德斯鸠的老朋友。早在1721年,他们就有书信往来。德米兰和当时的很多法国学者一样,非常关心中国。他经常和来中国的传教士通信。1730年至1740年间,中国传教士帕瑞宁(中文名巴多明)写给他的信被收入《耶稣会士简章》,其中介绍了中国的科技、历史和现状,并谈到了中国的一些缺点。孟德斯鸠和德米兰经常谈起中国,直到1755年孟德斯鸠去世那一年,他们谈起中国,争论激烈。孟德斯鸠事后深感不妥,写信给他的另一个好朋友瓜斯科,请他代表自己向德梅朗道歉,以免让这场争论影响他们的友谊。
从1713年与黄的谈话到1755年与德梅朗的争论,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兴趣盛极一时,长达40多年。这一时期,正是欧洲传教士在华达到了中国礼仪之争的高潮,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著作。马莱布兰奇、德·苏吉、普瓦夫尔等学者关于中国的著作也在这一时期出版,更不用说1729年出版的路斯·艾特的著作了。孟德斯鸠有机会讲讲这些关于中国的书,但我们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证实。
孟德斯鸠没有机会亲眼看到中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应该说是相当丰富的。这为他研究和探讨中国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并把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作为建立自己理论的原料和基础之一,这使他和伏尔泰、魁奈一样,被公认为18世纪最了解中国的法国人。
02
早在1713年,当孟德斯鸠接触到有关中国的材料时,他对中国的怀疑和否定就显露出来了。他在中国泰莎读孔子时,经常不同意作者白英利对孔子思想的分析。他说:“他(白英利——作者)带着偏见解释汉语术语来支持他的论点;我发现了很多谬误。
这种态度在他与黄的谈话记录中更为明显。他说:“让我们摆脱偏见。我们把他们(中文——作者)说得这么好,这是一种夸张。”“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很神奇,和尚怎么会在一瞬间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
后来他在读传教士的著作时,经常对他们描述的中国表示怀疑。例如,他在读《中华帝国的全志》时写道:“在杜·赫德神父介绍的八个省中,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惊人的、美丽的、美丽的...大自然真的只有美,一点也不丑吗?”
孟德斯鸠的疑惑并非没有道理,其中有些颇有见地。问题是他用欧洲的习俗和心理来推测中国,所以他的怀疑主义往往反映了他的偏见。相反,他深信中国的各种弊端和丑恶现象,如饥荒、弃婴、酷刑等。,甚至信了中国吃人肉这种鬼话。
因为孟德斯鸠对中国并非没有偏见,虽然他与伏尔泰等人关于中国的接触大致相同,但他对中国的看法却与伏尔泰等人大相径庭。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暴力专制的国家。
众所周知,孟德斯鸠将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制和专制政体三种。共和政府以道德为原则,君主制以荣誉为原则,专制政府以恐怖为原则。
孟德斯鸠研究的共和国大多是古代城邦。这种政体虽好,却是历史遗迹;君主政体是他心目中现实中最好的政治制度;他不遗余力攻击的是他所痛恨的专制政权。
在他看来,东方国家大多实行专制,中国也不例外。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原则是恐怖”。在他看来,中国君主把宗教和世俗的权力结合起来,对臣民实行残暴的独裁统治,使人民根本没有自由。皇帝经常以叛国罪对待他的仆人和人民。“任何事情都可以作为借口,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摧毁任何家庭。”在他看来,中国的刑罚是严厉的,烧灼、凌迟等酷刑是骇人听闻的,往往涉及九家。人们在颤抖,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他认为中国人口众多,耕地不足,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每次饥荒,到处都是饥饿。即使在正常年份,由于温饱不足,也无力抚养后代,弃婴随处可见。他还认为,中国既没有议会,也没有三权分立,因此它具有独裁政权的性质:“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反复无常的爱好统治那里的国家。”
总之,中国绝不像传教士描述的那么美好,也不像伏尔泰等人所赞美的那么理想。相反,“中国的专制主义,在万恶不赦的压力下,愿意给自己带上枷锁,却徒劳无功;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自己,变得更加暴力。”。
孟德斯鸠肯定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但根据传教士提供的材料,他将中国与一般专制国家区分开来。他写道:“如果帝国的大使有一个威权政府,那么这是所有威权政府中最好的。”这句话写在他不打算发表的笔记里,挺直白的。在他发表的作品中,他委婉地说:“由于特殊情况或独特情况,中国政府可能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腐败程度。”

▲传教士画的中国地图
那么在他看来,这些“特殊情况,或者说独特情况”是什么呢?
首先,孟德斯鸠给专制政权下了一个定义:“专制政权既没有法律也没有规定,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任性的性情来领导一切。”在另一个地方,他说:“一个专制国家没有基本法律,没有法律保障机构。”
孟德斯鸠认为,中国在这一点上的情况相当特殊。虽然没有他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特别是以限制君权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法,但是中国有类似法律的道德、礼仪、习俗。
他说:“他们的习俗代表他们的法律。”
这种法律的主要目标是和平,是让人努力,让他们平静的生活。为了和平,应该提倡服从。因此,虽然君君、大臣、父亲和儿子属于道德范畴,但他们在中国具有法律效力。老百姓勤劳勤劳,生活更容易得到保障;如果人民能得到足够的食物和衣服,国家就会相对和平。他认为,这部集礼仪、风俗、道德于一体的法律,是中国古代君主制定的,几千年来一直有效。历代皇帝都要尊重它,人民也习惯遵守它。所以中国是一个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法律的国家,和其他专制国家不同。
其次,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人口众多,人民生活贫困。人虽然勤劳,地理气候条件好,人可以衣遮体,吃饱饭,但是生活水平很低,几乎没有储备。天灾人祸一旦发生,就没有生计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统治者过于暴力,很容易引发民众的反抗。一旦发生叛乱,生活贫困的人民就会对一切做出反应,君主就会失去他的帝国和生命。在其他专制国家,即使行政暴力,因为人民没有饿死,也不会冒险起来。
中国的君主面临着随时可能爆发的起义,所以他们必须对专制统治进行克制,以防万一。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1)不要在欧洲实行税包制度,以免税包人剥削人民;每当有饥荒,皇帝也下令局部减税;(2)政府鼓励种田、织布、兴修水利,增加产量,防止人民挨饿。为此,皇帝每年春天还实行并举行亲农仪式;(3)不实行卖官封爵制度,而是用科举选拔学者,让各级人民都有当官的机会;(4)朝廷有专谏陈辟过错的谏官;建立对各级官员的监督制度,奖罚分明,所以政治相对宽松;(5)倡导一套以儒家为中心的伦理,以减轻法律的强度。
第三,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防止人民造反,中国统治者建立了土地私有制。这就是“中国有一个好政府,不像其他亚洲国家那样衰落”的原因

▲中国皇帝乘车旅行
第四,孟德斯鸠认为,由于气候的影响,中国人容易卑躬屈膝,所以以孝为主要内容的伦理观念源远流长,在中国根深蒂固。统治者将孝的观念运用到政治中,要求民众尊敬君主如其父,而君主对待民众如子女;整个国家就像一个亲戚,从上到下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孟德斯鸠说:“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经营家族的思想为基础的。”因为这种伦理观念深入人心并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就少了对抗性,中国的专制制度也比其他专制国家宽松。
虽然中国有许多非专制政权的因素,但孟德斯鸠并没有改变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看法。他可以肯定中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但他在政治制度的性质上从来没有放松过。
当时,许多人认为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国家相对稳定,政治制度优秀。孟德斯鸠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这样,纯粹是地理条件使然。中国的边界不是海就是山和沙漠,外敌只能从北方入侵,安全更有保障。
他进一步推断,如果欧洲国家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它们的历史肯定会比中国长。孟德斯鸠认为,这也是中国长期保持统一的地理原因。虽然分裂,但很快又恢复了统一。第一,中国以长江为天然屏障,分为两部分。由于气候原因,北方人好斗好斗,南方人温顺胆小。北方人一旦渡过长江,不需要长时间的战斗就能迅速控制全国。南方人习惯服从命令,不容易分裂。第二,中国饥荒频繁。一个省缺粮的时候,其他省的救济很难生存。所以各省都是靠外省,缺乏相对独立性。统一局面的长期维持也得益于此。
由此不难看出,孟德斯鸠确实看到并承认中国有很多优点,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一些威权政权不应该有的或不具备的优点。但是,他总是用地理、气候等客观原因来解释,虽然这些解释并不总是令人信服。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的结论在他的著作中从未动摇过。
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当然不限于政治制度。他对中国的历史、哲学、宗教、人口等等都有很多论述,有些颇有见地。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省略。
03
关于如何评价中国,为什么孟德斯鸠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有那么大的不同?有学者讨论过这个。早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人卡尔卡松就指出,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等人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在于孟德斯鸠阅读了一些商人和外交使节的游记。他们的作者要么没有深入调查就访问了中国,要么敌视中国,肆意夸大中国的缺点,不反映这个国家的真实面貌。孟德斯鸠从这些书中对中国的认识与伏尔泰对中国的认识是不同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这种游记真的影响了孟德斯鸠的中国观。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他对中国的不良印象,不仅来自这样的游记,还来自他一生中接触过的唯一一个中国人黄。
孟德斯鸠从黄那里得知,中国远没有那么美好。黄说,中国的刑罚是严厉的,一年以后执行死刑的时候把犯人切成六十多块,切到最后一块死,否则就把刽子手处死。他还说,中国新皇帝继位时,第一个皇帝的三宫六院都被送到市场上公开出售。这个说法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口中,当然会给孟德斯鸠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对传教士所描述的中国的美好事物产生怀疑。
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否定态度并不是因为他读了游记。
这是因为,首先,孟德斯鸠在第一次接触到关于中国的资料时就表现出了明显的怀疑态度,而此时他还没有读过关于中国的游记。他于1713年在中国泰莎读孔子时所作的笔记,以及同年与黄谈话后所作的笔记,均可证明。
其次,说到游记,对孟德斯鸠中国观影响最大的是孟德斯鸠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安森的《环球游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正在读安森勋爵的神奇的书……我现在正在读,以后还会再读。在我看来,这本书有很多启示。”
这个游记对孟德斯鸠的影响可以由此看出。然而,安森的第一版游记是在1749年。当时不仅《波斯人的书信》出版了20多年,而且《论法的精神》也出版了一年。也就是说,孟德斯鸠在写这两部名著时并没有使用安森提供的材料;换句话说,安森的游记对孟德斯鸠中国观的形成并没有起到重要作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孟德斯鸠的中国观,基本上是在安迅游记出版之前很久就形成的。
在这一点上,顾·阿斯戈的回忆提供了证据:“安森游记出版时,他(孟德斯鸠——作者)大声喊道:‘啊,我早就说过,中国人没有耶稣会士们想让人相信的那样诚实。’据我们所知,孟德斯鸠对安森游记的使用仅限于在1758年版的《论法的精神》中增加一句话:“我也可以找一个名人,安森勋爵,作为证人。”
相比之下,与孟德斯鸠对中国持有不同看法的伏尔泰等人,也读过这类游记,但并没有接受作者对中国的看法。魁奈在《中国的专制政权》一书中,曾问孟德斯鸠为什么不信任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到过很多省份的传教士,而信任只在中国呆了很短时间的商人。
众所周知,《耶稣会士全集》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并不是一味的赞美中国。在他们的信中,巴多明和其他人谈到了在中国看到的许多不良现象。但是,对于同样的事实,由于每个人的基本观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比如雍正帝,曾经杀了两个天主教王子。孟德斯鸠就此事写道:
巴多明神父的信描述说,皇帝惩罚了几个王子,因为他们皈依了基督教,这让皇帝不高兴。这些信件向我们展示了那里经常实行的暴政,以及按套路即无情地摧毁人性的概况。
伏尔泰评论了同样的事实:
耶稣将为许多中国人而被杀害,特别是为帮助和善待他们的两位至亲周。这些祭司来自天涯海角,让中国皇室不高兴,不放心;两名王子被判死刑。
魁奈更进一步。他驳斥了孟德斯鸠的说法:“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因宗教原因惩罚了大量烈士...但这件事与中国的专制主义无关……”

▲魁奈
事实上,当时关心中国的人所阅读的资料,无论是伏尔泰、奎尼还是孟德斯鸠,主要是《耶稣会简集》和《中华帝国的全志》。可以看出,即使材料相同,由于读者的观点不同,结论也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所以以孟德斯鸠读了一些游记为主要原因来解释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厌恶似乎是不合理的。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孟德斯鸠的思想体系和方法。
如上所述,三种政体理论是孟德斯鸠的主要理论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是他所有理论的核心部分。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其他制度,比如教育、司法、税收、贸易等等;政权更迭,一切都变了。
孟德斯鸠在阐述他的政体理论时,不仅使用了推理的方法,而且注重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事实来支持他的论点。如上所述,他用古代城邦解释共和国,用当时欧洲封建王国解释君主政体,用东方国家解释专制政体,其中中国就是专制政体的典型例子之一,所以他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国。
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其政权必然是专制的,因为他的政体理论断言“小国适合共和政体,中等国家适合君主统治,大帝国适合专制君主统治”。
孟德斯鸠还认为,君主政体除了有约束君主的基本法外,还必须有介于君主和平民之间的“中间物”——贵族,他们在议会中起主导作用。中国既没有欧洲贵族,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议会,只能归为专制政权。
孟德斯鸠还认为,即使有了《基本法》和“中间体”,如果没有三权分立来制约权力,掌权者就会滥用权力,把君主政体改造成专制政体。中国皇帝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绝对没有分权。所以,中国只能是一个专制国家。
这三点是孟德斯鸠不能把中国归为君主制,而只能归为专制政体的主要原因。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是不科学的,专制政体和君主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同一个国家既有君主政体的特征,又有专制政体的特征,这是很自然的。中国就是这样,孟德斯鸠自己也看到了。他在笔记中写道:
中国是一个混合政治体系;它因其强大的君权而具有专制政府的显著特征;......它有君主制,因为它有固定的法律和正式的法院。
然而,这个闪现在他脑海中的想法并没有被收录到他出版的作品中。原因是什么?他决心捍卫自己的政体理论,所以他必须坚持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是一个专制国家,否则他的政体理论将是不完整和不完善的。此时,他毫不掩饰地写道:
我们的传教士告诉我们,庞大的中华帝国的政权是值得称赞的,它的原则是恐惧、荣誉和道德的结合。那么,我建立的三个政权的原则的区别就没有意义了。
他说的非常清楚和坦率,我们不需要再解释了。结论是,孟德斯鸠为了建立他的政体理论,可以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承认中国有这样那样的可取之处,但中国是一个建立在恐怖原则基础上的专制国家,这一根本点绝不能动摇。
可见,孟德斯鸠的研究方法之所以超越前人,是因为他注重用事实来支撑理论,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先下结论,再去寻找甚至剪裁事实来支撑这个结论。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建立了一些原则。我看到个别情况受制于这些原则,好像它们是从这些原则衍生出来的;所有国家的历史都只是这些原则的结果。”。因为他建立了一些原则,中国作为一个“个案”,不得不“服从这些原则”,也就是说,服从建立他的政治制度理论的需要。
孟德斯鸠执拗地用中国作为威权政体的典型来建立自己的政体理论,当然不是脱离现实政治的纯学术讨论。他的政治理想是一个开明的君主政体,其王权受到基本法和“中间体”的制约,他的政治制度理论服务于这一政治理想。
在他看来,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期的法国已经从君主政体退化为专制政体,君主政体的本质基本法和“中间体”没有任何作用,而专制政体的内在特征在法国日益显露。因此,在《波斯人的书信》中,他极力揭露和批判当时法国的各种丑恶现象。
《论法的精神》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提出了防止法国向专制政体转变的途径,即根据他的政体理论建立开明的君主政体。既然政体理论如此重要,他当然会尽力去建立,去完善,去捍卫。既然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专制政权,即使有些事实不能证明,也是无关紧要的。
平心而论,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描述和评论并非不夸张。这是因为他们把理想献给了赞美中国,多多少少把中国的现实理想化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中国是空捏造的,而是说他们回避或者粉饰中国弊病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孟德斯鸠对中国采取了冷淡而严厉的态度,他看到了中国的许多缺点。但由于他带着偏见观察中国,无法分辨他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材料的真实性,所以他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并不具有说服力。但是,他的一些观点很有见地。比如他曾经指出,中国的科举制度导致知识分子重视文学和轻武器,导致国力衰弱,自然科学落后。他对中国的人口问题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所以应该说,他的研究也有助于让欧洲人了解和认识当时的中国。
孟德斯鸠的中国不是当时中国的真实写照。它补充了伏尔泰的中国,纠正了彼此的偏颇。我们不否认伏尔泰对中国的描述是唯心主义的,是因为他对中国的无限敬仰,也不否认他的研究和结论是因为孟德斯鸠当时否定了中国。
【原文发表于1985年《法国研究》第二期,文字略有改动】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由哲学与社会、文史、政法、经济管理四个编辑部,以及主要负责编辑出版文史、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维科项目组组成。出版的著作包括以《世界学术名著汉译丛书》、《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国当代学术集锦》、《大师文集》为代表的各种学术译著和原著。
1.《孟德斯鸠大学 孟德斯鸠笔下的中国》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孟德斯鸠大学 孟德斯鸠笔下的中国》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shehui/11488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