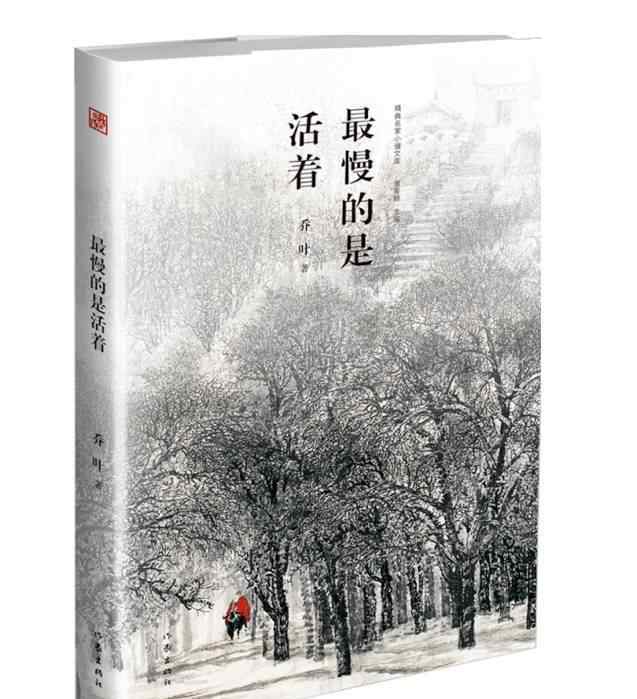
一个
那天,窗外下着慢慢的雨。我和朋友在茶馆聊天。不知怎么的,她谈到了她的祖母。她说她奶奶很节俭。从小到大,她记得奶奶只有七双鞋:两双冬天穿的厚棉鞋,两双春秋穿的厚布鞋,两双夏天穿的薄布鞋,还有一双桐油做的高帮鞋,专门在雨雪天穿。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如果她早点离开学校,她会负责烧火。只要炉子里的火焰跳出炉子,他们就会被奶奶骂,让她把火按到炉子里,说火焰出来就是浪费。
"她已经去世快20年了。"她说。
“如果她还活着,知道我们花几百块钱买水,在外面八卦,她会生气吗?”
“当然,”我的朋友笑了。“她是那种在农村撒尿就上自己的地,在城市撒尿就上公共厕所的人。”
我们一起笑。我想起了我的祖母。——这个说法不准确。也许最好用她自己的话来形容:“别想了,也忘不了。钉子扎进了墙,里面生锈了。”
我的祖母王兰英1920年出生在河南省北部的一个小镇焦作。焦作煤炭资源丰富。当时有很多有能力的人都拥有私人煤矿。我曾祖父在一个大煤矿当簿记员,家庭生活很体面。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曾祖父认识了我奶奶的父亲,并达成了相亲协议。我奶奶十六岁的时候,嫁给了焦作城南十里的杨庄。杨庄村成了我老家最详细的地址,也成了我奶奶最终的葬身之地。她于2002年11月在这里去世。
2
我总共有四个兄弟姐妹。性别顺序是男、女、男、女。大牌依次是萧蔷小丽小杰萧让;他们经常被称为大宝、牛大、鲍尔和牛二。我是李,第二个女孩。虽然“萧让”这个名字是最常见的,但它是四个孩子中唯一一个花钱的。因为生活艰苦。农村话说:人生软硬。前十五天出生的人生已经够辛苦了,但最辛苦的是二十天出生的。“十五的第一天不辛苦,到了二十岁就像钉子一样硬。”我出生在农历七月二十日,日子过得像钉子一样辛苦。为了让指甲更柔软,妈妈说,我出生那天,奶奶请了一位风水先生给我看。风水先生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名字上犯个错误,让上帝可以大大咧咧,让他饶了我这个孽缘,从此我就要福无双至,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给了我“让”字。在我们的方言里,“让”不仅仅是回避的意思,更是软的意思。
"它值50美分。"奶奶说:“买两斤鸡蛋就够了。”
“你对我不好。我不怕害人!”
我这样说话的时候已经上小学了,和她顶嘴已经成了惯例。这种顶嘴不是撒娇的那种,是真正的不相容。因为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当然,作为一个弱者,我的选择是被动的:她先不喜欢我,所以我不喜欢她。
亲戚互不喜欢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因为一个屋檐下,不喜欢就要经常看到,自然会有一种温暖。尤其是刮风下雨的晚上,我和她一起躺在西丽。虽然一个个都睡在一张床上,但是听着她的呼吸,让她觉得踏实而平和。但是因为实在不喜欢,在这种低凹的温暖中有一种高凸的MoMo。在人口众多的日子里,MoMo造成的厌恶感几乎让我们无法对视。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她不喜欢我。有句话叫:“老大有魅力,老大有魅力,就是不要生个中腰。”然而,作为一个老人,我没有得到她的任何恩惠。她就是家里的慈禧太后。如果她不宠爱,她的父母也不会宠爱——他们只是没有时间去宠爱。父亲在焦作矿务局工作,母亲是一个小村庄的私教,所以都很忙。
因为不被喜欢,所以小心眼的时候会记仇。而她让我记仇的细节无处不在。比如她经常睡的水曲柳黄漆大床。那张床是清代电视剧中常见的一张大木床,四周是木板,木板上刻着牡丹、荷花、秋菊和冬梅。还有一个高大的木屋顶,也是花里胡哨的。床头和床尾还嵌有一个黑色的鞋柜,几乎是我家最华丽的家具。我渴望那张大床,但我从来没有机会睡在上面。她只带二哥睡大床。我和二哥只有三年的距离,但是这张床的待遇差别太大,我很不平衡。有一天晚上我上溯,洗好脚,早早爬了上去。她一看到就着急了。她掀开被子啪地一声,“趴下!”
我蜷缩在床角,说:“奶奶,我占不了地方。”
“那不对!”
“我只和你睡一次。”
“小姐!”
她下定了决心。被她如此坚决的拒绝,对自尊心是极大的伤害。我哭了。她就去拽我,我抓着床杠坚持着,却死活不下来。她真的别无选择,只能抱着二哥睡我的小床。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占据了大床。我哭着睡去,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又哭了。
她毫不掩饰对男孩的爱。谁生了儿子,她说:“添人。”如果她生了女儿,她说:“是个女孩。”如果一个儿子是一个人,一个女孩只是一个女孩。女生不是人。当然,谁要是娶了媳妇,她也会说:“她进了。”——这个家庭的女儿成为那个家庭的媳妇。所以自己家的女儿来别人家只能算一个人,不能算自己家的人。这每一天,她都知道真正的儿子。我小时候每次看她给灶神告白,听到最多的就是那一句:”...你总是说更多的好话,但你总是说得更少。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可以传给松子娘娘腔,让她多给骑马射箭的,少给穿针引线的。”骑马射箭的都是男生。是那个穿针的女孩。在她意识里,儿子不多,女生是至亲,无所事事,四处走动。百年升天有这只手给他们梳头洗脸就够了。所以多一个是多余的——我是最典型的多余。她本来期待我是个男生,可是我的到来让她失望了:一个不争气的女生,不仅占了男生的名额,还占了男生的秉性,日子过得好辛苦。她怎么能对我?
当她做错事的时候,她对男生和女生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如果大哥二哥做错了,她不会让爸爸妈妈说一句重话,理由很好:饭前别说,因为该吃饭了。吃饭的时候什么都不要说,因为你在吃饭。吃完饭就不说了,因为刚吃过。放学后不要说什么,因为你必须做作业。睡觉前不要说,因为你想睡觉……但是打骂女生也没关系。她以前在餐桌上教我的左撇子。我从会拿筷子开始就是左撇子,什么事情都喜欢用左手。她平时看不见。她一坐到餐桌上,就开始管教我。我怕影响大哥二哥三姐吃饭,把我从一个角落赶到另一个角落,从那个角落赶到这个角落。反正我不喜欢,而且是在我坐的地方碍事。最后她一般都要坐我左边。当我终于坐下来开始吃饭的时候,她的另一个节目开始了。
“喂!”她的筷子碰到了我左手背上的指关节。痛,痛。
“换手!”她说:“如果我要求你改变,你不会改变。左耳进右耳出!”
“没有。”
“不会去上学。不学这个就得学!”
知道再跟她下去,饭菜就要被哥哥姐姐们吃完了,只好换了。我撅着嘴,右手拿起一块冬瓜。冬瓜默默地落在餐桌上。我又挣扎着捡起一根南瓜丝,它依然落在餐桌上。当我终于把最厚的萝卜条抓到嘴里的时候,萝卜条突然落在了粥碗里,粥汁溅到了我的脸上和衣服上,引起了哥哥姐姐们的大笑。
“无论你用哪只手吃东西,你都会把它含在嘴里。什么重要?”妈妈终于开口了。
“那怎么会一样呢?以后怎么找婆家?”
“长大了就不找婆家了。”我连忙说道。
“不找婆家?新娘家还养你一辈子。给你一个老姑娘的坟。”
“我养活自己,不要你养我。”
“难道我们养的,是你从石缝里跳出来的?养活自己这么大?”
她一开始不讲逻辑。我知道我打不过她,只好保持沉默。
下次,还是一样,我会用不同的方式回应她:“你放心,我不会嫁给一个同样是左撇子的人?我不信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左撇子!”
她生气了,笑了:“这么小的姑娘说找婆家,却不知羞耻!”
“你先说的。”
“哦,我先说了。嘿——如果我能先说,你还不能说。”她得意洋洋。
“四姐妹中,只有你看起来很小,但只有你和她不对。”母亲纳闷,“奇怪。”
三
后来听她和姐姐聊天,我才知道,她小时候,家里的家境很好。当时我们李家的情况虽然不错,但绝对比不上她的王氏家族。他们这个大家庭四五代都有四五十个人。男人很多,家里有十几个长工。女人不用下地,在家轮流做饭。这一茬有八九个女生。他们从小就没出过大门,第二扇门也没开。他们只是学着做女红,会做饭。方圆最大的磨坊和面粉厂有五六只大动物和几十只猪。淡季的时候,面粉厂把面条磨成粉,粉条在面粉厂生产。所有的牛都派上了用场。猪也有剩饭吃。猪粪再次上涨,毫不迟疑的去了庄地。在集市的那天,他们的祖父会开着马车,带他们四处逛逛,买一些衣服和头巾,然后给他们每人买一个烧饼和一碗杂碎。家里一个表哥娶了新老婆,会偷偷去房间不告诉长辈,当然也经常被发现。当他们听到爷爷的咳嗽声时,他们就会散开。有一次,她跑了,被一块砖头绊倒,敲了一个大大的黑蓝色的碗。
她结婚的时候,因为知道丈夫家境不如母亲,又怕姑娘受苦,所以嫁妆格外丰厚:一个带镜子和小抽屉的脸盆架,一个雕花衣架,一个红漆四抽屉的首饰盒,一张方桌,一对太师椅,两个带鞋柜的大樟木盒子,八条绸缎被子……还有水曲柳的黄漆木床。
"总共有二十部电梯。"她说。当时嫁妆是关于“举”的。小的两个人扛一样,大的四个人扛一样。有二十部电梯,真的很大。
说到上升,她会打开樟脑盒,给妹妹看新婚时的红色棉裤。几十年过去了,棉裤的颜色还是很鲜艳的。红底有淡蓝色的花,既喜庆又安静。还有她的珠宝。“文革”期间,打破资本主义的人偷了很多,她却偷偷留了一些。她打开层层红布包,拿给妹妹看:两个长长的有羽冠的银簪,因为时间长,银的是灰色的。她说有一对雕龙绘凤的银手镯。在三年的困难时期,她响应国家号召向灾区捐赠物资,全心全意地捐赠了那些手镯。后来发现是一个村干部的女儿戴的。
“我把她叫到我们家,哄她洗手吃馍,把镯子拿回来。他们最后亏了钱,不敢再问我了。”
“手镯呢?”
“卖了,换了二十斤大豆。”
当她生下父亲时,家人给了她银发以庆祝满月。每个有三个重量,一英尺长。它配有复杂的银铃和胖乎乎的小银人。她说一共七个,但是当她打破资本主义的时候,她被抢走了四个,只剩下三个。后来大哥和二哥生了孩子,都生了儿子,她就给家里生了一个。姐姐生了个女儿,没生。
“你再生,我就给你生个儿子。”她对妹妹说,又转向我,“看你们谁有能力生儿子。早晚是你的。”
“来吧。我不要。”我说:“知道我最小,最晚结婚。它根本不打算给我。”
“你说得对,不是给你的,是给我孙子的。”她又小心翼翼地把它包好。“如果你们都有儿子,把这个锁回炉子里,做两个小的,一个一个。”
偶尔,她会和姐姐谈论她的祖父。
“我比人家大三岁。女学妹,捧金砖。”她说她总是用“家庭”这个词来指代她的祖父。“我很久没进门了,但是我很乱。煤矿和工厂都关闭了。你太爷爷的时候,回家闲着,在家的日子也不如每天。什么金砖?银砖不是我捧的,都是我捧的。”
“人话不多。”
“我见过一面,连人家的脸都不敢看,就嫁给人家了。我当时结婚的时候,谁不晕头转向的嫁?”
“和人家三年了,哪一年没空肚子,前两个都是四六级风。可惜都是男生。我出生的时候还好好的。第六天就死了。如果早知道我会在火上烤剪刀然后剪断脐带,你爸爸一个人会被丢在哪里?”
后来“一家人”当兵离开了。
“八路军过来的时候,人们上扫盲班,学读书。人有脑子,学得快...然而,谁能说出世界上什么时候发生事情?如果你笨,你可能不会跟着队伍走,你现在还能活着。”
“谁傻了想去当兵?团队来了就不行了。”她毫不掩饰她祖父当时的落后思想。“我就是不跟随这些人,还有国民党和杂牌军,哪个人都不能放过。还有旧日。”以前,他们是日本鬼子。
“旧社会不杀人。进屋看到我们家提供的菩萨,赶紧跪下磕头。见孩子给糖吃,便失手,见人就杀。我还挑了一岁小孩在刺刀尖上玩,怎么叫人?”
旧日来临时,她的脸上满是锅灰。
“一家人”打到徐州,她去看他,想过黄河。黄河上的桥散落一地,只剩下一个铁架子。白天不敢活,晚上才敢。她带着父亲,一步一步踏上长长的铁架子,跨过黄河。
“月亮是白色的。是脚底下的黄河水,吓人。”
“当时人家已经有通讯员了,部队里的人对我们很好。吃好,但要吃饱。呆了两天,我们回来了。家人不能多活了,看看就好。”
那次探望回来,她又怀孕了,生了个女儿。女儿白白胖胖,长得像满月,爱笑。然而,有一次,一个邻居为了好玩把孩子抱起来,不小心摔倒在地上。第二天,孩子早逝。才五个月。
我和她谈的时候坐在门下。街坊慢慢走着,和她打招呼。
“休息?”
“休息。”她友好地同意了。
“别理他!”我讨厌她无原则的慷慨。
“那还可以吗?账目怎么这么清楚?他并不担心。”她叹了口气,“死人都死了,活人还得活着。”
1.《乔叶 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乔叶 乔叶:最慢的是活着》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yule/16667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