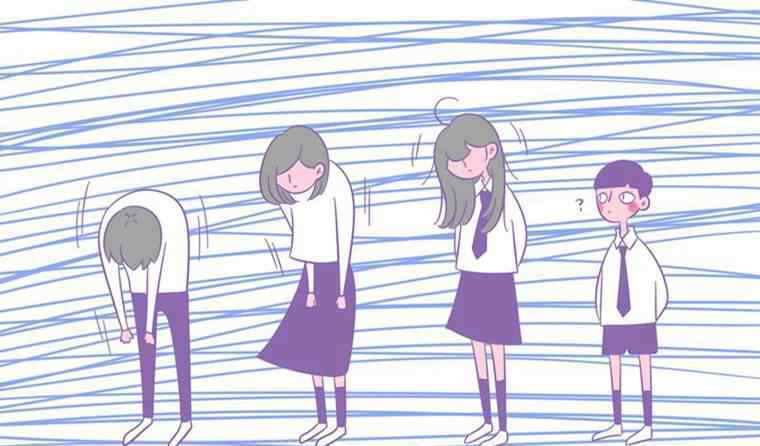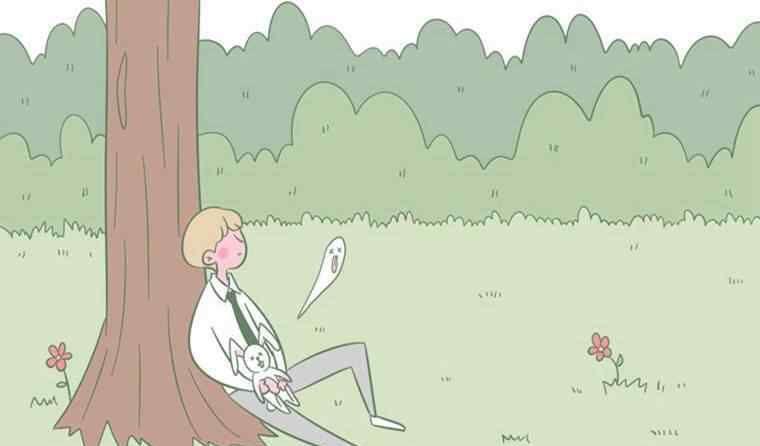2019年,这一年,郑榕95岁。
他曾出演的话剧《茶馆》,也是一个“老人”了。
5月,郑榕为中央戏剧学院教学而著述的新书出版,书中多有回顾自己半生话剧事业所得。有来访者登门,他往往提前电话里就问明来意,见面时,与访问有关的内容已被他写在了稿纸上,字迹工整,逻辑清晰。等到坐下聊天,遇到相关内容,他就看着稿纸讲给对方听——他怕自己年纪大,记性差,不提前写下来,恐辜负了来访者。
来访者愈加感动这位老人的认真,欣欣然向他讲起他工作大半生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里,人们从凌晨便排起长长的队伍,等着天亮时话剧《茶馆》演出票开售……
1958年3月,34岁的郑榕和他的同事们,把老舍的剧作《茶馆》搬上北京人艺的话剧舞台。这些同事包括曹禺、焦菊隐、夏淳、于是之、蓝天野、英若诚……这是一串闪光的名字。

郑榕。郭红松摄/光明图片
2019年,话剧《茶馆》首演61周年。它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中国话剧史上的里程碑,“一部《茶馆》,半部中国话剧发展史”。它被视为老舍最优秀的剧作,北京人艺的镇院之宝,话剧迷心目中的必修课,话剧演员以能扮演其中的角色为荣;有西方观众第一次看到它时,不知用何种语词才能形容自己遇到中国珍宝的心情,只说“它像是一个历史画卷,可以和《清明上河图》媲美”。
郑榕在《茶馆》中扮演常四爷。这个角色常常被列于第二位,和于是之扮演的王利发、蓝天野扮演的秦仲义,并称《茶馆》“仨老头”,是贯穿《茶馆》全剧三幕的三个重要角色。
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焦菊隐版《茶馆》原班人马在首都剧场举行告别演出,《茶馆》前后演出了374场,郑榕也扮演了374个常四爷,“《茶馆》几乎是我演剧生涯的主角,常四爷这个角色的成长也是我在修养和演技上不断成长的过程。”他说,就是在演《茶馆》的这个阶段学会了如何认识人生和创造角色,他也用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34年,见证了《茶馆》作为经典穿透岁月的熠熠光辉。
这是一个老人对另一个“老人”的回顾,像将军回忆他历久弥新的勋章,像画家回忆自己的佳作如何画出了第一笔……但不管倾听者对此有多么迫切,面对《茶馆》,郑榕总是愿意从许多年前的一个冬夜谈起。
1.“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曹禺
1940年,这一年,郑榕16岁,长安大戏院公演曹禺的话剧《日出》。“北京剧社一年难得演一场,我买票去看了。”但是,“那个时候的环境不好,戏还在演着呢,就不时有压低帽檐的人走进来,喝令戏停下,打开灯——找人,等他们走了,灯光再暗下来,演员在舞台上接着演。”就这样断断续续演到结尾,陈白露喝安眠药一场戏深深触动了郑榕,“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看完戏,郑榕说不清的心情低落,“那时我高中一年级,散戏以后,我在马路上走了很久,那是冬天的夜晚,刮着风,掉着树叶……”那一年南京成立了汪伪政府,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而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城,年年月月都是寒冬。
16年后,与郑榕同样经历过黑暗旧社会和新中国成立的老舍,写出了三幕剧《茶馆》,那个令郑榕印象深刻的看戏夜晚,就发生在《茶馆》第二幕与第三幕之间的年代。老舍曾谈及希望通过《茶馆》的三幕,完成“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成型后的话剧《茶馆》,三幕分别发生在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在一个叫裕泰的茶馆里,各色人等轮番上场,展现出这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经历的黑暗腐败。

郑榕扮演的常四爷。资料图片
1979年复排《茶馆》上演,一位老人看后呆住良久,说道:“把我一生的经历全都回想起来了,看完觉得还是社会主义好。”1989年,郑榕和同事们去欧洲演出《茶馆》,英国的一位芭蕾舞演员说:“看了《茶馆》,知道了为什么中国革命是必然的。”
《茶馆》所歌颂的新时代,也为创作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宽松氛围。排演《茶馆》时,导演焦菊隐常与老舍及演员一起谈笑交流,经典的“焦版话剧《茶馆》”正是经过大家多次讨论修改而得。当时的畅快淋漓,被记录在一张张老照片中,藏在郑榕的书里、相册里,脑海里。
2.“现在要教会你怎么在舞台上生活”——焦菊隐
1953年,这一年,郑榕29岁。他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焦菊隐时,焦菊隐说:“过去你是知道怎么在台上演戏,我现在要教会你怎么在舞台上生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验生活。
“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个笔记本,每天早晨八点到晚上五点,下到现实生活里去体验,回去后把当天收获写在本子上,交给导演写批改意见。”就这样,郑榕演《龙须沟》体验生活两个月,《雷雨》六个月,到了《茶馆》,体验生活已成为人艺的传统。
对生活的体验,焦菊隐运用到了排演《茶馆》开场第一幕中,“第一幕茶客众多,聚集了当时社会的三教九流。”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听老舍读剧本读到这一幕,惊喜不已:“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好作品的心情。这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如何表现好这一幕,焦菊隐和执行导演夏淳、设计王文冲反复思量,为了强调艺术的真实,设计了舞台上茶桌高低不等错落的摆放。此外,“《茶馆》有很强烈的节奏感,这种节奏感是通过生活内在的发展规律形成的。第一幕开场是在茶馆里的群众场面,它造成一种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氛。”郑榕在其所著的《我与北京人艺》里,详细讲述了导演如何根据内容来调整节奏,“开幕时用强音,各桌谈论得极为热烈,有一桌谈道:‘洋人把县太爷绑在树上活活地抽死了!’吸引了邻桌的注意,静下来听,又吸引了另一桌,这时只听见这个桌上的谈话了。然后又嗡嗡起来。接着进来一个卖福音书的,大家对这人很不习惯,他走到哪桌面前,那桌就静了下来。这样等于给每桌拍了个呆照,让观众能有重点有顺序地把茶客都看过来。”这样的动静节奏,出现在《茶馆》舞台上,俨然一出美妙的交响乐。
焦菊隐还把京剧中的“亮相”用在了《茶馆》人物的出场中,“因为老舍在《茶馆》中多用的是画龙点睛之笔,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人物,不容观众再等待半天才看出是什么人。导演和演员琢磨要像戏曲‘亮相’一样一上场就给观众留下鲜明的印象。”这才有了观众眼里“连面部肌肉表情都印象深刻的庞太监”。
中国戏曲的表现程式正是千百年来从民族生活的独特方式中汲取和提炼而成的。当时的国外报纸评论《茶馆》里的演员:“每一位身上流的都是老舍剧中人物的血。”
焦菊隐和夏淳是话剧《茶馆》首演时的导演,在长达一个甲子的岁月里,老舍的《茶馆》经历了许多次修改、排演,衍生了诸多版本,然而唯有焦菊隐导演的版本最为经典,被大家约定俗成为“焦版《茶馆》”,而今每年在人艺舞台上演,一票难求的,也是焦版。
在人艺博物馆的陈列柜里,郑榕的日记本静静述说着那段历史。
3.“一定要把茶馆的文化演出来”——老舍
1982年,这一年,郑榕58岁。《茶馆》要被拍成电影,他第一次看到当年自己演《茶馆》的录像,“那时候三十几岁,对常四爷这个角色有偏见,觉得剧本中必须有一个说正面话的硬汉子,上了舞台,也就按照概念化的方式去表演,塑造了一个‘硬’汉子。”
看着录像里那个“张牙舞爪、高声粗气”的常四爷,郑榕羞愧难当,他忽然想起,一次看《茶馆》排戏后,老舍对演员讲:“茶馆里有着高度集中的文化。中国人是聪明的,在封建社会他们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只好钻研品茶、玩鸟、放风筝……在茶馆里可以听到各种新闻,学到各种知识,其中每一项都可以写出本书来,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你们一定要把茶馆的文化演出来。”
如何通过常四爷演出茶馆的文化味儿?
老舍的话首先启发了郑榕演《茶馆》第一幕。“那时候的常四爷是个旗人小官吏,坐茶馆是为找乐子去的,决不是为了寻衅斗殴。”郑榕改变了一上来就横眉立目的演法。“这是一场遭遇战”,他把与二德子的冲突戏处理成意外、躲闪、对英法联军的不满和最后交手时的临危不惧,“这样表现常四爷的‘硬’,就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他的思想性格。”
老舍也曾提到父亲的死:一个普通的旗人库兵,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为保卫一个粮店而战死后,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家里人只拿回他的一只布袜子……郑榕又想起自己体验生活时在茶馆里遇到小心翼翼说话的老旗人满脸皱纹的面孔。“这又使我获得了常四爷的灵魂,《茶馆》看的是民族魂,而不是看热闹,常四爷也是有灵魂的。”
所以在第二幕里,郑榕表现的常四爷乐观而成熟:牢狱折磨使他学会了老练小心,改朝换代铁秆庄稼没了,常四爷自食其力卖青菜,“凭力气挣饭吃,我的身上更有劲了!”——“此时此地常四爷的‘硬’应该表现在豪情满怀上,并且藏在他面对特务老练成熟、虽不服气又不被抓到把柄的话语上。”
有了这种贯穿人物灵魂,却又随际遇有所变化的“硬”,到了第三幕,郑榕扮演的常四爷愤然喊出“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才是鲜活而有说服力的。
老舍曾笑谈“茶馆里的人物都好像是我看过相,批过八字似的。”和常四爷一样鲜活的人物,在《茶馆》剧本里有70多个。
4.“观众对我是宽容的”——于是之
1992年,这一年,郑榕68岁。恰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40周年,7月,《茶馆》上演,这是由于是之、郑榕、蓝天野三人扮演“仨老头”的第一版《茶馆》的告别演出。
“那天在剧场门口,通过‘黄牛’花上150元也很难买到一张票。”7月16日是最后一场,扮演掌柜王利发的于是之年纪大了,表演中偶有忘词,自己觉得十分愧对观众。
“我记得他一再感叹‘观众对我是宽容的’。”郑榕认为,观众之所以宽容,其实来自于演员的伟大。“我觉得于是之有两大特点很值得我们话剧演员学习——重视生活与重视修养。依靠这两点能冲破一般化、概念化的表演恶习,在舞台上创造出有血有肉的生命来。”
于是之说:“老舍先生的剧本看来好演,淡淡几笔,给演员留下广阔的创作天地;但倘若缺乏深厚的生活基础,你就会感到无从下手,是断然不会演好的。”
焦版《茶馆》结尾三个老头的一场戏,曾经过反复试验。
“当时于是之不满意,摇摇头说:‘得闹起来。’起初我不懂,我想这是王掌柜即将自杀前的戏,应以悲愤为主。他却说:‘像王利发这样的人,一辈子胆小怕事,谁也不敢得罪,生怕说错一句话。到他下决心要死时,忽然一切得到了解脱,他觉得什么都不用害怕了!他要把平日憋在肚子里的话一下子都吐出来,还想对这个欺压人的旧社会开一个大大的玩笑,因此才叫常四爷撒纸钱……’”于是之深刻理解了王利发之死,同时也准确地领悟了老舍的喜剧精神。
在这样理解的基础上,焦菊隐借鉴中国传统戏曲的手法,让演员朝着观众演,直接和台下观众交流,《茶馆》的结尾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的时候,是黎明前的黑暗,“后来焦先生说,你们都朝着我演试试,我们才明了,这是控诉,不应该去表演个人的哀伤,不是谈个人的经历。焦先生要让观众看到光明。”
以笑代哭,以喜演悲,“仨老头”的形象立时增添了光辉。如此,老舍心目中“观众含着眼泪的笑,或许才是深刻的喜剧”,终于成了。
5.“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经典”——郑榕
2005年,这一年,郑榕81岁。人艺复排焦版《茶馆》,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接棒新“仨老头”,郑榕成为艺术顾问小组成员。
2018年,《茶馆》首演60周年,濮存昕演《茶馆》也快20年了,但他仍旧战战兢兢,他说,自己仍记着郑榕当年对他们说:“不怕没演好,就怕糟蹋了。”
2012年,这一年,郑榕88岁。他参演人艺新戏《甲子园》。怕人家笑话这么大岁数还演戏,他曾认真回答记者:“为什么我还要来演呢?其实我是想试试,人艺过去的表演传统——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如今还灵不灵。那是我们经过了多年的学习、探索和借鉴,积累下来的。中国话剧的立足点是中国大地,根基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离开了这两点,还看什么呢?”
2017年,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郑榕写了《我对中国话剧的自信从哪里来》。这篇文章被他放在新书里,面对这样好的《茶馆》,来访者和濮存昕一样担心经典易逝,郑榕把书中的这句话与2012年的回答一起大声念给大家听,他总结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经典。”
“感觉到跟观众心贴心了,好像观众底下什么反应、什么动作都能获知了,我知道这就是进入人物了,只要有这种成功,我就觉得做什么都不算累了。我最喜欢下装以后,半夜里一个人在马路上走,好像还能让那个人物在你身上多活一会儿,这是一种很大的幸福感。”说这话时,郑榕仿佛还是16岁散戏后走在路边的那个少年,只是,此刻,心中是力量和光明。
《光明日报》
1.《郑榕 郑榕:“《茶馆》伴我一起成长”》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郑榕 郑榕:“《茶馆》伴我一起成长”》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yule/4658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