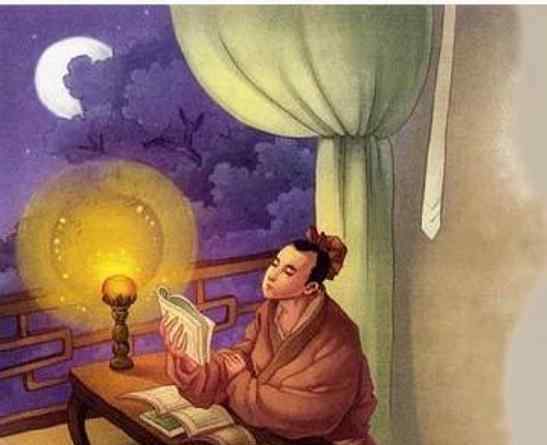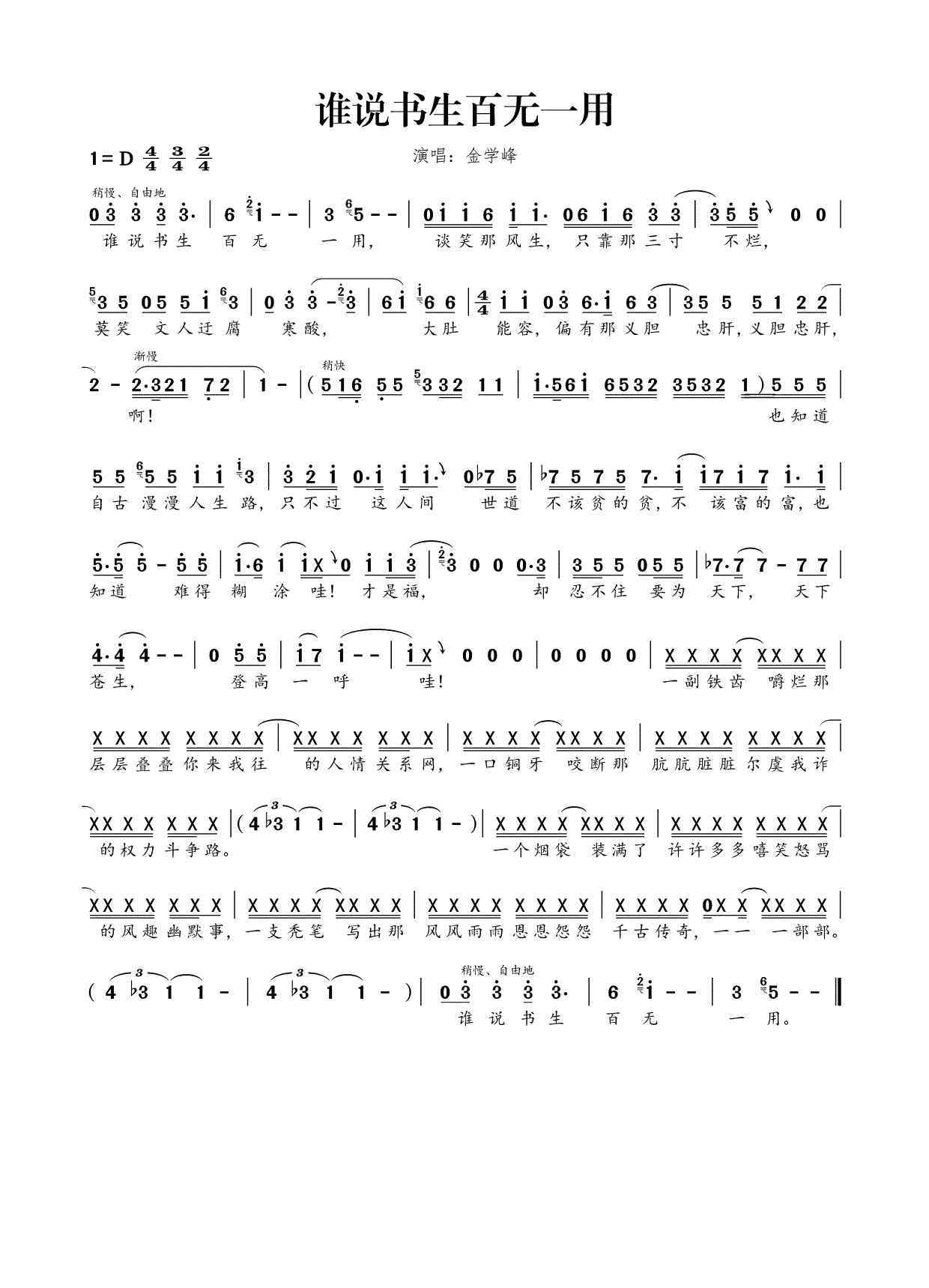前不久,蒲松龄亲手誊抄的手稿本《聊斋志异》印刷出版。据悉,《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作者手稿保存至今的唯一一部作品,虽然目前仅发现半部,但价值非凡。在中国,不是所有读者都阅读过《聊斋志异》,但几乎人人都知道聊斋故事。它们早已经从蒲松龄的手稿中走出,走进曾经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里,走进幻化瑰丽的荧屏银幕中。
大半生科考失意
蒲松龄的大半生,就像他笔下的书生一样,既贫且苦。祖上荣光久远,让后人也倍感荣耀,蒲松龄也不例外。他的家世“科甲相继”,尤其是远祖,曾在元代为一方主管,叔祖也曾中过进士。蒲松龄很是引以为傲,尽管到父亲一代已经以生意糊口,但书香传统并未中断,蒲松龄读书科考,以期踏入仕途。
据山东大学邹宗良博士论文《蒲松龄年谱汇考》,1659年,20岁的蒲松龄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因前往参加诸生岁试后之童生试,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甚”。可以想象,当时的蒲松龄是如何意气风发,他与友人结诗社,谈道义,吟风雅,广交游。
看似就要如祖辈那般凭科考赢得功名,重振门楣,可在那之后,蒲松龄却屡试不中。1664年,25岁的蒲松龄赴济南参加岁试,再试再败,怀才不遇之感甚重。同一年秋冬间,蒲松龄与父兄析箸分家,自立门户。对一心科考得功名的蒲松龄来说,这意味着他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专事读书,他要考虑妻儿的生活经济。蒲松龄一家分得了20亩田地,以及5斗荞麦、3斗小米,彼时正值连年大旱,粮食歉收,这些对蒲松龄一家来说远远不够。迫于生计,蒲松龄开始设馆执教,补贴家用。
读书人蒲松龄深切感知着贫穷带来的窘迫,以及摆脱贫穷时的无力。在《除日祭穷神文》中,他写道:“穷神!……你着我包内无丝毫,你着我囊中无半文,你着我断困绝粮,衣服俱当尽,你着我客来难留饭,不觉的遍体生津,人情往往耽误,假装不知不闻。”蒲松龄自嘲为穷神“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祈求穷神离了他的门。
今天的我们大概很难理解古时读书人对科考的执念。据《蒲松龄年谱汇考》,1709年,“以蒋陈锡升任山东巡抚,在珍珠泉抚院衙门考试士子,松龄往济南应试。”这一年,蒲松龄70岁。
蒲松龄一生逐功名入仕途,未能如愿,可是一部科场之外的《聊斋志异》却让他留名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聊斋志异》中的男主人公多是一些落魄失意或自由不羁的书生,这像是蒲松龄的自我投射和期许,而他们与婀娜美艳女子的相逢遭遇则像是蒲松龄生前一场又一场的白日梦。
书生白日梦被嘲笑
《聊斋志异》问世后,风行一时,尤其是在乾隆年间,不仅传阅甚广,而且模仿者众,引发了又一轮志怪小说写作热潮。鲁迅曾如是评价《聊斋志异》:“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
蒲松龄生前若成功入世,门生故吏簇拥,《聊斋志异》或许甫一问世便在一片赞颂中风靡文坛,当然,也可能根本就不会有《聊斋志异》这样的小说,可是他大半生科考失意,只是籍籍无名的教书先生,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他的创作传播只能始于亲朋的口耳相传。《聊斋志异》创作于康熙年间,但直到乾隆时期才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小说,它的版本从手抄到印刷,足见市场需求之大、流行之广。
《聊斋志异》也引发了当时主流文坛的注意,却未被收入官方编纂的《四库说部》。主持编纂的纪昀对《聊斋志异》“有微辞”:“《聊斋》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述者之笔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必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嬿昵之词,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从何而见闻,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予诚莫逮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
在纪昀看来,《聊斋志异》的题材固然好,但是叙述文本有些“不伦不类”,过于随意,不够严谨,而那些书生艳遇的绮丽故事,更是不值一提。用今天的话来说,蒲松龄或许进行了一场文本实验,得到了市场认可,却未被主流文坛所接纳。
纪昀大概对《聊斋志异》的流行相当不齿,他甚至专门写《阅微草堂笔记》以告诉世人,真正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反仿蒲松龄笔下的狐仙故事,揶揄书生的白日梦:“此怪非鬼非狐,不审何物,遇粗俗人不出,遇富贵人亦不出,惟遇人才之沦落者,始一出荐枕耳。”纪昀不掩对蒲松龄的嘲笑,那些美丽的姑娘凭什么只对落魄的书生情有独钟?
科考之外收获声名
仕途通达的纪昀无法理解蒲松龄,也无法喜欢《聊斋志异》。身为普通人的我们,却痴迷于蒲松龄的鬼怪传说,佳人钟情于落魄的才子,无视钱财这些身外之物,更见情感的高洁。在很多个没有收音机、电视机以及电脑、手机的夜晚,人们围坐一圈,听老人讲这些久远的传说,打发漫长的时间。到了后来,《聊斋志异》里的那些故事被拍摄成影视剧,抽象的文字和言说化为具象的画面,让人更是念念不忘。
《聊斋志异》不仅深受中国读者欢迎,也走向世界,让外国人对其中那个神秘、瑰丽的世界着迷。据上海外国语大学李海军博士论文《从跨文化操纵到文化和合——英译研究》,1842年,来华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翻译了《聊斋志异》中的故事,1880年,伦敦的T·德拉律出版社便出版了两卷本的《聊斋志异》。之后,关于《聊斋志异》的版本和研究更是不计其数。蒲松龄写的那些故事发生在中国,对外国读者来说,为其所吸引固然有对东方古国的好奇心,但最终让它获得全世界共鸣的或许是其中的善恶人性和凄美爱情。
后来发生的这一切,无论批评还是赞誉,蒲松龄都没有机会听到了。1687年正月,蒲松龄与故交王士禛重逢。“花辰把酒一论诗”,与志同道合的友人相聚,只有诗酒,没有琐事。1701年春天,62岁的蒲松龄将《聊斋志异》编辑为两册,寄给王士禛,请他帮忙为之作序。对这位乡村教书先生来说,彼时文坛大家王士禛的认可和推荐都十分重要。蒲松龄正忐忑期待读者,对《聊斋志异》的未来一无所知。
那时候的蒲松龄根本不能预料,闲暇之时所作的一部《聊斋志异》会在后来成为一部文学巨著,而他的名字也被铭刻于文学史。他在科场的一次次的落魄失意,使其一生不得昂扬,困在彼时的价值观和成功学里,但在《聊斋志异》中,他可以放下戒律,解放身体和意志。尽管那些故事曾被嘲笑为书生的白日梦,可是创作它们的那些时间,或许是一个穷困书生暂时忘却现实,在另一个世界里最自由的时刻。
1.《说聊斋 你也说聊斋 我也说聊斋》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说聊斋 你也说聊斋 我也说聊斋》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yule/5052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