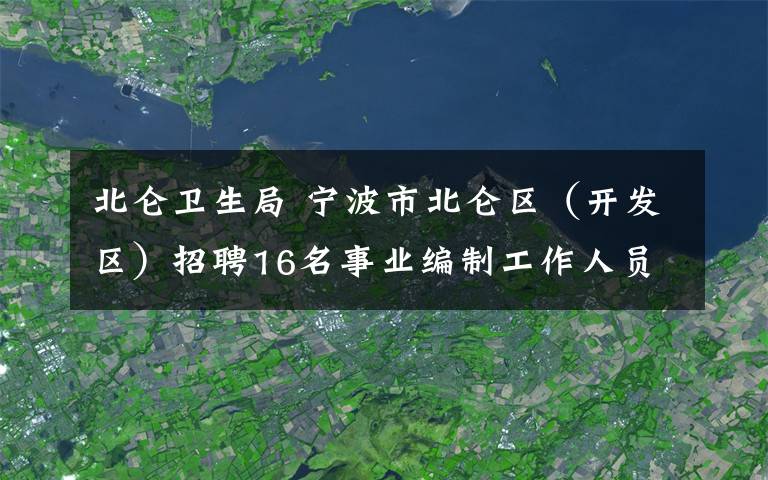许国璋是语言学家和英语教育家。1915年11月25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市,1927年考入嘉兴秀洲中学,1934年6月苏州东吴中学毕业,同年9月进入上海交通大学。1936年9月,调到北平清华大学外语系。1939年9月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先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1947年12月赴英国留学,先后在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17、18世纪的英国文学。他于1949年10月回到中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
24年前的今天,1994年9月11日,许国璋教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向许国璋先生致敬
正文|季羡林
保姆告诉我,北京外国语大学打来电话,说许国璋教授去世了。我忍不住“哎哟”了一声。我过去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场合听到过这种不寻常的尖叫。一方面说明了对我的严厉打击,另一方面背后也包含着一种极其深刻的悲伤,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这是我事先从来没有想到的,我只能惊呼“哎哟”。
张果和我不是最老的朋友。然而,我们认识了将近半个世纪。在解放初期的会议狂潮中,我们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见面。会议虽然种类繁多,但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外语和文学。我们不是一个行业的,他是搞英语的,我是搞印度和中亚的古代语言的。但是因为都是国外品牌,所以有机会见面。我从小学开始学英语,后来在清华,虽然我主修德语,但所有课程实际上都是用英语进行的,所以我不敢说我是英语门外汉,因此我有资格了解张果的英语造诣。他说英语的同事都钦佩他在英语方面的高造诣。但是,他在这方面毫无傲气。他待人真诚、单纯、真诚、谦逊,但他不装谦虚。他说话很实际,从不含糊。所以,他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而难忘的印象。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他自然难逃一死。听说他是外院“外国三村”的大老板。中国诗歌讲究两重性,“四人帮”帮派虽然胸无墨迹,我们的祖先却忠实地继承了这一遗产,既有“原生三村”,也有“外来三村”。张果和其他三位在外院的英美语言文学的著名教授,碰巧遇到他们,很受欢迎,于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外国三村”出现在海报上。众所周知,“屠三村”是“十年浩劫”的直接导火索。不存在的事实,被“四人帮”及其徒子徒孙“炒”成“事实”,举世闻名。中国变成了外国,土壤也变成了外国。当时崇洋媚外是极其罪恶的。其实四人帮才是灵魂深处最崇洋媚外的——“屠三村”十恶不赦,“洋三村”肯定十恶不赦。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张果遭受了身心折磨。
拨乱反正,天就更亮了。我和张果先生有更多的接触。据我个人估计,我们在大灾难前后的接触,性质和内容都大不相同。抢劫前的集会大多是静修;灾后大会侧重于实用主义。曾几何时,我们这群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在国外的老知识分子,一开始是理智的,有自知之明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以所谓的“解放”为荣。但是,天天见面,“查经”,“学习”,天天唱歌。人是万物之灵,但他也是一种非常弱小的动物。久而久之,他就被打成了后现代主义最新的“基督徒”,脑子里想着“原罪”,简直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罪孽深重。除非脱胎换骨,否则见到长辈会又羞又羞。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是中国当代伟大的哲学家,在国内外都很有名。他的头发已经黑白分明了。就是这样一个老人,竟然在开会,声音低沉,眼睛几乎流泪,痛苦的检讨自己。原因是什么?他千方百计想买一幅明代大画家文徵明的画。当时我在灵魂最深处瑟瑟发抖,觉得自己的“原罪”观念太差了,应该好好向老师学习。

许国璋主编的大学英语教材
张果和我也参加了许多这样的会议。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反正他是老党员了,他的“原罪”意识应该超过我们了。我完全不认为中国的老知识分子是完美的。我们有自己的缺点,也要改革思维。然而,事实是最无情的。当年,一些挥舞“资产阶级法权”大棒来骗人的人,原来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不但有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思想。这不是最大的讽刺吗?
这已经走得很远了,让我们回到过去,谈谈灾后集会。此时,四人帮已经垮台,“双百”方针真正实现了。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积极的思想和新的活力。外语文学界也不例外。我和张果先生,还有“外国三村”的全体成员,还有从南到北的同事,经常在离开十几年后聚在一起开会。然而,现在它不再是对犯罪的无休止的回顾和无休止的承认,而是为了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一些外国语言文学问题进行认真细致的讨论。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语言卷》的编纂。这时,我们的心情真的很好,仿佛透过云层看到了天空。那“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都是虚无缥缈的,还没有人说得清楚,但它们就像泰山的大帽子,“三座山半坠入云霄”。我们赤裸而轻盈,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每次见到张果,我都会微笑,就像“佛来花来,叶佳笑”和“然而我能感受到神圣独角兽和谐的心跳”。

1986年语言学家聚会
左起:季羡林、吕叔湘、王力、周有光、许国璋
最难忘的一幕是我被任命为《语言卷》主编的时候。这么一本能够而且必须代表世界上有着几千年语言学研究传统的大国的语言学研究水平的巨著,落在我的肩上,我真的很害怕,如履薄冰。我考虑再三,外语部分必须请张果先生负责。国内研究外语的学者不多,但造诣深厚、中西合璧、能随时吸收当代语言新理论的就更少了。有了这个想法,我和李宏建同志约好了。一个风大冷天,我从北京大学坐公交车,在龚伟村下车,穿过北京外院东校区,穿过马路,走到张果先生在西校区的家。我认真地说了话,并请他承担这项重要任务。他二话没说,立即同意了。我就是受尽了冷风空调的折磨,心里忐忑不安。我无意中瞥见了他房间里摆放的高高的鹅毛笔梅花,它似乎在为我高兴,向我挥手祝贺。
从那以后,我们的联系增加了,有时和百科有关,有时无关。他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了荷兰豆,摘了几颗最肥的,亲自带到我家。可以想象,这些当时还很少见的荷兰豆,在我口中品尝,其中蕴含着真挚的友谊。用普通的词语来形容什么是“好吃”,什么是“脆”是不够的。只有用神话传说中的“h”,只有用梵文阿姆拉(不死之药),才能表达千年。
他几次请我担任他的硕士生博士生答辩委员会主席,还邀请我去他住处附近的餐厅吃饭。有一次,我居然吃了一个火锅。他也来过我家几次,我们互相倾诉,无话不谈。大家互相说说各自的流派,中国文坛特别是外语文学的新情况新动向,以及当下的社会风气。谈论最多的是年轻人的海外热。我们俩都在国外很多年了,绝不是土包子。但我们不赞成长期外出,甚至无视自己的国民性和个性,厚颜无耻地待在一个鄙视甚至侮辱自己的国家。当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呆很长时间。张果特别说,一个黄皮的中国人,除了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社会很难进去,除了在唐人街鬼混,或者和有强烈民族歧视的美国华人出去。有些中国人可以一辈子不说英语。根据神话的传说,一个人成功了,鸡犬升天。然后一些中国人就把中国的一块完好无损地搬到了广阔的太平洋对岸,和鸡犬在中国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忍不住和张果一起哭了。"忆寒夜,明昌,哭几行相对南关." alt="璋 季羡林:悼许国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