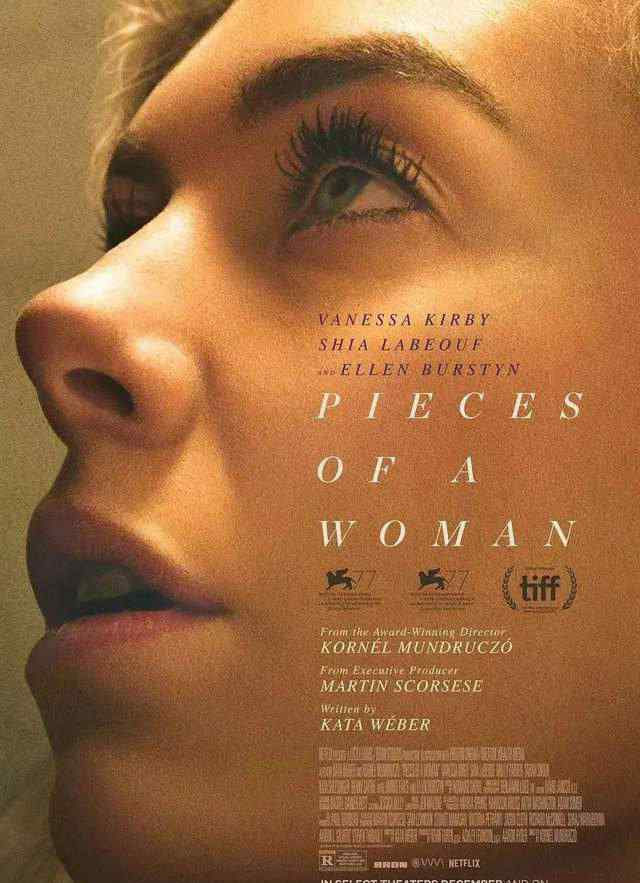原马思杰新青年电影夜船收录题目#新青年电影夜船11#电影评论9

刺客聂隐娘:世界末日
马西杰
戴锦华在《昨日之岛》一书中评论侯孝贤早期电影时表示,“有某种锁定的现在时,斗争延伸...从时间和意义上来说,它象征着断裂和悬挂。”导演侯孝贤擅长用一个长长的、舒缓的镜头重复那个永不回头的时代。在一个时间空里,他回望着短暂的少年时光和遥远的过去,记录着破碎的山河和他在历史洪流中的人生跌宕起伏,顺便用一双充满悲悯的透明的眼睛,眺望红尘中四处奔跑的红男绿女。这些电影无一例外地以一种“世俗”的心态反思“台湾省在中国百年历史中的身份”。对于《刺客聂隐娘》,侯孝贤改变了以往的顾虑,将目光投向了8世纪的古代中国,通过遥远的历史媒介思考民族文化的走向和电影叙事的未来。一首关于自我认同和自我寻求的悲歌,在垂死之际,当诗意的远射飘过唐山河中游时,逐渐响起。
被颠覆的侠客与自觉的女性意识
固定布局
在工具栏上设置固定的宽度和高度
背景可以设置为包含
可以完美地对齐背景图像和文本
并制作自己的模板

刺客聂隐娘的故事源于唐代裴傲写的《传奇》中的聂隐娘,但其内容被颠覆。《聂隐娘》这篇文章只有短短的1700字,讲述的是在唐德宗贞元时期,聂风的女儿聂隐娘在十岁那年被一个乞丐尼姑在黑暗中带走。五年后,尼姑送回来的聂隐娘,把自己在山里的武功,帮尼姑杀恶人的事,告诉了父母。尹娘的父母吓得不敢问她的下落,渐渐疏远了女儿。之后,阴娘主动嫁给了那个擦亮镜子的少年。父亲死后,魏帅命他去刺杀我们的特使刘昌毅陈旭。然而,在暗杀的途中,他被刘昌毅对正义的深刻理解所打动,并几次转到刘昌毅的门下保护刘昌毅。后来,聂隐娘拒绝了刘昌毅的邀请,一同进京。给丈夫找了一份工作后,她独自周游了世界。直到刘昌毅去世,聂隐娘才来到京城悼念他。唐文宗开年间,刘昌毅之子柳宗出任灵州刺史,在四川栈道与聂隐娘相遇。聂隐娘给了刘一颗药丸,告诉他只能保命一年,并劝他辞职退休。刘纵不从其言,一年后真的死在了陵州。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聂隐娘。
小说文本叙事极其简单,围绕女侠客聂隐娘讲述了五六件事,既弱化了聂隐娘的家庭氛围和童年经历,又隐藏了时代背景和政治纷争。随着故事的展开,聂隐娘的女性身份逐渐消失,最后随着她的行踪消失。我们甚至可以说,聂隐娘女性身份的这种设定,除了能更好的吸引读者进入阅读层面的这个故事,似乎没有别的意义。全篇几乎没有什么自觉的女人味。但是,这一点在影片中得到了很大的改编。聂隐娘的多重身份和鲜明的女性特征贯穿影片始终。
影片讲述了一个武功超群的女子,为了完成自己的教学,奉命刺杀朝廷要员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找到了自己,寻找自我认同的途径。聂隐娘因婚姻破裂陷入痛苦,因不小心伤人被父母送到道观。唐传说中神秘而浪漫的“神奇侠”成了电影文本中的“刺客”。童年的创伤,家族的牵累,中唐藩镇割据的混乱,在一次失败的刺杀和反复考虑“杀”与“不杀”中慢慢铺开。
聂隐娘的多重身份隐藏在她身边人的不同名字里。回到家,家仆叫来了充满敬意和爱心的“七娘”,唤醒了尘封的童年记忆,而蒸腾的水汽则冲走了尘封的岁月。石榴裙婀娜艳丽,独自挂在衣架上,湿漉漉的长发披散开来。灰色的剪影里,那个爬过屋檐,带着冰冷英气走过墙壁的刺客,只是一个无助的少女。这是聂隐娘女性身份的清晰展现,多年被包裹和隐藏的女儿终于在洗澡的时候获得了解放。母亲小心翼翼的和阴娘说话,权衡着自己的话来为嘉诚公主过去的断婚正名。在“瑶娘”这个名字的背后,这位公主对她既无奈又愧疚。在聂父母的对话中,“别扭”是挂在嘴边的名字,比嘉成公主刻骨铭心的自责更浓,凸显了聂隐娘的女儿身份。然后,在午夜暗杀之后,田纪安的声音“姚期”是短暂的浪漫和甜蜜。淡淡的帷幕过后,昔日的恋人撕开了回忆的伤口,于是我们突然感受到了藏在冰冷面具下的温情脉脉。聂隐娘不再是生活在唐传说中的“奇人”,但她最终成为了一个失败的刺客。但与此同时,谁又能否认她曾经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姐,一个掌上的女儿,一个痴情的情人...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女性形象逐渐活跃在屏幕上。
作为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文学形象——聂隐娘,她的名字“隐藏的母亲”只存在于电影中那位镜花水月的少年的语境中。她在生与死之间遇到了那个擦亮镜子的少年,然后看淡这个世界,和她一起隐退。镜花水月少年视角下的隐士,是千帆破茧后重生的隐士,是恢复自我意识的独立身份。这个设定无疑是对唐代传奇文本的又一次解构。如果说聂隐娘与小说中那位镜花水月的少年的独立婚姻是对中晚唐自由侠客梦想的追求,那么电影叙事中的相互理解更多的是基于明确身份认知后的第二次建构。
影片以聂隐娘为连接点,以一个舒缓的镜头,画出了一群绚烂苍凉的中唐女性。不同于女权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维尔(Laura Muville)在她的文章《守望快感与叙事电影》(Watching Journal and叙事film)中总结的那样,主流商业电影的叙事结构是男性被看到,女性被看到。《刺客聂隐娘》的叙事视角完全以女性为中心,女性成为观看的主体,而隐藏在母亲周围的则是被观看者,这也跳出了原著小说中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在通常的商业电影中,“男主的英雄冒险才是剧情,美艳神奇的女性才是壮观的单元。”这种模式在《刺客聂隐娘》中得到了彻底的解构。导演完全去除了小说中的主要叙事,作为工具,消失的女侠客被拉回世俗层面。武侠影视作品中没有英雄传奇式的冒险,也没有被惊艳过的女性。在凝重而缓慢的镜头里,无数暗流潜伏在平静的生活表层之下。嘉诚公主、嘉信公主、阿姨、田妻、胡姬,几个烙上时代印记的女人,无助地挣扎着,独自寻找着。他们无一例外地局限于政治情欲,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人,没有一个同类”的命运。
身份的重构和彼此的多重镜像

影片在生活场景中投入了大量镜头,其中聂穆和田的妻子在晨钟暮鼓中对着镜子自拍打扮。在中国古代价值观中,往往强调“女人是取悦自己的”,女人的镜子后面,隐喻着取悦别人,可怜自己。镜子,一个具体的物象,与电影中“青鸾舞镜”的传说遥相呼应,“镜像”成为我们了解电影中人物的绝佳入口。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潜意识是被建构的,是他人的语言,潜意识的结构就是语言的结构。在他的镜像阶段理论中,他提出主体的形成过程是基于一个三部分结构,即想象、象征和真实。刺客聂隐娘通过三次暗杀完成了聂隐娘主体意识的构建。
认知建构的第一个阶段是寻求认同。这种认知的建构往往是基于另一种。拉康认为,人永远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人总是认识“他者”。自我是人与自己之间的一种想象关系,是与“他者”的混合体。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次完美刺杀后,聂隐娘在第二次任务中失败了,不是因为她不如别人,而是因为她“不忍心杀她,因为她很可爱。”。显然,师父“剑道无亲,圣人无忧”的训斥,只是增加了她内心的疑惑,预示着她自我身份的萌发。然后,谷道公主把尹娘送回家,导演在洗澡换衣服的时候故意穿插了一个长长的心理蒙太奇。从远处的近景镜头看,杂花和茫茫的元夜是固定的,嘉诚公主远嫁祎凡的孤独命运就围在其中。此时,冰冻长镜头对准弹钢琴的公主,人物一下子充斥了整个场景。《山流水》的旋律在公主指尖流淌,超然的心境不言而喻。青鸾本来是无类的,不唱歌,看到镜子后没有马上在夜里跳舞。这就是对自我的终极坚守。嘉诚公主是青鸾自描述的,但对公主有着复杂感情的隐母现在通过“青鸾舞镜”的记忆来表达自己。“娘娘是青鸾,孤身一人,无同类。”这是对公主身世的哀叹,也是彩娘自我聆听的过程。嘉成公主是隐母照顾的另一个,为隐母探索自我打开了大门。之后,在持续数秒的空镜头里,一个白牡丹在烟雨的天空下,纯净的摇曳着,很像留下的“灵性母女”。
除去粗糙的刺客服装后,彩娘重新找回了女儿的身体,并将在第三次暗杀中彻底完成身份探索。这个象征性的过程伴随着主体的丧失和身份的颠覆。隔着窗帘看去,明暗交替,烛光跳跃中的深情和软语进一步激化了隐藏的母女俩的认知,被阻隔多年的女儿沉重而开放。胡姬的那句“七委屈”,让彩娘拾起了久违的情感和柔情。之后,彩娘无疑开始把胡姬当成自己的“同类”,努力去祛魅被蛊害的胡姬。可以说,胡姬是充满女性情感的隐母的镜像,隐母通过观察胡姬来再现自己。
最后一个阶段是自我重建。在此期间,隐藏的母亲通过擦亮镜子的少年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重构。舍身救下擦亮镜子的年轻人,治愈木屋里的病人,是对流浪隐士的安慰和保护。与嘉诚公主的恋母情结和胡姬的互相欣赏不同,这个镜花水月的少年带来了一种与异性完全不同的亲密关系,治愈了刀伤,抚慰了感情。隐藏的母亲最终在镜子里重建自己,她的自我寻找也就完成了。
从真正的“花前月下”的“物”意象,到《青鸾舞镜》的自传体“镜语”,最后到电影中的三重“画像”,既有外在又有内在,互为镜像,聂隐娘在深层隐喻中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重构。这个过程就像“一部只有一个人的长独幕剧。”人物是最终被称为主体的个体,道具是镜子。整个故事发生在一个人和一面镜子之间。"
影片中除了主人公,其他主要人物都是彼此的镜像。嘉诚公主是哀镜的绿色女神,激发了含蓄的母亲自我意识,体现了姐姐嘉欣公主对“道”的坚持;元氏县,深宅大院的小姐,养尊处优,精明无情。众所周知,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假面杀手“精警”,也有着很深的血仇,作为她的“影子”而存在;田纪安陷入了政治漩涡,却又不愿自拔,与擦亮镜子的少年的自由随和形成了极端的反差,似乎是对镜像的解构。
丽芙诗歌与沈从文美学
固定布局
在工具栏上设置固定的宽度和高度
背景可以设置为包含
可以完美地对齐背景图像和文本
并制作自己的模板

在电影开场时灰白色色调凝聚的压抑气氛中,隐约可见太阳的全盛时期。微微摇曳的枝叶,沙沙作响的蝉鸣,以及“风暖鸟群鸣”的慵懒画面,很快被“流星般呢喃”的矫健姿态打破。银幕上出现绯红奔放的“刺客聂隐娘”人物时,背景是平原森林和沙漠,西方寒鸦星罗棋布,意为“半河沙沙,半河红”。舒淇说,拍《聂隐娘》的意思是“等待风、云、鸟散去”。这种在等待中达成的意象与其说是电影,不如说是流动的诗篇,每一帧都是从唐诗中提炼出来的意境。
导演侯孝贤非常热爱沈从文的小说,在拍摄实践中不自觉地实践着沈从文的视角。侯导曾经说过:“看完之后,突然觉得眼界开阔了。感觉作者的观点不是批评,不是悲伤,其实是更深的悲伤。沈从文不会从某个角度去挖掘和批判人。那些人死在他的话里很正常,都是天底下的事。”在他看来,这种沈从文式的美学有自己的胸怀和气度,它远远地停下来,静静地看着人间的一切悲欢离合。在《聂隐娘》中,除了大量使用空镜头外,描写的故事和人事都极其平淡。作家阿城曾经说过,侯导在剪辑这部电影时并不追求逻辑因果,只想要一种自然的质感。叙事埋在山水长卷的背后。复杂多变的光影,凄厉神秘的配乐,简洁凝练的台词,对具体情节已经不再印象深刻。而是“鸟来山,鸟来山,人在水声中唱着哭着”的感觉深刻而永恒。
虽然文学带来的弊端难以避免,但在看电影的很多瞬间,我还是被青鸾凄美的歌舞,隐母的冷漠与孤独,画框的古意和苗苗的余韵所打动,再现了一个想象中的唐朝。最终阴娘带着擦亮镜子的少年隐退,青山隐隐,绿水一路。这个关于孤独的故事,在回家的宁静中告一段落,但在广阔的世界里,独自行走,岂止是从前的隐者?
明天群山将把我们分开,明天之后——谁能说呢?。
(本文为2020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电影与文化研究”期末作业,获“2020年新青年电影夜船优秀影视评价”)
参考文献:
1.李云:《太平广记》,中华书局,2013年
2.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戴锦华:《昨日之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结束-
阅读原文
1.《夫君谋 《刺客聂隐娘》:尘世的尽头》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夫君谋 《刺客聂隐娘》:尘世的尽头》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guoji/7988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