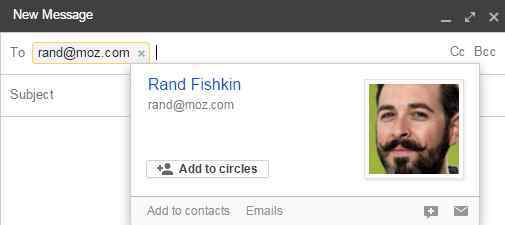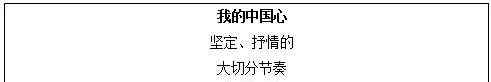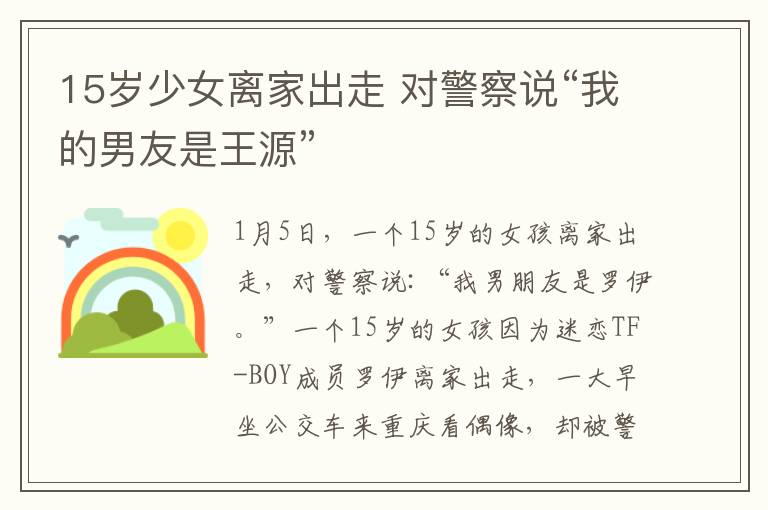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是我父亲的靴子。他和哥哥一起开了一家店,这家店有两条开放式的人行道,开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已经不存在了,但那时候是位于伦敦西区的一条新街。
这家商店有一些简单而安静的特点。门面上没有为皇室服务的招牌,只有写着自己日耳曼姓氏的“哥斯拉兄弟”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如果我要解释为什么橱窗里的靴子总是不更换,我总觉得很尴尬,因为他只做订单,不卖现成的靴子;说那些靴子因为他做的不对而被拒绝,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他买那些靴子是为了装饰吗?似乎也不可思议。他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店里展示不是自己做的靴子。而且,那双靴子太漂亮了——有一双轻盈的舞鞋,纤细到用语言都无法形容的地步;那些带布嘴的漆靴,让人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棕色的马靴,闪着奇异的黑色和明亮的光彩,虽然是全新的,但仿佛已经走过了一百年。只有见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精髓,的确是模型产品。当然,我是后来才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约十四年前我有资格和他一起做成人靴的时候,我对他们两兄弟的性格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因为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觉得做靴子,尤其是做像他这样的靴子,简直就是一门绝妙的手艺。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年轻的脚放在他面前,害羞地问:“哥斯拉先生,做靴子难吗?”
他回答:“这是一门手艺。”从他咬破的红胡子根部,突然出现了一个微笑。
他本人有点像皮革制成的人:脸色发黄,满脸皱纹,头发和胡须微红,呈波浪状,脸颊和嘴角之间有一些整齐的皱纹。他的声音单调,喉咙沉重;因为皮革是一种坚硬的物体,所以有点僵硬和沉闷。这是他脸的特点。只有他蓝灰色的眼睛里隐含着单纯严肃的神态,仿佛痴迷于理想。虽然他哥哥因为工作努力,看起来各方面都比较瘦,比较苍白,但是两兄弟很像,所以在我的早年,有时候要和他们一起订靴子,才能确定他们是谁。后来我想通了:如果我不说“我想问我哥”,那就是他;你说这个,就是他弟弟。
当一个人老到荒唐到可以邀功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他从来不邀功哥斯拉兄弟。如果有人默认了几双靴子的价格,比如说两双以上,觉得还是他的顾客很舒服,就走进他的店铺,把脚放在蓝色的铁眼镜下面,这就有点太不对了。
人家不能经常去找他,因为他做的靴子很耐穿,一时穿不烂——他好像把靴子的精髓缝进去了。
当人们走进他的商店时,他们并不觉得“请把我想买的东西带给我,让我走”,而是平静地走进教堂。客人在唯一的木椅里等着,因为他的店里没有人。过了一会儿,你可以看到他或他哥哥的脸从商店二楼的楼梯上往下看——楼梯很暗,同时又透出一股皮革的味道。然后可以听到一种喉音,狭窄的木楼梯上拉木拖鞋的踢踏声;他终于站到了来访者面前,上身没有穿外套,有点驼背,腰间围着一条皮围裙,袖子卷着,眼睛眨着——好像他刚从靴子梦中醒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只被太阳打扰的猫头鹰。
于是我说:“哥斯拉先生,你好吗?你能给我做一双俄罗斯靴子吗?”
他会默默的离开我,回到原来的地方,或者去店铺的另一边;这时,我继续坐在木椅上,享受皮革的香味。不久之后,他回来了,瘦瘦的手里拿着一个棕褐色的皮革。他盯着皮革对我说:“多漂亮的一块皮革啊!”我夸完之后,他继续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啊!等你方便的时候,我去要。”于是他说:“半个月后,好不好?”如果答案是他哥哥,他说:“我想问问我哥哥。”
然后,我会含糊地说:“谢谢,再见,哥斯拉先生。”他说了声“再见”,继续看着手中的皮革。走到门口,听到他木拖鞋的踢踏声,把他送回楼上,梦见他的靴子。但如果他还没有为我做一双新款式的靴子,他一定要循规蹈矩——叫我脱下靴子,拿在手里,用马上变得挑剔而又爱抚的眼神看着它们,仿佛在回忆他创作这双靴子时的热情,仿佛在责怪我把他的杰作穿成这样。后来他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在外边划了两三次,然后用他敏感的手指来回摸我的脚趾,想找出我要的要点。
有一天,我有机会和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天。我对他说:“哥斯拉先生,你知道城里最后一双走路用的靴子嘎吱作响吗?”
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好像在期待我收回或者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
“那些靴子不应该嘎吱作响。”
“对不起,他打电话来了。”
"你的靴子还穿着的时候湿了吗?"
“我不这么认为。”
听了这句话,他皱起眉头,仿佛在寻找那双靴子的记忆;很抱歉提到这件严肃的事情。
“把靴子送回去!”他说:“我想看一看。”
因为我那双吱吱响的靴子,我心里觉得可惜;我完全可以想象当他把头埋在靴子里时,他不断的悲伤。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了就不好了。如果我修不好,这双靴子就不收你钱了。”
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穿着在大公司买的靴子,因为急用,不小心走进了他的店。他接受了我的命令,但没有皮革给我看;我能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看我脚上的劣质皮革。他最后说:
“那不是我的靴子。”
他的语气中没有愤怒或悲伤。甚至没有鄙视,但是有潜在的潜在因素可以冻血。为了讲究时尚,左脚的靴子让人在一个地方不舒服;他伸手用一根手指按住它。
“这里疼,”他说。“这些大公司真是失礼。丢人!”然后,他心里好像有点不耐烦,就说了一系列讽刺的话。我听他谈了他的职业处境和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垄断了一切,”他说。“他们用广告代替工作来垄断一切。我们喜欢靴子,但他们抢走了我们的生意。现在——我们很快就会失业。生意一年比一年慢——你以后会明白的。”我看着他布满皱纹的脸,看到了一些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痛苦的事情和痛苦的挣扎——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被很多灰胡子覆盖了!
我尽力向他解释我买这双倒霉靴子时发生的事情。但是他的脸和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果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就点了很多靴子。这太可怕了!这双靴子比以前更旧了。戴了快两年了,没想到去他那里。
后来,当我再次去他家时,我惊讶地发现他店外的两扇窗户中有一扇上画着另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一个鞋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皇室服务的。那些普通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它们高贵的风格,挤在不同的窗户里。里面现在已经缩成了一个小房间,店铺的楼梯间也比以前更暗,充满了皮革味。我等的时间比平时长,只看到一张脸向下窥视,然后传来木拖鞋的踢踏声。最后,他站在我面前;他透过生锈的铁架眼镜看着我说:
“你是——先生?”
“啊!哥斯拉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你知道,你的靴子好结实!看,这双还是很体面的!”我向他伸出了脚。他看了看靴子。
“是的,”他说,“人们似乎不需要结实的靴子。”
为了避开他责备的眼神和语气,我赶紧接着说:“你的店怎么了?”
他平静地回答:“费用太大了。要不要做靴子?”
虽然我只需要两双,但我还是向他订购了三双。我很快就离开了那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以为他的心被抓住了,是他用心不良的一部分;也许不是反对他,而是反对他的理想靴。我觉得大家不喜欢那种感觉。因为过了几个月,我又去了他的店;记得我去看他的时候,心里就有这种感觉:“哦!发生了什么事?我摆脱不了那个老人——所以我去了!也许你会见到他哥哥!”
因为我知道他哥哥太老实了,即使在暗地里也不能怪我。
我的心安定下来。出现在商店里的是他的哥哥。他正在整理一块皮革。
“啊!哥斯拉先生,”我说,“你好吗?”
他走近我,盯着我。
“我很好,”他慢慢地说,“但是我哥哥死了。”
我才知道我遇到的原来是他。但是多老多瘦啊!我以前从未听他提起过他的兄弟。我吃了一惊,于是喃喃道:“啊!我觉得对不起你!”
“的确,”他回答,“他是个好人,他会把靴子做好的;但是他死了。”他摸了摸自己的头顶,我猜他好像在说明他弟弟的死因;他的头发突然变得像他可怜的兄弟一样稀疏。“他又失去了一个车间,他的心一直很硬。要不要做靴子?”他举起手中的皮革说:“这是一块美丽的皮革。”
我做了几双靴子。这双靴子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但这双靴子比以前更结实,穿起来也不会差。不久之后,我出国了。
我回到伦敦已经一年多了。我去的第一家店是老朋友的店。我走的时候,他已经60岁了。回来的时候,他好像75岁了。他看起来又老又瘦,不停地发抖。这次,他一开始真的不认识我。
“啊!哥斯拉先生,”我说,感到有些恼火,“你的靴子太棒了!看,我在国外的时候几乎总是穿这双靴子;连一半都没穿破吧?”
他细看了我的俄罗斯靴子很久,脸上似乎恢复了平静的颜色。他把手放在我的靴子上,说道:
“有合适的吗?我记得做这双靴子花了很大力气。”
我向他解释说那双靴子非常合适。
“你要做靴子吗?”他说:“我很快就能做到;现在我的生意很清淡。”
我回答:“求求你,求求你!我非常需要靴子——各种靴子!”
“我可以做出新的风格。恐怕你的脚已经长大了。”他很慢地画了一张我的脚型图,又摸了摸我的脚趾头,只抬头看了我一眼,说:
“哥哥死了,我告诉你了吗?”
他变得这么老了,看到它真的很难过。我很高兴离开他。
我对这双靴子不抱任何希望,但有一天晚上它们到了。我打开包裹,把四双靴子排成一排;然后,在双一试穿这双靴子。完全没有问题。这双靴子是他为我做过的最好的靴子,无论是款式还是尺寸,加工还是皮革质量。我在他的靴子里发现了他在城里散步的账单。账单上的报价和以前一模一样,但是我吓了一跳。他从来没有在四季截止日期前打开过账单。我赶紧跑下楼,填了一张支票,马上自己寄出去了。
一个星期后,我走过小街,我想我应该进去向他解释他为我做的新靴子如何合身。但是当我走近他店铺的位置时,发现他的姓已经消失了。橱窗里还陈列着细长轻盈的舞鞋,布开口的彩绘皮靴,彩绘长款马靴。
我进去了,感觉很不舒服。在商店的两个门面里——现在两个门面合二为一——只有一个长着英国面孔的年轻人。
“哥斯拉先生在店里吗?”我问。
他惊奇地同时愉快地看了我一眼。
“不,先生,”他说,“不。但是我们很乐意为您服务。”我们已经转让了商店。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到了隔壁门上的名字。我们为上级做靴子。"
“是的,是的,”我说,“但是哥斯拉先生呢?”
“啊!”他回答说:“死了!”
“死了?但是我刚收到他上周三给我做的靴子!”
“啊!”他说:“真奇怪。可怜的老人饿死了。”
“仁慈的上帝!”
“慢性饥饿,医生是这么说的!你知道,他就是这样工作的!他想让商店继续经营;但是除了他自己,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他接到命令后,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客户不想等。结果,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他总是坐在那里,只是做着做着——我想为他说话——在伦敦,没有人能做得比他更好的皮革,他必须自己做。他就是这样。按照他的想法,你还能指望他什么?”
“但是饿死——”
“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我知道他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直到最后一刻。你知道,我经常在我身边看着他。他从不让朋友吃饭;商店里从来没有一分钱。所有的钱都花在房租和皮革上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活这么久。他经常停止做饭。他是个奇怪的人。但是他做了一双好靴子。”
“是的,”我说,“他做了一双好靴子。”
1.《品质高尔斯华绥 约翰·高尔斯华绥:品质》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品质高尔斯华绥 约翰·高尔斯华绥:品质》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jiaoyu/10721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