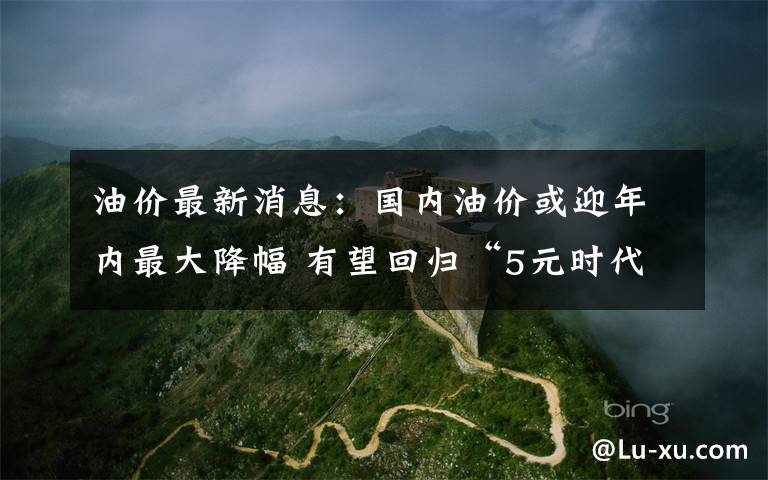很多年前的10月14日,我在一个新旧教学楼上课。从教室窗户望出去,有一座宏伟的天主教堂和一个干净神秘的庭院。那时,天总是蓝的,夏日的阳光倾泻在教堂的红瓦上。我总是不得不歪着头去看教堂塔楼上的巨大十字架,因为它太高了——在老城区建造那几十栋建筑之前,它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
有时候,我到学校很早,就会趴在窗台上看教堂,但是我从来都不够。它的伟大往往让我觉得渺小,过于简单机械的学习让我难以想象未来。学校发言人老是放各种公告,夏天下午特别气人。但偶尔也会神奇地响起一些旋律,比如《未来的主人》。那一瞬间,天上飘着白云,我第一次需要音乐。

那个时候,罗大佑总是让人很累,因为他太喜欢问问题了。比如1980年我出生的时候,他问“我知道什么是爱,但永远是什么”。二十年后,他在《情歌2000》里问:“你还想认我吗?”但是答案在哪里呢?
当我第一次听鲍勃·迪伦的《随风飘荡》时,我已经离开了教学楼,甚至离开了这座城市。我不再相信罗大佑,因为我知道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们这一代人都不会成为未来的主人。至于那些问题,答案还在风中飘荡吗?我曾经相信。但是很多年后,当我步入中年,我知道了人生的悖论:你的问题越来越多,而答案却越来越少。“答案飘”也是提问,结果也没什么不同。
我出生晚,没有经历过左翼运动席卷全球的60年代。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如果我在局里,我注定是时代的炮灰,而当时的中国只是活在外面的世界。从当下回望历史,大时代的幸运儿终究是少数,即使他们拍了大部分的风景。
鲍勃·迪伦当然是幸运的。1961年,他从明尼苏达大学退学,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1962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砂纸般的声音》令人难忘。1963年,他发行了专辑《随心所欲的鲍勃·迪伦》,其中的《随风飘荡》和《一场大雨的坠落》使他成为反战的灵魂。前者是他最动人的作品,后者充满诗意和末日情怀,已经成为古巴一切恐惧之和的代名词。去年描述古巴所有恐惧的年度好书被称为“上海黎明”。1964年,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后,迪伦发行了专辑《时代在变化》,重点是民权运动,使其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宣言之一。
在《随心所欲》的封面上,照片中的人物是鲍勃·迪伦和苏西。
那一年的大起大落远不止如此。在那个“自由的夏天”,大学生们纷纷参加民权运动。那年冬天,伯克利掀起了抗议学校禁止反越战抗议的言论自由运动,800多名学生被捕。时代变了是学生们的主题曲,但鲍勃·迪伦自己选择了告别革命。
为此,在很多人眼里,他真正的辉煌甚至停留在60年代,或者停留在前三张专辑里,从来没有拿走过。这可能是因为他深刻的知道创作过程是不可复制的,即使骄傲,也需要告别自己的神话。他曾经说过:“写这些歌,你要有主宰精神的力量。我做过一次,一次就够了。对我来说,我出现的时间是对的,我也很理解我的时间。如果我现在出道,很难想象灵感会从哪里来,因为你要呼吸正确的空才能有创意。”
人不能复制自己的创作过程,反而好的音乐可以跨越时代,弥补这个缺陷。《时代变了》上映二十年后,1984年,乔布斯读了《时代变了》的歌词,开始了自己的时代。
1965年,鲍勃·迪伦发行了他的专辑《重返61号公路》。他最初选择民谣是因为他不信任摇滚。“摇滚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它们朗朗上口,节奏很强,让你飘飘欲仙,但不够认真,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当我接触到民谣的时候,是比较严肃的音乐。那些歌有更多的忧郁,更多的悲伤,更多的对超自然的信仰,更深的感情...生活太复杂,无法反映摇滚乐。”此时的民歌,刚刚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民歌复兴运动,具有左翼倾向。这时,他告别了纯粹的民谣,甚至得罪了他的歌迷。专辑《像一块滚石》自成一家,多年后成为滚石杂志评选的“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的第一首。
《重返61号公路》专辑封面
他也爱《垮掉的一代》。1959年,他读凯鲁亚克时说:“凯鲁亚克,金斯堡,科索,费林格,他们太神奇了...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像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他喜欢“垮掉的一代”的逆反心理,这种逆反心理不涉及政治,即使与他曾经追求的左翼文化相悖。他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像一块滚石》,像《在路上》,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图腾。
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迫切需要鲍勃·迪伦。左翼运动不是鼓吹共产主义,只是想对抗主流文化,重估一切价值观。这一切甚至有些道理,甚至需要走自己的路,离经叛道的鲍勃·迪伦来纠正偏差,让一切更接近真正的理想主义。
至于鲍勃·迪伦,也许他更需要苏西。许多年后,他们分开了,但后者被赋予了许多头衔,如“20世纪伟大的缪斯之一”、“迪伦的缪斯和导师”、“启发迪伦创作他的一些最伟大的情歌的缪斯”等。对,都是缪斯。没有她,就没有20世纪60年代的鲍勃·迪伦。
1961年,他们相遇了。在鲍勃·迪伦的回忆录中,他写道:“当我第一次见到苏茜时,我一直盯着她。她是我见过的最性感的生物。她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是意大利人。空空气中瞬间弥漫着香蕉叶的味道。我们开始说话,我的头开始发晕。丘比特之箭曾经在我耳边呼啸而过,但这次它击中了我的心。遇见她就像走进《一千零一夜》,她的笑容照亮了一条繁华的街道。她就像罗丹的雕塑,被赋予了生命。接下来的整整一周,我都被她迷住了。我知道我这辈子第一次爱上了她,即使在30英里之外,我仍然能感觉到她的呼吸。”也许,仅凭这段话,鲍勃·迪伦就能获得文学奖?
鲍勃·迪伦和苏西
一周后,他们开始恋爱,并于1961年底开始同居。当然,他给她写的最著名的一首歌就是那句“我给了她我的心,但她要的是我的灵魂”。
如果苏茜只写情歌,她就不是缪斯女神。她在《放手的时候》中写道:“我们认识的时候,鲍勃对政治没有概念,我把对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兴趣转移到了他身上。”换句话说,苏西参与左翼政治是她能成为缪斯的原因。
兰博在写作上对鲍勃·迪伦影响深远,也是苏西的“牵线搭桥”,也是鲍勃·迪伦的诗性源泉。
所以在他最红的时候,有人称他为大诗人。但即便如此,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有人愤怒地说,“那么多诗人,为什么要给一个歌手颁奖”。
事实上,鲍勃·迪伦的伟大在于他已经超越了诗歌本身,这正是他超越诗人的地方。那个澎湃风云的大时代,不是他手中只有文字呈现的。他的问题,他的答案在风中飘荡,也在他独特的声音和旋律中呈现。他的表达比诗歌更广泛。
很多年前的10月14日,我在一个新旧教学楼上课。从教室窗户望出去,有一座宏伟的天主教堂和一个干净神秘的庭院。那时,天总是蓝的,夏日的阳光倾泻在教堂的红瓦上。我总是不得不歪着头去看教堂塔楼上的巨大十字架,因为它太高了——在老城区建造那几十栋建筑之前,它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
有时候,我到学校很早,就会趴在窗台上看教堂,但是我从来都不够。它的伟大往往让我觉得渺小,过于简单机械的学习让我难以想象未来。学校发言人老是放各种公告,夏天下午特别气人。但偶尔也会神奇地响起一些旋律,比如《未来的主人》。那一瞬间,天上飘着白云,我第一次需要音乐。

那个时候,罗大佑总是让人很累,因为他太喜欢问问题了。比如1980年我出生的时候,他问“我知道什么是爱,但永远是什么”。二十年后,他在《情歌2000》里问:“你还想认我吗?”但是答案在哪里呢?
当我第一次听鲍勃·迪伦的《随风飘荡》时,我已经离开了教学楼,甚至离开了这座城市。我不再相信罗大佑,因为我知道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们这一代人都不会成为未来的主人。至于那些问题,答案还在风中飘荡吗?我曾经相信。但是很多年后,当我步入中年,我知道了人生的悖论:你的问题越来越多,而答案却越来越少。“答案飘”也是提问,结果也没什么不同。
我出生晚,没有经历过左翼运动席卷全球的60年代。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如果我在局里,我注定是时代的炮灰,而当时的中国只是活在外面的世界。从当下回望历史,大时代的幸运儿终究是少数,即使他们拍了大部分的风景。
1.《2016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伟大在哪里 听听这几首歌就知道了》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2016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伟大在哪里 听听这几首歌就知道了》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junshi/10757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