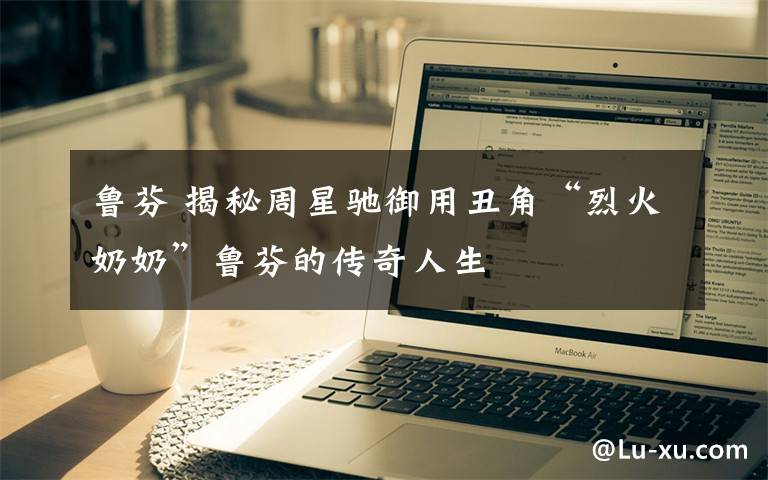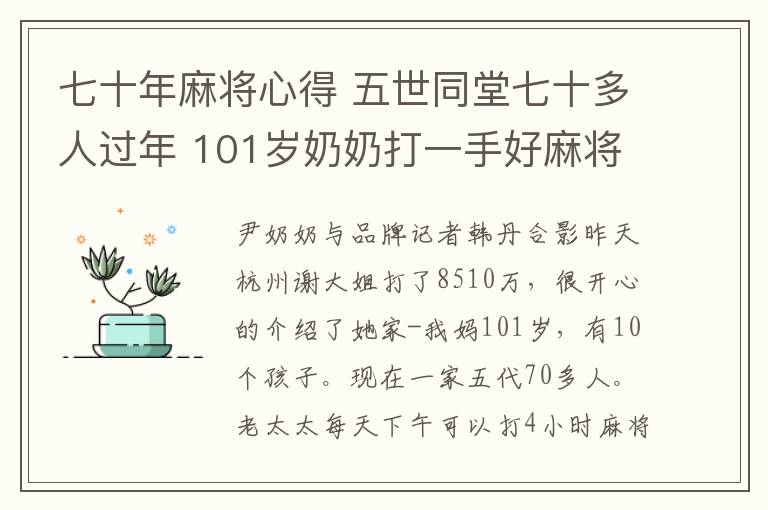如花奶奶,摇晃着豁开了二道口子的蒲扇,招呼着街坊的几个老姐妹。一边催着如花,端茶倒水,老槐树下,顿时热闹了起来。西边低垂的天际,残阳如血,红得醉人。几条大狗,也跟随着主人,走向街角。西北的小镇,普通的几乎没有特色,在这傍晚时分。张秃子家的婆娘扯嗓子的骂声,跟随着小秃子的脚后跟,也挤进了黄昏的喧闹。小秃子滑得像泥鳅,一眨眼的工夫,已经不见了踪影。燥热的空气中,飘浮着燃灰堆的残烟,一阵风起,塑料燃烧的恶臭味,让如花奶奶骂开了口:那个缺徳货,尽做这好事。秃子的婆娘也附和着,满嘴的唾沫星子,让旁边的李二婶,连忙用手捂着脸。二婶的粗糙双手,还是挡不住那一阵子浓浓的唾沫星子。这时远处的狗急促的叫声,顺着街道频频地传来。近外的狗也帮腔地胡乱的叫着,好像习义务似的。昏黄的路灯,几条模糊的身影,正朝着大槐树走来。大麦茶的焦香味怡和中带着丝丝甜味,能消食解腻。土坯子茶缸,厚重实在,有远古的粗犷之风。如如花奶奶和她的街坊邻居们,竟然不穿上衣而围桌闲聊。
如花奶奶,摇晃着豁开了二道口子的蒲扇,招呼着街坊的几个老姐妹。一边催着如花,端茶倒水,老槐树下,顿时热闹了起来。西边低垂的天际,残阳如血,红得醉人。几条大狗,也跟随着主人,走向街角。西北的小镇,普通的几乎没有特色,在这傍晚时分。张秃子家的婆娘扯嗓子的骂声,跟随着小秃子的脚后跟,也挤进了黄昏的喧闹。小秃子滑得像泥鳅,一眨眼的工夫,已经不见了踪影。燥热的空气中,飘浮着燃灰堆的残烟,一阵风起,塑料燃烧的恶臭味,让如花奶奶骂开了口:那个缺徳货,尽做这好事。秃子的婆娘也附和着,满嘴的唾沫星子,让旁边的李二婶,连忙用手捂着脸。二婶的粗糙双手,还是挡不住那一阵子浓浓的唾沫星子。这时远处的狗急促的叫声,顺着街道频频地传来。近外的狗也帮腔地胡乱的叫着,好像习义务似的。昏黄的路灯,几条模糊的身影,正朝着大槐树走来。大麦茶的焦香味怡和中带着丝丝甜味,能消食解腻。土坯子茶缸,厚重实在,有远古的粗犷之风。如如花奶奶和她的街坊邻居们,竟然不穿上衣而围桌闲聊。  这里年轻的男人们已很少见,成片的贫瘠的土地,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地干活也出产不了几个钱,能出去的人都亲帮亲邻帮邻,天南地北地去拓展寻活,总比守候着家里强,家到成了过年的象征,浓烈的思潮也在年关,绝大多数时间几乎会忘记了家乡的味道。古老的习俗,总刻画在生活中,眼前的一切,外乡人见之绝对是瞠目结舌,见怪不怪,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几条黑影已经到了眼前,在狗子们吠叫声交织的一路护送下。还是李二婶眼尖:这不是瑞芳家的姑爷吗?秃子的婆娘,一边用左手抓起干瘪下垂的乳房,右手不停的挠着痒痒,也忙着打招呼:瑞芳家的姑爷,怎么晚上有空过来?
这里年轻的男人们已很少见,成片的贫瘠的土地,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地干活也出产不了几个钱,能出去的人都亲帮亲邻帮邻,天南地北地去拓展寻活,总比守候着家里强,家到成了过年的象征,浓烈的思潮也在年关,绝大多数时间几乎会忘记了家乡的味道。古老的习俗,总刻画在生活中,眼前的一切,外乡人见之绝对是瞠目结舌,见怪不怪,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几条黑影已经到了眼前,在狗子们吠叫声交织的一路护送下。还是李二婶眼尖:这不是瑞芳家的姑爷吗?秃子的婆娘,一边用左手抓起干瘪下垂的乳房,右手不停的挠着痒痒,也忙着打招呼:瑞芳家的姑爷,怎么晚上有空过来?  如花,如花,快给姑爷搬条椅子。如花奶奶,站起又坐下,暗影里那二个乳房摇晃了几下,又服帖地贴在胸前。如花瘦小的身体,双手用力的抱着一把椅子过来,瑞芳家的姑爷,连忙接着,挨着如花奶奶坐下。小秃子他娘,停下挠痒的手,感觉指甲缝里满是了泥,左手从桌上的茶袋里,拿起一粒大麦,挑剔着右手的每一个指甲。李二婶皱了皱眉,顺势往边上移动了坐椅。
如花,如花,快给姑爷搬条椅子。如花奶奶,站起又坐下,暗影里那二个乳房摇晃了几下,又服帖地贴在胸前。如花瘦小的身体,双手用力的抱着一把椅子过来,瑞芳家的姑爷,连忙接着,挨着如花奶奶坐下。小秃子他娘,停下挠痒的手,感觉指甲缝里满是了泥,左手从桌上的茶袋里,拿起一粒大麦,挑剔着右手的每一个指甲。李二婶皱了皱眉,顺势往边上移动了坐椅。  瑞芳家的姑爷是方园几十里出了名的人,也是惟一一个还没有出门闯荡世界的人,是有故事的人。一句话,不简单。每个地方,同龄的人和不同龄的人都各自有自己的梦想,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每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也是社会舞台框架不可缺少的材料。瑞芳家的姑爷姓赵,叫一民。地方上的人口顺,会开口的都叫姑爷,虽然有些没大没小,到也显得亲切。赵一民从手包里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一会儿通了,就随手递给如花奶奶。手机里响起,如花爸爸的声音:给娘请安了。娘儿俩一问一答起来。奶奶又把联系交给了如花,如花的眼睛里已经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快要掉下来了。赵一民从口袋里掏出一大一小的二个信封,打开手机的照明功能,仔细地看了看信封上的字,分别交给了如花和如花奶奶,嘱咐她们收好。
瑞芳家的姑爷是方园几十里出了名的人,也是惟一一个还没有出门闯荡世界的人,是有故事的人。一句话,不简单。每个地方,同龄的人和不同龄的人都各自有自己的梦想,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每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也是社会舞台框架不可缺少的材料。瑞芳家的姑爷姓赵,叫一民。地方上的人口顺,会开口的都叫姑爷,虽然有些没大没小,到也显得亲切。赵一民从手包里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一会儿通了,就随手递给如花奶奶。手机里响起,如花爸爸的声音:给娘请安了。娘儿俩一问一答起来。奶奶又把联系交给了如花,如花的眼睛里已经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快要掉下来了。赵一民从口袋里掏出一大一小的二个信封,打开手机的照明功能,仔细地看了看信封上的字,分别交给了如花和如花奶奶,嘱咐她们收好。  仰望天空,宇宙浩瀚。回家的路上,赵一民觉得脚下的路每一步都不平坦。想到如花,一民的心情又不好起来。翠山乡以前是很有名的地方,山青水秀,民风独特,古老与淳朴兼容。十多年前,省里规划,要修一个超大水库。有利有弊,翠山乡的命运从此改变,一个失去了大山的滋养,土地都会荒芜。翠山乡管辖的几个自然村,村民们逐渐外移,打工觅活,天南地北地闯荡。一年一年,剩下的老弱妇孺,大多过着清苦的日子。如花命运多舛,腿有残疾,不能与父亲一起出去打工,只好在家与奶奶一起生活。快二十岁的姑娘,那有不向往外面的世界。如花心里,一民叔叔是个好人。上次与父亲通话已经有一个月了,与上次一样,好多好多话都还没说,这么多人在一起也不方便说。夜风一停,闷热得衣服都湿了一大块。虽说翠山乡风俗特异,姑娘家可是规规矩矩的着装。没嫁人生娃,没上了年岁,是不能光膀子乘凉的。
仰望天空,宇宙浩瀚。回家的路上,赵一民觉得脚下的路每一步都不平坦。想到如花,一民的心情又不好起来。翠山乡以前是很有名的地方,山青水秀,民风独特,古老与淳朴兼容。十多年前,省里规划,要修一个超大水库。有利有弊,翠山乡的命运从此改变,一个失去了大山的滋养,土地都会荒芜。翠山乡管辖的几个自然村,村民们逐渐外移,打工觅活,天南地北地闯荡。一年一年,剩下的老弱妇孺,大多过着清苦的日子。如花命运多舛,腿有残疾,不能与父亲一起出去打工,只好在家与奶奶一起生活。快二十岁的姑娘,那有不向往外面的世界。如花心里,一民叔叔是个好人。上次与父亲通话已经有一个月了,与上次一样,好多好多话都还没说,这么多人在一起也不方便说。夜风一停,闷热得衣服都湿了一大块。虽说翠山乡风俗特异,姑娘家可是规规矩矩的着装。没嫁人生娃,没上了年岁,是不能光膀子乘凉的。  如花,如花......如花的爹,梦中猛的惊醒,浑身的汗水象被雨水淋湿一样,心口兀自起伏不定。如花的爹又重复了这个梦境,每次都会惊醒,每次都是大汗淋漓,真是又恼又悔又惆怅。这个滋味谁也无法理解,自责自埋怨。这几年拚死拚活地干活,就是要让自己心安,让如花过上个好日子,也对得起如花的娘。如花奶奶老了,精神已大不如前。刚才接过赵一民递过的手机,与如花她爹说话,自己耳朵听不清楚几句,听见儿子的声音心里格外亲切,知道自己心里也着实惦记着,说几句已经欢喜的不得了。儿子也是很孝顺的,每月都给寄钱,每次都是赵一民过来,放在信封里。多好的一民,瑞芳的姑爷。赵一民一走,李二婶悄悄地问:她爹都好吧?如花奶奶,擦擦眼角,连忙点头:都好都好,谢谢二婶。张秃子家的也裂开嘴:她爹这回给了多少?我家的秃子,二个月了,还没一个子寄回家,再不寄钱,我和小秃子都要上山啃草了。如花顾不得天热,怔怔地看着远方出神,旁边的话语,一点都没往心里去。思绪万千,夜空星星点点,远方、远方......
如花,如花......如花的爹,梦中猛的惊醒,浑身的汗水象被雨水淋湿一样,心口兀自起伏不定。如花的爹又重复了这个梦境,每次都会惊醒,每次都是大汗淋漓,真是又恼又悔又惆怅。这个滋味谁也无法理解,自责自埋怨。这几年拚死拚活地干活,就是要让自己心安,让如花过上个好日子,也对得起如花的娘。如花奶奶老了,精神已大不如前。刚才接过赵一民递过的手机,与如花她爹说话,自己耳朵听不清楚几句,听见儿子的声音心里格外亲切,知道自己心里也着实惦记着,说几句已经欢喜的不得了。儿子也是很孝顺的,每月都给寄钱,每次都是赵一民过来,放在信封里。多好的一民,瑞芳的姑爷。赵一民一走,李二婶悄悄地问:她爹都好吧?如花奶奶,擦擦眼角,连忙点头:都好都好,谢谢二婶。张秃子家的也裂开嘴:她爹这回给了多少?我家的秃子,二个月了,还没一个子寄回家,再不寄钱,我和小秃子都要上山啃草了。如花顾不得天热,怔怔地看着远方出神,旁边的话语,一点都没往心里去。思绪万千,夜空星星点点,远方、远方......  泥鳅似的小秃子,又泥鳅似地回来了,远远地站在他娘前,一手拿着几枝莲蓬,一手拿着一张硕大的荷叶,遮住下半身,裂着嘴,斜着头,头上挂着几根湿漉漉的水草。小秃子试探地叫喊着:好热好热。小秃子娘刚在心里埋怨了张秃子,气还没消,见小秃子浑身滚泥带水的样子,猛地站起来身来,去抓小秃子。二只干枯下垂的乳房,剧烈地抖动着,好像要脱离了身体,又无奈地被牵扯住。小秃子眼尖脚利,又一次泥鳅似地逃脱掉了,直往家里去。背后是光光的屁股,反映着昏黄路灯的颜色,惊得街上的狗又一次集体狂吠。一轮明月,已悄悄的爬上山头。
泥鳅似的小秃子,又泥鳅似地回来了,远远地站在他娘前,一手拿着几枝莲蓬,一手拿着一张硕大的荷叶,遮住下半身,裂着嘴,斜着头,头上挂着几根湿漉漉的水草。小秃子试探地叫喊着:好热好热。小秃子娘刚在心里埋怨了张秃子,气还没消,见小秃子浑身滚泥带水的样子,猛地站起来身来,去抓小秃子。二只干枯下垂的乳房,剧烈地抖动着,好像要脱离了身体,又无奈地被牵扯住。小秃子眼尖脚利,又一次泥鳅似地逃脱掉了,直往家里去。背后是光光的屁股,反映着昏黄路灯的颜色,惊得街上的狗又一次集体狂吠。一轮明月,已悄悄的爬上山头。  李二婶不紧不慢地喝着茶,轻轻的:这娘俩。如花奶奶叹了一口气。如花的眼睛,顺着土路顺着街道顺着赵一民走去的方向,月光下的世界,清清亮亮了许多,也宁静了许多。起风了,老槐树胡乱地摇着枝丫,绞碎的月光,如水般洒下来。虫鸣四起,时快时慢,一刹间,又彻底沉默。在这月光下的天地大舞台,好像有一个主宰,主宰着虫鸣的起伏。天空突然有流星划过,拖着细长的尾巴。月亮,扯了一朵云,把自己藏了起来。没有了月光,天地又变得昏黄,虫声仿佛也模糊不清。如花奶奶的茶正有滋有味地喝着。 翠山乡到底有多大,谁也无法说清。从有地名到现在,也算有头有脸地经过了上千年。远的不说,就捡近的说,人民公社那年,翠山乡也是远近闻名。翠山乡远近闻名的原因是,没有一点政治觉悟。全国各地都大张旗鼓放卫星,讲政治、练钢铁。这样的年代,那里不出点事。就是这翠山乡,无事可出。其实也不尽然,从另一个方向说,是极端的事。若大的一个乡,没有人讲政治。看天吃饭,听天由命,天道酬勤。这十二个字是古训,也是树在人心里的标杆。如花奶奶的奶奶,就这样说的。到了如花爷爷这辈,日子虽穷,但也穷得自在。翠山乡是山连山,水连水,耕地种田代代相传。省政府决定修水库,超大的容量。断了水道的翠山乡,从此不复从前。与命运抗争的最大本钱,首先你得有命,有命才有一切。
李二婶不紧不慢地喝着茶,轻轻的:这娘俩。如花奶奶叹了一口气。如花的眼睛,顺着土路顺着街道顺着赵一民走去的方向,月光下的世界,清清亮亮了许多,也宁静了许多。起风了,老槐树胡乱地摇着枝丫,绞碎的月光,如水般洒下来。虫鸣四起,时快时慢,一刹间,又彻底沉默。在这月光下的天地大舞台,好像有一个主宰,主宰着虫鸣的起伏。天空突然有流星划过,拖着细长的尾巴。月亮,扯了一朵云,把自己藏了起来。没有了月光,天地又变得昏黄,虫声仿佛也模糊不清。如花奶奶的茶正有滋有味地喝着。 翠山乡到底有多大,谁也无法说清。从有地名到现在,也算有头有脸地经过了上千年。远的不说,就捡近的说,人民公社那年,翠山乡也是远近闻名。翠山乡远近闻名的原因是,没有一点政治觉悟。全国各地都大张旗鼓放卫星,讲政治、练钢铁。这样的年代,那里不出点事。就是这翠山乡,无事可出。其实也不尽然,从另一个方向说,是极端的事。若大的一个乡,没有人讲政治。看天吃饭,听天由命,天道酬勤。这十二个字是古训,也是树在人心里的标杆。如花奶奶的奶奶,就这样说的。到了如花爷爷这辈,日子虽穷,但也穷得自在。翠山乡是山连山,水连水,耕地种田代代相传。省政府决定修水库,超大的容量。断了水道的翠山乡,从此不复从前。与命运抗争的最大本钱,首先你得有命,有命才有一切。  如花,如花。看着远方出神的如花,眼睛有些发涩。月亮,星空,都是那么的遥远,如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又是那么近在咫尺,象一民叔叔的手机。如花想爹,知道爹爹在外面打工很辛苦。这个世界上,如花只有二个亲人,奶奶和爹爹。如花也想娘,可娘亲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模糊很快记不起来了。只有几张照片,记录下来娘的模样。日子如流水,一天天过去。一天天过去的还有女孩的青春,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翠山乡,青春的岁月,有些单调和沉闷。女孩的心思,有谁知道,又有谁可以倾诉呢?月亮总算钻出了云层,地上到处都是明亮的月光,远远的望去,窄窄幽幽的街,却格外明亮。 夜已经深了。夏虫似乎沉默,沉默的还有狗狗们的叫声。有一些露水,悄悄的降临,纳凉的人们陆续回屋睡觉去了。放下蚊帐,洗漱过的如花,只穿一件小褂,感觉特别舒服。月光从窗外进来,无拘无束地柔摸着床,还有床上的如花。如花肆意地躺着,任月光触摸,从发梢开始一寸寸一分分地漫过额头漫过眼睛漫过青春的肌肤和微耸的胸部......时间仿佛停滞,如花愿意这温馨的氛围,散漫自己的些许无名状的心思。很久很久,月光还不忍释手,那柔和的月色,还有那清凉的夜风,在如花的清梦里,随着时间悄悄的一起离去。
如花,如花。看着远方出神的如花,眼睛有些发涩。月亮,星空,都是那么的遥远,如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又是那么近在咫尺,象一民叔叔的手机。如花想爹,知道爹爹在外面打工很辛苦。这个世界上,如花只有二个亲人,奶奶和爹爹。如花也想娘,可娘亲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模糊很快记不起来了。只有几张照片,记录下来娘的模样。日子如流水,一天天过去。一天天过去的还有女孩的青春,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翠山乡,青春的岁月,有些单调和沉闷。女孩的心思,有谁知道,又有谁可以倾诉呢?月亮总算钻出了云层,地上到处都是明亮的月光,远远的望去,窄窄幽幽的街,却格外明亮。 夜已经深了。夏虫似乎沉默,沉默的还有狗狗们的叫声。有一些露水,悄悄的降临,纳凉的人们陆续回屋睡觉去了。放下蚊帐,洗漱过的如花,只穿一件小褂,感觉特别舒服。月光从窗外进来,无拘无束地柔摸着床,还有床上的如花。如花肆意地躺着,任月光触摸,从发梢开始一寸寸一分分地漫过额头漫过眼睛漫过青春的肌肤和微耸的胸部......时间仿佛停滞,如花愿意这温馨的氛围,散漫自己的些许无名状的心思。很久很久,月光还不忍释手,那柔和的月色,还有那清凉的夜风,在如花的清梦里,随着时间悄悄的一起离去。  雄鸡高鸣,晨曦微露。朝震如胭脂涂抹着天空,越变越浓,天色也越来越亮了,几朵炫丽的云飘浮在空中,五光十色变幻莫测。山际线起伏有致,厚重的颜色勾勒出分明的轮廓,如巧手的剪纸。初阳照射着大地,也照射着老街,卵圆形泥青色的溪石路,光滑得让人猜不透到底留下了多少岁月的印痕,直直的街,从老槐树通向阳光升起的方向。老街老了,已不复从前的热闹。祖宗传下的逢十市集,几乎空于形式。阳光下的老街醒了,如同一个老人,有些守旧。泛黄的颜面,记录了太多的岁月风霜。 一夜好睡,如花醒来,奶奶已经把早饭做好。青皮的咸鸭蛋切成均匀的二半,油油的蛋黄被洁白的蛋白包裹着,散发出诱人的香味。炒包心菜带着铁锅的味道,这二样都是如花平时爱吃的。几只鸡围着门前,不肯离去。太阳已升得老高老高,南边的云朵正在堆积,风吹过,老槐树叶发出一阵细碎的声音。如花告诉奶奶,要去邻村看望同学,响午饭就不回来了。如花刚要去推自行车,正巧李二婶过来串串门,奶奶从缸里抓了把谷子,撒在门口,公鸡咯咯咯地欢叫了起来。奶奶边嘱付如花路上小心,边从柱子上拿下来一顶草帽,递给如花。如花的自行车,穿过老街向东骑去。洪玲是如花最要好的同学,小学和初中都在一起读书。洪玲的家离学校近,走十多分钟的田埂路,再到机耕路,就快到学校了。小学时是混编的班级,等到了初中,赵一民除教语文,还兼教除数学以外的所有课程。当时,瑞芳教全校的数学。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二个班级,三间楼房,一个不大不小的土操场,还有一口石围子水塘,农忙时操场就成了村民晒稻谷的地方。操场的另一边,是乡村办公室,除了老乡长,会计,还有个电工。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如花和洪玲沉浸在回忆中。青春的血液里澎湃的激情,是对明天的憧憬和向往,更是对外面世界的期待。山岚骤起,万树欢乐。翠山乡……啊! 上篇完
雄鸡高鸣,晨曦微露。朝震如胭脂涂抹着天空,越变越浓,天色也越来越亮了,几朵炫丽的云飘浮在空中,五光十色变幻莫测。山际线起伏有致,厚重的颜色勾勒出分明的轮廓,如巧手的剪纸。初阳照射着大地,也照射着老街,卵圆形泥青色的溪石路,光滑得让人猜不透到底留下了多少岁月的印痕,直直的街,从老槐树通向阳光升起的方向。老街老了,已不复从前的热闹。祖宗传下的逢十市集,几乎空于形式。阳光下的老街醒了,如同一个老人,有些守旧。泛黄的颜面,记录了太多的岁月风霜。 一夜好睡,如花醒来,奶奶已经把早饭做好。青皮的咸鸭蛋切成均匀的二半,油油的蛋黄被洁白的蛋白包裹着,散发出诱人的香味。炒包心菜带着铁锅的味道,这二样都是如花平时爱吃的。几只鸡围着门前,不肯离去。太阳已升得老高老高,南边的云朵正在堆积,风吹过,老槐树叶发出一阵细碎的声音。如花告诉奶奶,要去邻村看望同学,响午饭就不回来了。如花刚要去推自行车,正巧李二婶过来串串门,奶奶从缸里抓了把谷子,撒在门口,公鸡咯咯咯地欢叫了起来。奶奶边嘱付如花路上小心,边从柱子上拿下来一顶草帽,递给如花。如花的自行车,穿过老街向东骑去。洪玲是如花最要好的同学,小学和初中都在一起读书。洪玲的家离学校近,走十多分钟的田埂路,再到机耕路,就快到学校了。小学时是混编的班级,等到了初中,赵一民除教语文,还兼教除数学以外的所有课程。当时,瑞芳教全校的数学。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二个班级,三间楼房,一个不大不小的土操场,还有一口石围子水塘,农忙时操场就成了村民晒稻谷的地方。操场的另一边,是乡村办公室,除了老乡长,会计,还有个电工。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如花和洪玲沉浸在回忆中。青春的血液里澎湃的激情,是对明天的憧憬和向往,更是对外面世界的期待。山岚骤起,万树欢乐。翠山乡……啊! 上篇完 
《筆尖亂彈》系列文叢之三如花奶奶抖了抖开了两个口子的蒲扇,招呼了邻居几个老姐妹。一边开着花,一边喝茶,在老槐树下,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西边天空低低的,夕阳红如血,醉人。几只大狗,也和主人一起,向角落走去。西北小镇,平凡又几乎毫无特色,就在今天晚上。张的老婆扯着嗓子,跟在小的后面,挤进了黄昏的喧闹中。小光头像泥鳅一样滑了一下,一眨眼就不见了。在热空的空气中,燃烧着的灰堆的残烟漂浮着。一阵风起,烧塑料的臭味让茹奶奶骂开了嘴:那是缺货,干这好事。光头老婆也附和着,满嘴唾沫星子,让李二姨挨着她,赶紧双手捂着脸。二姨粗糙的手,一时还挡不住浓浓的气息。这时,狗在远处的快速吠叫声沿着街道频繁地传来。外面的狗也狂吠着要它们,仿佛在学习义务。昏黄的路灯下,几个模糊的身影,正朝着大槐树走去。大麦茶,香气灼热,味道甘甜,能消化食物,缓解油腻。土坯茶壶厚而实,有古糙风。比如如花奶奶和邻居没穿外套围着桌子聊天。“笔尖轻弹”系列的第三部分
沙尔图形
2017年
1.《赵一民 如花》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赵一民 如花》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junshi/6458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