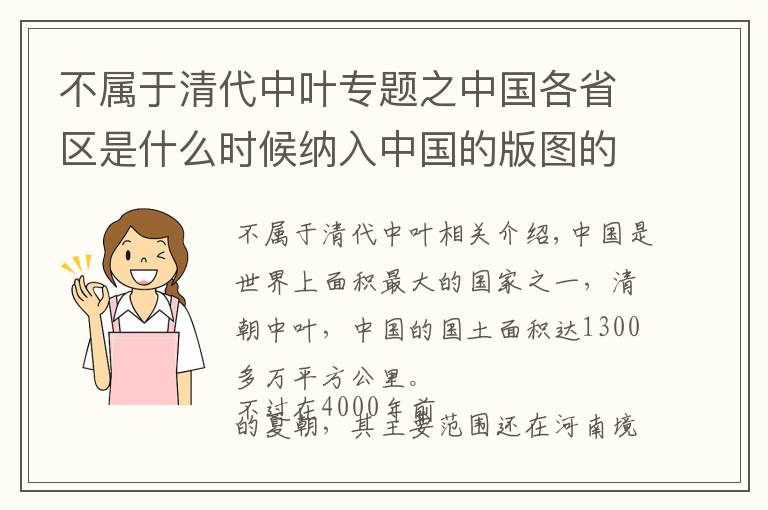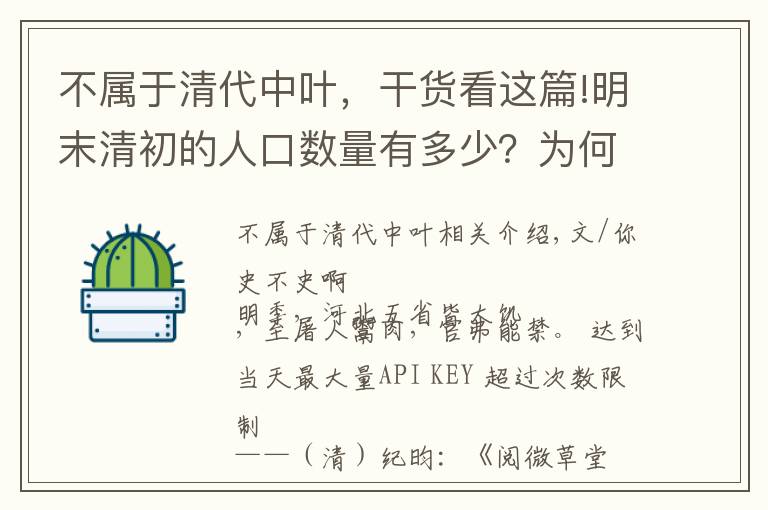《维正之供: 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周健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448页,88.00元
您的书名很有意思,清代将田赋视为“维正之供”,是否意味着田赋不仅仅是财政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周健:书名有标题党之嫌。当下的风气,好像没有一个醒目的主标题(通常是四五个字),就没法取书名了。这对于制度史、社会经济史的著作,可不是一件友好的事。用“维正之供”作书名,理由也很简单:它是清人指称田赋时最常用的术语,而且又是四个字。它最基本的意思是“正供”“正项”,即对于政府而言最重要的财源。在绝大多数语境下,“维正之供”四字专属于田赋,因其重要性明显超过其他税项。
“维正之供”原作“惟正之供”,典出《尚书·无逸》:“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惟正之供”,伪孔传和孔疏解为恭行政事,宋代蔡沈《书集传》以降,始多以常贡正数作解,后者影响较大,与明清政书中的涵义比较接近(经义的不同理解,承牟发松、于薇两位教授指点)。在本书利用最多的清代中后期的档案、政书中,多写作“维正之供”。称田赋为“维正之供”,其涵义我概括为:田赋是国家财政中最重要的部分,其额数是固定的,征解俱有经制。因其为度支所系,关系匪浅,小民应竭力全完,官员应勉力催征,不可使其额缺,致影响国家俸饷之支放、王朝大政之运作。
在传统中国,土地税始终是政府岁入之大宗。有清一代,田赋一直是中央政府的首要财源。在1850年以前,田赋在各税项中占有支配地位,占国家岁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十九世纪中期以降,清朝的财政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厘金、洋关税等新财源出现,田赋的重要性明显下降。但据王业键先生估计,直至1908年,田赋仍占清朝岁入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一,尚居收入栏前列。以上是在中央政府的层面,说的是田赋正项。对于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州县政府)而言,田赋附加税/盈余始终是最重要的公私经费来源。这也意味着,田赋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可谓当日最重要的“国计民生”。
王业键先生名著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回到问题,确如您所言,田赋不仅仅是财政经济,它也是政治,联系着更大的问题。可以说,正是这一点吸引我持续关注这一课题。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最强调财政经济的意义的史家,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黄仁宇先生。他认为,明清中国之不能从“数目字上管理”(此语屡屡被望文生义地误读,黄的定义是“以商业组织作为国家基干”,“注重加速交换”),明太祖以来一脉相承的财政税收制度要负相当之责任。他以个人之经验向后学建议,研究明清以来的历史,可以从财政税收问题打开出路。
确如他所言,研究财政税收势必牵涉国家与社会的整体架构。比如探讨国家的岁入岁出、军费之筹措、户部之职掌则涉及上层机构,描述民众的土地占有、赋税负担及承应赋税之组织则涉及下层机构,而关注州县政府对于人户、田土之控制、赋税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则涉及各层之间的制度联系与管理方式。也就是说,财政税收绝不只是专门的经济制度,它是一个广泛联系的动态体系。由此来切入,或可展现国家与社会的运转方式,丰富我们对于明清、近代的基本认识。
但其实我们对于赋税财政的政治意义一向多有强调,常常将其视为王朝政治盛衰或重大事件爆发的背景或原因,习惯于在税收与政治之间建立过于简单、未必经得起推敲的联系,比如赋税繁重、民不聊生永远是政权覆亡的首要原因。似乎不提炼出类似的重要意义,赋税财政就不是值得关注的课题。在这种倾向下,我们对于税收制度的内在结构及其演进脉络的理解与把握反倒是欠缺的。因此,我觉得对于相关研究者来说,有两重相互联系的挑战,一方面需要从最关键的技术细节入手,真正读懂赋税财政制度,但同时又不能仅将其作为专门史来研究,而应将赋税财政问题合理地定位于大历史的叙述中。
非专业读者可能未必了解,清代田赋制度究竟是怎样一种制度,可否对其基本情况做一介绍?
周健:清代田赋与财政的基本结构确立于十八世纪前期的雍正年间。从明代中后期的“一条鞭法”改革开始,赋役财政的变革趋势是走向“现代田赋制度”(梁方仲先生语)。其特征可以概括为:政府的财政成为可预算的,以银为会计单位,并通过定额的税收向民众征收。这一趋势存在反复,至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与“耗羡归公”才大体确定下来。这套田赋与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一是税制的简单化,二是财政管理的高度中央集权,其利弊都十分明显。
关于税制,“摊丁入地”后,民众的赋役负担已经合并、简化为只依据土地所有缴纳田赋。田赋的征税标准是“地产”,由田地面积与几乎固定的“科则”(税率)来确定税额,以户为单位进行征收。这是一种最简陋的土地税形式,它的缺陷在于无法对土地收益的提高、物价的增长做出调整。
在此税制下,田赋收入增长的惟一动力是纳税地亩的扩大。但问题在于,清朝从未进行全国性的土地清丈,只是以明万历年间的土地数据为基准略作调整。自十八世纪中叶纳税地亩面积恢复万历原额之后,出于观念、财力及利益等方面的考量,各级官员都以维持既有的地亩与田赋原额为行事原则。1890年前后,清朝登记在册的纳税地亩是九点一二亿亩,而实际耕地据估计为十二点四亿亩。土地登记的大量缺漏成为清代田赋管理中最大的缺陷,这从根本上限制了田赋的增长。在清季财政支绌、筹款维艰之际,中央政府始终无法加增田赋正项,地丁银实征不过三千余万两,甚至不及1850年以前的水准,最根本的原因便在于地籍不清。但当日国家处多事之秋,各省督抚绝不敢冒社会失序的风险,推行全国性的土地丈量。
与之相关的奇怪现象是,州县官普遍是在田产、粮户难以稽察的情况下征收田赋。地方官并不直接掌握征税必需的地籍、户籍信息,但他们又必须完成所属州县的赋税额数,否则考成难以过关,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于是,他们便依赖各种中介群体来完成征税任务,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类书吏与差役。也就是说,州县官将本应亲自主导的征税一事不同程度地外包于书差,由后者负责向各户催征,完成州县应解之税额。这种“包征包解”的模式,为当日田赋征纳之常态。
再来看田赋的征价与民众的负担。前面讲到,自十八世纪中期起,除边疆省区的开发外,田赋与地亩的额数是相对固定的。但在物价的长期上涨、政府开支增加的背景下,这样固定化的税额实际上不可能持续。因此,老百姓的实际负担,是田赋税额乘以征价。打个比方,你本年下忙应纳的税额是一两(一年分上、下忙两个纳税期),而这一两又须按照1.2两或者折钱两千文来完纳,这才是真正的税率。此外,完纳之时,经征书差的规费也是必不可少的,常见的有纸笔费、跑腿费等。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田赋负担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征价。征价的决定权理论上在中央政府,清代最重要的一次全国性征价调整是雍乾之际的“耗羡归公”。耗羡(以银的倾熔损耗为名义的附加税)的合法化,意味着各省的田赋征价从每两征收一两增至1.05-1.16两(即正项一两,附征耗羡0.05-0.16两)。但在这以后,中央政府长期未调整征价,地方政府的养廉银与公费(即耗羡最重要的支项)早已不敷支用,各地遂形成符合各自情况的征价惯例。比如我发现,1850年前后,湖北省各州县田赋的平均征价为每两1.506两,超过法定征价1.1两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七,这些官民默许的相沿成例并不被视作浮收。直到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及长江流域各省督抚出于筹饷、善后的考虑,调整了早已不合时宜的定章,提高了漕粮、地丁征价,我把这次田赋改章称为“第二次耗羡归公”。至二十世纪初年,各省为筹措庚子赔款、新政经费,普遍加征田赋附加税,这是清代第三次全国性的田赋征价调整。
尽管田赋征价从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一路上涨,但考虑到物价的因素,实际负担并不呈同比例的增加。我们能从清代文献重读到很多类似“民困不堪”的记载,然对比同时期的日本、欧洲,或者此后的北洋、南京政府时期,清代的田赋负担并没有那么沉重,未对民众生活构成严重的威胁。据王业键先生估算,即使在清朝最后的二十五年中,多数省份的实际田赋负担仅占土地产值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仅苏州、上海附近地区稍高,占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他的重要结论是,清末的赋税负担并非王朝覆亡的主要原因。
王业键先生(感谢黎志刚教授提供照片)
但有两点需要补充。第一、田赋负担轻重与负担公平问题联系在一起。清中后期不存在制度上的优免权,但绅衿大户常常凭借身份地位获得更低的田赋征价,甚至得到税额的额外豁免(常通过捏报田亩荒歉的形式)。大户的负担以多种方式转嫁至小户,小户田赋负担沉重的背后,是负担的严重不均。第二、在某些特定时期,因为货币、物价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民众的收入明显减少,而田赋负担则因此加重,以致抗粮事件频发,比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及清末最后几年。
如果抛开田赋,制度似乎是本书最重要的关键词,这对于研究清代财政、经济问题有怎样的启发作用?
周健:《维正之供》这本书常被定义为经济史或财政史,这当然没问题,但我自己觉得这归根到底是一项制度史研究,或者说是从制度史的角度来讨论财政、经济问题。
和国史中的其他制度一样,我们研究清代的赋税财政时,都会注意到制度的两重性问题(更准确说是多重结构),纸面上的定章是一回事,官吏军民的实践可能是另一回事。整体而言,在广土众民的集权国家统一推行某项制度,势必会有各种因地制宜的变通。可以说,没有不经历“地方化”而能落地的制度。更不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定章本身的僵化与不合理之处便会日益凸显。这些可以解释各地制度实践中的溢出、脱序与变异。
对于这些不同于定章的惯例、“积弊”,先行研究已经指出了它们的重要性,颇具启发性。王业键先生用的是正式与非正式制度(formal and informal system),他尤其肯定后者的意义。岩井茂树教授用的是“正额财政”与“正额外财政”,并以“原额主义”来解释后者的存在。
《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04年)
但要真正了解非正式、额外的部分,其难处在于:田赋的实际收支不见于任何正式的“预决算报告”。我的工作之一,是利用地方政府在田赋征解过程中形成的账簿、“指导手册”(这可能是最接近制度实态的文字记录),尽可能地勾勒田赋的实际收支与管理方式。由此我们了解到,在额外财政最为膨胀的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田赋盈余的大体规模如何,又如何在地方各级政府间分配。如果把这一切面放在“耗羡归公”以来的制度脉络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十八世纪后期以来,额外财政体系是如何在社会经济、财政结构、吏治风习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再次出现并全面扩张的。制度的两重性自然是常态,社会科学的研究常做各种总结归纳,而史学的工作则需将其定位于某一时期,并展现变迁的过程。
另一方面,如果回到具体的场景,定章与实践也不能简单地二分,两者在纠缠互动中共同构成制度的内涵。举例来说,清代田赋征纳的定制是自封投柜,即粮户亲身赴县,将应纳钱粮投入县衙的银柜之中。这一制度存在技术、效率方面的缺陷,在征收中作用有限。地方官须借助其他征收方式,作为自封投柜的替代或补充。最常见的是依赖书差等代理人包征,伴之以带有强制色彩的下乡催征,另一种变通是在各乡设置“乡柜”征收。
作为定章的自封投柜并非最重要,但它依然普遍存在,且对其他征收方式起到制约与规范的作用。比如革除各种包征、恢复自封投柜每每成为贤宦传中最具典型性的事功。但这也正说明,多数州县官更倾向于书差包征。这是由于,州县官并不掌握主导征收所必需的地籍、户籍信息,官方的户籍钱粮册难以作为征收的依据。而将田赋征解交由书差包办,不但可以相对高效地完成赋额,免去考成的压力,又可以固定地分润盈余。因此,无论从能力抑或动力来看,书差包征都是州县官的合理选择。是故,很少有地方官愿意冒险去变革包征制,这一点甚至被写入官箴书,作为经验之谈。为了钱粮不误奏销,地方官甚至放任、鼓励粮差揭征(即提前代完民户钱粮,再下乡催征),尽管这扰民甚重,最为时人诟病。
只有明白了制度下的“人”何以如此选择,揭示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我们才可能对制度有更为深入的理解,而定章与实践的区分也许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从这一层上说,近年刘志伟教授等提出的“从人的行为出发的制度史”“自下而上的制度史”都是极富启发意义的提示。
但要去理解制度中的人的选择,揭示其行为背后的结构,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对于古人和今人都是如此。我们考察历史中的制度,依据的大多是时人的观察与感受。然而,这些言论大多平平无奇,不过人云亦云,常见的是从道德正确的立场进行批判或赞扬,其中不乏“表态”的意味。但在赋税财政这样的领域,道德正确与制度运作之间,常常存在不小的分歧。如果轻易地和这些响亮的声音保持一致,可能会阻碍我们对于制度原理的理解。毕竟把简单明快的批判作为结论是容易的(本书中自然也不乏这样的问题),反正那些被批判的官员与政府也无法回应。真正的挑战是去捕捉少数洞见者的声音,他们可能是务实的,警觉的,怀疑的,无奈的。我常常觉得,如果能够利用不同角度的记载,真实地呈现各方的难处与制度的困境,我们对于制度运作何以不得不如是,也许就有了足够的理解之同情。
您在书中提到清代财税制度的两条红线:“永不加赋”以及不计成本供应京师的漕运,这两条红线对于制度的运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周健:“永不加赋”常被视作清朝的祖宗家法,但查阅文献,相关依据应是康熙五十一年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那一道上谕称:“嗣后编审人丁,据康熙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其新增者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地以前,赋役负担有地银、丁银两种,其中丁银按照编审的丁数(此时“丁”的实际涵义是纳税单位)派征。故“永不加赋”的本义是不再加征康熙五十年后加增之丁的丁银,使其额数固定在康熙五十年的水平。“永不加赋”之前是有“盛世滋生人丁”这一大限定的。
但这一限定常常被时人遗忘,“永不加赋”成了圣祖以来的家法。尽管如此,有清一代,加赋之事始终存在。一个政府当然无法在数百年间保持固定的税额。雍乾之际的“耗羡归公”便是真正的加赋。四川清初赋额极轻,咸丰军兴后,开始以津贴、捐输为名开征田赋附加税,在原额之上加征若干倍。庚子以降,几乎所有省份都因赔款、新政等事加征田赋附加税,名曰粮捐、亩捐、规复钱价等。“捐”字意为绅民主动的捐输,不同于正项。以各种名目来遮掩加赋之实,足见当日官员对于加赋之顾忌。可见,尽管加赋之事不绝,但“永不加赋”仍有相当的约束力。
关于这条红线的影响,岩井茂树教授的“原额主义”概念是很精彩的讨论。所谓的原额主义,是指对于经济扩张毫无应对的僵硬的正额财政收入,与随着社会发展、国家机构职能扩张而增加的财政需求之间的不整合,这势必导致各种额外的附加征收普遍存在。因此,僵硬的正额财政与具有较强收缩性的额外财政形成互补关系。
我还想强调的是,“加赋”在当日非为含义确定的概念。在本书考察的嘉庆四年清厘漕弊的讨论中,户部和疆吏对于加赋的界定便存在分歧。我们还能看到,在讨论提高税率的财政合理化改革时,有时祭出“加赋”的名号便可中止变革,它成为了因循的借口,比如1820年,出自道光帝圣裁的清查陋规因此遭到疆吏集体抵制。而有时官员又可避开“加赋”的羁绊,务实地推行财政合理化改革。比如雍乾之际、咸同年间,疆吏两次发起并主导了“耗羡归公”式的财政改革。这些差别自然与不同的时代、政风与关键人物的作用有关。我觉得关于清代“永不加赋”的理念与实践,都有进一步讨论的可能与必要。
漕运在本书中占了较大篇章,我想原因主要是,漕务是这一时期田赋问题的焦点,相较于地丁,有关漕务积弊与变革的讨论不时成为大历史的主题。
我们常说的漕运,更准确地说是漕务,包括漕粮的征收、交兑、运输、交仓、支放多个环节,是明清王朝国家的一大政。具体来说,清朝在江浙等有漕八省征收漕粮,由州县交兑世袭军户(旗丁),由其经运河挽运通州,主要作为京城八旗兵丁甲米和官员俸米支放,也有少部分供皇室食用。解运层面的特殊性,使得漕粮与地丁在会计层面成为两种税项,但它们同属按亩征收的田赋。漕粮是田赋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对京师的粮食供应极为重要。
十八世纪中期苏州胥门与运河(徐扬:姑苏繁华图》)
我把明清时代漕务运作的逻辑定义为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它的含义是,作为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供应京师的漕粮,其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其运作是不计成本的。漕运的成本,除运输费用外,还包括维持漕运官僚系统、安置运漕旗丁,修造漕船,以及疏濬、维护运河等一系列支出。1801年,户部专管漕务的云南司郎中祁韵士估算,每石漕粮北运的成本是十三、十四两,而当日京师的米价大约是每石一两,甚至略低于江南。很明显,这是极不划算的事,但漕运是不算经济账的,它属于需要集中力量去办的大事。既为国家经久之计,“圣天子固不惜(每岁)数百万帑金”。
但到1850年前后,漕运已不再能以这种方式延续,经历了四百余年来未有的剧烈变革。其原因是漕务浮费空前膨胀,有漕省份不堪负担河运的高成本,同时河工基本失效,运河通行能力显著下降。而战争又于此时降临,太平天国切断了长江与运河,成为漕务变革的重要契机。变革的趋势,一是漕粮的采买海运,二是漕粮的折征折解。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漕务已经形成与战前完全不同的新格局:征收方面,各省漕粮普遍折征银钱;解运方面,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和河南各省改为起解银两,不再起运米石,江苏、浙江漕粮改行海运,仅山东、江北漕粮仍行河运。这些变化都降低了漕运的成本,比如此后成为主流的海运,便远较河运便捷、省费。
但多省漕粮一经折解,以贡赋方式运京的粮食便大为减少。故同治年间,户部不断地要求江广三省(江西、湖北、湖南)规复河运旧制,他们把上述新格局视为战时之权宜。但各省既享受了降低成本的红利,便不再愿意恢复本色征运。最终,江广三省与户部达成妥协,实行折征兼筹采买,以新成立的轮船招商局为关键角色。
我近年阅读盛宣怀的来往函札,发现招商局的重要采办地是安徽合肥的三河镇,那是巢湖边的一个粮食贸易重镇,米价低廉。所谓折征兼筹采买,是指两湖的粮道将漕折银汇给招商局,由后者遣员在三河采购,两省每年各三万石,经巢湖、长江水运至上海,再由招商局的轮船海运天津。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新现象,两湖的漕运完全不在本省办理,却以最低廉的成本、最符合市场的逻辑,实现本色米石运京。同样的,额漕较重的江浙州县也较少在本地征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两省漕粮大多在无锡采买,再运沪海运。清季江苏的漕粮征价甚至以无锡米价为基准,形成历年调整的弹性定价机制。
以上的现象都反映出十九世纪中期以降的变化:各省督抚始终在计算成本,并且深度依赖市场,不再接受每两费银十三、十四两的运作方式,这是漕务运作逻辑的根本性转变。甲午、庚子以降,京师的粮食供应转为主要通过市场来解决,此期中枢曾多次讨论是否彻底停止漕运。但直至1911年,江浙两省仍需每岁海运数十万至百万石漕粮,显示出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
但总体而言,此期漕务的市场化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使市场化的过程落实到具体的细节。我绝不否认,明清时代的漕务一直存在市场化的调整,但那始终是本色、河运框架内的变通。咸同以降,由于一系列新的因素出现,包括内战的影响,运河的废弛,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兴起,东北、直隶等地的农业开发,海内外市场的进一步开拓,漕务运作突破了旧有的框架,以贡赋支应京仓的王朝定制在近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田赋管理涉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清政府,通常认为,晚清以来中央权力下移,督抚对于地方财政的主导权是否也扩张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周健:如您所说,中央与省的关系、督抚权力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问题之一。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尔纲先生讨论清季“兵为将有”问题,中央权力的下移、督抚权重便成为咸同以降近代史最重要的解释,具有长久的学术影响力。咸同以降,督抚权力在领兵筹饷过程中得到扩张,确为显而易见的事实。但需要思考的是,这种扩张的限度在哪里。
督抚权重已经使得中央集权的统治瓦解了吗?督抚真的可以有效地管理省以下各级吗?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么单向度地论证权力内轻外重,势必会有过度想象和推衍。此外,我觉得讨论晚清中央与各省的关系,不仅要区分时期(比如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和预备立宪时期就很不相同),而且应该落实到非常具体的问题。就财政关系而言,必须从各重要税种的收支与管理入手,奏销额数便是很关键的分析指标。
如果从田赋奏销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田赋征收额数的显著下滑,这种趋势甚至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了,经太平天国战争后程度更甚。这确实可以说明户部对各省财政管控能力的下降,但这并不能和督抚专权划等号。我在讨论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苏的漕粮海运时发现,即便作为主战场的江苏筹饷压力巨大,截留漕粮成为事实上的选项,但保证漕粮的起运额数仍是督抚的重要职责。不仅中枢可以通过人事的升降赏罚来防止疆吏渎职,官员的责任心也促使其对京师仓储负责。比如1857-1859年间,两江总督何桂清着力从关税、厘捐筹饷,以支应江南大营,全力保证漕粮的起运。他在任的三年,是1853年太平军进入江南后直至1900年间江苏起运漕额的最高峰。
光绪年间的漕粮海运:轮船招商局丰顺号航行图
光绪年间的漕粮海运:轮船招商局上海金利源栈房码头
但在这一过程中,督抚要有效地管理属下其实并不容易,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州县官吏。基层官吏最常见的舞弊方式是捏报荒歉,即无论年成丰歉,一概报灾,以便征多解少,侵蚀中饱。由于每岁田赋应征额数受灾歉影响最大,故稽核歉分、确定赋额是田赋管理的关键环节。此事名义上由督抚主政,但因赴各属查勘难有实效,歉分、赋额实际上由各州县的一纸详报决定,捏报灾歉之锢习遂牢不可破。
咸同年间,各省督抚先后从州县手中收夺田赋管理权,重订本省的钱漕收支章程,既核定征价,也确保盈余。但各省的田赋实征额数始终低迷,户部对此几乎无能无力。相对于中央与州县,督抚之财权确有明显的提升。不过,正如何汉威教授所指出的,除去历来强调的各省之离心、脱序之趋势,也需要对中央政府的整合努力及其效果给予足够的重视。
甲午战后,清朝的财政收支平衡被长期打破,中央政府屡屡借助强制摊派的方式,责成各省解交相应的款项(大宗包括甲午战后的三笔外债,庚子赔款,练兵经费等),其规模、强度远超以往。在田赋领域,自1897年以迄清末,中央政府一再提解各省州县的钱漕盈余,作为相应的筹款方式。在中央的财政压迫与银价腾贵双重作用下,州县的田赋盈余被不断侵蚀,不再能提供必需的公务经费。清季财政状况恶化的背景下,中央政府过度地集中财权,终于导致中央与地方(省、州县)在田赋分配中彻底失衡。在这一过程中,省一级显然无力抵挡来自中央的压力,州县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清季中央与省、州县间的财政关系,而不仅仅以“督抚专权”“内轻外重”一概论之。
从这些现象回到清代各级间财政关系的原理,我觉得这一兼有“集中”和“分散”的管理模式,用时人常用的表达,便是“包征包解”。1906年,梁启超说:“包征包解一语,实为现在财政制度一贯之原则也”。在该模式下,财政管理的各重要层级户部——布政使、粮道——州县之间,构成一种定额的摊派——承包关系。
在清代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下,各地所征田赋应尽征尽解,地方政府大量的必需经费不在考虑之列,甚至田赋的征解经费亦须自筹。那么,手握田赋经征权的州县势必通过附加税解决问题。他们将田赋正项解交司道,也按惯例向上司呈解规礼、摊捐。各省布政使、粮道则按额向户部奏销田赋,并呈缴相应的部费。在这些财政任务之外,只要未滋物议或引发京控、民变,地方政府的额外加征与经费授受是被默许的。州县官可以相对自由地筹款,支配盈余,上级并不了解其收支的详细曲折,通常也不加干预。
问题在于,此种模式下,各级政府间的财权与职能并不做清晰的划分。在支出层面,不存在国家之事、地方之事或州县之事的区别。一旦上级政府遇有经费缺口,便以向下摊派来解决,地方财政的独立性并不被承认。这导致了清末中央与地方间的失衡、上下财政支离破碎之局面。因此,宣统年间的清理财政中,在田赋项下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以田赋附加税作为地方政府办公之用,成为重要的议题。这是清末未能解决的问题,也长久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历史。
宋元以来就有江南重赋的说法,您认为后来在晚清终结了,终结的原因是什么?
周健:如您所说,江南的重赋始于宋元,至明初洪武年间达到顶峰,此后历经多次核减。重赋的成因,主要是宋明以来江南官田的扩张,即政府在该区域大规模藉没民田,充作官田,按照租簿之重则征税。洪武年间,官田的税率可达民田的十倍。嘉靖年间“均粮”后,官田名目被取消,重赋便均摊于全部田地、全体粮户之上。
重赋普遍存在于江南各府,其中又以苏州、松江二府最甚。时人常以比较的方式来说明江南、苏松赋额之重。同治年间,苏州绅士冯桂芬称,苏松二府负担“十八省未有之重赋”,比毗邻之常州重三倍,比同省之镇江重四五倍,比他省重一二十倍不等。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重赋,主要是以漕粮为主体的本色征收。
1892年湖北牙厘总局银锭
王朝国家核减正供额数(而非额外浮收)本属少见,而太平天国战争末期至战后初期(1863-1865)的同治减赋,则是清代规模最大的额赋核减。从政治的角度看,它是太平天国战争善后的标志性事件,时人视为“荡平东南第一德政”;从财政的角度看,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七的额赋核减以及减赋后的长期短欠,可以认为江南重赋问题就此终结。此后,我们很少再能看到关于江南重赋的议论。
规模如此之大的减赋得以实现,最重要的背景是兵燹之劫。作为太平天国战争的主战场,江南遭受之打击可谓惨重。至1863年初,战争进入尾声,清军克复江南可期,江苏官绅于此时提议减赋,有相当直接的政治考量,他们意在借此与太平天国争夺民心,以便更快击溃对手,同时也有谋划善后、培养元气之考虑。除时局之外,重赋背后的“问题”——江南的漕务也到了穷则必变之时。道光后期,漕务浮费之重、民众负担不均,已经使漕粮的足额征解难以维持。兵燹之余,无论是官员还是绅民,都觉得重赋需有实质性的轻减,而核减额赋在此特殊背景下确有实现之可能。
江苏的减赋于同治二年(1863)五月十一日出奏,官绅依据咸丰年间的实征额数,奏请将漕额由一百六十余万石减为九十余万石。减赋的要求很快获准,但额数则经户部议覆后,减为一百二十余万石。由于战争进程、人事纠葛、观点分歧等一系列因素,直到同治四年(1865)五月,江苏方面才再次出奏,请将地丁钱粮一并核减十分之二,这一请求仍被户部驳回。因此,江苏同治减赋的最终成果是核减米粮五十四万三千一百二十六石,约占原额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七。同一时期,浙江也搭江苏的便车,核减米粮二十六万六千七百六十五石,约占原额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七。
同治减赋是在官绅合力下展开的。由于冯桂芬留下了诸多的相关文字,先行研究多注重苏州绅士的筹划与推动,强调其对地方利益的维护,这当然是问题的一面。但如果更全面地阅读减赋相关的公牍私函,就会发现此事始于松江府的禀请,其运作始终由李鸿章、曾国藩、刘郇膏等疆吏决策、主导。因此,有必要从重赋之下地方官员的应对这一角度,重新思考减赋的动力。尽管“恤民生”“苏民困”的表述多见于相关文献,也是减赋的动机之一。但在核减额数等关键讨论中,官员是否能够完成赋额,以应付奏销,始终是首要的考虑。1865年,李鸿章得知减赋请益遭驳,第一时间致信刘郇膏:“将来钱粮考成、奏销难办,只有多捏灾欠。”可见,为地方官员减负,才是更实际的考虑,恤官成为减赋的重要动因。
如果追问为何如此规模的减赋得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实现,我觉得这和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动直接相关。咸同以降,厘金、洋税等新式税收在岁入中的比重日渐加增,而田赋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1864年起,江苏的厘金增幅显著,岁入两百至三百万两,成为本省及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源。既然这一新财源可以满足中央与省级政府日益加增的经费需求,且征收成本远低于田赋,各级政府遂以厘金为重,而对田赋的态度相对消极。否则,我们很难理解这样的事实:十九世纪后四十年,财赋重地江苏的漕粮获得近三成之核减,但减后仍常年短欠四成左右,实征额数持续低迷。可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既无动力、也无勇气对田赋制度进行彻底的清厘,以恢复十九世纪中期前的征收水平。清末民国时期的田赋增收,始终是在地籍不清、正额难增的情况下,以不断加征附加税的方式实现的。
1.《不属于清代中叶专题之周健谈清代的赋税与财政》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不属于清代中叶专题之周健谈清代的赋税与财政》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lishi/20856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