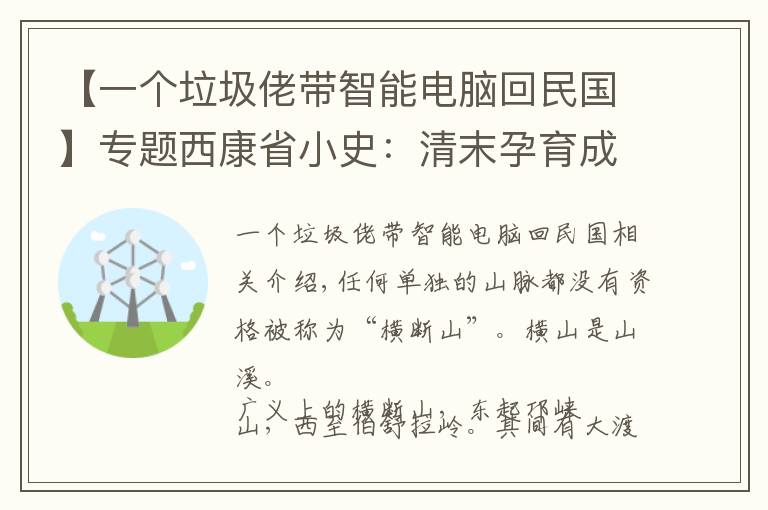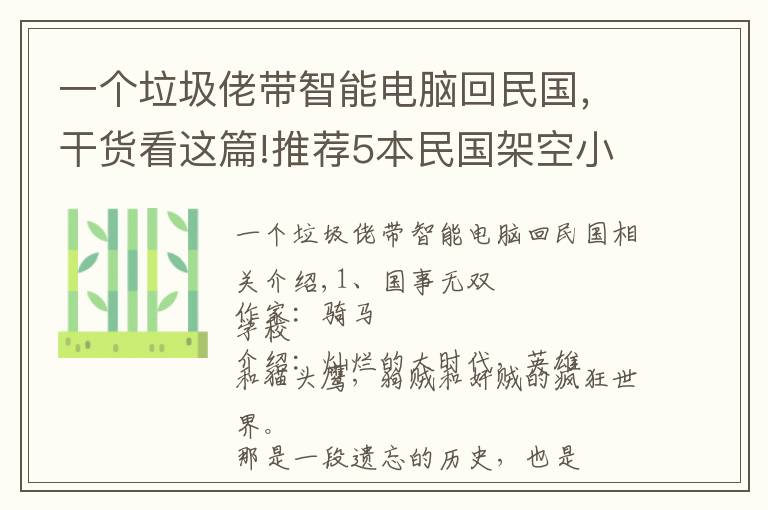许国涛第一次走上吉林大桥时才十二岁,那年他随着父母工作调动来到了吉林市,父亲为了让他尽快适应新环境,带他到桥上照几张相,洗出来的照片还煞有介事地打上“吉林大桥留影”六个宋体字。那是九十年代末,日常审美里依旧可见蒸汽朋克风格的宏大与空洞,但街上开始出现失魂落魄的下岗工人。舞厅、刨锛儿、小姐、气功……这些带有魔幻色彩的词汇成了大人酒桌上的点缀,没几个人意识到:东北成为孤岛的时代到来了。
许国涛当然也意识不到,一方面父母的干部身份给了他从小到大足够的庇护;另一方面,对于出生在小县城的他来说,这座有几百万人口,康熙皇帝都巡视过的北国江城,已经完全满足了他对于城市生活的全部幻想。他上中学后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北京是一头匮乏拥挤的巨兽,那里只属于王朔这样的痞子或者电影明星;上海炎热而无趣,春晚小品里的上海男人没一个有爷们儿样的;广州深圳是投机倒把者的天堂;香港刚回归没几年,以后跟大陆肯定一样了……
“哪也没有家好”是许国涛对于世界最坚定的判断。
许国涛连高考都报了吉林市的大学,轻轻松松考取轻轻松松毕业,在父母的安排下又进了林业局,混了个事业编。媳妇是亲戚介绍的,公务员,长相厚实刚健,一看就是“过日子人”。俩人工资加起来不到六千块钱,婚后第二年生了个儿子,白白胖胖,找了个算命的给取名叫“许子轩”。
一个人孤独,两个人幸福,三个人可以致青春,都是寂寞殊途。一家子安稳的小日子过久了,内心世界总体坚固,也难免会有一些松动和锈蚀。一场大水也许没咋地,但架不住今年春节他遭受了连续冲击。
一
第一次冲击来自他的表弟大壮,和追求安稳的表哥不一样,大壮这孩子从小就对冒险有着浓厚的兴趣。初中毕业后直接去中专学了美容美发,在发廊当了一阵小工后,又自立门户,在老家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店。
许国涛从小就看不上大壮,觉得他粗鄙简陋。大壮交了个女朋友,是他理发店的收银员。大壮曾暴打过一个骚扰她的客人,为此还被拘留了几天。许国涛见证了那场恶仗的全程,他就记得那个姑娘看着咸湿佬被打的眼神,似乎有一种母亲或班主任似的惋惜,嘴里还不停地发出啧啧的声音,好像在责问:你说你这老灯何必呢?被我对象打了吧?
大壮就是这样一个人,热衷于用野性维护秩序,而他生活的秩序里又全是野性。
今年的大年初二,大壮和那个姑娘也来了。俩人一人一部一万多的苹果手机,都穿貂,造型冷酷,能吃能造。
“去年生意不好,我那小店一年才赚了三十多万。今年开春俺俩就寻思去上海开店了。”
“你是不是寻思上海跟你们蛟河县一样呢?那地方是你能去的吗?”许国涛放下酒杯,一脸凝重。他自己也说不好他凝重的点究竟是表弟不切实际的野心还是“三十万”这个数字。
“哥,你是不知道,现在这买卖老难做了,现在蛟河的年轻人都往外跑,没有年轻人我开发廊的赚谁的钱?去年是赚了三十万,这三十万扣去水电、扣去税,扣去房租,我其实没剩下啥。正好她老舅现在在上海有个门市,我俩一商量趁年轻该闯就得闯!”
“行啊,反正你们混不好再回来,也不耽误啥。”
许国涛这顿酒喝得五味杂陈。
送走了表弟,许国涛刚要睡觉,没想到妻子却在一旁叹起了气:“哎,你说你成天掐半拉眼珠子看不上人大壮,你看人家开个理发店一年能赚三十多万,给对象又买手机又买貂的。你说你天天卡个破眼镜子像个文化人似的,一年到头那点破工资也就到人家零头……”
“大过年的,你要是不想过了可以直接说,不用在这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许国涛从被窝直接钻了出来,在客厅点了一根烟。他觉得现在的生活概括起来就俩字:不像。一个念了大学的人赚的还没一个中专生多、一个打架斗殴的前科犯敢去上海当老板、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县城居然连家理发店都留不住……谁他妈也不像谁,啥也不像啥。四周皆是虚妄,他又不敢随意倒下眯一觉。
二
第二次冲击来自同学聚会,许国涛已经好多年没参加过高中同学聚会了,他当年所在的班级是尖子班,班上同学除了他几乎都考到了外地的重点大学,毕业后也都留在了外地。
带了一瓶五粮液的许国涛抱着成为主角的雄心壮志赶赴饭局,但到地方发现没有人能跟他喝白酒,他只好悻悻地自斟自饮。
大家都在聊KPI、消费降级、北京的户口政策、年终奖……没人羡慕他那引以为豪的大胖儿子,也没人关心他今年能评上什么职称。饭店的包房就像一个被切割成两块的异次元世界,他在这头,其他人在那头。酒过三巡,许国涛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摇摇欲坠,他不可能卑服。
“这顿饭AA是不?那这顿完事我安排大家唱歌!”
许国涛站起来,用最大的嗓门来捍卫坐地炮最后的尊严。
“还是国涛敞亮!”“这当干部的就是不一样!”
谁也说不好这应和的话里有多少是捧场,有多少是敬佩,又有多少是调笑。反正到了饭局尾声,这种应和的话越来越多,许国涛感觉很满意。
许国涛订的歌厅包间很有排面,一百多平米的空间硬生生立了三个罗马柱,墙上画着来自希腊神话里的裸女,形体丰满造型可疑。妆容好似山魈的女经理,穿着黑丝袜蹬着高跟鞋,特意给她口中的许哥送了一盘蘸酱菜和一瓶廉价红酒。
“国涛唱一个吧!”“对,国涛先给咱打个样!”
志得意满的许国涛拿起麦克风:“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他唱得青筋暴起,眼角泪光闪烁,同学们在一旁叫好,今夜的许国涛,是北国江城夜场里最靓的仔!
这一顿花了许国涛三千二,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年快过完了,许国涛发现除了跟他大吵一架的媳妇外,似乎没有几个人记得那天晚上他的挥金如土,微信群里身处北上广的大家还在聊着他插不上嘴的话题。哎,那家歌厅叫什么来着?对,金龙商务KTV,名字里透着一股专属于东北的酷,是中年人们孤独的迷梦。
三
越是没落的经济背景,越需要有执拗的堂吉诃德来创造幻境。据说美国大萧条时,电影院天天爆满;日据上海时,租界里的舞厅“蹦擦擦”始终不断。人们需要摆脱苦闷的日常,获得释放。金龙商务KTV的老板倪金龙深谙此道,他本是中石化的普通工人,国企职工的身份虽稳定,但并不能给他带来富裕的生活,于是他一边领着工资,一边投身商海。他用几年的时间就做成了人们口中“不指着单位挣钱,上班就是为了玩”的成功人士。
倪金龙最早开了一家“金龙舞厅”,在江北最破败的工业区拔地而起,价格亲民,二十块钱可以摸半小时的嗨曲,完全为下岗工人们量身打造。刘欢当年梗着脖子高唱:“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黄宏在春晚舞台上失心疯般地大喊:“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都不如倪金龙手下的小姐妹们有效。
公安机关自然不能纵容这种社会丑恶现象,但又无可奈何,谁又能证明那昏暗的灯光下一定有见不得人的皮肉生意呢?你说我这有色情服务,你怎么知道的?你来玩过?
倪金龙就是靠着这种泥鳅般的市井智慧与体制周旋多年,当然他在区公安局当副局长的二舅也功不可没。
生意越做越大,倪金龙也开始越来越膨胀,他从舞厅开到歌厅,再从歌厅开到连锁酒店。社会上都在传说倪金龙的奢华生活,他有几个老婆、几辆悍马、多少套房子。
倪金龙其实也有烦恼,一到过年,家人团聚,他的老母亲就告诉他:钱赚差不多就行了,赶紧回中石化好好上班,国企是铁饭碗,做买卖哪是正经营生?你在中石化好好干,你儿子大学毕业了还能接你班。
没错,整个东北,都把国企、编制、铁饭碗这些概念,当成一个人获得安全感的唯一渠道。只不过老太太不知道的是,她的宝贝孙子虽然还在上学,但早已下定决心毕业后当个北漂,不再回来了。
“能让我爸这种人发家的地方,肯定没啥发展。”
过完年没多久,倪金龙的好日子基本到头了。他那临近退休的二舅突然被纪委带走,据说涉嫌“严重违纪”。倪金龙深知凶多吉少,赶快给儿子打了一笔钱,并发了条微信:“不管出什么事,都别回来。以后也别回来了,毕业就在北京吧!”
倪金龙被带走那一天,儿子和几个同学拿着父亲给的钱开始创业,在望京租了一层写字楼,做小程序。吃住在公司,出门挤地铁,谁也看不出这是东北大炮子的后代。而那千里之外寒冷的家乡,在这个年轻人眼中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四
倪金龙被捕的消息,让曾视他为偶像的崔龙君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次从韩国回吉林,崔龙君已经听到不下十个人说起倪金龙的事。崔龙君生在一个有些失败的朝鲜族家庭,他的父亲酗酒无能,母亲早早改嫁到了韩国,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少年,自然会对倪金龙式的草莽英雄产生崇拜。崔龙君在高中毕业后,也毅然抛弃了颓废的父亲,前往韩国留学。
韩国这个国家,对于很多东北朝鲜族年轻人来说有着某种宿命般的吸引力。崔龙君的母亲、姑姑、表哥表姐都先后移民韩国,他们在语言相通的异国打拼,却很难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被歧视、被打压、被清理、被规划。身份认同的错位构成了独特的心理坐标,迷茫的他们在异国他乡逐渐活成了纠结的函数。但这都不要紧,他们依然前赴后继,为了得到更好的生存环境,他们无所畏惧。
崔龙君刚到韩国的那年,为了赚学费什么活都干过。在工地搬砖活活累出了腰脱;在夜店当服务生,因为上错了果盘而向客人下跪道歉;甚至为了丰厚的报酬冒死给制药厂试药,充当人体小白鼠。
但真正让他感到恐惧的,是2010年寒假前的一个上午,他走在上课路上,看见美军的装甲车在街上行进,天上盘旋着黑鹰直升机。他走进教室,发现班级里只有女同学。打开教室里的电视他才知道——朝鲜人民军炮击了延坪岛,战争似乎近在眼前。
韩国的男同学都去部队报到了,而他,一个来自中国东北的小城青年,就这样被孤独地扔到了历史洪流的边角。
在那一刻,崔龙君决定回老家。
回到吉林后,崔龙君想试着考公务员,但是由于语言不过关始终过不了面试;他又试着开个朝鲜族饭店,但无论怎么整改,消防检查就是不合格;他想去应聘个销售岗位,可那些私企给的薪资待遇连他在韩国搬砖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在吉林,上面没人儿,干啥都干不起来!”那几年,崔龙君颓废得像只道口烧鸡。
在母亲的召唤下,崔龙君只好又返回韩国,和继父在釜山共同经营一家超市,也算是混了个衣食无忧。
今年春节刚过完,崔龙君得到消息,父亲因为饮酒过量猝死在家中,他只好回来奔丧。料理完丧事后,他约上几个小伙伴,在一家烤肉店喝了个大醉。他又哭又唱,间隙骂几次阿西巴,似乎很不喜欢给他富足生活的大韩民国。
第二天醒酒后,崔龙君来到了吉林大桥,把父亲的骨灰洒在松花江里。无奈天公不作美,起了一阵风,骨灰一半洒进了江水里,一半被风吹散在四周。洒进江水里的会奔向大海,被风吹散的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都是被风吹散的——崔龙君心想。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凤凰周刊】创作,独家发布在今日头条,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一个垃圾佬带智能电脑回民国】专题出东北记:老家开酒店的父亲被抓,让留在北京创业的儿子别回来了》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一个垃圾佬带智能电脑回民国】专题出东北记:老家开酒店的父亲被抓,让留在北京创业的儿子别回来了》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lishi/21174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