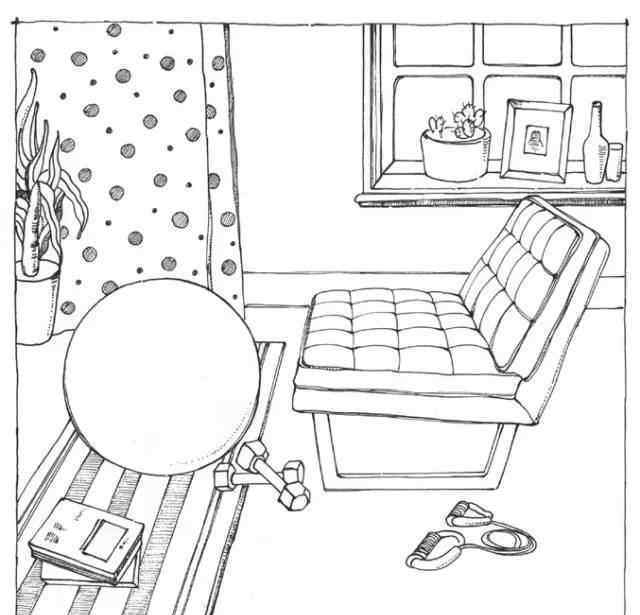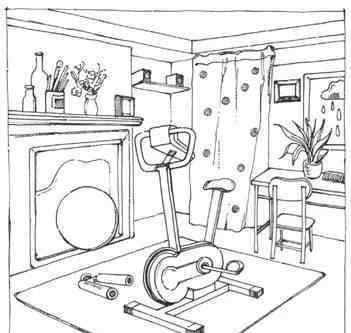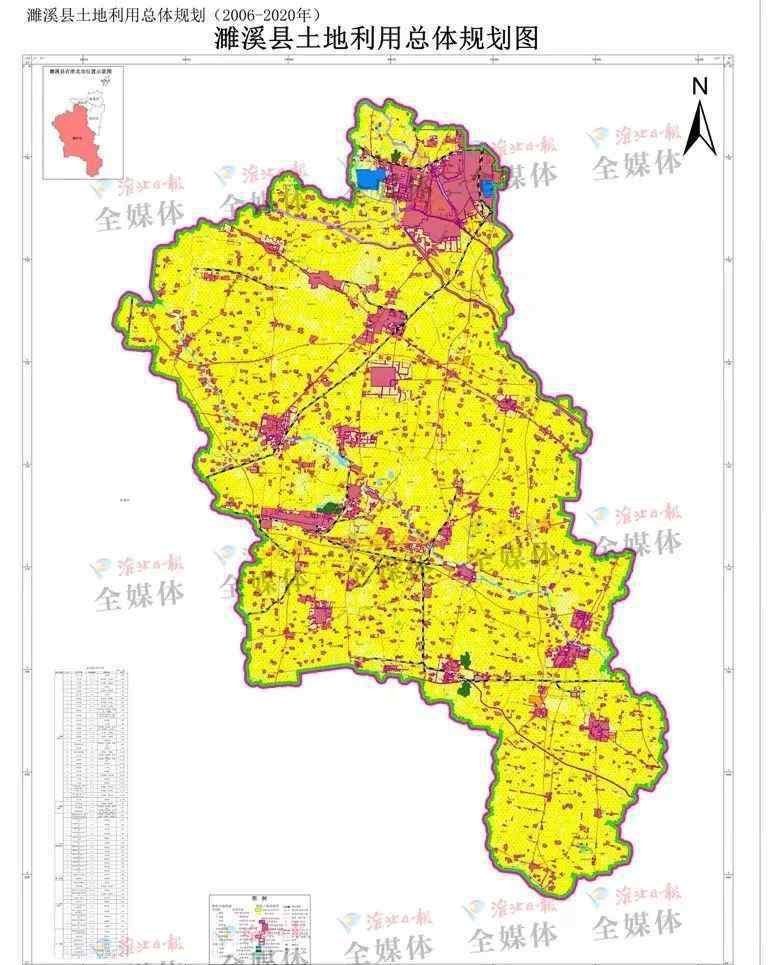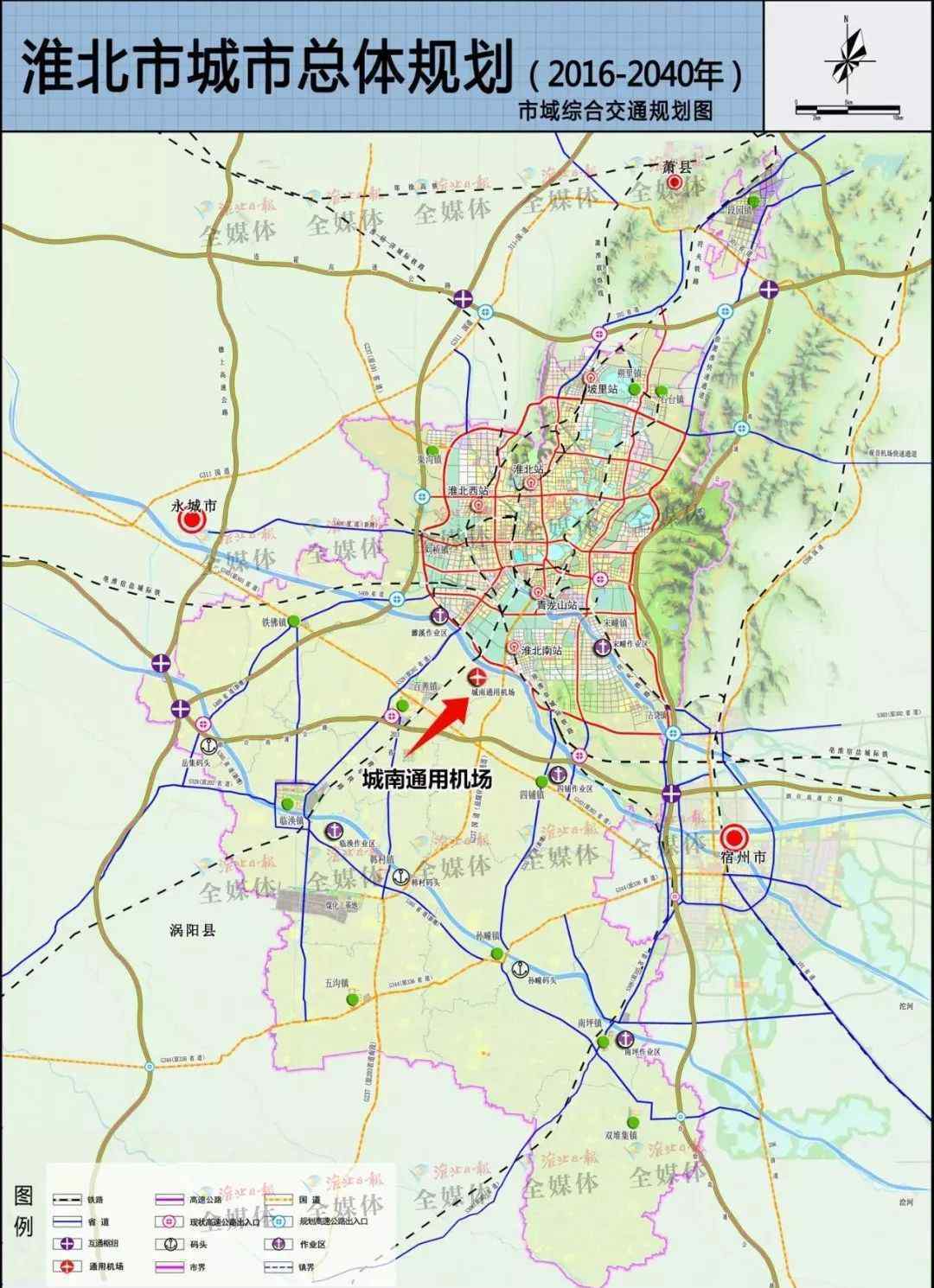萧红,1911年生于黑龙江呼兰。著名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女神”。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极度的艰辛和坎坷中,以一个孱弱体弱的身体面对世俗,经过反叛、觉醒和挣扎,一次又一次与命运抗争,一生从未向命运低头。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出版了他的名著《生死场》。1936年,他去日本摆脱精神痛苦,写了散文《孤独的生活》和长诗《沙粒》。1940年随端木蕻良赴港,后出版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小说《呼兰河传》。
萧红于1942年1月22日在炮火纷飞的香港去世。这篇文章只纪念它。
-张莉

小红在香港

香港萧红墓地拍摄于1942年
作家的重生
——萧红与中国当代文学
文本|张莉
萧红的一生短暂,这让她失去了很多机会:她的红楼和马伯乐,她看不完一半;她不可能是我们文坛的世纪奶奶,膝下有儿孙;她没有机会回忆当年的情感隐私,让未来的遗产执行人年复一年地制造出版“炸弹”,粘在读者“八卦”的眼睛里;她更没有能力在晚年发表口述历史,表达她的观点和对与她有情感联系的男人有缺陷的回忆录的蔑视。——厄运一下子吞没了她,把她拖入永恒的黑暗。
然而,她用生命的血泪写下的文字,却神奇地飞出了死亡。70多年来,特别是过去的30年,当我们作为普通读者,谈起著名的故乡,谈起文学史上最难忘的呼兰小镇;当我们谈到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时,我们不禁会谈到她。当代评论家似乎也越来越多地想到她。在阅读难忘的作品时,他们往往喜欢用类似的句式来表达:“他/她让我想起了萧红……”“这让我想起萧红的《呼兰河传》……”
一个
“我们爬上了最高的山峰,山顶寒冷多风,开着白色的碎花。”这是《我的阿勒泰永远卡乌图》里的话,因为这句话出自北疆少女李娟,也唤出了遥远的天山世界;一个直爽自然的女孩,一个耐心乐观的妈妈;夏天拄着拐杖微笑的祖母;一个贫穷但仁慈的家庭。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广阔的空房间,里面有舞蹈,有歌曲,有沙漠,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白云,有蓝天,人们和牛羊相互追逐,人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作为一个2010年突然来的作家,李隽的散文勾勒出的新疆,不是风景,不是传奇,不是戏剧。用她的话,我们和她建立了一种神奇的关系:关于阿勒泰,我们相信她的故事,认为关于她的一切都是有趣的、新鲜的、陌生的、迷人的。
李娟是一个生活在北疆的年轻人,以经营杂货店为生。她的文笔与众不同,开场风格独特。“我在乡村舞会上遇到了梅西拉。他是个漂亮温柔的小伙子,我一看就很喜欢他。”(《乡村舞会》)“在图书馆委员会里,我每天花很多时间睡觉——不睡觉还能干什么?”。“我听到房子后面的塑料棚发出嘎嘎声,帐篷也在摇晃。不好!我捡了个家伙去赶牛。”她的开头总是那么直接,那么舒服,属于年轻女性特有的纯真,自然,自然,而不是做作。
这让人不自觉地想起七十年前的萧红。像上师街的萧红一样,李娟喜欢写自己的日常生活:陪着妈妈和奶奶,和牧民一起在辽阔的土地上从这里走到那里。年轻人离开家,把兔子或老鼠留给母亲和祖母,他们把小动物当成她。“兔子死的时候,我妈叫我再也不要买这些东西了。如果你能回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她是一个多么有趣和可爱的祖母啊。她老了每天拄着拐杖赶牛。奶牛一回来,她就和动物们交谈并咀嚼。“记得夏天的牧场,午后的阳光又浓又重。两只没有尾巴的小老鼠试图在草丛中拱一根草茎。世界那么大,我奶奶拿着棍子站在旁边笑着看。她暂时的快乐因为这个‘暂时’而如此悲伤。”
李隽的老奶奶让人想起小红后花园的老爷爷,想起老幼如何在荒芜的花园里自由相处:“爷爷戴大草帽,我戴小草帽,爷爷种花,我种花;爷爷拔草,我就拔草。”他为她遮风挡雨,摘水果,给她讲故事。两位作家关于祖孙情爱的故事基调也很相似:魅力四射,生动热烈,日常生活通过他们的文字变得温馨恍惚,让人感到惆怅。其实他们说的只是一句俗语,也是讲自然平淡的东西。然而,他们有自己的神奇力量,这是一种天生的写作技巧。
出生在新疆的李娟,对大陆这个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不是一个没有家乡的人。我没去过的地方,在我奶奶和我妈的故事里反复触动了我的本能和命运,永远留住了我。”悲伤让天真无邪的女孩遭受更多的沧桑空。但她笔下的另一种悲伤也是迷人的,是关于爱情的片段。她在乡村舞会上爱上了一个叫梅西拉的年轻人,但她无法了解和爱他。“我想我真的爱梅萨拉。我可以肯定这份爱。我真的很想他——但那又怎么样呢?我不认识他,更重要的是,我不能让他认识我。谁知道谁,谁不知道谁...我不是说我只是因为年轻才爱吗?或者还能怎么办?白白年轻。”
阿勒泰作为一个地域,水清云淡空千里,却因为这份忧伤,风景成了风景:阿勒泰温暖,空空旷而遥远,成了一种象征。对于写故乡的作品来说,重要的是感到一些孤独,一切都会因为孤独而变得满足——阿勒泰,李隽不同于我们的想象,因为故乡的感觉和异乡的感觉在她的地方成功发酵,发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这和萧红离开家乡后回望家乡很像。用李隽的话来说,阿勒泰作为一个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在我们通常的文学意义上,在纸上显示出它的本土。它丰富、神秘、热情,一个象征性的阿勒泰世界正一天天地展现着它的光芒,就像“呼兰河”。
为什么我们读李隽的时候会想起萧红?因为他们每个人在纸面上都有自己的籍贯,因为他们生来就有“天真”,本质上就是“两全其美”。当李隽讲述母亲在森林里与蛇打交道的时候,两人互相震惊,然后各自向各自的方向逃跑;当她讲述自己与牛、羊、马追逐相处的故事时,这样的场景总会让人想起《呼兰河传》中孤独少女美好感情的再现:“砖头晒太阳,泥巴陪。有破罐子就有破瓮。哪里有猪槽,哪里就有铁犁头。就好像他们都是天生一对,结了婚。每个人都有新的生活要带给世界。比如缸里的鱼不是鱼,缸底的潮虫,猪槽上的蘑菇,等等。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立刻认出李隽笔下的萧红的最隐秘的原因:在他们的世界里,动物、植物、人都存在于同一个世界里,自然在他们的笔下既是主题,又是意味深长的光芒;另外,他们写日常生活和自然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少女”的娇声:天真中有莫名的诗意,娇憨中有无缘无故的失望。
二
天真清新,但与萧红相比,李娟更明亮、年轻、开朗。——难怪李隽没有萧红那种“被毒渗透”的生活,那种被痛苦紧紧包裹的生活。萧红无疑是个“命苦”的人,饥饿、寒冷、疾病似乎总是伴随着她。然而,这些阴暗的负担,在萧红的话语里消失了。在上士街,萧红写下了他们生活的艰难:“有了木屋,没有饭吃,还等什么?”越等越饿。教完武术,他跑出去借钱。当他借钱买了一个又大又厚的蛋糕时,木箱里只剩下一块了。这是怎么做到的?你不能吃晚饭。面对这片木头,我爱它,恨它,可惜。“没有自怜,甚至有些自嘲。尽管身体饥饿,但这种饥饿并不仅仅属于她。寒不是,丧也不是:“哭在墙脚,在墙角。老人、孩子、母亲...哭的都是被永远抛弃的人!“她看着自己就像看着他们一样,他们也在看着自己。——萧红能从个人苦难中抽离出来,写自己就像写别人一样:
窗户在墙的中间。就像空。我从窗口站了起来...大风吹断了我的头发,飘到了我的裙子上。城市街道和一张颜色不清的混乱地图挂在我眼前。屋顶和树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霜,整个城市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撒着一层银。我的裙子被风拍着,我很冷。我感到孤独,独自站在山顶。每个房子屋顶上的霜,不是一瞬间的银片,而是雪花,冰花,或者更冷的东西在吸我,像在冰水里洗澡。
这是一篇有切肤感的文字,饥寒交迫的形象直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萧红耐心地写生,保持沉默,让饥寒交迫的形象终于跃出她的肉身,成为一幅象征性的画面。
天真是萧红作品最大的标志,是年轻的李娟无法企及的。没有人比萧红在写作和理解苦难上更痛苦和直接,也没有人比她更冷静和克制。幸运的是,2008年,我在塞壬的散文集《不知去向的人生》中看到了萧红面对苦难的强大认知。塞壬是一位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年轻作家,也是一位擅长写普通人生活的散文家。也许塞壬和萧红在生活上有共同点:都是流离失所的人;他们都没有固定的住所;经常受到疲劳和痛苦的攻击;他们心里都有很浓的文学气质。
塞壬喜欢写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断的流浪和徘徊。她看着公交车上的街头艺人:“拥挤的人群,其中许多来自农村,男人有着黝黑的面孔,油腻腻的头发,下垂的头发,袖口周围有黑色污渍的皱巴巴的衬衫,破旧皮鞋的侧面有泥。”。他们一走近说话,当地口音就伴随着刺鼻的气味。.....这些来自农村的人,远离土地,离开了家园。此刻,他们和我一样,要从昌平去虎门谋生。车厢里呈现的物品信息散发出它们存在的真实气息。201路公交车记录了真相的表达。它们在城市中如此突然地存在。他们笨拙怪异,像卑微的尘埃,城市根本不理他们。”塞壬和生活在哈尔滨底层的萧红一样,有着在深广莞生活的边缘体验和“底层视角”。
就像萧红的《伤逝》描述了一个时代的饥寒一样,塞壬的《不知去向的生活》描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不由自主”:我们情不自禁地奔跑,情不自禁地被入侵和剥夺。当然,虽然没有萧红的纯真和天籁之音,但她要注意的是时代和苦难的率直和无惧:她描述自己坐在火车上看到的人群,诉说自己在路上被摩托车上的人突然抢了钱包,被车拖到地上拖了几米远,手肘被鲜血大口大口;她的钱包没了,手机没了,身份证没了……她在说自己,但通过她的叙述,你会觉得她在告诉我们,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个人写作”保持着距离。有一种写作,作者喜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放大他的痛苦,在他的哭泣中加入扬声器。——这样的话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变相的撒娇,以弱者的名义向读者索取。塞壬的魅力在于将她“自己的痛苦”与他人联系起来。
就像饥肠辘辘的萧红多次看到窗外断腿的穷人一样,塞壬睁大眼睛环顾四周,知道穷人也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他是其中之一:“我看到一些人那样,我能闻到他们。他们三三两两地走着,或站着,在城市里,在乡村里,在每个角落里。他们又瘦又苍白。他们看人的眼睛很大,像水一样清澈。他们看不到苦难,也不讨厌。他们避开它,沉默不语。突然觉得这就是力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力量并没有消失,它只持续到永远。”对“这种力量”的直面和理解,让塞壬的写作熠熠生辉。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她的《转身》中,塞壬讲述了她从1994年到1998年的工人经历:国有企业的价值观,机器的巨大轰鸣声,被裁员,被分流,“被切断”,从而结束了一个时代。
毕竟塞壬剧本有一种与土壤有关的生命力,它的质感和萧红剧本一样。这种美让人想起山野北部的植物,也许是向日葵,也许是大胡椒花,也许是马蛇菜肴...他们在园冶繁盛,有自己的春天。《呼兰河传》曾经写过那段美好的场景:“这些花从来不浇水,让风吹,让太阳照,却越来越红,在花园里盛开。
三
用李隽和塞壬的话来说,遇见萧红就是“幸会”。但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牵强的。他们和萧红当年的样子差不多。突然之间,他们的人物在文坛上开朗、旺盛、温暖、闪亮,受到了很多同行、读者和评论家的推荐。事实上,李娟和塞壬在采访中都提到,许多读者当面或写信告诉他们,他们是从谁那里想到萧红的;就这两位作家而言,都承认自己是萧红的读者。可惜这种关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毕竟“影响论”是个神秘的东西,提倡实证研究的研究者喜欢“安全”。——在萧红研究领域,在讨论萧红作品的当代影响时,人们通常会谈到一些同样出生在东北的女作家,如孙惠芬。
《麻鞋山庄的两个女人》是孙惠芬的著名作品,描写了一个村庄里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和友谊。海涛和李萍因为互相欣赏而成为闺蜜,但嫉妒让海涛泄露了李萍曾经的“小姐”身份,毁了一段美好的婚姻。小说讲的是姐妹情谊的脆弱,自然的嫉妒如何破坏一个人的内在美。孙惠芬进入了人物的内心肌理,她写了几千遍女性心灵的秘密,这也使这部作品成为当代文学中女性友谊书写的一个极好的收获。
萧红的《生死场》也描写了女性之间的友情。女人去看瘫痪在床的岳影,帮她擦洗,听她诉说,为她的悲惨遭遇流泪;农村妇女聚集在老王婆的家里听她“讲故事”,听她是怎么死而复生的,听她孩子是怎么死的,听她怎么理解人的生死。通过对这些女性聚集的特定场景的描述,萧红描写了女性的经历在民间传播的方式。相比之下,孙惠芬更注重女性心理的迂回书写,更擅长具体意义上的女性友谊和情感的书写。
《生死场》描写了特殊时代男性的存在和尊严。他们的生活贫穷贫瘠,生老病死如蚁。日本鬼子的入侵,唤起了他们独特的尊严。正如刘贺在《归来》中所说,当半残的两里半被当作男人,和老赵一起去与外族人作战时,男人因为战争的到来而获得了男人的尊严。这是战时特有的体验。孙惠芬的《民工》是关于本世纪的农民的。她和萧红一样,以女性特有的敏锐洞察力,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最不堪忍受的痛苦。今天的农民来到城市建筑工地,成为农民工。但是,他们仍然饱受饥饿之苦,生活和基本生活权利得不到保障,而留在农村的妻子则死于疾病和孤独。《民工》的结构精巧细致。通过哀悼,孙惠芬不仅描述了农民工父子俩的尴尬和贫穷,也描述了一个永远沉默的死去的女人——她的痛苦、她的疾病、她丈夫和儿子离开村子谋生后的无助和脆弱。
凝视东北大地的农民和女人,但孙惠芬和萧红对人的书写角度也不同。萧红并没有进入人物心理的内在肌理,而是深入挖掘了她/他们内心的褶皱。年轻的萧红对具体人事的理解不如孙惠芬,萧红似乎天生对全局的东西敏感;或者可以说,萧红在现实意义上的乡村体验是短暂的、异化的,这就决定了她只能写出自己理解的水平。而孙惠芬的优秀之处在于从萧红最差的地方写作,从乡村生活体验来说,她比萧红更丰富。
研究者将孙惠芬与萧红进行比较,主要停留在他写作的散文追求上。孙惠芬的作品《小窗雨》、《变调》、《宋哭》、《歌手》都有这种倾向。“她的散文风格和萧红差不多。东北大地,尤其是东北农村的氛围,通过她们细致委婉的女性笔触表现出来,显示出她们的气场和一种生命的气息。”孙惠芬的小说《商汤书》使这种联想更加强烈,书前的简单介绍可以作为一起讨论孙惠芬和萧红的“证据”:“虽然没有男作家笔下描写的大悲、大喜、大苦,但仍是一部血泪之作。它深深的痛苦和深深的爱,让人想起农村经典的《呼兰河传》,诞生在同一片土地上。
《上唐书》确实可以算是当代版的《呼兰河传》,试图以上唐地理、政治、交通、通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历史等为题写一个村庄整体。与萧红的《呼兰河传》相比,《上唐书》中人们的爱恨情仇是具体而扎实的。——《商唐书》中,小心而耐心地讲述了的出轨与痛苦,鞠的无法言说的痛苦,以及农村妇女的愚昧与无奈。但小说无法让读者把一个农村女教师的爱情理解为“我们的人间之爱”,也无法把村里一个大家都仰慕的男人的痛苦理解为“我们的痛苦”。
一想到《呼兰河传》里那种大眼睛像向日葵的王达,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世间一切淳朴之人的爱情的“森然”。一想到永恒的泥坑,一想到无缘无故被折磨的小团圆老婆,不禁想到惰性和从众,想到常态对“他者”的野蛮摧残……萧红不擅长写人际纠结,也不擅长想象别人的情绪。她的能力在于通过她的个人世界书写“我们的爱”和“我们的命运”。当然,《上唐书》是当代文学中独一无二的作品。但与《呼兰河传》不同,它的魅力在于它的脚踏实地,而《呼兰河传》的独特之处在于《呼兰河传》中暧昧的艺术光芒。
孙惠芬2002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街路宗教》更接近萧红《呼兰河传》的审美追求。也许用贴近个人经历的材料更舒服,也许作家面对非虚构题材更舒服。他的作品写得自由、从容、真诚。是情感和空影响了整个作品的流动。儿童之家,前门、后门、庭院、粪场、公园、前街、小夹子,都承载着作家童年的回忆,也能看到萧红影响的影子。《街路宗教》具有朴素、美好的美德。特别是这部作品没有《上唐书》中交通、通讯、教育、贸易等抽象而令人望而生畏的字眼,使作品脱去了与这些字眼相关联的僵化和异化。
孙惠芬关于萧红的一段话让人感触颇深:“萧红的《呼兰河传》让我百读不厌。她写的荒芜之地的悲凉情怀,童年的自由心灵,让我知道,一个好的小说家更像是大地上的一株野草,无论在哪里倒下都能生根发芽,随时可以自由思考空”是基于真实记忆的写作相对较弱,结构上更舒服,还是散文写作更强调一种随情感而动的心,环境是心生的?《街路宗教》是作家孙惠芬向萧红致敬的作品。从她对萧红写作特点的理解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与孙惠芬的其他作品相比,《街路宗教》因其“随意性”而更接近《呼兰河传》的“自由”魅力。
四
当然,今天讨论萧红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有一个名字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那就是迟子建。迟子建初入文坛时,就已经和萧红有了交往。——戴锦华认为她的秧歌像《生死场》一样,在身边写下了沉重而艰辛的一生。30年来,关于萧红和迟子建的比较研究论文很多,研究者也在不断探索迟子建和萧红的联系这个话题:他们都出生在东北黑龙江省,善于以情打动人,都在追求小说散文文化的倾向;作品中有一些带露水的轻盈;都受到萨满教的影响;写作的每一刻,都有黑土地和白雪的渗透...就连这两位小说家也喜欢用“空”和“具象”的方式来命名,如《生死场》、《伤逝街》、《呼兰河传》、《后花园》,迟子建还有《额尔古纳河右岸》
他们都喜欢把“生”和“死”并排写,尤其是迟子建的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从中年开始。在这部具有宝石般光泽的小说中,迟子建描述了各种离奇的死亡。同时,她也写人的一生:无常、悖论、卑微、无奈。这是迟子建的《生死场》。不像萧红的《生死场》,清晰透明。萧红笔下的人物,死的像蚂蚁,活的像蚂蚁。萧红通过这些人的混沌存在,把人的“生”与“死”写成了“物质层面”。迟子建在《人的感情》中谈到了“生”和“死”。
在萧红的世界里,人对生死的理解并不敏感,人的感情甚至是平淡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就不一样了,每一个死亡都是震撼人心,感人至深的。——当蒋百嫂尖叫着说出我们这个时代在夜里停电后埋在地下的痛苦;当“我”打开爱人留下的剃刀盒,把这些胡须丢进河里时,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显然都感受到了一些共同的痛苦。“我不想让浸透了他鲜血的胡须被囚禁在黑匣子里,囚禁在我的留恋里,让它们随清流而去。”——情感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子午线,个人情感和悲悯交织在一起,就像叙述者最后把自己的辛酸留在了悲悯的河流里。她咽下悲伤,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都有哭泣的人,她只是其中之一。正是在这里,迟子建和萧红在一个奇妙的高度获得了共鸣:他们都抛开了自己的喜怒哀乐,把目光投向了远方。
但是萧红和迟子建对世界的理解还是有很大的差异。萧红最后是“熊”,和张爱玲很像。从《生死场》开始,萧红的世界就是“人间无情”“生死混沌”;即使她在《呼兰河传》里写了祖孙之情,写了人间的温暖,但她明明有着告别时的洞见和“释怀”;而且,萧红有很强的批判精神。甚至当她写自己心爱的家乡的人事时,也有讽刺、痛苦、严峻的审视。
迟子建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直是“人生之爱”和“人间之爱”。迟子建的世界里总有温暖的蜡烛。即使在最简陋的地方,即使在寒冷的地方,她也要顽强地为读者和自己点上一把微火:迟子建用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让读者相信这里的美好。所以,即使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写“哈尔滨”的生活,两个人对世界的温度也有不同的感受:萧红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人类的生活:饥饿和寒冷;即使面对罕见的瘟疫,迟子建的《白雪公主的乌鸦》也是耐心、深情、正义的。
萧红和迟子建是在“生”与“死”的书写中相遇的;正是因为对世界观的整体认知不同,两位作家才分别出发,各奔东西。这也意味着两个人的风景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内在质感却有着巨大的差异。萧红是萧红,迟子建是迟子建。所以有了“河灯”的细节和“河灯”的习俗,因为立场和情感的不同,你看到的世界也不一样。
迟子建的《河灯》包含了她的委屈、思念和爱:
它一入水,先是在一个小漩涡里耸了耸身子,仿佛在向我做最后的告别,然后悠闲地顺流而下。我把剃刀放回原处,关上黑暗的外壳。虽然那里没有光,但我觉得已经不再是空空和黑暗,清澈的月光和凉风一定在里面荡漾。心中不再有被抛弃的委屈和悲伤。在这个夜晚,天空和大地完美相连。我相信清澈小溪上的河灯可以一路走到银河。
这是萧红的《河灯》:
但放下河灯时,僧人击鼓击鼓,以庆祝鬼魂重生;读经就像是一个紧急咒语,预示着这个时间是一个宝贵的时刻,不要匆忙放弃。男女鬼,快点抱灯投胎吧。
与此同时,河灯从上游挤上来,飘了下来。缓缓漂浮,平静而安稳,在水中绝对不可能看到幽灵来抓他们。
灯光一落,黄金忽明忽暗,观众上千万,真是大招。河灯不计其数,大概有几千个。台湾海峡两岸的孩子们拍手,用脚欢迎他们。淡淡的灯光照在河上,空的月亮跃上水面。生活是什么样子,才会有这么好的情况。
迟子建看着河灯,从这岸边望着彼岸,从地上许愿上天。萧红的“看”就是“天”看“人”,“彼岸”看“此岸”,对“世界”有留恋,对“世界”说再见。
迟子建的创作在中年时期越来越受欢迎,她的小说从平淡变得厚重,她的悲凉之美变得压抑。迟子建的变化有无限空的区间和可能,而年轻的萧红却被定格了。但迟子建的写作还是会让我们想起萧红以及他们与土地和人民的共同关系:他们都分享着一些与东北土地有关的悲悯。
萧红和迟子建是什么关系?萧红和迟子建的关系是影响者还是继承者?萧红和迟子建谁写得更好,谁超越谁?这是很多研究者愿意探讨分析的课题。我猜想它也会成为未来学术研究领域的“显学”,就像今天很多人讨论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关系一样。也许没必要。作家之间的传承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世界上哪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总是走在别人后面?一个总是走在别人后面的作家,从来没有超越过大关,哪一个可以称得上优秀?
把萧红和迟子建的关系,甚至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关系,看成是世界上所有优秀作家都应该有的关系,可能更合适。每个作家都生活在一个伟大而优秀的文学传统中,她/他们会“发挥自己的才能”,闪耀自己的光芒,打造自己的明星空。或者说,传统优秀的文学史就像一条蜿蜒的路,两端都有方向。人可能在萧红之后来到迟子建的站;相反,迟子建之后,人们也会回归萧红。正如余华在分析作家与文学史的关系时所说,“两个独立的作家就像是各自独立的地域。一定的精神道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已经把彼此最好的一面带了出来。”
如果我们不在文学研究领域以“地域”来限制我们对文学传承关系的理解,如果我们不把萧红的影响理所当然地视为对东北女作家的影响,不把“相似性”作为“影响”的唯一依据,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萧红,正在滋养着中国当代的许多作家。萧红的名字不仅出现在林白和红柯的散文作品中,也出现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卫卫写了清雅的小城微湖门;周晓峰面对女性身体疾病和污秽的冷静与审视...
从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中偶遇熟悉的萧红是什么意思?
不是谁在试图模仿谁——那些被认为受影响的作家只是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写作变成优秀文学传统的一部分;那些以萧红的形象被看到的作家,正是因为他们作品的一些特点,才进入了文学史写作的无尽链条。作为链条中的一员,萧红因与同龄人“共同的声音、共同的精神”而获得了优秀作家的重生。
原出版于2011年,《文艺争鸣》,3期。
张莉,河北保定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来到历史的表面之前》《姐妹镜》《捧小火者》等散文《陌生人的美》等。他获得了汤涛青年文学研究奖、最佳中国散文奖和图书权力排行榜十大好书奖。
扫描下面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官方账号
1.《混沌生死诀 张莉:一个作家的重生——萧红与中国当代文学》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混沌生死诀 张莉:一个作家的重生——萧红与中国当代文学》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caijing/16400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