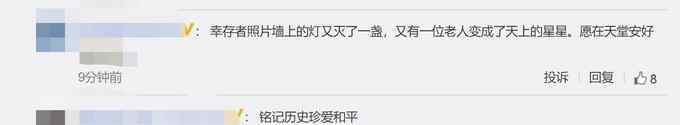截至目前,2021年以来,共有五位幸存者离世。一盏接一盏的灯,灭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面挂满幸存者照片的墙上,只有67盏灯仍在亮着。
人们在黑白影像里看到的南京城堆满尸体的街道,这在84年前,对12岁的陈文英来说,是“脚底下走过的场景”。
1937年的冬天,日军攻占南京。她躲进了金陵大学。6周的屠杀后,家倒了,死去的三姐躺在地上。
那成了她心口的一道疤,总是想起,疼得直哭。2021年4月10日下午,陈文英去世,享年96岁,是今年去世的第四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20天后,又有一名幸存者去世。截至目前,经“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认证的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剩67位。

2021年4月10日下午,陈文英去世,享年96岁,是今年去世的第四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图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方微博
永远18岁的三姐
九十多岁的时候,陈文英还在怀念她的三姐。
“我到现在仍然想她,别人我不想,我就想她,小时候她对我最好,最心疼我。”92岁那年接受采访时,陈文英回忆起三姐仍会颤颤巍巍地流眼泪。
“她初中毕业,在剪子巷乌尔堂里面当医生,当小儿科医生,一个月挣两个钱,给我买各式各样的衣裳。睡觉时看我手指甲长,给我剪指甲;她自己睡一点点,让我睡中间,害怕我跌下来。她每天早上给我五个铜板,对我好得不得了,真对我好得不得了,我妈妈我爸爸也没这样子对我。”
陈文英的记忆里,三姐一向讲究又体面,指甲总是修剪得整齐。直到1937年12月,日军攻进南京,三姐的生命定格在了18岁。“多漂亮的姑娘,多好的姑娘,就给他糟蹋了,好好的一个人就没有了,就搞没有了。可怜,真是,人家讲她身上连一件布衫都不给她穿,连鞋子什么都没得,可怜死了。”
比起三姐,她是幸运的。那年,12岁的陈文英躲进了金陵大学——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金陵大学设立了最大的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最多时达3万人。“我们躲进金陵大学,那里人很多,我们就睡在地上。有的人手上有老茧、头上有帽箍印子就被日本兵带走,妇女也被抓走。”
她逃过一劫,但心口烙了一道疤——从金陵大学出来,遍地是尸体和流淌的血,三姐躺在土地上。
“我们快过年时才回家,街上尸体很多,在新路口,有个大广场,码了很多尸体,像柴堆一样,有好多堆。后来我从难民区回家后,曾去雨花门弄菜,看到尸体被狗猫啃,脸上不像样子。”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陈文英留下了自己的证词。
再后来,被抓差的三姐夫回了家,夜里偷着将三姐尸体埋在地洞里。陈文英家里的三间瓦房被日本兵烧毁,父亲放弃了原本织缎子的生计,改卖小孩玩具,生活很苦。
曾经的陈文英也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姑娘,爱跳舞,也爱唱“小燕子”。那之后,她一双巧手摸上缝纫机,做针线活,也在厂里做纸箱、糊纸盒。
三十年过去了,五十年过去了,八十年过去了。老伴儿去世了,长子也去世了,她换了住处,但那道疤仍疼得她哭。
像三姐一样爱干净的老太太
陈文英像三姐一样爱干净。
“她身上一点儿味儿都没有,九十多岁的时候,还每天洗澡、洗头,特别讲究的一个老太太。”长孙女
张宇静记得,奶奶有一把粉色塑料边的旧镜子,背面印着图案,陈文英对着已经裂开的镜面,用一把木梳子,梳几把灰白的短发。洗完脸后,拧开“雅霜”的绿盖子,手指蘸一点点,涂在脸上。“家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虽然不是很大,家具也老了、旧了,但奶奶特别爱收拾,柜子里那些衣服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张宇静的记忆里,奶奶从不穿大红大绿的衣服,偏爱深色、方便穿脱的开衫,“她不穿那些鲜艳颜色的衣裳,给她买那样的衣裳她都不穿。”衣服破了,补上布丁再穿,但是一定洗得干干净净。

陈文英和长孙女张宇静合影。受访者供图
陈文英认真过自己的日子。没事哼哼小曲、嗑个瓜子儿,再含一颗老上海的话梅糖,还总馋小笼包和红烧肉。以前的家里有个后院,被陈文英种满了花花草草,老伴儿在的时候,两人一起养着一只小猫。
80多岁的时候,她能一个人从新街口走到汉中路,一公里多。哪怕最后两年,腿脚不利索了,陈文英还总想让孙女带她去看看,城南剪子巷那个她原来居住过的地方。
“每次我们去看她,她总是有一种渴望的眼神,就是希望儿女能在她身边的时间多一点。我们到那,她就拉着手不放,每次都叮嘱我们,没事多去陪陪她。”张宇静说,手机通讯录里,陈文英把儿孙的号码都设置成了方便拨出的短号,孤独的时候,能聊聊天。
又一盏灯灭了
“时常有幸存者打电话或者来纪念馆和我聊天拉家常,就像家人一样。我能有机会为幸存者服务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李雪晴告诉新京报记者。
她是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的工作人员。该协会于2004年成立,以“关注战争受害者,援助历史见证人”为宗旨,为幸存者报销医药费、发放生活补贴及节日慰问金、提供健康呵护服务、组织活动等工作都由他们负责。

近年来,援助协会工作人员在春节慰问陈文英。受访者供图
李雪晴从事这项工作近9年,多年的相处、服务,让她把这些曾经素不相识的老人当成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她的微信好友列表里,基本都是幸存者家属。
近年来,陈文英身体不好,李雪晴和同事时常给家属打电话或发微信,“随时了解奶奶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每逢节日、纪念日,她组织人员上门慰问陈老的同时,还组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健康呵护服务队”的医护人员上门为陈老提供健康呵护服务。
每到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陈文英都会在家看电视新闻。
她不理解,“难道他们没有亲人、没有妻儿吗?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要杀无辜的百姓?”
偶尔去纪念馆,看到影像资料上的日本兵,陈文英气愤;有记者采访她,触到记忆里的伤口,陈文英又难过;和长孙女张宇静聊起往事和岁月,她“眼泪就哗哗直掉”。
最近几年,看完新闻,陈文英总觉得,三姐就在窗户边走来走去。家人劝她不要乱想,她只说,“三姐在叫我一块过去呢。”
4月10日下午,96岁的陈文英离世。纪念馆为她举行了线上“熄灯”仪式,点亮陈文英照片的那盏灯熄灭,照片也由彩色变成黑白。“工作中难过的时候,就是得知幸存者去世的消息。”李雪晴说道。
截至目前,2021年以来,共有五位幸存者离世。一盏接一盏的灯,灭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面挂满幸存者照片的墙上,只有67盏灯仍在亮着。
截至目前,2021年以来,共有五位幸存者离世。一盏接一盏的灯,灭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面挂满幸存者照片的墙上,只有67盏灯仍在亮着。
人们在黑白影像里看到的南京城堆满尸体的街道,这在84年前,对12岁的陈文英来说,是“脚底下走过的场景”。
1937年的冬天,日军攻占南京。她躲进了金陵大学。6周的屠杀后,家倒了,死去的三姐躺在地上。
那成了她心口的一道疤,总是想起,疼得直哭。2021年4月10日下午,陈文英去世,享年96岁,是今年去世的第四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20天后,又有一名幸存者去世。截至目前,经“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认证的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剩67位。

2021年4月10日下午,陈文英去世,享年96岁,是今年去世的第四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图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方微博
永远18岁的三姐
九十多岁的时候,陈文英还在怀念她的三姐。
“我到现在仍然想她,别人我不想,我就想她,小时候她对我最好,最心疼我。”92岁那年接受采访时,陈文英回忆起三姐仍会颤颤巍巍地流眼泪。
“她初中毕业,在剪子巷乌尔堂里面当医生,当小儿科医生,一个月挣两个钱,给我买各式各样的衣裳。睡觉时看我手指甲长,给我剪指甲;她自己睡一点点,让我睡中间,害怕我跌下来。她每天早上给我五个铜板,对我好得不得了,真对我好得不得了,我妈妈我爸爸也没这样子对我。”
陈文英的记忆里,三姐一向讲究又体面,指甲总是修剪得整齐。直到1937年12月,日军攻进南京,三姐的生命定格在了18岁。“多漂亮的姑娘,多好的姑娘,就给他糟蹋了,好好的一个人就没有了,就搞没有了。可怜,真是,人家讲她身上连一件布衫都不给她穿,连鞋子什么都没得,可怜死了。”
比起三姐,她是幸运的。那年,12岁的陈文英躲进了金陵大学——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金陵大学设立了最大的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最多时达3万人。“我们躲进金陵大学,那里人很多,我们就睡在地上。有的人手上有老茧、头上有帽箍印子就被日本兵带走,妇女也被抓走。”
她逃过一劫,但心口烙了一道疤——从金陵大学出来,遍地是尸体和流淌的血,三姐躺在土地上。
“我们快过年时才回家,街上尸体很多,在新路口,有个大广场,码了很多尸体,像柴堆一样,有好多堆。后来我从难民区回家后,曾去雨花门弄菜,看到尸体被狗猫啃,脸上不像样子。”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陈文英留下了自己的证词。
再后来,被抓差的三姐夫回了家,夜里偷着将三姐尸体埋在地洞里。陈文英家里的三间瓦房被日本兵烧毁,父亲放弃了原本织缎子的生计,改卖小孩玩具,生活很苦。
曾经的陈文英也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姑娘,爱跳舞,也爱唱“小燕子”。那之后,她一双巧手摸上缝纫机,做针线活,也在厂里做纸箱、糊纸盒。
三十年过去了,五十年过去了,八十年过去了。老伴儿去世了,长子也去世了,她换了住处,但那道疤仍疼得她哭。
像三姐一样爱干净的老太太
陈文英像三姐一样爱干净。
“她身上一点儿味儿都没有,九十多岁的时候,还每天洗澡、洗头,特别讲究的一个老太太。”长孙女
张宇静记得,奶奶有一把粉色塑料边的旧镜子,背面印着图案,陈文英对着已经裂开的镜面,用一把木梳子,梳几把灰白的短发。洗完脸后,拧开“雅霜”的绿盖子,手指蘸一点点,涂在脸上。“家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虽然不是很大,家具也老了、旧了,但奶奶特别爱收拾,柜子里那些衣服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张宇静的记忆里,奶奶从不穿大红大绿的衣服,偏爱深色、方便穿脱的开衫,“她不穿那些鲜艳颜色的衣裳,给她买那样的衣裳她都不穿。”衣服破了,补上布丁再穿,但是一定洗得干干净净。

陈文英和长孙女张宇静合影。受访者供图
陈文英认真过自己的日子。没事哼哼小曲、嗑个瓜子儿,再含一颗老上海的话梅糖,还总馋小笼包和红烧肉。以前的家里有个后院,被陈文英种满了花花草草,老伴儿在的时候,两人一起养着一只小猫。
80多岁的时候,她能一个人从新街口走到汉中路,一公里多。哪怕最后两年,腿脚不利索了,陈文英还总想让孙女带她去看看,城南剪子巷那个她原来居住过的地方。
“每次我们去看她,她总是有一种渴望的眼神,就是希望儿女能在她身边的时间多一点。我们到那,她就拉着手不放,每次都叮嘱我们,没事多去陪陪她。”张宇静说,手机通讯录里,陈文英把儿孙的号码都设置成了方便拨出的短号,孤独的时候,能聊聊天。
又一盏灯灭了
“时常有幸存者打电话或者来纪念馆和我聊天拉家常,就像家人一样。我能有机会为幸存者服务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李雪晴告诉新京报记者。
她是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的工作人员。该协会于2004年成立,以“关注战争受害者,援助历史见证人”为宗旨,为幸存者报销医药费、发放生活补贴及节日慰问金、提供健康呵护服务、组织活动等工作都由他们负责。

近年来,援助协会工作人员在春节慰问陈文英。受访者供图
李雪晴从事这项工作近9年,多年的相处、服务,让她把这些曾经素不相识的老人当成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她的微信好友列表里,基本都是幸存者家属。
近年来,陈文英身体不好,李雪晴和同事时常给家属打电话或发微信,“随时了解奶奶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每逢节日、纪念日,她组织人员上门慰问陈老的同时,还组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健康呵护服务队”的医护人员上门为陈老提供健康呵护服务。
每到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陈文英都会在家看电视新闻。
她不理解,“难道他们没有亲人、没有妻儿吗?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要杀无辜的百姓?”
偶尔去纪念馆,看到影像资料上的日本兵,陈文英气愤;有记者采访她,触到记忆里的伤口,陈文英又难过;和长孙女张宇静聊起往事和岁月,她“眼泪就哗哗直掉”。
最近几年,看完新闻,陈文英总觉得,三姐就在窗户边走来走去。家人劝她不要乱想,她只说,“三姐在叫我一块过去呢。”
4月10日下午,96岁的陈文英离世。纪念馆为她举行了线上“熄灯”仪式,点亮陈文英照片的那盏灯熄灭,照片也由彩色变成黑白。“工作中难过的时候,就是得知幸存者去世的消息。”李雪晴说道。
截至目前,2021年以来,共有五位幸存者离世。一盏接一盏的灯,灭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面挂满幸存者照片的墙上,只有67盏灯仍在亮着。
1.《南京大屠杀幸存 登上网络热搜了!》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南京大屠杀幸存 登上网络热搜了!》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guonei/16126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