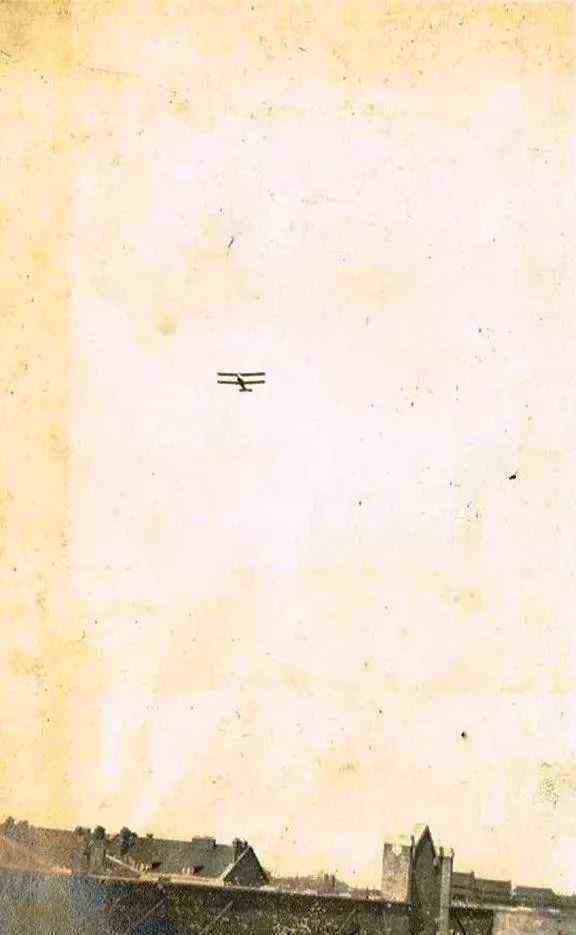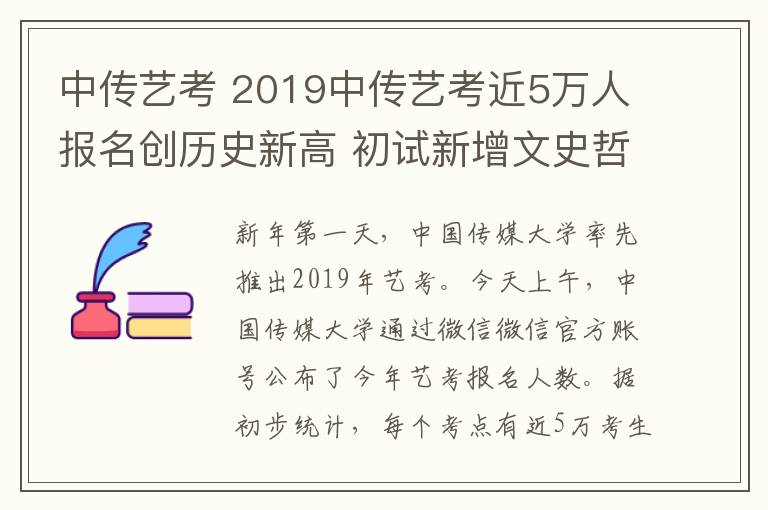杨钊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杂家”。他有很多活跃的社会身份,比如作家、学者、媒体人;写了很多不同的风格,涉及很多领域——新闻、文学、政治、历史、经典、音乐、育儿教育,都有很大的成就。他们出版了一部又一部的专著,甚至连以学识渊博著称的张都笑着说:“我不太清楚,一切向杨钊请教。”
作者 张玉瑶
杨钊的“人生核心古迹”是一个“问清一切”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下的职业历史学家,但他与普通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从“象牙塔”走向“过街”。20世纪80年代,在他所谓的“台湾省政治最奇怪的时期”,他就读于台湾省大学历史系,大二时开始参与社会运动。国立台湾大学毕业后,他去哈佛大学深造,师从杜维明和张广智。1987年,台湾省宣布“解严”,让早年有社会关怀的杨钊坐不住大洋彼岸,开始评论政治时代。1993年,他有机会回到台湾省,在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导师杜维明觉得杨钊放弃博士学位很可惜,一直催促他回去完成论文。然而,在历史语言学院待了一年后,他的学术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打破了杨钊对学院的想象。再加上台湾省现实政治的召唤,他很快做出了放弃学历,成为社会作家的决定——“我自己想清楚了,所以没有遗憾。”
但他告别了学院,却没有放弃多年的历史学术训练。对于杨钊来说,阅读历史文献和学术期刊已经从研究变成了一种更自由、更持久的兴趣,历史研究所所追求的“万物有其源”也成为他涉猎各个领域的底线。
从2007年开始,应龙敏讲堂和台湾趋势讲堂的邀请,他开始教授中国通史,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历时十年。最近,这本13卷本的《人人共享的中国历史》逐渐在mainland China出版。当我们仔细阅读时,它与我们一直习惯的讲述历史的方式完全不同。而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线性的讲故事,不去描述那些有很大成就的人。而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导向,引用大量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更“硬核”。同时,我们有从课堂中诞生的大众导向,引导学术殿堂走向普通读者。
学院内外的特殊位置有人问杨钊,学术界会怎么看待他的十年课程?杨说:“幸好我不在学院,所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否则“一想到写通史,同行就会骂死我——写通史太嚣张了”。
杨钊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己动手的野心。据他说,他一直在“等待”。“我一直觉得学院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成果与普通人的历史常识差距很大。我一直在等这样的书,感觉会有人想到这样做,但是——我从来没有等过。”一次偶然的机会,龙敏讲堂邀请他开始上课,他下定决心要用自己最想要的方式讲述中国历史。时间长了也没关系,就算“没人上课,也就停了”。
但是相比一般的大众论坛,杨钊想要的方式有些偏颇。他试图探索学术前沿,讨论了许多专业问题。一开始他还担心没多少人愿意听这一套。他还同意报告厅的意见,即如果登记的座位少于60个,就不会开放90个座位。没想到,人满了。很多没学过文史的同学都来了,有理工科背景的也不少。他们从小到大一路看历史教科书和通俗读物,看这种“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是怎样一种“新”的方法。
杨钊解释说,所谓“新”,在于常识。“人们对中国历史有一定的常识,但这些常识经不起一百年来史料和历史研究的检验。”关键是要把“中国历史看成同质的”,“说到皇帝,不,皇帝不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比如夏商周,一般认为是三代相继,即商汤伐夏杰,王武斩草除根。但根据二里头等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和古代史专家接受了夏、商、周很可能呈现“共主”结构的观点,这是在三个不同地区产生的三种不同的新石器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即夏人并没有因为商人而获得共主地位。“所以大家都低估了中国历史。我不知道中国历史这么丰富,这么多变化,重新认识就是为了弥补这种复杂性。”
但即使有学者背书,这样的内容还是属于很小的认知领域,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脱离并进入我们现有的“常识”。杨钊感叹这是史学界的悲哀,与大众的差距很大。即使有了突破性的研究,也会因为不符合大众的常识而被忽视和重视。在他看来,这与学术界日益专业化有关。钱穆以自考生的身份进入北大,提出由一个人教授中国通史课程,而不是由专门教授不同时期的老师来教授,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对中国历史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但在目前的大学环境下,秦汉史有专家,隋唐史有专家,很难跨领域。“但如果不跨越一些东西,就无法进入常识层面去交流。”
杨钊没有用PPT,是因为他不想让学生不把注意力放在他说的话上,而是去读这篇“我替他们记下的笔记”。虽然这是个麻烦——没有PPT提示学生很容易走神——但杨钊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已经学会了用问题邀请他们进来,让历史不再是既定事实,而是一系列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问号。
他将自己定位为“勤奋、忠诚、不相信和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他不在学院,却能完成这样一套课程和一部通史,但正是由于这个“缺席”的位置,“不仅关心学院的成绩,而且不在学院——在学院里,很难做到这一点”。他自信是因为他身后有很多“大牌保镖”。“你不能认识我,但你不能不认识陈、、、杜和白川静。我不伟大,我只是拉他们的东西,让大家知道。”
历史是可以实证的《中国历史为大家》第一卷从理论建设开始,包括颜若渠对《伪古尚书》的考证,顾颉刚的《古史已倦而撰》,金石学的发展。尤其是解释什么是考古,考古是怎样的,考古与文字记载的关系,需要很大的篇幅...人们一开始打开书,甚至以为是拿着一本考古科普书。
杨钊本人确实和考古学有些联系。来到历史系,考古学与人类学导论是必修课,对“挖死人的骨头”不感兴趣,导致期末被“考试指南”“不及格”,只有62分。他很生气,补课,才发现人类学这么开放,给历史带来了新的氛围,以至于他一度想转到考古人类学系,可惜失败了。到了哈佛后,虽然杜维明是导师,但他在很多课上错误地跟着张广智,而且联系非常密切,对学术的影响远远大于台大时期。“研究历史的人总会有一种困惑。有什么办法可以回到源头了解历史?和张老师一起学习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中国怎么来的,历史怎么来的,考古可以处理这个事情。”
杨钊说,考古之所以被放在那么高的位置,是因为考古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最伟大的成果,尤其是在越古老的时代,它就越重要。“考古让你在文学如此混乱的时候安心。这些都是可靠的证据”。因此,他没有谈及唐,而是从新石器时代姚的考古资料中,谈及良渚玉器所隐含的社会分化,谈及夏代捣固技术带来的国家组织上的突破,谈及甲骨文背后的氏族制度,谈及商代的占卜和鬼神信仰...
刚开始讲考古的时候,杨钊担心太枯燥,学生们提不起精神。出乎意料的是,学生们,尤其是那些有理工科背景的学生,对它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以前进不了历史,就是一直抱着‘历史是真的吗?“客观吗,”毕竟古伏羲女娲和姚舜禹汤编造的故事太多了,但是从考古开始,我给他们讲了碳14和断代,他们才放心历史可以有根据,可以论证清楚。这让我有点吃惊。如果我们认真与公众沟通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不要把历史人物看得太重,这是他的另一个命题。中国人理解历史,往往是从人的理解出发,从二十四史的传记体,到英雄传奇剧本。杨钊澄清说,中国的正史不是这样的传统。司马迁《史记》中的列传,表面上是皇帝,背后却是大事记,其次是书和表,然后是家传。但在后面,这些逐渐消失,核心变成了传记和传记。“所以我以后再说中国历史。都是在说人。当然,最重要的是帝王将相。它产生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用文字解释历史。比如《仓颉》怎么可能塑造人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大汶口文化开始就出现了表意符号,甲骨文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文字体系。”“过分强调人,就不会看到或者看到很多不对的地方。”
也需要破王朝。“以朝代的历史作为审视中国历史的工具,对我们的阻碍远远大于帮助。背后是循环的历史观。”比如杨照说,你说朝代,你就说谁建国,然后是谁创造盛世,然后是谁复兴,最后是谁灭亡。“好像四个人就能概括一个朝代。”。
十年十三卷,杨钊完成了一套通史框架。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一方面帮助读者梳理和思考当下的文明和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也能让读者确切地感受到中华文明内在的多样性。那么,在这个“通史框架”中,中华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呢?杨照认为,中华文明有它的起源,这个文明的轴心产生于周朝,包括氏族制度、人伦秩序、非音系等等。“就像门轴一样,门会移动变形,但它始终围绕着这个轴。这个轴心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并告别了传统中国。”
历史的意义在于多样性当代中国人的历史知识往往处于混乱状态。他们一方面很少看专业的历史书,但另一方面很容易受到影视剧里的段子和框架空的影响。“常识”就像是一片人们共同生活的荒地,比如前段时间围绕电视剧《霍去病》的争议。
虽然身处海峡对岸,但杨钊对大陆的流行文化并不陌生,尤其是得益于互联网和文化交流。近年来,宫中皇后的《如意宫皇家爱情》、《颜夕宫故事》等宫剧在海峡两岸都很流行,他对它们的盛况也有所了解。杨钊认可存在是合理的。他笑着说:“它们能影响到很多人,中国历史的呈现和传播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所能做到的。"
但问题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一个合格的现代中国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历史知识素养和辨别能力?毕竟,“这些剧呈现的历史是有问题的,比如《颜夕宫物语》就不会有农民。”。真实的历史远比这些剧丰富、多样、复杂、有趣。”在这一点上,杨钊认为,除了给群众写史书之外,关键和极其困难的一点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应该如何教历史。在他看来,历史不是按照课本来教的,所以孩子要知道课本只是一张简单的地图,跟着课本走可以探索更多的风景,而不是让孩子背地图。”如果有机会,就像美国的历史教育一样,让孩子从自己家附近的历史考察开始。这个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它的起源是什么?了解这个小地方的历史,必然与更大或更长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这些都和你的生活直接结合,和你自己的出身有关。"
如今的新媒体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解构,更倾向于将历史扁平化,缩短距离,用互联网时代的语言来包装。而杨钊却极其反对这种“以古为邻,老王”的叙事,及其背后的以现在的眼光用过去来换取现在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的意义在于向我们展示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不同时代的人。“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了解孔子?正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孔子,找不到一个有这样的人生价值和人格特征的人。尊重古人是因为他会讲我们讲不出来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价值。”
1.《杨照 杨照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我们小看了中国史》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杨照 杨照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我们小看了中国史》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guonei/8156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