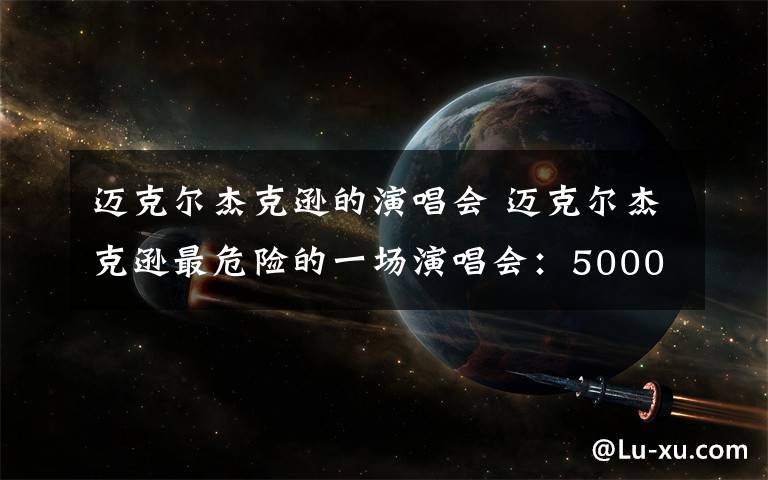上周五,米洛斯·福尔曼去世,享年86岁。
有些读者可能不熟悉这个名字,但他们一定看过《飞越疯人院》。米洛斯·福尔曼凭借《飞越疯人院》(1975年)和《莫扎特传》(1984年)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米洛斯·福尔曼
其中《飞越疯人院》在豆瓣电影250强中排名第42位,评分30万人,60%给予五星好评。
当我们谈论疯狂和文明,反叛和逃避时,我们无法避免米洛斯·福尔曼的《飞越疯人院》,美国评论家称之为“一个自由人和一个不能容忍他的社会之间的伟大斗争”。好像和我一样,大部分观众一直都把这部电影当成一部反体制的电影。
而北大电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教授则从叛逆的角度给出了更多的解释。在她看来,《飞越疯人院》是魔鬼母亲的神话:在精神病院里,妇女和黑人掌握了压制、监禁和毁灭的力量,他们一起制造精神疾病和疯狂。
因此,戴锦华认为,《飞越疯人院》仍然是一部好莱坞的神话,一部关于制度而不是反制度的神话。
《飞越疯人院》漫画版
以下内容摘自戴锦华的文章《飞越疯人院:叛逆故事的背后》。有点长。希望你能耐心看完,感受一下被我们忽略的人性缺陷。
电影中的几个基本命题;
疯狂与文明,监禁与秩序,话语与权力
好莱坞电影的制作体系一直是美国现有社会体系的子系统之一,也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效、强大和迷人的组成部分。好莱坞经典电影的编码模式无疑是美国社会现存秩序与权力话语的同构。
《飞越疯人院》一举获得五项奥斯卡奖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它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和西方观众中的成功销售。
《疯人院之外》无疑是一个寓言,但它不是一个关于反叛的寓言,而是更接近于福柯寓言的重写版。因为我们不难从电影《飞越疯人院》中找到福柯所关注的几个基本命题,比如疯癫与文明、禁锢与秩序、话语与权力。
米歇尔·福柯(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是法国哲学家、思想史家和社会理论家。
而且从电影的故事层面也不难发现福柯所描述的现代疯人院的基本模式:不像人们对疯人院的恐怖想象,没有绳索和捆绑的衣服,美国电影弗朗西斯甚至没有迫害和残酷。这些都是“解放”的疯子,大部分都是自愿来“医院治疗”的。
开篇之后,疯人院(叙利亚)里的元社会出现的是安详安详:在悠扬的音乐和护士长温暖话语的呼唤下,患者排队吃药然后散开,在活动室里选择自己喜欢的卡片或桌游,像孩子一样温顺幼稚。
那些管理和维护疯人院秩序的人“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权威的”。护士长拉希德作为这种权威的体现,并不狰狞可怕。她总是端庄典雅,白色的制服和黑色的休闲服总是平平整整,一尘不染。
她那永不褪色的笑容,那充满无尽耐心,从不抬高嗓门的声音,把所有的对话者都变成了愚蠢、固执、无理取闹的顽童,对话者的一切要求都成了哭闹吵闹的孩子的糖果。如果一定要用强制手段,这一切都由楼上电疗室的护士来执行,不会玷污这个由护士长控制的特定空房间的安宁。
护士长拉契德(路易斯·弗莱彻饰)《飞越疯人院》
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是:四次集体治疗研讨会,展示了护士长运用她的权力——
“带着一种迟钝、痛苦的责任感,而不是由疯狂引起的无限恐惧。恐惧不再是监狱大门另一边的傲慢,它也会攻击灵魂深处。”
护士长权威的确立,是为了让恐惧成为疯狂者的内化力量。
正是同一个小组治疗的讨论,显示了现代精神病医疗实践的特点:“无休止的审问”取代了“粗鲁武断的判断”,“他们始终逃脱不了被谴责和被指控而没有任何证据,因为他们在疯人院的生活构成了被指控的内容。”
至此,《飞越疯人院》这部电影似乎确实成了福柯批判性、揭示性寓言的电影版——一部反体制的电影。它旨在去除民主社会的伪装,揭露压迫、迫害、监禁和流放异端的真相。
但是,等一下,稍微仔细考察一下,不难发现电影《飞越疯人院》的寓言和福柯的寓言,以及西方现代社会结构,都错位在它们的核心部分。
福柯尖锐地指出,在现代西方社会,疯癫永远离不开“家庭”的辩证法,它一半是虚构,一半是真实。疯狂包含暴力亵渎,永远是对“父亲”(父权制)的攻击。作为一种隐藏的颠覆力量,经常被用来反对家庭结构的巩固及其古老的象征意义。
因此,现代疯人院的诞生,作为一种秩序和压抑的机构,作为一种看似非暴力的国家机器,其潜在的作用是疯狂地复兴父母(父亲)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威望。
因此,疯人院里的医生必须戴上父亲和法官的双重面具。
“因为从一开始,医生就代表父亲、法官、家庭和法律,所以他在疯人院里可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医疗实践只是对旧秩序、权威和惩罚实践的补充。”
但在电影《飞越疯人院》中,占据“父亲、法官、家庭、法律”象征性位置的不是医生,而是护士;不是男人,是女人——拉希德。
《飞越疯人院》是一个恶魔母亲的神话
如果说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是当代世俗神话最强大、最体面的形式,那么必须指出,这是一个神话体系。当一个女性表征在一个寓言结构中占据了经典的男性位置,就会推翻或改写那个寓言的可能寓意。那么护士长Rachid是男扮女装吗?是代孕妈妈吗?答案是:没有。
无论是影片中饰演瑞秋的弗莱彻(一位端庄美丽的新生女演员),还是原著中反复强调的瑞秋惊人的胸部,都强调了这个角色的性别。
如果《飞越疯人院》是一部神话,那么它就不是关于秩序的神话,而是后精神分析时代魔鬼母亲的神话;如果是寓言,那就不是揭露隐藏的父权制的寓言,而是旨在警示男权社会:侵犯母权制和女权是如何悄悄侵蚀男权社会的根基,如何入侵和阉割作为“母亲”和爱的话语的男性,如何创造和强化男性和男性社会的疯狂和病态。
事实上,在肯·凯西的原著中,这呈现了一个毫不含糊的主题:
“我的朋友,在这里,我们都是母系氏族制度的受害者。医生不能像我们一样抵制这种制度。”
《飞越疯人院》作者:[美国]肯·凯西,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出版年:2015-1
首先,在本文的故事层面,护士长拉希德是经典男性地位和权力的篡夺者和篡夺者。在这个病房(叙利亚的元社会),她垄断了权力,成为所有医疗实践的执行者。是她,不是男医生,甚至不是女医生,主持了集体治疗的讨论和无休止的审问。
影片叙事场景中出现的三位医生无一例外都是白人中产阶级男性,但在拉希德面前都显得那么柔弱苍白,却又亲切正常得多。当迈克·墨菲第一次来到疯人院时,他对医生的采访是亲切和谐的。
他们聊起了钓鱼,女人——典型的男性话题,男人之间交换着狡猾而默契的眼神。没有审讯,也没有判刑。在谈到迈克·墨菲的疯狂症状时,他反复深刻地强调:“他们认为……”这与护士长在集体治疗中进行的残酷而恶毒的审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原著中,护士长不仅是篡位者,更是女性阉割的生动赤裸裸的体现。没有医生可以或愿意与她合作;
“我一到那个病房,和那个女人一起工作,就觉得血管里充满了氨。我一直感冒,孩子不肯坐我膝盖上,老婆不肯跟我睡。”
事实上,这就是拉希德在这篇文章中的真实角色:她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治疗者。
如果说现代疯人院的意义在于通过罪恶感和罪恶感的折磨,以及因废除量刑而导致的无休止的审问,迫使疯人最终重新做人,重新做人,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从而纠正秩序,恢复父权制,那么拉希德所做的恰恰相反。
她主持的所有治疗的意义在于“留住”她的病人。就像在关于魔鬼母亲的话语中,这个“母亲”的“爱”的全部意义在于阉割。她在心理上阉割自己的孩子(她儿子),是为了留住他,永远占有他,以此来填补她曾经冰冷阴暗的内心缺失。
拉希德之所以成为众多恶魔母亲之一,就在于她的工作,就是利用超越的力量,把那些已经长大却遭受心理挫伤的男人,变成被阉割的温顺的孩子,让他们经历一个不可逆的胎儿过程。
在原著中,麦克·墨菲用他独特的粗俗语言解开了这个谜:
“老护士不是怪物,是只大鸡,伙计。她是切鸡蛋的专家。”
“老鹳就是这么做的,来到你的致命地点。”
然后,当哈定解释所谓的白质切除时,他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
“如果她不能去除腹部以下的东西,她就必须去除眼睛以上的东西。”(哈定本人进入疯人院只是为了逃避他滥交的妻子。)
影片删除了这些直白的对话,但保留了一个更有意义的脚注角色:耐心的比利。
耐心的比利
要治好病人比利,就给他一个女人
是比利定位并确认了护士长妖妈的身份。这个形象以他像孩子一样瘦弱的身材,一双清澈的眼睛,常常充满恐惧和难以忍受的口吃,引起了观众的无限同情和认可。
如果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永远是他社会心理年龄的直观表征,与他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成正比,那么比利不完全的语言能力恰恰是他作为未成年人的心理诉求。
其实在影片的叙事中,心理上被锁定在青春期、难以成长的“孩子”比利,是自己的母亲和另一个妖妈邪恶的占有欲创造。
因为在精神分析话语中,对于一个母亲和一个女人来说,只有凭借她的儿子,她才能在象征秩序中占据一个想象中的法拉和一个模棱两可、岌岌可危的位置。
因此,他的母亲残忍地剥夺了他青春期可能的女伴,把他送到疯人院,并设法把他留在那里。只要他被拘留一天,他就永远是一个“孩子”——他母亲的孩子和一个“未成年人”。
其实治愈比利的方法极其简单:给他一个不需要添油加醋的女人,他就可以结束漫长的童年,穿过男人的成年之门。
护士长拉希德作为比利母亲的好朋友,在影片中始终是比利母亲的代理人,是她母亲权力的缺席参与者。她以母亲的名义和权力来照顾和约束比利,用一种“慈爱”的眼神和威慑把比利钉在永无止境的青春期的尴尬和痛苦中。
就像比利在电影的元社会模式中把护士长定位为魔鬼母亲一样,比利也把迈克·墨菲定位为父亲和兄弟。
如果说拉希德象征着母权制的邪恶本质和母爱的入侵,那么迈克·墨菲则呈现了父权制的理性、父爱的大胆和温情。正是麦克·墨菲的到来,逐渐恢复了这个由死亡的和平与秩序所控制的疯人院的生机和活力,逐渐为疯人唤起了一点尊严和勇气。
影片结尾前的大组合,无疑是好莱坞经典电影不可或缺的“剧情坨”,也是戏剧性的高潮。
其实这段话不仅把麦克·墨菲对疯人院秩序的反叛和颠覆推向了高潮,而且始终被一个局部的悬念支撑着:麦克·墨菲的逃脱,这似乎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动作,被推迟了两次,两次是因为比利,永远是因为比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迈克·墨菲为比利牺牲了自己。
在这个组合中,迈克·墨菲为所有疯狂的人组织了一个节日和嘉年华。他给了比利一个女人——他自己的女人。这是迈克·墨菲最温柔的一幕:他把爱人抱在怀里,内疚地问:“宝贝,就这一次,为我做吧!”然后一挥手,所有疯狂的人把坐在轮椅上的比利团团围住,把他送到了“洞房”。
这是一场家庭式的“婚礼”,一切都充满了欢乐和温馨。面对紧闭的病房(洞房)的门,迈克·墨菲在与主任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后,带着解脱和疲惫闭上了困倦的眼睛。
家庭式“婚礼”
第二天,护士长走进病房,发现比利时还睡在他的“婚床”上,护士长不再掩饰她的邪恶和凶狠。她的双手叉腰,眼神凶狠,但是出现在前景的比利却露出了开心而灿烂的笑容。
他回头看护士长的时候,站在她面前,直接面对她,说得很流利很勇敢,“我可以解释一切。”怒不可遏地问她:“那你解释一下!”他带着男人的调侃回答:“一切?”他的语言能力恢复了,他不再口吃了,他被治愈了,他长大了。
于是,在护士长的正面特写中,她自信地环视了一下笑着的病人,然后威慑地对比利说:“我很担心你妈妈会怎么想。”
反砸镜头里的比利突然缩了回去,记忆中母亲的权利和惩罚又活了过来(注意,不是拉康所谓的“正常社会”中的“父亲的名字”和“父亲的法律”,而是母亲的名字和母亲的邪恶和“罪与罚”),比利又结结巴巴地说:“你...不要..必须..告诉我妈妈。”护士长得意洋洋地笑了:“不用吗?我和你妈妈是老朋友了。”
至此,比利新近获得的语言能力急剧消退。在恶魔之母的联盟面前,他不仅没有说话,最后还背叛了他的父亲和朋友麦克·墨菲。他跪在护士长面前恳求道:“别告诉我妈。”
这时,护士长的手漫不经心地温柔地抚摸着比利赤裸的肩膀:她成功了,比利变成了一个知道自己错了又害怕的孩子,他只会发无意义的单音节词。所以,尽管比利哭了,她还是告诉一个黑人护士,“把他带下去,给他洗澡。”
并不是父权结构成功压制了年轻一代的反抗,而是邪恶的母权制再次扼杀了儿子健康正常的成长——最后比利在恐惧和绝望的重压下死在血泊中,半裸的身体蜷缩成了胎儿的形状。恶魔母亲们实现了他们阴险的“转世”儿子的目标。而这种残忍血腥的杀戮最终激怒了麦克墨菲。
接下来的不是所谓的暴力场面,而是一个经典美国英雄诞生的瞬间;一直缺乏社会常识和责任感的迈克·墨菲,变成了一只复仇的爱与正义之狮。
而结果是更成功,更残酷,甚至是不流血的残酷。脑白质切除把叙利亚唯一健康的男性——一个阳刚(有些太阳刚)而难以驯服的人——迈克·墨菲变成了一个准植物人——一个绝对愚蠢、温顺、无知的“婴儿”。
除了一个完美愈合的又长又深的疤痕,这个阉割和重写过程没有留下任何血迹。至此,邪恶、凶残、变态的母权制的统治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疯人院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尽管带护颈的护士长拉希德在微笑时有一点困难,但她的“善良”和权威依然如故。
酋长:通过拒绝语言秩序,他完全拒绝了现存的社会秩序
文本中的另一个重要症状是一个制造误读或谎言的重要人物,他无疑是印第安酋长。不是反叛者麦克·墨菲,而是他成功飞越了疯人院。
首先,他是印度人,而印度人是五月花“访客”最初的敌人。印第安人的灭绝是美国荣耀和梦想历史的起点,也是不可磨灭的污点。作为美国民族神话的重要电影类型(尽管美国“民族”本身是一种神话),西部片是建立在白人与印第安人、文明与野蛮的对抗之上的。
因此,印度文化似乎一直是美国文化的对立面。其次,电影里的酋长是个聋子。如果语言秩序是神话社会秩序的同构体,那么酋长的行为就是通过拒绝语言秩序来抗议制度。
原著中,酋长作为叙述者,是现代社会典型的精神病患者——机械恐惧和迫害妄想症。是迈克·墨菲用慷慨的爱和无畏的勇气治愈了他。但在影片中,酋长是一个智者,一个比迈克·墨菲更健全、更强大、更有洞察力的现代隐士。他之所以身处疯人院,是因为他知道“大藏于市”的道理:在逃不掉的中央监控塔内是最安全的,中央监控塔是现代社会的风暴眼。
然而,正如美国电影理论家亨德森指出的那样,在整个美国历史上,美国政府对印度人的同化是一种有意识的政策。早在1871年3月,美国政府就通过立法,“期待印第安人最终成为美国社会的参与者”。
到20世纪,印第安人不再是美国社会的“他者”和敌人,而是成为美国社会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作为美国社会的天敌,印第安酋长无疑是电影意象认知系统的成功误导,是主流话语实现的谎言效应。这部电影的解读者忽略的是,酋长并没有通过装聋作哑——拒绝语言秩序——来完全拒绝现有的社会秩序。
相反,他在影片的三分之二部分都有发言。一旦他开口,他就使用非常标准和正确的英语。他的语言能力证明了他作为美国社会“合格的”和“合法的”成员的真实身份。
影片有一个非常温暖、悲伤、含泪的结局:酋长面对着已经被完全改写成“婴儿”的迈克·墨菲,含泪温柔地对他说:“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你。”然后他很温柔的把枕头放在脸上说:“走吧!”迈克·墨菲在窒息中本能地挣扎抽搐,渐渐停止了呼吸。
在高速摄影的镜头里,酋长大步走了出来,用尽全力拿起沉重的高压水阀,在疯人院的窗户上砸了一个大洞,然后带着疯狂的人们莫名的兴奋和欢呼奔向晨曦的地平线。这是母系权力蹂躏下的兄弟情颂。酋长完成的正是迈克·墨菲没有飞越疯人院(母系监狱)的事情。
正如亨德森所揭示的,在美国历史和美国现实中,从来没有得到印第安人所得到的“宽容”和礼物的,是非洲裔美国人。美国黑人,而不是印第安人,一直是美国社会的天敌和慢性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印第安人的同化政策是加强对黑人的压迫、迫害和奴役的有效手段之一。
那么,通过考察《飞越疯人院》叙事中的黑人形象,似乎更有利于揭示电影的意义结构和修辞策略。其实电影里护士长的三个助理——护士都是黑人。如果说“罪犯”迈克·墨菲像个大顽童,那么这三个黑人护士更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典型反派。他们麻木,邪恶,面无表情,眼睛是空洞,就像穿着白色制服的机器人。只有当他们使用暴力时,他们才能在脸上看到一缕虐待狂和邪恶的微笑。
影片的最后一个组合,在后面的镜头里,三个黑人护士排在护士长后面,以纳粹的步伐向前走,后面是暴力和悲剧的场景。另外两个黑人形象也是护士长的帮凶:一个是黑人护士,一个是最后一幕的夜班服务员。前者幼稚、胆小、温顺,像护士旁边的陪衬或提线木偶;后者无疑是种族歧视话语中典型的非裔美国人:懒惰、愚蠢、贪婪、好色、嗜酒。
如果护士长拉契德病房里的病人除了上面提到的酋长以外,都是白人男性,那么不难看出这就是寓言《飞越疯人院》的真谛:构成这种压抑、禁锢和毁灭的,是女性和黑人的邪恶和病态的共同统治,她们共同制造着精神疾病和疯狂。
至此,《飞越疯人院》获得奥斯卡的谜团似乎已经揭开——
不是反叛的故事,而是秩序的故事;这不是好莱坞神话的翻版,而是对好莱坞神话的微妙改写。
其中,神话和经典的性别和种族编码在精彩的修辞策略中得到了成功的重述。一个悲剧,一个控诉,但悲剧的制造者和控诉的对象只是美国社会和当前美国制度的宿敌。
米洛斯·福尔曼凭借电影《飞越疯人院》为好莱坞经典电影系列增添了一部新作品。
他将当代美国最受欢迎的畅销书改编成一部艺术优雅的电影:一部颠覆性的社会寓言和一部关于“禁闭和反叛”的“反神话”电影。
但事实上,这仍然是一个好莱坞式的神话,一个关于制度而非反制度的神话。这似乎又一次证明,新好莱坞毕竟是老好莱坞的忠实继承人,是一些更聪明更狡猾的后来者。
戴锦华经典电影十八讲节选
作者:戴锦华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年5月
1.《飞越疯人院结局 《飞越疯人院》导演去世,而你可能依旧误解这部电影》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飞越疯人院结局 《飞越疯人院》导演去世,而你可能依旧误解这部电影》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keji/6831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