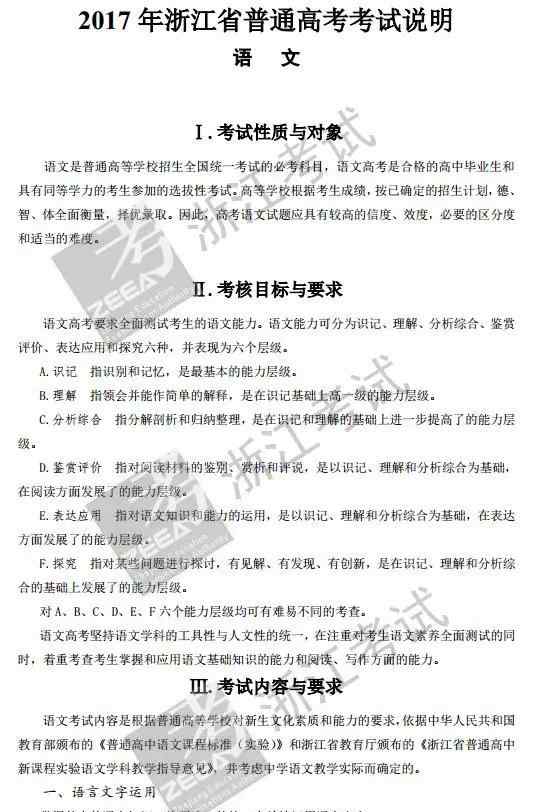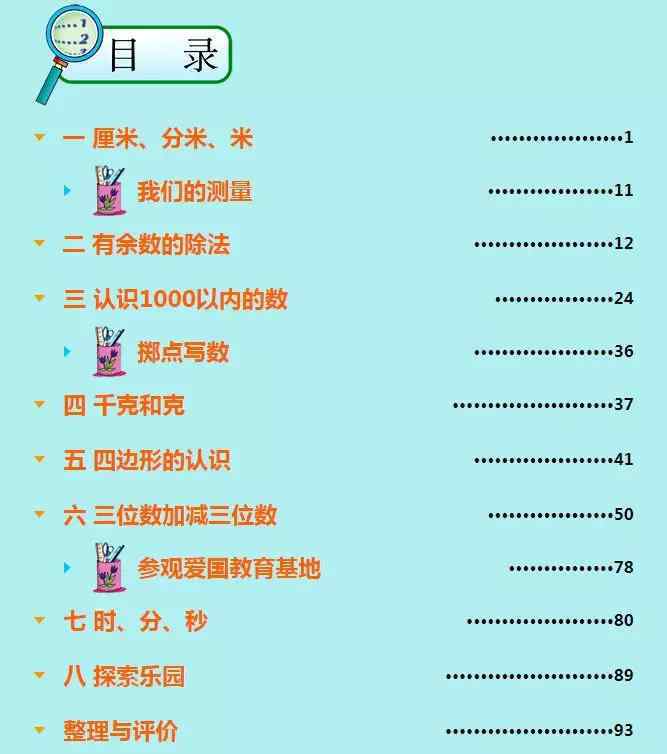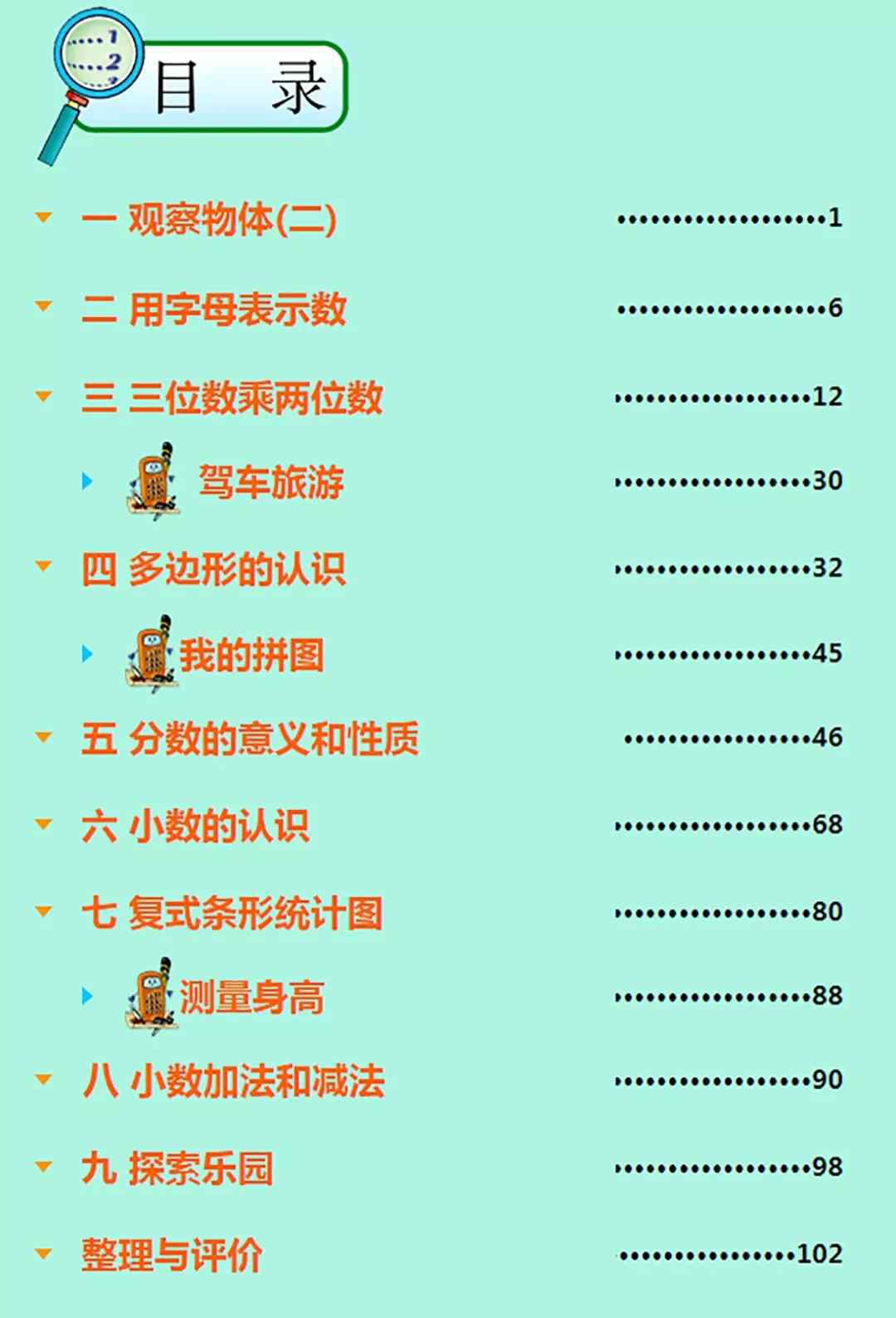2011年10月24日,“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南开大学省立大楼举行。来自国内外的33位院士和许多数学家回顾了陈省身先生对数学的杰出贡献。照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Xi南华正在为学生回答问题。
袁亚湘院士正在给本科生上课。
国立科技大学副校长Xi·南华院士。
周翔宇院士教本科生。
今年大二的莫雅金,经常听到校园里特别的“吵架”。
这个“吵架”不涉及利益冲突或感情纠葛,内容抽象深刻,场合很随意。像一个穿着华丽衣服的人,他突然冲到街上。
大一开学没多久,莫雅金正在大澡堂的隔间里洗澡,突然听到左边两三个同学在讨论“小区域内流体速度分布的欧拉表达式”。一个同学提到哈密顿算符可以用于欧拉表达式,马上另一个同学谈到数学处理的不足。在正确的隔间里哼着小曲的学生也加入了这场战争,指出会有多大的错误...雾和水声谁也说不清,但不妨碍大家踊跃发言。
在莫雅金所在的中科院大学,这样的场景时有出现。
这所大学被学生戏称为“中国数学物理大学”。本科生无论学什么专业,大一大二都会被分配上比较难的数学课。
他们的老师都是国内资深数学家,包括中科院院士。
9月20日晚,可容纳800多人的国立科学大学礼堂坐满了年轻学生。主讲人是Xi南华,他是国家科技大学负责教学的副校长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给大一学生教《线性代数》,2016级是他教的第三个。
演讲结束后,Xi南华遇到了一个常见问题:学习纯数学是什么体验?
“这是个可爱的课题,很好玩,而且没有实验设备。世界上有很多朋友。我转了很多国家,免费旅游。等我说完,结果就是你的了。”Xi南华笑了。“如果你想要这么可爱的东西,就去做吧。”
“数学家每天都是星期天”
53岁的Xi南华,又高又瘦,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
他声音沉稳,语速适中,演讲中偶尔会晃一些数学笑话。正因为他讲笑话不笑,所以在同学眼里特别搞笑。
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样的:“如果你理解了一个命题,知道了它的证明,那么你就可以写一篇论文,发表在数学杂志上;如果你理解一个命题,但不知道它的证明,可以把论文发在物理杂志上;如果你不理解它的命题,当然也不可能知道它的证明,那么你可以把论文发表在工科期刊上。”
礼堂里立刻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这个笑话也揭示了纯数学研究的特点,追求真理,要求获得真理的逻辑过程无懈可击。
得益于这一特点,当代数学家依然保持着古典学者的风格,能够像几百年前的前辈一样,以良好的心态深入思维领域。他们不需要把自己绑在实验室或者使用任何特殊设备。他们周游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同龄人交流,这也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大二,我在线性代数的时候,多次听Xi南华说数学家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比较自由,什么都可以想,吃饭走路。
在学习数学的这些年里,Xi南华访问了世界著名的数学研究机构,如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德国波恩马普数学研究所和日本京都大学数学分析研究所。法国的梧桐树,日本京都的红叶,新英格兰的田园风光,都成了他和同龄人思考的背景。
Xi南华的同事、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翔宇引用他的研究生张卫平院士的话说,“数学家每天都是星期天”。周翔宇解释说,并不是指数化者每天都在休息,而是他们在周日工作,可以随时工作。
有时候,即使是在床上,问题也会潜入醒着和睡着的间隙。1993年,正在德国访问的Xi南华正在研究“量子群在单位根的表示”。有一次他迷迷糊糊睡着,突然被一个相关的念头击中。这时,人们会突然醒来。
在办公室里,冯琪向《中国青年报》和中青在线记者描述了“思考数学”的具体感受。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学院的研究员。和Xi南华、周翔宇一样,他也在国立科技大学教本科生,研究领域是数理逻辑。
对冯契来说,思考数学是“舒服”的。当沉浸在问题中时,没有什么能打扰他。有时他不知道自己吃了没,清醒过来就觉得饿了。
“很纯洁,不是开小差。对自己微笑。大脑特别兴奋,不是我让它兴奋,而是天生兴奋。”冯琪说。
Xi南华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不选择工作环境。他走路和在车上都会想。生活中分心是常事。如果他想进去,噪音自然会飘走。
冯琪没有学数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大三秋季,对数学感兴趣的他,研究了一段时间“连续统假设”的问题。
到了最后一周,他觉得自己解决问题的希望很大,激动得几乎整整一周没怎么睡觉。
“根本睡不着。”后来冯琪和一个德国同事分享了这段经历,他完全理解。这位同事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看到希望,脑子里沸腾的像一锅水,停不下来。想清楚之后,他睡着了。
与当时兴奋难眠的冯琪同龄的国科大学生,逐渐开始体验到脑子停不下来。
今年刚入学的龚俊成,高中就有了学数学的想法。高二休学备战奥运会的时候,我连续4个月每天学11个小时的数学,但并不觉得无聊。一个问题可以研究很久,不会被其他事情分心。
前阵子他想到了一个线性代数的题目。有一天他醒来,恍惚中想起有很多符号闯进了他的梦里,在那里游荡。“我是不是有点着魔了?”龚俊成半开玩笑地说道。
李昕泽是龚俊成的大四哥哥,也是一名大二的数学专业学生。他发现有些问题太迷人了,以至于他想到了吃饭和走路。当他想不起来的时候,他会在校园里游荡。
去年初夏,李昕泽在练习中遇到了一个与“乔丹标准”非常相似的矩阵结构。晚上10点,他还在操场上走着,想着怎么把矩阵安排的更有序更完美。走着走着,他突然有了主意。
李昕泽回忆说,当时他很开心,觉得走路可以漂浮。而这种喜悦,外人是不知道的。说到,并没有伴随着球员进球时的欢呼。李昕泽说他最多露出一个假笑。
没过多久,冯契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关于“连续统假说”的错误,但他无法顾及自己的挫败感:“第一次,我觉得我的大脑可以这么兴奋。在此之前,我不会知道人的状态会有这么大的不同。”
直到现在,冯琪还说每天短时间内,一般在凌晨3点到6点之间,仍然可以进入极度舒适的状态。20年来,他习惯在这个时候起床,不吃饭,不喝咖啡,不沉思数学。
他提到了一个让很多数学家产生共鸣的现象:如果他特别激动,那么这个结论通常是错误的,所以最好不要说话。第二天冷冷静静的看,就会发现哪里不对劲。当你真的对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很平淡,很平淡”。
数学家有很多这样的“平淡”时刻。Xi南华在攻读博士期间,研究仿射威尔集团。一天午饭后,他坐在宿舍窗户前,懒洋洋地看着外面的风景。楼下是篮球场,对面是另一栋宿舍楼,女生住的地方,路上有一些行人。毫无征兆地,他突然想到,他可以利用一位荷兰数学家的工作来解决他正在思考的问题。
如果当时有人碰巧在窗口看到Xi南华,他们绝不会想到这个年轻人的思想和内心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不需要记笔记,总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
楼下是篮球场,对面是另一栋宿舍楼。路上有一些行人,但一切都不一样。
“最美的是数学的思想,美得不得了。”
“美”“美”“雅”是很多数学家在描述数学时常用的词语。
齐张成记得他的学术导师袁亚湘院士经常对年轻人说:“数学很有趣。”“最美的是数学的理念,美得不得了。”
Xi南华在大一的演讲中谈到了数学美:“数学美显然是内在美,需要你的细心理解,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比如市长向欧拉提出的“七桥问题”,欧拉抽象出这个问题,“图论”就诞生了。欧几里德对素数无穷性的证明,说明了逻辑的力量是一种美。勾股定理,把不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美。简单的事物揭示复杂的事物,也是一种美。”
数学的美和乐趣,就像“兄弟情”的联合代码,把说不同语言但使用同一组数学符号的人联系在一起。不像有些数学家以为埋头伏案打坐,数学家其实有很多机会去旅行,因为高质量的同行交流是数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冯契对那些形容科学家是“苦行僧”的故事有些怀疑:“没有人愿意活在痛苦中,必须在快乐的状态下工作。”数学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很开心,因为他们在思考让他们着迷的事情。
Xi南华认为数学不会带来孤独。他研究的东西周围的人不清楚也没关系。世界上有人能说清楚。
从东到西,当太阳扫过地球时,世界各地的许多数学研究机构每次都开始“下午茶”。数学家聚在一起寻找有趣的问题,交流自己的进展。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此配备了专门的厨房,那里的美食令Xi南华难忘。
周翔宇院士在苏联时,经常参加莫斯科大学的定期讨论课。“最难的教材”的作者科斯泰金和卓里奇辱骂了现在的国立科技大学的学生,他们是讨论课的常客。
在饭桌上的一个小讨论中,数学家和数学家“撞在一起”,也能产生一系列的思维涟漪。有一年,数学家邱承东来中科院数学所讲学。之后,Xi南华请他吃饭,邱承东在餐巾纸上写了一个他研究多年的问题。这促使Xi南华研究“代数群的无限维表示”,相关论文被审稿人认为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南华与数学家张的交流也是在饭桌上进行的。其实不是靠吃,主要是靠数学家之间的共同语言。
2013年的一天,南华得知张已经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的弱版本”:“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意思。周一去数学研究所开会。我说我们介绍这个人。”
其他机构也很快参加了比赛。Xi南华说:“北大校长请他吃饭。这是他的母校。清华校长请他吃饭,杨振宁陪他。数学学院也请他吃饭,但他没有找领导,而是找了几个年轻的同学跟他聊数学和数学。他很喜欢文学,包括古典文学、俄罗斯文学等。我们也谈论它。最终,他可能会发现,数字学院是一个学习的地方。”
Xi南华在2016年国科大新生演讲中分享了这个故事。他一说完,大厅里就响起了一阵掌声和笑声。Xi南华对他的观众有足够的信心。对于这些梦想成为科学家的年轻人来说,“学习的地方”是一个必须鼓掌的小高潮。他在讲台上笑了笑,给台下的学生留了足够的时间鼓掌。
这些台下的年轻人也在组织自己的“数学讨论班”。龚俊成的班级QQ群是一个活跃的在线讨论区。在午餐期间或睡觉前,人们几乎每天都在讨论问题。
大二学生魏毅,对自己获得了哥哥的“宝贵遗产”颇感自豪。作为现任书画社社长,收到过老社长的多种电子数学书,有10 G的。说起这些电子书,他的语气有点像小男孩提到他的限量版玩具。
学数学需要爱,但是环境对年轻人有很多诱惑,到处打电话赚钱成名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Xi南华、周翔宇和袁亚湘的成长过程中,中国人对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有着极大的热情。
15岁时,Xi·南华在阅读描述陈景润数学研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时迷上了它。虽然他不懂数学内容,但他兴奋地读了几遍。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中科院数学所收到全国各地的雪花信,门口排起了长队。人们聚集在这里请教数学题,或者声称自己完成了某个证明,有的甚至带了被褥,没有确认结果就不回家。
然而,多年后,当数学所所在的中关村出现越来越多昂贵的高层建筑时,人们对基础科学及其研究人员的热情逐渐下降,出现了许多担忧。
当2014年国家科技大学第一次招生时,来自云南的大一新生刘以豪面临着许多警告:“当你的同学硕士毕业,有车有房,你还在做实验,读博士,什么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一场贵族游戏。如果家里有钱,当然去哪里上学都无所谓。”……
今年,山东省顶尖科学学者孙浩选择了国立科技大学之后,知乎问答社区也出现了类似的讨论。得票率最高的答案来自孙浩本人,被赞2900多次:“对科研的贡献和回报的粗略认识。在此基础上,物理学的理想依然坚定。”
当Xi南华还是一名博士生时,他的室友建议他转学经济学。“我们学数学太普遍了,收入翻了一倍多!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转行,因为纯数学是我的兴趣所在。”
冯琪直言,学纯数学注定是一个赚不到专项钱的行业:“额外收入不能和数学统一。学习数学需要对自己的领域有热情。不能分心,不会分心,也不想分心。”但是现在的环境对年轻人有很多诱惑,到处都在呼吁赚钱成名。
想早点自立的李昕泽对数学感兴趣,但他不确定是否能以此为职业。“我问过几个助教,数学系工资不是特别高,结婚年龄也晚。我们助教的水平还是很高的。”
在数学世界里,这项需要人不断创新的工作,也可能导致研究者在思考上遇到挫折,或者陷入自我怀疑。
大一的龚俊成,入学以来见过很多厉害的学生。虽然他梦想做数学,但他觉得自己没有优势:“我能看到远处的山,但看不到脚下的路。有时候上课到周三,突然觉得三天过去了。虽然每天都在做题,但是感觉没有方向。”
龚俊成向他的学术导师Xi南华表达了这种感受后,Xi南华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笨鸟”经历。
事实上,Xi南华大学最初并没有获得本科学位,而是被一所大专院校的数学专业录取。工作一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Xi南华回忆说,在这一步,他仍然在挣扎:“我写论文非常努力。我的许多同学在第一年就发表了论文。我读了第三年,论文写不出来。”
Xi南华刚刚完成硕士答辩,就已经开始在湖南工作了。他的导师曹西华问他要不要继续读书。“想想!”“那就考吧,读博士。”
直到现在,成为院士后,Xi南华仍然觉得自己很平庸:“与伟大的数学家相比,我的成就算不了什么。”
他很惊讶自己能走到今天:“我的学校也不好。北大复旦的人多的是。我怎么会在现在的位置,既不聪明,也没有名校学历?我觉得很奇怪。”
后来他想出一个道理:“当时我不懂,同学说懂了。时间长了,我知道他们搞错了,但是他们不明白。”Xi南华说:“有什么区别?我知道我不懂,但他们不知道我不懂。我知道我不懂,我会努力去理解。”
Xi南华谈了潜在研究人员的特点,但没有什么神奇的:他们需要某些品质,热爱数学,然后是坚持不懈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让学生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学数学,学数学”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一楼的展览室里,有几份华《多元复变理论中典型场的调和分析》的手稿。我本来要带一个记者去参观,但当我看到激动的场面时,李向东也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李向东在国立科技大学的学生中被称为“东方之神”。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在国立科技大学开设“微积分”等课程。在之前的采访中,他提到自己在学习研究的时候,读过华1958年出版的书。书中精彩的推导和巧妙、巧妙的计算,让李向东读得“赞不绝口”。
应邀在北师大做数学讲座的院士,再次提到华的书:“我们这一代人做数学,受华的影响很大。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做过多变量自控功能。后来回国,完全在国内环境下,在典型领域做了多重复杂功能的研究。”
华,新中国数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老师。他创造了“一站式”教学方法,把数学系的所有课程都沿着一条线引导,全部由他带来。他还培养了许多数学家,如王元、陈景润、万哲贤、陆其铿等。
现在,国立科技大学的老师们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Xi南华不否认给本科生讲课和管理教学工作会影响他的研究。那些萦绕许久的“大问题”——关于基环的猜想,“代表不可约特征标记的模块”——需要摆脱外界的干扰,进行长时间的沉思。
“我要么不做,我要认真做。”Xi南华拒绝当学校领导,但后来培养人是非常重要和有责任的。上任后,他要求国家科学图书馆对各个专业进行全球前五名学校的调查,并在相关调查报告的基础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确定了国家科技大学的本科课程体系。
在李昕泽眼里,Xi南华上课不看讲稿,只凭记忆引出、证明、接收定理,最后一口气总结出相互关系。
然而,李向东的课程是另一种风格,被学生们评价为“无拘无束的法国学校”。他班上的学生魏毅说,李先生的课表面上看起来很随意,但他充满激情,非常注重诚信,概念之间有着清晰的联系。他没有使用指定的教材,而是向同学推荐了几本参考书,并选择它们进行讲座。魏上学期用了不少于10本书。
在招生规模不大的国立科技大学,刚从法国回来的李向东,专门想为学生打造“巴黎师范大学”的培养模式。
“让他们跳出教科书的框框,更好地了解数学发展的历史原貌、各个阶段的特点、困惑和研究的问题...不知道数学的源头,就不知道要做什么题,很难把握数学的过去,也很难预测数学的未来。”李向东说:“让学生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学习数学,学习数学。”
易对许多国立科技大学的数学老师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这些日常接触已经成为“被教”的一部分。
他看到教“抽象代数”的王松老师,走着走着,思考了好几次。“看着自己的眼睛,就是让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两届国际奥林匹克金牌得主王松是数论专家。
“再分析”教授崔,在菅直人眼中是一个“非常洒脱”的人。他经常告诉他的学生自由跟随你喜欢的任何东西。以后做什么都不一定是数学,但一定要自己喜欢,有自己的思考。这样才能快乐,做的才是真事。
作为易的学术导师,院士曾在晚上驱车前往玉泉路与几位本科生见面。他每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工作,事情很多,但是和学生聊天要一两个小时。
袁亚湘经常在周末带学生去爬山。他年轻时喜欢长跑。现在他爬山。二三十岁的人谁也跟不上他。
Xi南华在教书时,对数学史和数学家的故事非常熟悉,他能清楚地讲述一个问题的历史。目前已经学了《代数导论》第三卷的课,想到当时老师在课堂上指出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铺垫。
数学家的特点和轶事与课堂上的笑话无缝衔接。如果你看到你的同学躺着做笔记,Xi南华会提到俄罗斯数学家庞特里亚金:庞特里亚金从不做笔记,而且做笔记需要太多时间。
在周翔宇眼里,学生有动力,学校氛围好,科学家认真办学。基本上都是出动,完全毫无保留的使用自己的力量。周翔宇说,学生现在学的东西比他们当年学的东西更先进。
然而,学生也面临多重挑战。Xi南华平时很温柔,考试很严格。“学不好,学不好就失败。”。2014级班级,60多名学生中,春季学期结束有12名不及格,有10名补考一轮就不及格,只能下次重考。
9月的最后一天,Xi南华飞到四川的一所高中,教中学生数学之美。
在一万米高空空,闭眼的Xi南华正在思考如何写《线性代数》第二卷。他认为科斯特利·金的《代数导论》很好,但翻译后有些错误,表达不流畅。所以从今年开始,他用他的新教材《线性代数》给班上的学生看,到目前为止只出版了第一本。
大约三个小时后,飞机着陆时,Xi南华的旧背包里有半张A4纸,上面写着零碎的单词,这是他暂时写下的关于新教材的一些想法:“测量向量之间大小的概念空是维度,所以有必要知道向量之间的联系。可以使用的运算是矢量加法和标量乘法,它们是线性运算。”
除了这个旧背包,还有安德烈·怀伊(Andre Wye)在197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数学史的论文——《数学史:为什么看和如何看》,以及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
1.《要命的数学 国科大的数学家们:最美好的是数学的思想,它美得要命》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要命的数学 国科大的数学家们:最美好的是数学的思想,它美得要命》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keji/7361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