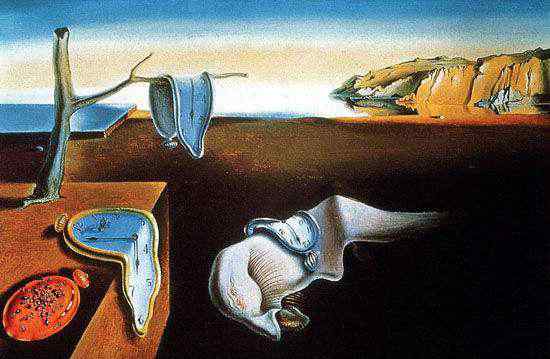李希凡先生住得离我很远,大约40公里远;老公的坟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大概三公里远,走路只要一刻钟。我现在不用跑很远的路去看他——不同的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自言自语,老公只是冲我笑笑,没说话。
作者李明新过去他笑着听我唠叨,时不时的笑。他听了我的话,耐心地指导我。现在他不说话,不劝我,不开导我,却还看着我笑,笑我,一个那么大,终于成熟了一点的傻姑娘!太阳如火,我放在他墓碑下的百合在他的笑容里慢慢枯萎…
2003年,我担任第一届春节曹雪芹纪念馆馆长,第一次去西番先生家做客。当时他住在建国门一个三居室的小公寓里,我很忐忑,因为我是村里人,但他是我认识很久的“小家伙”。我从不希望我的丈夫让我感受到温暖的春风。
他告诉我,他有三个女儿,妻子因哮喘住院。他说,别看我。这房子虽小,却是当年最好的!我在我丈夫的书房里看到了许超老师的照片。她长得漂亮,端庄典雅,我就真心称赞她“一定是班花吧?”呵呵先生笑着说:“不是班花,我们是校花!”
北京植物园的领导和红学界的“大佬”对我的工作都很支持,所以我做了一年馆长,逐渐形成了一个工作思路。好像是第一次和老公谈工作。我觉得曹雪芹纪念馆是中国第一个以“曹雪芹与红楼梦”为主题的景点,应该走“文化名人博物馆”的道路。王先生非常支持我,说我的工作思路是正确的。
我们和红学家相处,有一个“梗”,就是黄叶村的这个院子是曹雪芹的故居吗?1971年,象山正白旗39号院旧屋发现“壁诗”,引起社会轰动。坦率地说,中国没有红科学家支持这个作为曹雪芹故居。
曹雪芹纪念馆所在的正白旗39号院,是曹雪芹的故居。范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他根本不相信这种说法,所以他从未进入发现“壁诗”的院子。他还说,他在白家屯演了采风的角色,在山后面,找曹雪芹的住处。他说,收藏家问一个当地人是否知道曹雪芹是谁。当那个人说“是”的时候,他把他们领到一个农民面前,说:“他是曹雪芹。”我很认真的跟老公解释说:“这是民间旅游活动中很正常的事情,并不代表和曹雪芹没有关系。至于你对政白七39号院的态度,你连门都没进过,怎么判断?”
当时我完全沉浸在试图证明这个地方是曹雪芹故居的“氛围”中。本想请中科院用碳十四定年法来验证年龄,但是碳十四定年的误差是250到300年——曹公已经出生300多年了;我想考证一下正白旗39号院的原始功能,以及人们居住的身份,但找不到直接证据。后来朋友请了公安部的专家做笔迹鉴定,在“壁诗”、曹雪芹《废艺集》双钩本、曹雪芹书柜上的字上做了笔迹鉴定,鉴定结果是“一人”。但是这个人是不是曹雪芹还不确定,因为没有认出曹公的手。
虽然还有“更”,但以先生为会长,孙先生为秘书长的中国红学会,大概有一个共识,就是支持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为曹雪芹和《红楼梦》所做的一切活动,使之成为传播曹雪芹和《红楼梦》文化的基地。自1984年曹雪芹纪念馆建立以来,胡文斌先生一直帮助我们。我成为曹雪芹纪念馆馆长后,得到了更多红色科学家的支持,包括很多年轻学者,他们给我起了个人名字“村长”。
每次我邀请樊氏先生参加活动,他都会回答;王先生与众不同,因为他老了,因为他出名了。记得2005年,我组织了一个“曹雪芹红楼梦与奥林匹克文化”的论坛,邀请了两位著名的奥林匹克文化学者和十几位中国人民大学的红色科学家参加会议,会议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午饭后,西番先生对我说:“许超和我坐同一辆车来的。她正在花园里转身。估计现在都快转了。”我一听,就瞪着眼睛和老公一起生火。“你怎么能这样?”你清高。如果徐老师和我犯了错怎么办?植物园那么大,丢了怎么办?“哈哈笑了。”她这么大了,没事的!“之后,当我丈夫再来参加活动时,我会问徐老师来了没有。
次年春天,我邀请了范先生和先生到植物园赏花。同时邀请了我的老领导齐。齐主任退休多年,我和他女儿小文轮流推着他坐轮椅。当时西番先生和许超先生还很健康,基本不需要护理;其实王先生也很固执。他八十多岁了,从来不想被帮助。他看到我对老领导的关心,什么也没说,心里却给了我一个“好分数”,后来告诉了我。
我一直很直白,不要虚伪,讨厌虚伪;樊氏先生同意我的坚持和纯洁,并相信我是一个人。现在想想,我离老公36年了。我们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由于他的宽容。作为一个长辈,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引导我,鼓励我。那些话是发自内心的,而今天我要来了,让我感觉像是一股洪流!
2003年春至2018年10月29日,老公去世。这十五年间,我一年去看他三四次,更多的时候是打电话。我们无话不谈,但我从未对外界说过一句话。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和老公经常谈起老人的苦恼。2012年,许超老师去世,并完成了追悼会。我帮助我丈夫走出大厅。他说:“村长,谁走在前面谁就幸福。”从此觉得老公老了,真的老了。每次见面都会说:“村长,我们这一代该走了!”
我还记得他九十岁生日的时候,几个老红科学家给他办了一个小小的生日聚会。当他推着轮椅进电梯的时候,他说:“大家都祝我健康长寿。你为什么活这么久?”知道的人越来越少。".的确,人老了是孤独的,樊氏先生也是人啊!
前年夏天,先生和夫人李从杭州回到北京作短暂停留。我知道老年人虽然思念对方,但是交通不便,很难见面;我以为蔡义江先生的孩子都在杭州,回北京可能很远。我和老公一起开车,带着蔡先生夫妇去了西番先生家。他们那次聊得很开心,我也趁机找了两位先生给我的藏书签名,还签了几张红楼梦的明信片。老人眼睛不好,很难签名。蔡先生一句话也没说,戴着眼镜,一个个签名。范老师觉得有点累,问我:“村长,还有,怎么这么多啊?”我说:“来,先生,快完成了!”李老师指着我笑道:“那是,村长可以‘支持’他们。你又累又开心!”
我是2015年退休的,当时辞掉了社会工作。我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我听了我丈夫的建议。听完我的故事,他叹了口气,“村长,把你的东西写好!”
我后悔没有最后一次见到我丈夫。2018年重阳节前夕,他让李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会去参加活动。“我爸很想老朋友,说要见我一次,少见一次。”。我说我不参加活动,我要回家看他。可惜王先生突然走了,尽管他已经是一个长命百岁的人了,尽管他无数次说“我们这一代该走了”!
在西番先生的墓地里,有许多文化名人,如国学大师王国维、著名作家俞平伯、著名文艺理论家钱、郝、、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等...虽然它们已经降落在地面上,但它们仍然闪闪发光。
我想这里会建立一个新的“群体”——王国维先生和俞平伯先生可能会成为范先生的客人。樊氏先生的骨头很硬,他一生中从未害怕过任何人或任何事。在这个“群体”里,他一定会坚持不懈地硬化!
我为我的丈夫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再忍受老年的孤独了!但是我也很想念他。
微风吹来,百合颤抖了几下,老公又在嘲笑我…
1.《李希凡 两代红学大师的忘年交,探究香山黄叶村与曹雪芹的故居之谜》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李希凡 两代红学大师的忘年交,探究香山黄叶村与曹雪芹的故居之谜》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keji/8183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