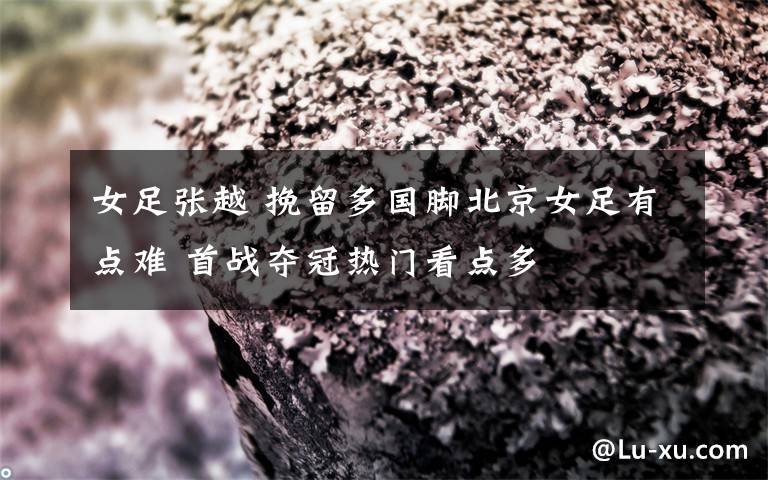2016年3月21日“春天脖子短”是北京的一句老话,意思是北京的春天很短。在“春”后面加一个“颈”,让你佩服北京人真是好修辞专家。“脖子”这个词让“春天”从一个表达季节的抽象概念变得可见和友好。
民国时期的中山公园
“春短”不适合很多刚入京的人,尤其是南方省市的人,比如从浙江温州来京的林斤澜。初到颜地,怀念南凉的丘迟,“三月春末,江南草长,树中花,莺飞”,不适合北京的“春短颈”。“北京人说‘春天脖子短’。“南方人认为这个‘脖子’只是名义上的,冬天刚过,夏天就要到了。”在林斤澜看来,这只是“春天脖子短”,简单来说就是“头连肩”。“杨树刚开,柳树刚吐,桃花“宣”,杏花“老”,一下子就热了。”因为“春有短颈”,北京的春天是最具爆炸性的“一夜之间,春风来了”。突然,从长城外葱郁的草原和沙漠,滚滚而来。”林斤澜真的爱上了北京这个“春天的短脖子”。“如果回江南,总是冷暖自知,最难还利息。永远是牛角的淡淡阳光,牛尾的烟雨。整个就像穿着湿布衬衫。墙角发霉了,有蘑菇和死老鼠的味道。你能不怀念北方的春风吗?”正是这种对北京的热爱,使江南人林斤澜成为“京派小说家”的代表。
作为“北行”文人向京派文化成功转型的代表,林斤澜显然不是这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被虹吸到北京古城,其中有大量来自江南和岭南的“南方文人”。他们来到酉阳后,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一些艰难的调整,最终爱上了北京这座古城。从最初的拒绝到最后的拥抱,他们写下了对古城气候、地理、文化、习俗的真实感受和认知调整,“春短颈”大概是最典型的感受之一。
周作人在《北平的春天》里写了他多年来对北京的感受。“春天似乎不是独立存在的。如果他不是夏天的头,那还不如叫冬天的尾巴。简而言之,当风和太阳都很暖的时候,我们很少一个人搭车到处乱逛,感觉冷的时候就会热起来。”。周作人气质冲淡,情绪不那么极端。另外,年纪大了,表达态度的时候也写的很舒服。“虽然北平几乎没有春天,但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丐帮已经享受春游很久了。”当年轻的福建人冰心写北京的春天时,他的情绪要激动得多。不同的是,在《一日之春》里,她写道,“去年冬天快结束的时候,我给一个远方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说我会尽我所能,把今年北平的春天吞下去。”“燕子”二字透露出一个天真浪漫的女孩对北国春天的珍惜和激动。冰心原名,父亲谢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她曾经是北洋水师学堂的炮官,创办时是烟台水师学堂的校长,后来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海军司令部二等参谋。冰心的父亲是一个开明的人,这为她成长创造了一个绝佳的环境。她从小住在上海,母亲去世后随父亲来到北平。良好的家庭环境是她“爱的哲学”的土壤。《一日之春》的风格是活泼而倾斜的。“今年北平的春天来的很晚,不知道春天在哪里的时候,抬头看到黄尘里的绿叶变得浑浊,柳絮乱飞,才知道在厚厚的黄尘沙幕之后,春天还没有出现,已经悄悄的引进来了。”
北京的春天很短。而作家凭借敏锐的感性和观察力,很容易捕捉到《北平的春天》的“存在感”。周作人写道,“北平终究还是有他的春天,只是有点太心慌了,又欠了点添油加醋,使人有时来不及品味他的味道,有时又觉得有点无聊。虽然它的名字还叫春天,但它真的被认为是冬天的结束,否则就是夏天的头。”北京的春天不仅短,还会被“冬天”打扰。“有一天,我看到湖面上的冰很软,心里突然欢喜起来,说:‘春天来了!’那天晚上,北风卷起漫天的黄沙,愤怒地扑到我的窗前,把我心中的春天又吹走了。有一天,我看到柳枝嫩黄的。下午,雨下得很大。晚上,冬天的衣服又穿上了。"
郁达夫,一个血迹斑斑的类型,去过几次北京,每次都只是短暂停留,加起来不到两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北京的一个过客,但他对北京的感情很深。他曾写过《北平四季》、《故都秋》等名篇,表达对北京的失望。“中国的大都市,我前半生居住的地方,不在少数;然而,当一个人静下心来回忆往事时,上海的热闹,南京的辽阔,广州的雾霾,汉口的武昌的混乱,甚至青岛的静谧,福州的美丽,杭州的从容,总不如北京...当你去北京以外的地方生活——除了童年的家乡,每个人都会不得不重新想起北京,又希望回去,模模糊糊的。这种体验本来是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人,每个人都有,但在我自己身上,感觉格外强烈,格外切。”带着对北京如此深厚的感情,他仔细体验了北京的一切,包括它的地理气候和季节,也仔细对比了北平和其他地方的差异。在谈到“春颈”时,他写道,“在北平,杰西·李的三季秋天是连在一起的;一年中似乎只有一个寒冷期,与温暖期相对。从春天到夏天,是短暂的一刻。从夏天到秋天,我只觉得午睡之后,有点冷。”北平的春天很短,到什么程度,郁达夫写道:“春来无信,春去无痕。眨眼间,在北平,春天会像飞马一样溜走。房子里的炉子刚刚拆了,也许你得马上给凉棚打电话。”
“风三儿”上世纪初的北海安吉大桥
沙尘暴是北平春季最常见的气候现象。曹太原曾在《老北平的沙尘暴与雾霾》中提到“老北平人都熟悉这句话:‘风三,风三,吹三日。’那时候冬春两季刮风,往往要连续三天放弃。七八级的强风夹杂着灰尘是很常见的。"
北平外省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复杂的风沙感。他们又恨又爱。比如梁实秋在《北平的街道》中写道,“无风三尺土,街上有雨有泥”,这就是北平街道的写照。也有人说下雨的时候像个大墨水盒,刮风的时候像个大香炉。这样的地方值得错过吗?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记得北平街的那一幕。”在北平,李健吾说,“灰色是北平的沙尘暴。带给你漠北的气息,骆驼的铃铛,奋斗的暗示。尘埃带你回到现实,但胡同是传说。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在北平呆的时间越长,就越习惯古城里的沙尘暴。"在北平生活久了,沙尘暴也干净了."鲁迅曾在日记中描述过沙尘暴,“风挟沙而霾,太阳明黄色”。但是,面对这场自然的沙尘暴,鲁迅似乎并不在意。《一觉》中,沙尘暴过后的场景是鲁迅作品中的场景,鲁迅擅长写生。而不是杂乱无章,透露出一点诗意。“窗外杨树的嫩叶在阳光下是金色的;榆叶梅也比昨天更灿烂,拾起散落一地的日报,拂去昨夜聚集在书桌上的苍白灰尘,我在四方的小书房,今天依然是所谓的“光洁的窗户”《一觉》是散文诗集《野草》的最后一篇散文。《野草》中的随笔大多是灰色的,但对这一场景的描写却非常鲜明而优美。上面是“飞机已经失去了投弹的使命,像一节学校的课,每天早上在北京飞。每次听到战斗的声音空,我常常会感到一种轻微的紧张,现在我目睹了“死亡”的来临,但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生命”的存在。隐约听到爆炸声后,飞机嗡嗡作响,在冉冉飞走了。也许有人死了,但世界似乎更和平了。所以比起现实社会的“风沙吹”和“虎狼成群”,自然界的风沙真的不算什么。
抗战爆发后,蒋梦麟先生迁居中国首都重庆,并在《西潮与新潮》中召回北京。“回忆过去的日子,就连北京飞扬的灰尘也充满了愉快的联想。怀念北京的尘埃,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蒋梦麟与其说是对尘埃的怀念,倒不如说是一个知识分子对战争中被尘埃覆盖的旧书房里稳定而规律的知识和生活的怀念。他越怀念,写得越深情,描写得越细致入微。“红木书桌已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轻沙一夜。拿起鸡毛扫帚轻轻刷掉桌上的灰尘,你会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快感。然后你刷掉笔杆和砚台上的灰尘;笔杆上刻有风景,可以顺便欣赏一下。砚台可能几百年来很多学者都用过,他们也像你一样认真擦过...书架上也有静静躺着的线装书,是西方还不知道怎么印刷就印刷出来的。用手指摸摸这些书的封面,你会发现飞尘也同样访问过这些古籍。”自然的感情根本不会让人觉得矫情。沙子和灰尘与稳定的旧时光融为一体。
钱歌川直接赋予了沙尘暴“北平精神”的价值地位。“北平和沙飞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飞沙,就不是北平。就在同一天,好久没感觉到地震的时候,我感到很孤独。如果北平没有飞沙,一定觉得有点无味,缺少一种构成旧都的元素,觉得有缺陷。同时,它可能要变脸空。精神会清新,花草会变色。”在他看来,没有经历过北平的风沙,他是无法真正理解北平的内涵的。他认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中国人,可以欣赏北平的古风,可以在尘埃里喝酸梅汤,可以在街上嚼‘硬面’。说到古物的保存,他特别支持自古流传下来的风沙。”
由于他们执着的文化情怀,五四知识分子大多能透过沙砾欣赏到北平的美,如郑振铎。在北平,虽然他写过春天北平沙尘暴带来的不适,“如果春天去北平,第一印象可能会给你一种很不愉快的感觉。你从前门下火车,一阵大风吹来,你不得不往回走几步。风卷起了一团泥沙;一不小心,眼睛就瞎了,难受。”我也写晚上可怕的声音和寒冷。“风吹了一天一夜,炉子的铅烟囱和纸窗互相敲打着,可能会让你半夜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我一睁眼,风还在虎啸,“但是沙尘暴和寒冷,比不上大风后北平的春光。“真正的黄色太阳明亮地照在墙上和窗户上。那种温暖平和的气息会立刻鼓励你跑出去。小鸟在细细的唱着,院子里有一朵杏花或者桃花,里面有苞片,浓浓的红色的就不放了。枣树的叶子正试图向外生长。北平枣树那么多,几乎每个院子都有一二棵。柳树柔软的枝条已经露出嫩黄色。”
作为女性,爱美是她们的天性,清洁是她们作为家庭主妇的职业。沙尘暴的到来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当人们走在街上时,灰尘吹在他们身上,使你的眼睛变窄,衣服变黄。人们在糊窗上用绿色的纱布,纱布的眼睛很浓密。风和沙还是会钻进来,地上会积一层。房子里各种器皿都没有厚厚的黄沙,浪费精神。”或许正因为如此,苏对缺少一种沙尘暴的感觉。
本文
1.《一日的春光 文人笔下的北京春天 北京的春天“没脖子”》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一日的春光 文人笔下的北京春天 北京的春天“没脖子”》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keji/8365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