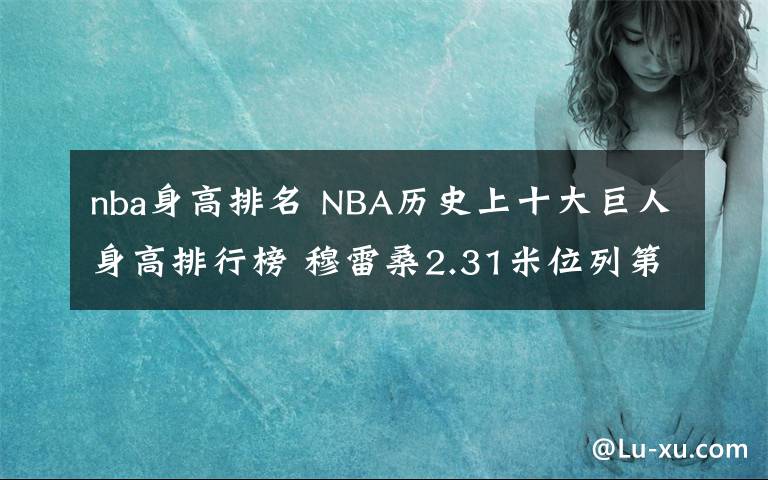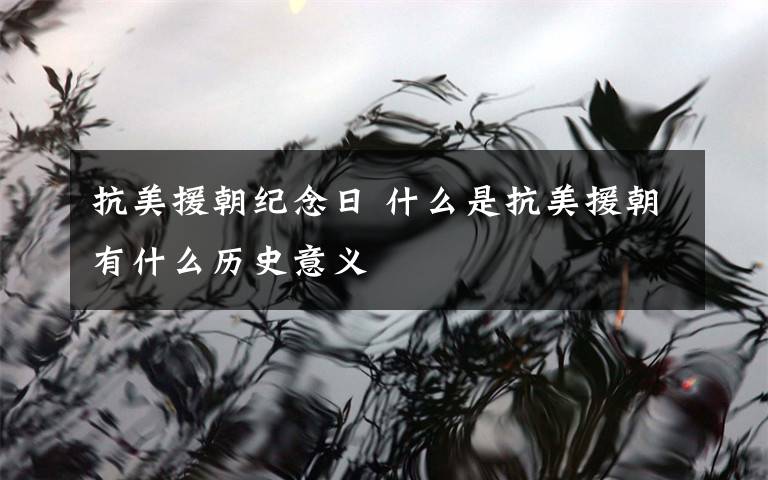李因
对风的执着追求
——青年学者王清飞
温
周作人有篇文章叫《大捕风》。“精神烦恼”的理论来源于《旧约全书》中的《传道书》。传教士说:“做过的事,事后一定要重复,做过的事,事后一定要重复。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我看我在太阳下做的一切都是空空,都是为了捕风”;“我也关注智慧的疯狂和无知,但我知道这也是一种对风的追求,因为智慧越多越愁,知识越多越愁。”周作人很喜欢这些人物。现有的事后会重复,做过的事后会重复。此生之所以“虚空虚空”。然而,他补充道,“话虽如此,虚拟空的唯一方式实际上是追求虚拟空。面对傲慢和无知,这是这个虚无世界中第一件有趣的事情。”“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要找出同类的狂妄和无知,还要思考自己的老病死。积极的人可以是一份很棒的工作,消极的人可以算是一种有趣的消遣。Virtual 空由它的virtual 空组成。如果你知道它是虚空,但你偏要去追本溯源,那么它就很有意义,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很棒的捕风器。”反思传统,改良社会,批判知识分子自身,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捕风者。捕风的必要性一直是知识界的话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但是到了90年代,随着思想界的急剧转向和分化,后现代、后革命时代的到来,这个话题真的变成了“虚空虚空”只能随风飘散。
后现代主义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者准确地说,它主要意味着关于真理、理性、科学、进步和普遍解放的宏大叙事,这些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思想特征的消解。如果说中国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使后现代的社会描述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将一系列理论从文学和文化理论翻译成了“消费社会”,对“现代性”(一整套文化/知识建构)的反思和对知识分子(作为现代性的发起者和建构者)的质疑成为了知识生产的新趋势——启蒙等概念并不自然。同时,艰难的现实是: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实践功能在20世纪90年代被削弱;一方面,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化等级制度的崩溃,使知识分子迅速失去启蒙地位。作家王小波在90年代末的突然离世,促成了一场带有时代症状的文化事件,这绝非偶然。作为世纪末的“文化英雄”,他在文学上塑造的恰恰是放弃启蒙、摆脱道德优越感、背弃甚至逃离大众的职业知识分子形象。在小说《红夜窃窃私语》中,知识分子李靖在朝廷和民间的攻击下,不得不作为街头流氓生活在集市上,而数学研究却成了一项偷偷摸摸、别有用心的地下工作。这是20世纪末知识分子开始与群众混战的画面。
“当代学者常常被五四运动的假象搞得晕头转向,认为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很美,近年来的精英文化已经失传。”人文学界从苦心思索开始呼吁“淡出观念,凸显学术”,呼吁知识分子“回归岗位意识”,甚至呼吁“回归普通人,平衡心态只能完成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同时以社会的良心和群众的代言人进行阅读。“60后”学者在呐喊边缘化、身份调整、学术转型。80后学者长大后,这一切早就尘埃落定,常态化了。对于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大学的一代人来说,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和专业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也许更适合80后青年学者的是福柯的质疑:你见过知识分子吗?
但在我认识和了解的后起之秀80后学者中,王清飞是个奇数。他的学术旨趣和批评风格比同龄人表现出明显得多的暖心“捕风”气息。其实每个时代都是异质杂音交织,每个学者总有不可约性和分类性的特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从左到右划分,而且在文化形式和专业领域上也划分为各种部落。然而,“捕风”王力可清飞很难用各种标签来分类。或许“经典”的捕风行为本身就是对差异化的排斥。当然,他和他同时代的人是一样的,我们都已经完全被时代从“伟大”和“浪漫”中冲走了。清飞不是正规学校出来的。他在南京大学学物理,后进入中文系攻读现当代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科技时代,如果要刻意渲染,那就是逆潮流而动的“传奇”,王小波称之为“反熵”。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避免对这段经历做情绪化的叙述,不重视它的意义,拒绝让自己的个人兴趣选择显得特立独行。久而久之,这种体验基本上变得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弃理从文”从来没有发出过应有的象征意义。真正与众不同和引人注目的是他“更真实”的性格,以及他对文学和历史知识、轶事甚至“破碎的鲍超”的杂项兴趣和广泛参与。
清妃性格温和幽默,学识渊博,机智风趣,在演戏和交友时一般都遵守“君子和而不同”。“据说如果你不能和他们说话就是失态。”。但是,每当他忍不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性格更真实的一面:看人,争事,争亲戚,争分歧。张,一个著名的男人,不能不上瘾地与人交流,因为他没有深厚的感情;人与人之间没有缺陷就无法沟通,因为没有真气。清飞经常这样看朋友。每个人都是有偏见有情感的凡人,所以他也喜欢那些忍不住有真性情的朋友,哪怕对方和自己有分歧有冲突。对雅丽来说,这是相当有学者遗风的。虽然我们生来都是读文学的,但是经过了从“学者”到“知识分子”、从“风度”到“精神”的现代转型之后,这样的遗产其实并不常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有所谓“学者”的酸味。相反,他忍不住与之争论的人事,通常不是因为观点不同,而是因为别人随口说出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标签或集体无意识的话,以及各种隐藏的传统继承思想和旧习惯的遗留。从日常师友八卦到静坐读书写字,类似周作人的那句“观同类之骄而不知”——包括观自己的骄而不知,清妃可谓一以贯之。虽然这不能完全概括清飞所有的学术和批判活动,但我认为基本上反映了他的精神品格。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学术趋势逐渐发生变化,“理念淡出,学术凸显”,从才子式的空谈转向倡导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学者们特别注重“辨章学术,审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正如陈平原所说,“今天的学术界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喜欢‘从头开始’,通过分析知识构成的历史来追问‘合理性’。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有“镜考起源”的思想,但更重要的启示来自法国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现当代文学而言,五四新文学以来确立的一整套“文学”概念,并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知识体系。”从古代的“散文分离论”到今天学术界流行的“文学史”的转变,应该归功于西学东渐的浪潮。这涉及到晚清以来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倡导者的自我确认,以及近百年来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型。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教育制度的演变。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的确立和演变一直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这些大问题和衍生话题,近十年来吸引了不少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当然也考验和锻炼了他们的智力和知识。清飞博士论文注重现代文学的发生与教育,注重学术体系的研究,需要整合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它不仅是文学革命的研究,也是依托“一派一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坦白说,我国文科博士培养的学制一般是三年,少数是四年。这样的研究任务对于仍然需要学术训练的博士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最好的情况是选择一个合适而巧妙的角度,把当地的问题解释清楚,或者借助一定的理论范式构建一个叙事,这样就很难系统而全面地呈现历史的进程和面貌。清飞发表过世界上见过的文章。其中有《1925年北大出教育部》、《30年代初北大人事改革》、《林语堂辞职与学风转变》、《胡适与考证倾向》、《溥仪出宫与北京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中心》、《笔名与责任》等。都可以归因于这样的主题,还有其他几个相关的研究章节。这些文章内容充实,平实严谨,但枝蔓散乱,没有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意识,也没有某一方面的历史叙述。它们更像是一系列需要策划和联系的“事件”。
老一辈学者非常重视史料的经验。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学术界喜欢引入理论和流行术语来更新他们的解释,并以不同的范式和视觉阈值激活他们的问题意识。博士论文写作因其普遍的依赖性和理论体系的拼凑而受到特别的批评。诚然,博士生的知识基础还是比较浅的,理论的运用会有些轻忽一物而失去另一物,但平心而论,他们之所以屡屡批判得病,是因为相对于其他研究路径而言,它是一种在有限时间内更为实用的方法。翻看史书,让新的“问题”自然产生,并持公正有理,是学术研究的理想状态。对于第一次看到唐傲的博士生来说,实际情况往往面临着大量的史料,这些史料松散而无尽,但他们整天环顾四周,却不知所措。相反,带着一定的问题意识或一定的理论范式框架进入史料阅读会形成蜡烛效应,某些东西的重要性会被感知凸显出来。原本铺好的、混在一起的数据,会逐渐变得脉络化,循着分支走,这可能不仅扩大了新史料的发现,也可能对旧史料做出新的解读。虽然博士生在学术训练中难免会用理论来制造突兀的史实,但勤勤恳恳的人会逐渐在理论、历史知识、史料之间找到平衡。但在博士学习期间,清妃却可以用这种学术时尚来形容“坐定”,徜徉于世海,执着于“文史互证”。在他们的同龄人中,拥有广博的文史知识,以及古今中外的学问,确实是难得的优势,但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学习提升所必需的“理论焦虑”。学习上没有新旧之分。但正如王国维所说,“中西学术会兴盛而衰落,风气开放而互助”。当代西方的知识理论和思想资源往往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视觉门槛,让很多原本被忽视的东西显现出来,更新我们的常识和认识事物的框架。对于学术史和现代文学发生学的研究来说,“审视镜子的起源”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但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不同,甚至截然不同;受福柯的启发,关注“话语、知识与科学”、“知识本位”之间关系的思想,与文史互证所关注的问题大相径庭。如果忽视学术热点背后的理论资源,研究很可能会暴露于史实,被思想所掩盖。说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清飞对现代文学与教育制度的研究显得零散,缺乏“主旋律”的原因。以他扎实的基础和对史料的广泛掌握,如果理论能够得到适当的培养,这一研究有望更加系统和深入。研究是昂贵的,而证词应该改进。
研究方法其实没有绝对的价值,理论和角度的选择要结合学者的个人天赋和禀赋,才能使学术多元化、丰富化。清飞的研究有点保守,但也避免了因依赖理论而出现的倚剑斩脚的弊端。而是一个成熟的年轻人,什么都懂,走正道,公平谨慎,有大的一面。这样的学术往往需要在某个领域继续运作,等到成果积累到一定规模,才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和价值。历史学家王凡森在《倔强的低音》中反思了一些历史思维方式,颇有启发,有些话题在我读清飞的文章时总会浮现在脑海中。近代以来,史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对‘历史’的新定义意味着,许多非进化的、看不到线性向上发展轨迹的事物是‘非历史的’。结合线性进化发展中的东西,很多秋千看不到来回,很多低音都没了。可以放入这个结构的是‘历史’;无关和不相关的部分不会出现在历史叙事中,也不会成为历史的焦点,这将导致我们对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发生许多扭曲。”这种扭曲包括我们常常忘记历史进程中没有单线清晰的事件发展;历史世界是不透明的、有限的,没有人知道“未来”,所以不是一切都是历史行动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历史是交响乐。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不仅只有一个基调,还有主调和副调,还有主流暗流。而我们这些已经知道历史结果的人,往往无法“后知后觉”地倒叙历史,在多元的人事世界中提炼和建构“本质”。王范森先生的作品总是对年轻学生有很大的好处。我不敢说清飞达到了王先生的史学家的学识,但我觉得他对现代文学和学术体系的研究与这些反思多少有些重合,他在尽力避免“后知后觉”方面有着明显的自觉。这也和“文笔”的选择有关。在学术史研究中,用“专题”和“问题”来组织讨论,联系人员,人员的详细程度以讨论问题的需要为准。而清飞则以部分核心人员为中心,尽可能详细地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顺便带出众多事件中学术思想的历史变迁,不以历史结果预断和描述事件的意义。例如,在1925年北京大学脱离教育部的叙述中,北京大学教授的“法日派”与“英美派”之争,显示了两个学派学者在教育观念、学术和社会政治观念上的差异。30年代初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森林丧失与文体转变、文学研究的胡适与考证倾向、商务印书馆与新文化运动等文章也是如此。
在这些历史叙事中,清飞的分析和论证都试图达到陈寅恪所说的“与作陈述的古人同在一个境界”,既兼顾人情又兼顾事物,既不为历史人物的功过辩护,也不为历史人物的功过责备。同时,他也充分展示了历史人物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方面,拒绝为他们选择一个点,做了简单的标签定位。如《胡适进宫与溥仪的公众形象》、《森林的丧失与学风的转变》等。,对胡适有着同情的理解,这不仅是对礼仪的明确,也是对他的人心的清醒。《1990年以来鲁迅研究中的自由主义与后殖民理论》一文,也从更为理论的角度对胡适与鲁迅的简单比较与庸俗“主义”切割进行了辨析与反驳(与这些论题相关的,有针对性的纯批驳文章也在此列),对于这种历史趣味与知识关怀,清飞借用了一句简单可爱的套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对自己进行注解:“辨人。“是的,其实在这些研究中,他最关注的是“人物”及其行为,更接近于传统的研究个案调查。王凡森先生曾感叹,“学一个案例”不仅仅是“学历史”,更是“做事情”,它还起到了引导人走出人生困境的作用,有着现实生活的实际层面。也就是说,学者的“知行合一”、心性、伦理等内容呈现在学习案例中,而不仅仅是矿化的知识和思想。这是人文学科研究中极其有价值的一部分。清肺遵从台湾京农的文学研究哲学,“活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无论是谈文学还是谈书画艺术,它与人的气节格局、精神状态、时代氛围融为一体,渗透着生命意识,所以在各种艺术中往往能突破界限,观察其传播。在这篇优秀而深情的论文《半个名人——论台静农赴台后》中,他也是这样研究台静农的。
陈平原先生在《感动历史,走进五四》的导言中有一段话:“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它们巨大的辐射力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要认真面对,这样你在冥想和对话中才能获得方向感和动力。五四运动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作为后者,必须与五四等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理论(包括思想理论、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保持持续对话。).这是必要的“思维练习”,也是“心智成熟”的必经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五四运动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它既是学术的,也是精神的。”“这是一块‘磨刀石’,用来打磨思想和学习。”我相信任何认真研究过五四的学者都会赞同这个发言。学者在研究生涯中被聪明帅气的人和天气吸引是非常重要的,这与格局、视野和性格有关。我们和研究对象之间不仅是单向的研究关系,研究对象也会滋养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清飞对五四运动和学术体系的研究是否成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和那个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游学”的师生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他们的研究给了我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有助于我在评论当前的文学作品时把握分寸。”
清飞并不是一个很快“临场”的文学批评家,他现在的批评家大多是有思想的作品,或者是多愁善感的作品。在这些批判性文本中,五四精神遗产非常明显,他不断“重新确认和推广五四先贤们引进和提出的现代价值观”,并走得更远。就当代文学批评而言,他用这种方式描述自己的批评理念太简单、太诚实了。听起来一点都不新鲜,而且让人对审美智能感到厌倦。但这种固执的批评观,既有当前实践经验的刺激,也有对鲁迅精神深刻理解和继承的来源。正如周作人感叹的那样,“做过的事,事后再重复,做过的事,事后再重复。天下没有新事。”。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无法摆脱“古代存在”的“经验循环”,这就构成了鲁迅深刻的绝望体验和怀疑基调。面对近代,面对民国,面对新思潮,面对各种新名词,鲁迅看到自己的皮毛改变了主意。这一再给他一种感觉:“现在我已经进入那个时代,我不知道。”我看到“老派的、寻求庇护的、不智的、愚蠢的、邪恶的,似乎都被300年前的新千年迷住了,也就是‘暂时做个稳定的奴隶的时候’”。对这一历史现实的绝望反抗构成了鲁迅杂文创作和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学者丸山昌Xi研究《阿q正传》,认为《阿Q=鬼》影响深远。丸山先生认为,鲁迅对阿q的命名隐含着“鬼”的含义,不仅仅是因为阿q从来没有获得过做人的权利,就像一个孤独的鬼在世界上游荡;也是因为阿q根本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识,脑子里充满了死人的想法——各种自古以来就存在了四千年的封建思想。所以阿q和他的中国儿女生活的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死人统治活人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鲁迅说“中国的灵魂写满了历史,预示着未来的命运”,而这样的中国总是重复着以前的命运。周氏兄弟一直受到易卜生对这种文化和历史“鬼”的理解的影响。周作人在《大捕风》里叙述易卜生在剧《鬼》里借了阿尔文太太的嘴说:“我觉得我们都是鬼。不光是父母传下来的东西活在我们的身体里,还有各种陈旧的观念和信仰。虽然不是真的活着,但也有埋伏。我们永远也逃不掉。有时候拿起报纸一看,好像看到很多鬼在两行字之间爬来爬去。世界上一定到处都有鬼。它们的数量像沙粒一样不清楚。”
清飞在接受采访时说:“鲁迅的意义在于他不懈地戳穿了几乎所有的集体无意识幻想,解毒了中国文化和大众心理中深藏的负面因素。那些集体无意识的幻觉,就像幽灵一样,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字眼留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们的嘴里,在我们的纸上蔓延,我们每天都在无意识中与它们混杂在一起。只有打破这些幻想,赶走这些幽灵,我们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才能真正有效地思考生活和未来。”我认为没有必要重复清飞具体的文学批评文章,这些文章足以描述他的批评实践和社会关注。在《张耀杰刀笔技法》一文中,清飞写道:“这是否意味着传统专制思想的幽灵还在许多人心中顽固地滋长?或许如辜鸿铭所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心里的辫子是无形的。’“在当代文学作品及其所反映的现实中,要坚持对这一无形的辫子进行检测和批判,不要被时代潮流所困。借用王梵森先生的“倔强的低音”,清飞可谓“倔强的捕风”。
这种“犟风钓”,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鲈鱼”。启蒙是近代中国和80年代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但现在它有些模糊和边缘化。这并不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和所倡导的现代思想达到了目标或“理想状态”,而是因为它所面临的当代社会和现实变得极其复杂。一方面,启蒙尚未完成,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现实困境和时代命题超出了启蒙资源所能做出的诊断和批判范围。所以很多时候,启蒙只能诉诸个人道德实践和人类伦理。这就像清飞在很多文学评论中的窃窃私语姿态:他把思想底线和文学温情诉诸于朴素的人类伦理。这些批判性的词语从概念到风格都是简单简洁的,有时简单到“笨拙”。我喜欢各种各样漂亮的解说文字,同时也很珍惜这样“笨拙”的文章。每一代文人和知识分子都是贤惠腐败的,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80后学生出生在“短暂的20世纪”,成长在“后革命”时代,也可以说是一种“轻松的一代”。要肩负起这个复杂而又双重的时代经验,要激励奋进,还是要坚持,我们这一代人要自律。"说实话既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能力."(李因,海南大学文学院)
1.《李音 李音|执拗的捕风——青年学者王晴飞》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李音 李音|执拗的捕风——青年学者王晴飞》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keji/9757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