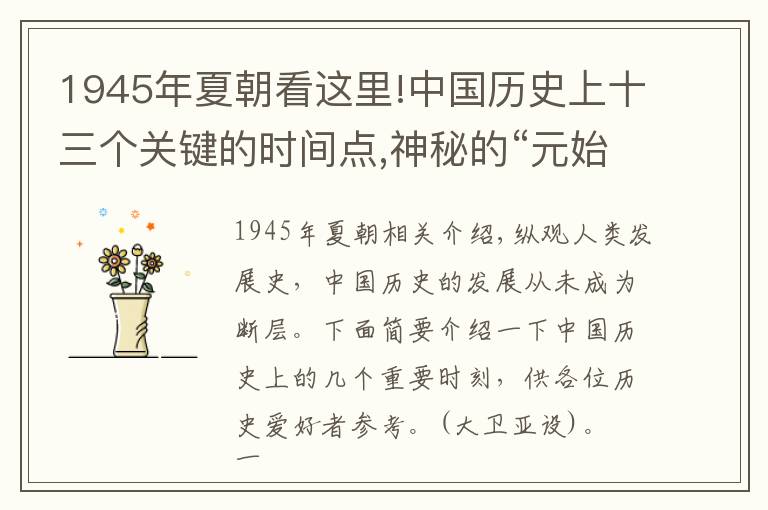悠悠妃
在讨论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群体时,游民总是引人注目。
宋元以来几次易代之际的遗民,给后世留下了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作为距今最近而影响最大的遗民群体,清遗民尤其值得关注。众所周知,遗民对于新旧世界态度和心路历程,在诗文活动和作品中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通过《郭曾炘日记》讨论清遗民如何思考他们的问题,寻找他们的生存策略。换言之,我想讨论遗民群体怎样在日记自叙中呈现个体的“人”,日记这种私人化写作对遗民的旧主、旧文化以及旧的人际关系意味着什么?郭曾炘(1855-1929),福建侯官人,原名曾炬,字春榆,号匏庵,晚号福庐山人,同治年间湖广总督郭柏荫(1807-1884)之孙,子郭则沄(1882-1946),一门数代,俱有文名。郭曾炘少有“神童之目”,光绪六年(1880)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宣统元年(1909),充实录馆副总裁,修《德宗本纪》,书成,加太子少保。宣统三年(1911),改典礼院副掌院学士。宣统皇帝大婚后,晋太子太保。郭曾炘曾上书言事,所论切中肯綮,张之洞称其为“百年以来,礼臣能识别大体者,一人而已。”辛亥以后,郭曾炘“蛰居都下,每岁时趋朝,值恩赉,戚戚不欢,言及辄流涕”。后谥文安。所著有《匏庐诗存》《匏庐賸草》《读杜札记》《论诗绝句》《邴庐日记》《楼居札记》等。(以上据王树楠《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头品顶戴署典礼院掌院学士郭文安公神道碑》)
郭曾炘像,据谢海林整理《郭曾炘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郭曾炘所记日记现存《过隙驹》《邴庐日记》等,有稿本、抄本及郭氏家刻节本存世,今整理完备者为窦瑞敏整理《郭曾炘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相关版本论述见《郭曾炘日记》“前言”及谢海林《郭曾炘<邴庐日记>的两个版本及其价值》(《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郭氏日记所记始于丙寅十月一日(1926年11月5日),至于戊辰十一月二十四日(1929年1月4日),即郭曾炘卒日。这四年来的日记,如郭曾炘所言,主要目的在“省愆尤”“辑闻见”“记交游”“倾吐胸次之所欲言者,而诗文亦间录存焉”。看起来这部日记与一般的日记并无区别,然通观是书,则其大旨在记载一位清遗民对清朝的故国之思。郭曾炘1928年九月初六日日记自白云:“余自辛亥以后,故国故君之思,每饭不忘。”这种明确的遗民身份的自我体认与高标,明白宣告其日记堪称一部清遗民的心史。
窦瑞敏整理《郭曾炘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
郭曾炘《过隙驹》日记书影,据窦瑞敏整理《郭曾炘日记》
一、清遗民是怎么想问题的
进入清遗民的思维世界,不难发现他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安顿清王朝的遗产,包括旧主(皇帝)、旧制度、旧文化,当然,也包括他们自身的出处和生活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他们身处一个新旧夹杂的时代,旧王朝(朝廷)还有遗存,而新民国业已据有天下。在这样一个半新半旧的时代,清遗民究竟怎么想这些问题?
在清遗民的思维模式中,历史典故根深蒂固地影响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思考结果。对许多清遗民而言,王朝始终存在复辟的希望,即便1924年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前往天津张园,使残存的王朝再度遭受重大打击。然而,他们并未因此绝望,一些大臣依然以古老的“东周梦想”自励,认为此举仿佛周朝的平王东迁,是王朝复兴希望的信号。不过,郭曾炘对此十分清醒,1926年十月初三日日记云,“余自辛亥后,即不复作东周之梦想。古来流离中兴,自少康后,已不再见”。在郭曾炘看来,王室东迁,周平王尚能维持半壁江山,然而希望以此作为中兴的基业,无异于痴人梦想。在郭曾炘看来,自夏朝的少康中兴以后,中国历史再也没有王室颠沛流离之后还能再度实现伟大复兴的。
此时已是1926年,距离清朝灭亡已经十五年了,一切都回不去了。可惜这种思维模式始终如幽灵一般萦绕在遗民的脑海中,在他们清醒的时候,理性告诉他们这是痴人说梦,但在酒酣耳热,恍兮惚兮之间,他们仍然不肯忘却这残存的幻想。可是小圈子内的幻想在外人看来简直可笑,于是遗民这种思维模式带来的只有痛苦。如1927年四月初七日,郭曾炘日记所云,“醉中乃得吾真,不特世故场中面目皆假,即如此册上,每日拉杂书写,亦不外闲人说闲话,满腔热泪,仍是无处洒也”。遗老末路,只能恸哭,连自己视为私密而真切的日记,最终也像是闲话一般。
在宏大的复辟迷梦之外,清遗民思考问题也有现实的一面。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逊清皇室的播迁问题,谁该承担责任?
尽管优待皇室的协议自清帝逊位即已生效,但民国政府对逊清皇室的供养却每况愈下。1924年,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之后,清遗民不能不直面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清遗民看来,太多的民国政客都该对此负责。从袁世凯以优待皇室为条件逼迫清帝退位开始,事情就变得不可控制了。起初承诺对清皇室的条件并不差,仅现银就每年400万元。不过这种优待的前题是民国政府自身安稳,遗憾的是,清帝退位以后,民国动荡不已,岂能确保优待。根据曾任逊清皇室内务府大臣的绍英(1861-1925)的日记记载,至1918年,民国政府拖欠皇室的费用已经超过1000万元。至于1924年,冯玉祥干脆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于是逊清皇室只能在风雨飘摇中动荡。
循着这条思路出发,清遗民很容易找出那些违背优待逊清皇室条款的政客,然而这种思考却是痛苦的,他们能够找出责任人,但对这些“罪魁祸首”却无能为力。于是这种追责式的思考只能诉诸情绪性的宣泄。在1927年底的日记中,愤懑的郭曾炘发出马后炮式的宣言,他声称早在十年前,他就知道“共和不宜于中国”。他认为,这不仅因为“共和”以后,不仅皇室经费得不到保障,全国的形势更会“全局糜烂,遍地荆榛”。郭曾炘并非孤掌独鸣,杨绛的父亲杨荫杭(1878-1945)也认为,“初不料共和之结果,一变而为五代之割据。无端而有督军,无端而有巡阅,使国人恶之如蛇蝎”。清遗民的这种情绪化的言说尽管是“马后炮式的思考”,但的确有一定的合理处。共和草创的兴奋期一过,党争与战事联翩而起,站在百姓的角度,国家生灵涂炭;站在传统道德文化的角度看,则世风日下。就此而言,郑孝胥的名言“民国乃敌国也”确实成为清遗民群体的普遍认识。
可惜,清遗民这种自以为清醒和高明的思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依然毫无用处,不堪一击。此时,北伐战争已经打响,南北局势骤然紧张。不安感和焦虑的情绪弥漫在清遗民群体中间,他们似乎停止了思考。在郭曾炘日记中,对于时局的看法颇为消极,许多时候更是保持沉默。对清遗民而言,他们所能作的是不断的聚会、饮酒赋诗,通过一次次雅集、诗钟活动,消磨岁月。几乎每个月,郭曾炘至少都有两三次诗社活动,既参加福建籍士人为主的榕社、合社,也参与地域色彩较淡的诗社如耆英会、蛰园诗社等社的活动。晚近诗社游戏各有不同,稊园主诗钟,郭氏父子主持的蛰园则维系福建诗社的传统——击钵吟,他们的思考从一种整体性的王朝命运,转为文人雅集和文人团体的地域情结上了。
郭曾炘著《匏庐诗存》,据《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7册
清遗民这种思维上的“延宕”,意外促成了民国诗词社的繁荣。潘静如《民国诗学》以为傅增湘藏园、关赓麟稊园及郭氏父子之蛰园雅集不绝,鼎足而三,实近世京津文脉所系。20世纪20年代,寒山、稊园、蛰园等诗社鼎足而立,号为宣南三社(相关论述见韩策《科考进士与民国北京诗词结社的兴衰》)。郭曾炘父子发起的蛰园集会在1926年短短一年间已举行20多期,参与者有樊增祥、夏孙桐、冒广生、傅增湘等人。1927年正月,七十三岁的郭曾炘在元日诗中颇有些自得地写下:“久闭柴荆逃热客,忽惊珠玉王粲篇。宣南酬唱多吟侣,敢与王卢论后前。”清遗民在政治上的思考无路可走,只好退回文学与书籍的世界中,不曾想这竟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收获和喜悦。
二、如何做好清遗民
清遗民思维方式的转变历程,大体可概括为从一种对广阔世界的思考逐步退缩到个人诗文小天地的琢磨之中。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与清遗民日常生活世界的活动能力逐步萎缩几乎同步。他们从庙堂退至江湖,从前官位和地位带来的收入及其他文化资本也相应地缩减。于是,如何做好一个清遗民,就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在此,《郭曾炘日记》呈现了郭曾炘如何小心翼翼地经营遗民生活的记录,因而也就提供了一份相对简单而颇有可观的“清遗民生存指南”。
利用好家族、姻亲、地域等关系,是清遗民在民国生存的基础。许多遗民都在新时代成为社会边缘的弃儿,被迫抱团取暖,寻求群体的力量庇护。这种对群的生活的经营,首先来自于家族关系的经营。如郭曾炘即利用其祖父郭柏荫(1807-1884)手钞《十三经》的故事,遍请京城、天津的名流题字。1926年十一月二十日日记云,“接沄儿信……言中丞公手钞十三经已征弢老及寓京名流题咏。”十一月廿九日日记云,“洪儿以中丞公手写十三经装潢已就,于津埠社友征题。请题一长篇,连日思索,粗完稿。……诗云‘晨书暝写日有程,阅二十年功始毕。……白头更遭沧桑变,烽火年年望乡国。礼堂定本半飘零,劫馀仅此犹完璧。迩来邪说方横流,洪水祸逾秦火烈。斯文终丧非天意,不见东瀛罗古帙。文身章甫疑无用,经训菑畬必有获。”郭曾炘一家珍护祖辈手泽,既是发扬祖宗潜德,也是在利用征集题咏不断激活家族社交圈。在这种有意的文化运作之中,郭曾炘定下的基调是:缅怀旧日的斯文传统,慨叹今日国家并日本也不如,这就使得这一风雅活动的意义从文献层面上升到对经典的再认及文化的反思层面。
家族之外,郭曾炘父子主要的社交圈集中在福建同乡中,郭氏父子积极参与福建人的团体活动,投身京师福建会馆的活动及闽中同乡的诗酒交流之中。通过京师的福建会馆,他们参与了家乡的赈灾等事务,与数千里之外的闽地仍保持密切往来。此外,郭曾炘父子也积极参与福建人在京城的文人组织——榕社。榕社的精神领袖是闽县人陈宝琛(1848-1935),同样也是一位铁杆的清遗民。陈宝琛在榕社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甚至诗社活动日期常因其行程而更改。如郭曾炘1927年二月廿八日日记云,“榕社新改于每月朔望,以弢老明日赴津,提前于今日。”陈宝琛和榕社的关系显示民国年间京师传统文人诗词雅集的两个重要特征:遗民为主,地域色彩。对郭曾炘而言,凝聚同乡关系同样是遗民生存的重要策略。在郭曾炘日记中,还能看到闽中文人内部的诸多交往故实,如他为林纾侄子林华所绘《寒灯课子图》题词等。
清遗民之所以竭力经营家族和同乡关系,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现实的局势发展十分糟糕。糟糕的现实环境增添了他们的不安感,而家族和同乡关系恰恰可以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以《郭曾炘日记》1927年前后北伐前后的记载为例,可见局势变化如何影响清遗民应对现实的生活方案。
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推进,清遗民的思维世界发生转变。他们甚至不再预设政治立场,只希望天下太平,可以优游度日。在这种心态背景下,连对覆亡清室要负主要责任的袁世凯,郭曾炘都不禁暗暗称赞,他认为袁世凯当权时是“纲纪犹张”,社会秩序大体安稳。然而,战争是无情的,南方传来的消息令清遗民忧心忡忡。郭曾炘1926年十月十九日日记记载,听闻“武昌逃难人来,目击比邻某大姓全家七人皆饿毙;又有赵姓者拥赀数十万,皆为南军抄没,今无立锥地。鲁青谓南昌劫掠不减武昌,城内无一完屋,滕王阁亦毁”。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摧毁了和平的局面,豪富之家破产,家产充军,连带文化名胜如滕王阁也一并毁于战火。彼时,郭曾炘老家福建发生台风灾害,外兼战事频繁,故在郭曾炘看来,彼时的世界简直是“遍地皆兵、遍地皆灾”。对习惯安稳生活的清遗民来说,恐怖的战争消息一再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1927年四月十二日,“有人言近日湖南每县每日平均计算,残杀有名人物约在三人以上,历朝鼎革后之祸,无此惨也。”局势变化最终打破了郭曾炘自己定下的不在日记中记载时事体例。1927年三月初六日日记,郭氏写道,“阅报知昨日军警包围俄馆,被捕七十馀人,获‘赤党’证据甚多。年来北京政府厌厌无生气,此举于前途成败未敢知,总觉差强人意也。”郭曾炘日记提及的此次事件即李大钊(1889-1927)等人被捕事。
局势的变化不断冲击遗老生活,对清遗民而言,此时的生存策略首先要求在心理上作出自我调适,否则他们很可能走向崩溃。
清遗民王国维之死在此成为许多清遗民反观自照的触发点。郭曾炘在1927年五月初五日听闻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当天的日记就花费大幅笔墨全面记载王国维的生平,尤其看重王国维的遗老身份。日记云:“甲子秋,逼宫之变,奔走日使馆,颇有接洽。张园定居后,回京就清华大学教员,仍不时赴津。闻此次沉渊,乃因赤氛紧迫,恐以后乘舆益无安处之地。忧思无计,愤而出此,其死与梁巨川相类。然巨川愤共和之失政,在以死讽世,于故国之痛,尚在其次。静安则纯乎忠赤大节,炯然又在其上。”关于王国维死因的说法甚多,郭曾炘日记所载当是时人的普遍认识,即他们认为王国维之所以自沉昆明湖,主要原因在于忧心皇室安危,无计扶危,才愤而自沉的。与1918年另一位知名遗老梁济(1858-1918,梁漱溟之父)自杀相比,郭曾炘认为王国维之死更沉痛,原因在于梁济只是愤懑于“共和失政”,而王国维则是为旧朝死节。
王国维之死对郭曾炘心理冲击很大。第二天,郭曾炘头脑十分清醒,然而愁闷无法排解,这促使他直面内心世界,甚而感叹:“能如静安之长睡不醒,岂不大乐哉!盖如彼之勇决,乃能得死所,空言祈死,皆惜死之人也。”郭曾炘坦白了内心的赴死之志,并谴责了自己的软弱。五月十三日,听闻王国维被皇室予谥“忠慤”后,郭曾炘认为“此等浮荣,徒滋谤议”,认为不如赏赐一篇诔祭之文为好。又过了几天,郭曾炘听闻谥号出自溥仪之手,并非左右为之,故而自觉失言,可是郭曾炘内心仍以为“忠慤”谥号不妥。嗣后,郭曾炘为王国维所作挽联为,“一代经师朱竹垞,千秋骚怨屈灵均”。挽联送出后,郭曾炘又拟一联云:“止水自澄,在先生固堪瞑目;浮云皆幻,愿来者各自折心。”后一联郭曾炘自认为“较为超浑”。推原郭氏衷心所指,恐怕在于前联仅仅高度评价王国维的学术及品节,而未及其余。后一联则将这种褒扬蕴于庄子的语言世界中,认为王国维的学术及品格均如止水自鉴,在不同人看来,如万川映月,各取所需。显然,后一联所以鞭策遗民及后来者的意图显豁得多。
郭曾炘墓志拓片《清故光禄大夫侯官郭文安公墓志铭》,据福州市博物馆官网
对动荡世界的清遗民而言,仅仅调试内心世界使之复归平静并不足够,他们的生存策略还必须应对实实在在的经济问题。毕竟,类似王国维这样的遗民,在心灵世界的危机之外,还面临另一重生活危机,即经济困难。不少清遗民步入新朝以后,失去官职,收入锐减,又谋生乏术,家庭负担顿时变成大问题。郭曾炘的友人夏孙桐(1857-1941)曾发出感慨,“常语生活两字,今日则不难于偷活,而苦于无以为生,此则第一难题目耳。”苟且活着诚然容易,但要说生活,在夏孙桐看来,确实是天底下的第一等大难题。据《郭曾炘日记》记载,林纾侄子林华1927年租住在大佛寺附近,三间房每月租金仅三元,可见寒伧,然而除了卖画,林华的谋生手段寥寥,也就无可奈何了。郭曾炘在日记中记载此类琐事,颇有身世同慨之叹。
大批清遗民的谋生之所以困难,并非他们不愿意去做事,而是无事可做。1926年十二月廿四日,郭曾炘与友人谈起“闲中苦况”,感叹“前清时,军队不及今日十分之一二,官僚不及今日之三四,国用不及今日之二三,何以到处无闲人,人人皆自得。此等大问题,非一篇大议论不能发挥尽致”。郭曾炘在此提出了重要问题,即1927年前后社会危机的重要根源在于经济和就业问题,普遍性的失业状况令整个社会充斥着游手好闲之人,人们不得安其业,自然就给社会埋下动荡的根源。由于无事可做,一些人在历史进程中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沉沦。如与郭曾炘家三世相交的许柳丞,因为郁郁不得志,不幸沉迷于鸦片烟,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就病逝了。念及这位旧友,郭曾炘不禁想起元好问的诗句“灯前山鬼泪纵横”。
持续性的经济危机甚至影响到逊清皇室的迁移计划,郭曾炘1927年正月二十日日记载:“弢老车中询及津埠能否安居,余谓一时似无恐,须看上海变局如何。又云或劝迁大连,则与京师隔绝,皇产清理益难,而从者贫甚,不能远涉。”在北伐战事正酣的局势下,郭曾炘敏锐判断出天津暂时安稳,但对劝逊清皇室迁往大连的建议,郭曾炘并不赞同,他的主要出发点是大连距北平太远,不利于皇室处理资产,且追随逊清皇室的人多穷困,无法跋涉千里继续追寻。一言以蔽之,没有钱,皇室身边的遗民队伍恐怕也带不动。
连逊清皇室的经济状况都左支右绌,一般清遗民的收支状况就更为糟糕。此时,清遗民热衷的文人结社也受到经费支绌的影响。据《郭曾炘日记》记载,天津严修(1860-1929)所创存社本拟请章钰(1864-1937)主持,约定经费由省长岁拨三千金,但郭曾炘认为“不甚可靠,恐难持久”。
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遗民的生存策略一是按兵不动,二是不断想方设法增加收入。在郭曾炘等遗老而言,他们的诗文才华也不再是个人吟咏的挥洒,而部分地转向了商业运作。郭曾炘1927年二月初一日日记载:“泉侄来,以大美卷烟公司售买(卖)康素、金银花两种,即以烟名出启征诗,意在以风雅代广告,请函恳樊山任评骘,即书付之。”二月初四日,樊增祥(号樊山,1846-1931)来书答应审阅大美卷烟公司征诗卷。七月十一日日记又云,“樊山书来,送所阅卷烟公司课卷。(系石琴求其阅定者,题为金银花七绝,康素二字凤顶。金银花、康素皆卷烟名也。)该公司征诗代广告,即以烟卷作奖品,此事发端于数月前,以资本未集,因并风雅游戏,亦为之搁置。樊山甚不悦,余居间亦甚惭歉也。”郭曾炘因为侄子之托,故邀请樊增祥作为评委审阅大美卷烟公司的征诗卷。樊增祥很快答应了。不过,卷烟公司这两款产品因资金运作失败而作罢,几个月后,郭曾炘已经把这件事忘了,直到七月十一日樊增祥来信提及,方才记起,深感抱歉。这次烟草公司的征诗广告以金银花和康素两款卷烟产品作为诗题,一则要求以“金银花”为题作七绝,一则要求诗联嵌入“康素”二字,作“凤顶格”。以征诗活动而作烟草广告宣传,前此罕见。看来,在商业化潮流下,清遗民的诗歌世界也不可避免地沾染商业气息。而清遗民中的名流如樊增祥等人轻而易举地答应担任商业征诗活动的评委,似又表明他们经济状况的窘态。
樊增祥《蛰园正月开社例以盆花为赠今年余得花九盆赋谢蛰云秘长并呈春榆宫保》,《铁路协会会报》1922年第123期
在生存策略面前,清遗民不免兜售甚至贱卖自己的诗文才华,这不免令人觉得伤感,然而,若从文学史角度考察,郭曾炘、樊增祥等人参与卷烟公司的征诗活动,也有新的意义。毕竟,这一活动表明诗歌功用在近代的转型,而其所续接的是清代颇为兴盛的征诗传统。另一方面,这样的诗歌活动也是商业潮流冲击的结果,最终意外促成了现代广告业与古典诗歌传统的交叉。
三、清遗民的分化与身份自塑
由于局势的变化,也由于应对现实策略的调整,清遗民群体内部不断分化。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清遗民群体进入“大分流”时代,他们重塑遗民身份和自我体认的过程,在《郭曾炘日记》中有着清晰的印记。
清遗民群体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流动性的群体,其内部一直在不断分化。复杂的局势和舆论环境影响着群体内部的交往,彼此之间的隔阂有时甚于鸿沟。如1927年正月十三日,郭曾炘在天津与康有为等人一道为溥仪庆祝生日,此时距他们1898年一面之交后,相隔近三十年。祝寿后,郭曾炘听闻康有为随即南下济南,为张宗昌贺寿,且在张宗昌生日席上侃侃演说“中国之必须君主立宪,滔滔不绝,始终未变”。尽管不赞同康有为所论,但对康有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信念,郭曾炘仍抱有同情之心。对待康有为晚年推动的“尊孔”运动,郭曾炘更是心有戚戚。故而听闻康有为逝世消息,郭曾炘在日记中写道:“闻吾乡已撤去文庙先师神位,改奉孙中山,果为南海尊孔之结局欤?”对康有为未竟的事业,郭曾炘深表遗憾,甚而写下《挽康有为》一诗。在读到康有为临终遗疏节本后,郭曾炘更对康有为表达深深的敬佩之情,日记写道:“此老抱定宗旨,始终不变,实为可敬,无怪瞿文慎、沈寐叟诸公之倾倒也。”
然而,当郭曾炘从陈宝琛处知悉康有为遗疏中有斥责慈禧的话,观点随即发生改变,认为“此君究何流人物,前数次日记但据传闻,谬有推崇之语,尚待参考也。”郭曾炘并非以为慈禧不可指摘,而是认为人臣应当尽臣节。他曾经对夏孙桐说:“晚明气节之盛,超轶前古,遂开大清二百馀年之景运,亦恐因此以结前二千馀年之成局也。”郭曾炘认为清代之所以有二百年国运,部分原因乃在于晚明气节之盛打下了基础。郭曾炘高标气节,故最不屑于毫无廉耻节义者。日记曾引晚清王照《读左随笔》,十分称许王氏针对欧阳修《新五代史》所发的议论:“谓《新五代史》之名,出于后人追谥。永叔初作原不为史,亦未尝欲取开宝诏修之史而代之。不过于读《五代史》时,痛恨五季忠义沦亡,风节扫地,爰别记其有关褒贬者,著为一家警世之言。其中以冯道为丧节之尤,故特创奇格……”在遗民群体日记稀少的背景下,郭曾炘在日记中写下这一大段感慨,显然是在讥刺清末民国的冯道之流。
郭曾炘对气节的褒奖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还体现在身体力行炘参与松筠庵的诗社活动上。松筠庵诗社活动为著名诗人林庚(1910-2006)之父林宰平(1879-1960)主持,其第二集到者有黄秋岳(1891-1937)等人。郭曾炘已十多年没有到过松筠庵,但此地为明末著名直臣杨涟(1572-1625)之祠,相传有杨涟手植的槐树。道光年间,僧人新泉出杨涟《谏草》付张廷济(1768-1848)犹子张受之刊石,碑刻刊成而张受之病逝。何绍基(1799-1873)为此作墓志铭,以为张受之之死较张际亮之死尤为可痛。此后,诗人张际亮(1799-1843)闻友人姚莹(1785-1853)因台湾抗击英军事系狱,奔赴千里至京师,不久即殁于京师,殡葬此处。其节义当时已风动天下。郭曾炘在日记中写道:“自谏草堂成后,咸同士大夫多就此为文宴之地。后来台谏诸君,每会议皆在此,其实忠愍并非谏官。”通过考辨松筠庵内部陈设及其历史变迁情况,郭曾炘对不同时代的气节盛衰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郭曾炘日记》所揭示的是民国年间清遗民特殊的“气节关注”现象。易代以后的读书人不断分化,他们对前朝的认同与否有时牵连到人们评价他们人格的优劣。刘声木(1876-1959)《苌楚斋随笔》卷六记陈夔龙(1857-1948)所编《梦蕉亭杂记》,称陈夔龙在辛亥国变后撰此书,乃辨别其非某党,而另有前清封疆大吏自编年谱则明确指出其为某党。在此,对前朝的认同与否和时事无关,但涉及传统士人基本人格的判断。在遗老看来,辛亥以后,世道衰微,廉耻日丧。如无锡《续梁溪诗钞》所载清末王世忠鼎革后黄冠道服,绝口不谈时事,张曾畴(1867-1911)遭革命家勒索,愤然投江而死。这些人,在刘声木看来才是“清末完人”。
在一些人看来,时代发展是“一蟹不如一蟹”,世衰未已,分化只能加速。一部分人走向追根溯源,探究清王朝何以覆灭。郭则沄等人每念及此,就称徐世昌(1855-1939)、袁世凯等人的罪过不可饶恕。郭曾炘1927年正月十五日日记,“与沄儿赴东海处,前此赴津与东海晤,皆泛泛常谈。此次坐稍久,颇谈及光宣时事。东海谓当监国时,一切朝事多由近支操纵,庆邸亦噤不敢言。情事或然,然终不能为政府诸公恕也”。对于清朝覆亡的责任,彼时身在中枢的徐世昌(号东海居士)认为朝廷事务多由慈禧的近支操纵,连庆亲王奕劻也“噤不敢言”,显然,徐世昌这番话是变相为自己的亡清之责开脱。清社既屋,郭曾炘尽管对这番话有同情的了解,但仍认为徐世昌等人负有不可推卸之责。
与回溯王朝往昔荣光及追究覆亡之责相比,在面向未来时,遗老们的分化更为明显。郭曾炘本人更是一典型,新朝的事务他并不参与,但对其子郭则沄,则勉励其入仕,故郭则沄的身份,就旧朝而言是翰林院庶吉士,就新朝而言则是北洋政府徐世昌的秘书。时局纷乱,京津地区的遗老由清入民国,辖于北洋统治下,十余年间,不少遗民已赖北洋而生,北洋覆亡,不得不再作冯妇,成为“北洋遗民”。与郭曾炘交往密切的友人孙雄即辑《旧京诗文存》,以悼念迁都南京以后的北京。郭曾炘对此不以为然,他所认为的是“军阀之局,政客开之。孟子谓‘善战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吾谓尚须一倒转也”,即政客、军阀当同罹其罪。对于清朝覆灭以来应该为时局混乱负责的人,郭曾炘一个也不想宽恕。这种追责还延伸到普遍的士人身上,在郭曾炘看来,“人生升沉显晦,各有定分,承平之世,人各安于义命,此天下之所以治。末世倖门一开,士争躁进。光绪中叶,如瓜分之恫喝,变法之条陈,皆曾文正所谓‘欲以语言欺人,先登要路’者,彼何尝真有国家观念在其胸中哉?一波动而万波随之,生灵受其涂炭,可哀也已。”由此可见,郭曾炘对光绪中叶以来清流一派的批判。
可惜,在所有的问责中,郭曾炘独独没有批判自己,他从不认为自己应该为清朝的覆亡承担一点什么。如此看来,《郭曾炘日记》揭示了清遗民分化的的根源,即几乎所有的清遗民都站在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做出选择,故而在对亡清的反思和清算中总想把自己置身事外。
四、“作为个体的遗民”的郭曾炘
对郭曾炘而言,回到过去是不现实的,他对未来却也不抱希望。面对错综的局势,郭曾炘在读顾炎武《日知录》后感慨,“今日者不惟光武、昭烈无可望,汉祖、唐宗亦未可见其人,即求如孟德、仲谋者,且不可得,乱何时定耶?迭阅报纸,南北战事之胜负虽尚未可知,而北方军阀一味纵欲败度,南方政党敢于惑世诬民,以民心之厌乱觇之,彼武士之剑端,终有屈于文士笔端、辩士舌端之一日。特南方胜北之后,若不回途改辙,恐犹是攘夺之世界已。姑志所见于此,以观其后。”这是1927年二月初二日所记,彼时乱局纷纷,郭曾炘读史而感慨如历史上收拾残局的伟人不可得。其所以将光武帝刘秀和汉昭烈帝刘备置于汉高祖、唐太宗之前,是因为光武帝成功让汉室中兴,而刘备则在汉祚已终之后再度复兴汉室,背后隐含者郭曾炘对清祚终结的悲慨之情。在郭曾炘看来,清室复兴无望,指望清室遗祚重来收拾天下残局不现实,而求之鼎定天下、再造乾坤的汉祖唐宗一流人物也不可再得。
然而百姓人心思定,郭曾炘亦预测南方国民革命军即将取得胜利,原因不仅在南军军事优势,而且归功于南军再宣传上的优势。但郭曾炘对南军胜利后的局面仍感到忧心忡忡,认为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如果不能改弦更张,全国的局面仍将纷纷攘攘、争夺未已。前途未卜,郭曾炘进退失据,又将目光回到传统儒家伦理。面对江浙涂炭,郭曾炘感慨,“锦绣江山,被一般政客破坏至此,彼等沦落无聊者不知凡几,其死于非命者尤历历可数,无非欲望太奢致之,孟子所谓‘不可不餍’者。”尽管谴责南北政客的乱政,郭曾炘归咎其因却转到部分民众奢侈之过上,无乃太迂。郭曾炘所寄望的人心返朴,并引《魏礼致张一衡书》来张本:“朴者,人之本,万物之根,世道治乱之源也。夫惟朴至于尽,而小人、盗贼、弑逆、烝报、杀戮之祸害相寻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朴,而其乱必先之以浮靡巧诈、言行乖戾,以酝酿杀机,天地莫可如何,遂听人之所为。”对郭曾炘而言,世乱求治根源在于道德人心的返璞归真,这种道德救国的理想与倭仁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何其相似!可惜,近代以来的历史给这种道德救国派以现实的嘲讽,面对列“阀”纷争,郭曾炘的理想只能悬居高阁,徒呼负负,并被后世贴以“顽固派”的标签继续加以揶揄。
不过,可敬的是郭曾炘内心并未冷淡,对局势仍有全面观察。对南北征战的原因,他也密切关注。1927年,他曾仔细阅读日本人布施胜治所著《苏俄东方政策》,并抄录该书结论云:“夫南军制胜之处何在,据某军事专家近日视察长江一带战事,归云南军强长处不在兵力财力,而在其背面之政治组织。盖即学苏俄革命之经验,仿照苏俄赤色军而编制军队,于革命之要素,无不备具,故能制胜等语。”郭曾炘抄录这段话为的是“以观其后”,可见他并非放弃对时局的思考。
可是,无论郭曾炘等人怎样思考,时势早已抛弃了清遗民。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做一个清遗民,除去前文所述的思考方式和生存策略外,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个体的行为,去定义世人眼中的遗民形象。
在复辟念想绝望以后,郭曾炘等遗民抱定“每饭不忘君”的态度,顽固地坚持清王朝的生活方式。据《郭曾炘日记》可知,他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示遗民的个体生活状况。
首先,尊崇旧主,遵行旧制度。清遗民极为尊崇逊清皇室。如郭曾炘经常从北京奔赴天津张园,觐见溥仪。另外,清遗民也照常参加重赴鹿鸣宴等集会。陈宝琛等大臣举行八十大寿时,不忘禀告皇室,请求溥仪的赐字。樊增祥庆贺乡举六十年之喜,得溥仪御书“耆英瑞事”四字,欢欣鼓舞,同人都来庆贺。对皇室的一举一动,清遗民也十分关心。例如在阅读报纸时,郭曾炘注意到紫禁城寿皇殿的清帝遗像被故宫博物院挪走,太监张成和拼死保护,最终故宫博物院归还遗像。郭曾炘认为“若辈尚能激于义愤,不惜以身殉职,吾人能不愧死耶?”并作诗云:“谁令大力负舟去,只当群盲评古图。公等岂忘盟府在,他年正恐故钉无。”对新朝人物极尽嘲讽之能。
其次,仍践行传统文人士大夫生活方式。这些侘傺而无所适从的清遗民,只能以诗酒自晦,沉湎于旧日的文酒生活中,日常参加习字、作画、把玩金石等等活动,新文化运动对他们而言似乎毫无影响。白话文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毫无位置,也因此他们对旧有的文学样态甚而有所拓展。如古典诗歌从未有给逝者行状题诗的,但在秦绶章(1849-1925)后人秦曾荣坚持索求下,郭曾炘写下《题秦佩鹤侍郎行状诗》,开拓了诗歌题材。在京城寓居无所事事的日子里,郭则沄等遗老们京城纷纷参与各类戏曲活动,推动了罗瘿公(1872-1924)等人记载梨园故事的《鞠部丛谈》一书的问世。
再次,他们始终努力维系日渐凋零的旧的生活方式,可惜那些生活方式连同背后的理念仍终于走向无可挽回的局面。他们频繁举行各类诗社活动,并试图增添一些新的元素。例如,还举办不少联欢活动,设有奖品,如1927年正月十九日,郭曾炘等人在灵清宫举办灯社活动,陈宝琛等人也参与其事。郭曾炘中了第二标,获得姚茫父的雪景山水画,此外,还收获水烟袋奖品。然而,随着国民政府1928年迁都南京,可以避世、娱情、广交游、通声气、扢扬风雅、砥砺气节、维持清议的旧京诗社,也逐步瓦解。
对于清遗民的生活方式,今人大可不必唱挽歌。毕竟,以清遗民为主体的诗社制造的诗歌多数成就并不高。那些社集的存在,不过是为了通声气,维持遗民共同体的一种必须的生活样态而已。诚如郭曾炘日记所言:“社侣日寥落,此局颇不易维持。”对于诗酒自饮,郭曾炘怀自己也有反思和自省,如1927年四月初四日日记云,“结社赋诗,乃承平之事,否则山林遗逸,今日为此,余极不谓然也。”不过,走在为故国招魂之路上,郭曾炘的诗歌观念却部分地因之而被扭转。在阅读《湖海诗传》时,郭曾炘认为集中所载康乾诸人如沈德潜等人,“不必以诗名,而所作皆有一种雍容华贵气象,自是盛世元音。吾所见同光台阁人物,去之远矣。”在诗歌关乎国运的传统论调下,诗歌和台阁人物都应该为世道的盛衰买单,郭曾炘此语令人想起钱谦益将明朝灭亡的文学原因归咎于竟陵派,所谓“诗亡而国亦随之亡”。从此不难看出,“作为个体的遗民”的郭曾炘,身心始终笼罩在遗民的阴云下。
“遗民”是研究易代之际历史和文学的重要词语,这一词语常常隐含复数的指称,即它往往与“遗民群体”对等。惯常使用的宋遗民、明遗民、清遗民/遗老,往往标识一群人的基本面貌。可是,将遗民视作一个群体性概念往往带来这样的问题:由于群体性的“遗民”概念掩盖每一个遗民个体的生命独特性,故人们总是强调“作为个体的遗民”,即一种对于遗民身份的普遍观感使人们厌倦了对于群体面貌的继续勾摹,转而探求个体在鼎革之际的独特人生轨迹与特殊品格。这就使许多研究倾向于忽视“作为遗民的个体”,去通过个体的表现修饰和重绘群体性“遗民”的面貌。
《郭曾炘日记》展示了一位对遗民身份高度自觉的清遗民,如何通过日记自塑自身的清遗民身份,进而通过这种身份的营造与体认,修改日常行为模式,从而自我定义了“清遗民”的基本内涵。研读这部日记带来的启示是:“作为遗民的个体”和“作为个体的遗民”始终处于紧密互动之中,“遗民”是“作为个体的遗民”不断塑造的流动性标签,在不断地自我构筑之中,“遗民”的涵义被这个群体自己修改了,而“作为个体的遗民”也逐步改变了“作为遗民的个体”的外在模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由澎湃新闻(www.)首发。作者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彭珊珊
1.《【1945年夏朝】日记探微︱《郭曾炘日记》:一个清遗民的“自我修养”》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1945年夏朝】日记探微︱《郭曾炘日记》:一个清遗民的“自我修养”》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lishi/20285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