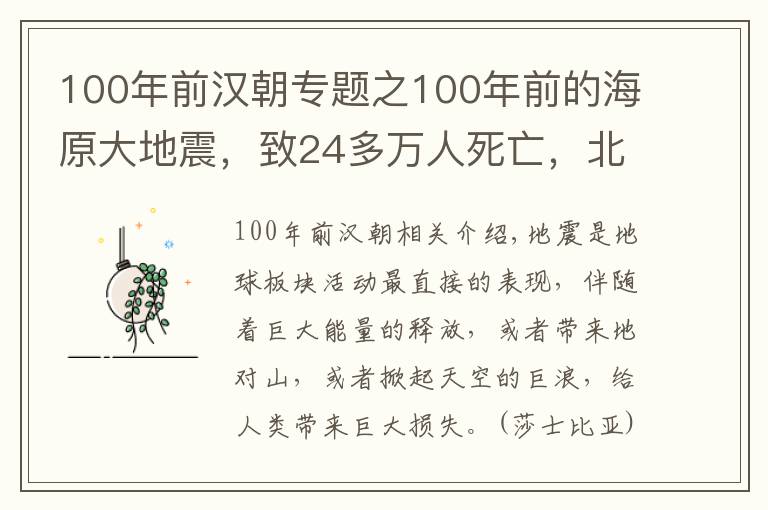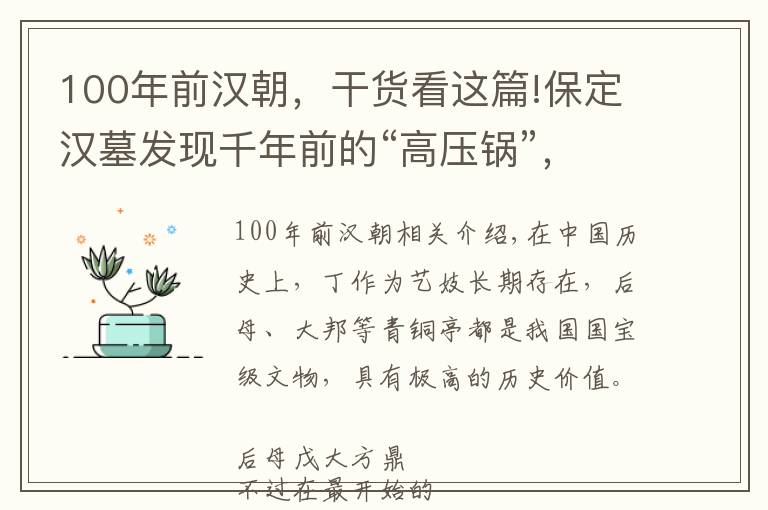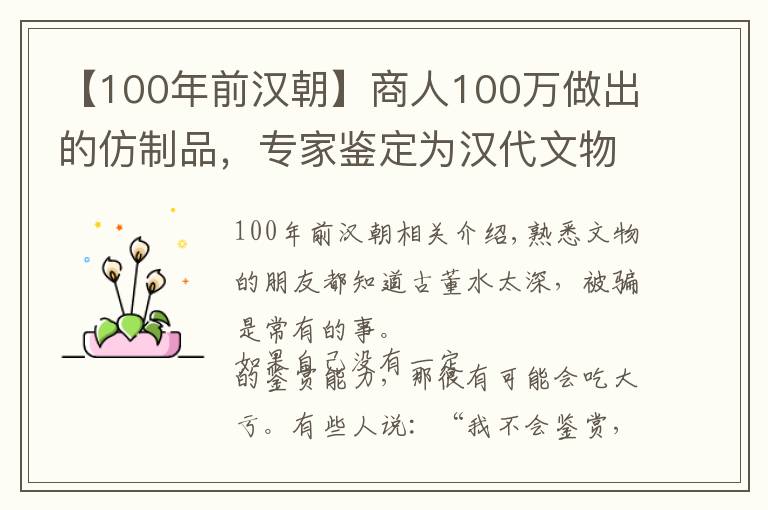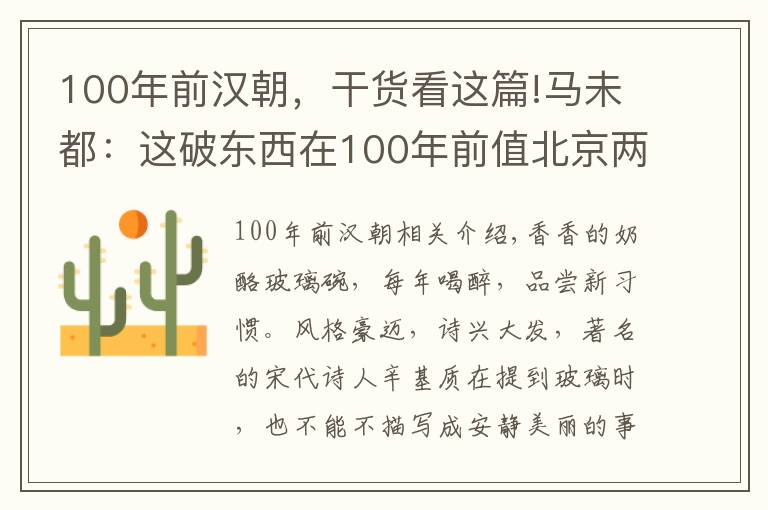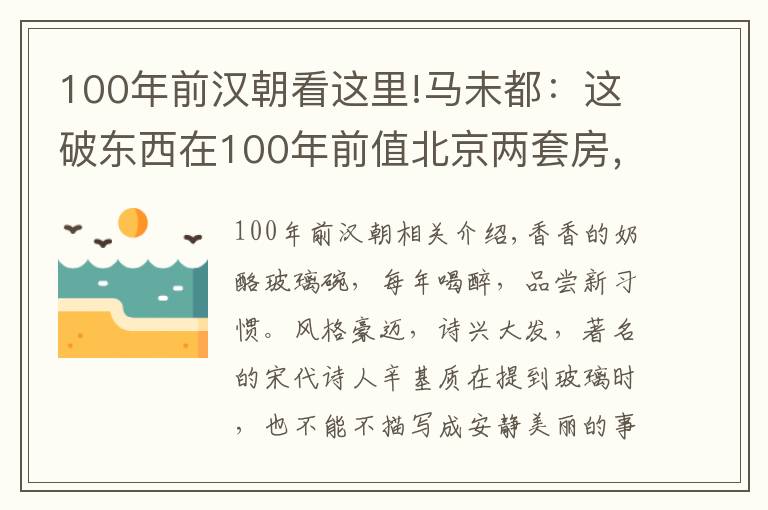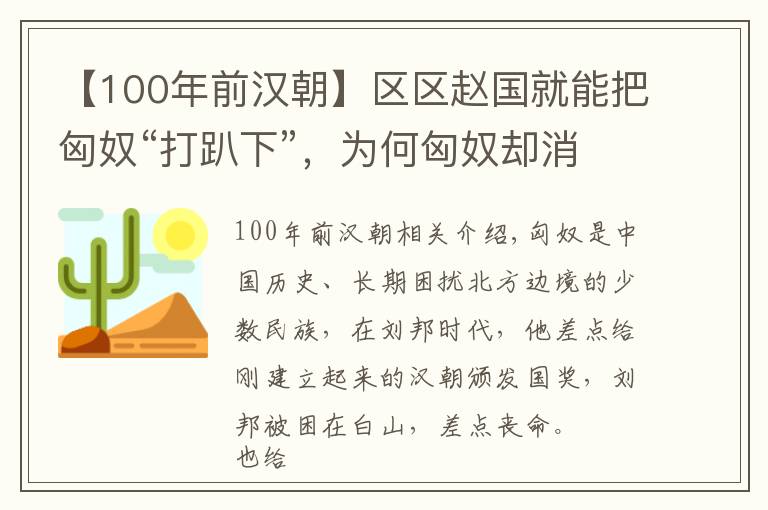西安几个汉代建筑遗址
《文物参考资料》
1957年第5期
编者:西安发现的几处汉代建筑遗址是研究汉代建筑的重要资料,上一期刊登了刘治平同志的文章,现在又刊登了纪永道同志的文章,可供参考。(莎士比亚)。
西安发掘出的三处汉代建筑遗址,対仅代建筑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体会。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先将遗址的现况简单叙述如下:
(一) 西郊大土门村遗址:于一九五六年建厂时发现。遗址在村北二百公尺处,北去汉长安城约二公里,东至西安城约三公里半。遗址中央是一个直径约六十公尺的圆形夯土台,高出当时地面一点九公尺,台的正中又高出一重方形夯土台,高出圆台约一点八公尺。由于晚期的破坏仅保留了很少的一段,因而原来方台上的建筑情况就不得而知了。方台四面各有建筑物,转角用廊屋相联,形成四合式的平面布局,但与门窗一律朝内的四合院建筑完全相反,所有门窗却一律向外。圆台外面是四面等M的院墙,每面约长二百一十公尺。据采査的结果証明,南面院墙的正中有大门一座,院墙四隅有曲尺形的建筑物。院内是否还有其他建筑物,尙有待于进一步的探査。墙外又圜绕一条水渠,圆径约三百七十公尺,渠宽二公尺,从出土遗物証明,与院内建筑确属同期遗迹。
四合式的一组建筑物,以西面的保存最为完整。室内分为三层,最外层是面阔八间方砖地面十字缝铺庆,外檐柱础为方整素平的靑石制成,无外墙的痕迹,似为敞廊;中层面阔改为五间,烧土地面,隔墙用单层土坯垒砌;最后一层为狭长的暗室,似为通往方台上的楼梯间,后墙与方台紧临,用双层土坯垒砌。南北两面大体与西面相同,只-是室内分为两层。个别性础用大块不规则的汉白玉石制成,上部打磨得非常光平。北面外檐有一点墙面抹灰的痕迹,与酉面完全敞开的做法不同。东面已毁,只余十几个柱窝,由分布情况来看,与西面的平面完全对称。(参阅本刊今年第三期九页图十)
(二) 西郊曹家堡的遗址:在村西南约三百公尺,北去汉城三公里,东至西安城约五公里,与大土门村遗址遥遥相望。据采査结果,知道遗址的外墻为正方形,每面约长二百七十公尺。现在已发掘的只有南面的一重大门。仅就大门的规模即可推断这个遗址的建筑规模是相当可覗的。大门长约三十公尺,寛约十四公尺,正中门道两旁为长方形夯土台,台外表有柱窝,可以看出每个夯土台的外表附有木柱。面阔五间,进深七间,每间的尺寸很小,由一点八——二点六三公尺;门道正中有门限的遗痕,门道前后各有不规则形状的两个柱础;门四周围铺石子路。门左边的夯土墙上还另开一个小门,距大门最多不过五公尺远。这座大门的形制与沂南汉墓画像石所刻的一座有些近似。(参阅本刊今年第三期十页图十五)
(三)北郊草滩区阎新村遗址:在村西约二百公尺姓。整个建筑群都筑在一个长方形的大夯土台上。现只淸理了东边的J部分。遗址情况相当复杂,共有四时期的遗存物,最上一层已挖掉,下两层尙未发掘。现在露出的是第三层,据陕西省文管会负责同志谈,根据出土遗物鉴定,第三层当为汉代遗址,主要保存的有两个小房子。东边的一间四面为夯土墻,地面夯土用圆头平夯夯制,夯窝圆径约八公分。西边的一间在北墻东端开门,西端开窗;东南隅有陶炉一个,有陶管与墻上管道相通,墻上管道砌在墙的里皮,应是一个取暖的设备;在北墙的窗内用陶圈砌成一座小井,下面用直径约十二公分的陶管通往室外低处,陶井制作颇精致,不像汚水池,有人认为是一个冷藏窖或是冷风设备是很有可能的;室内吊方砖十字缝铺厦,砖块大小与大土门村遗址近似。遗址的南面有一部份方砖地面和两条汚水管道,方砖外面还有甬道的砖牙子两条,原来建筑物的形象已不易看出。上述小房子中的设备若果如大家的推测,这将是我国建筑史上暖气和冷藏设备的最早例証了。
以上简单介绍的三处汉代建筑遗址,前两处,由其规模看来,都是属于公共建筑物中坛庙之类的建筑;后一处应为当时的高级住宅。通过这次勘査,使我们对汉代建筑的平面布置、结构、工程技术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兹将我们的一点体会介绍给同志们参考:
一九五四年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的一组建筑物,使我们了解到我国古代建筑平面布置的基本形式——四合院,在汉代已经形成。大土门村遗址的发现,更以实际例証说明了这一事实的存在。此外平面布局的中轴线,左右均衡对称的原则已是被广泛的应用着。
古人当说“高其台谢以鸣得意,,这次对于台的槪念更加明确。大土门村遗址的中央建筑群,都在直径六十公尺的圆夯土台上,高出地平一点九公尺,埋入地下约一公尺,上层方台若不破坏,夯土台的总高则应在六、七公尺以上。突出的是阎新村的遗址,整个住宅的建筑都建在长约一百多公尺、宽约六十公尺的大夯土台上,自第三层遗址地面至台下皮高约三公尺。细察其建筑物四面夯土墙的层次一致,绝无用板或木椽分段筑打的痕迹,所有柱窝都是在夯土墻上挖出,这种施工方法很明显的是先在建筑地址按整个所需面积筑打一座高高的大夯土台,然后再按照平面的布置挖掘出室内的空间,留出墙壁再挖柱窝及汚水管道等设施。简单的说就是在一大土堆上开挖出一座建筑物来。这种巨大的劳动是我们以前很难想象到的。
由于木构部分已毁,梁架的结构已无法详细知道,仅就残余柱顶柱窝的位置还能略知其槪况。最特别的是大土门村遗址每座建筑物的转角都用两个柱顶石,石上的柱痕表示出是用两柱角柱相错安置(也有用一块大石上面有两个柱窝的),这样结构就是转角处垂直方向的两根梁分别搭在这两根角SLE,可能由于当时工程技术还不足以解决转角处的复杂结构,但这种做法在规模较小或是单间的建筑上不见使用,是否由于某些典章制度的限制也未可知。
墙壁只有夯土墙及土坯墻二种,未发现砖堵。土坯墻的砌法相当规则,墻皮抹灰分为三层,底层似麦秸泥,中层为草泥,面层为极薄的白灰(?)。抹擦平滑,比之现代的抹灰技术毫无逊色。三处遗址的方砖尺寸皆近似,长宽各三十四公分,厚为四.公分,都是十字缝铺塡,砖缝平直,砖外四边有明显的磨擦痕迹。(只是磨平。与淸代通用的砍磨方法不同,淸代的砌磨方砖是将砖的四边斜砍后再磨光棱角。这里只是平磨,碑缝可以密合。)汉白玉石柱础的表面打磨得非常光平。石子路的锦坛也很精致。从以上所述这些细部结构的处理,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当时的建筑工程技术水平已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这些资料应该成为我国古代建筑遗产中极珍贵的一部份。
1.《100年前汉朝,干货看这篇!西安的几处汉代建筑遗址》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100年前汉朝,干货看这篇!西安的几处汉代建筑遗址》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lishi/20794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