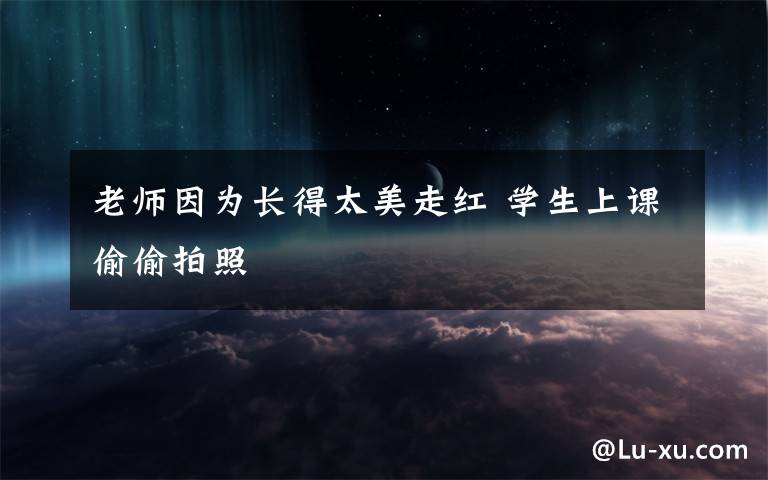2018年10月,同学们群情激奋,“如东中学80周年”成为热点。我无法参加活动,但幸运的是,我可以从我前面同学转发的视频和县里的微信官方账号中,见证和感受到校庆的盛况。
“在平淡的生活中,人们忘记了自己,觉得自己融入了社会;当世界沸腾时,我发现自己很孤独。行动的空隙被言语填满。我想写几段作为我作为一个乡下人的感受。这种感觉甚至有些骄傲。
时间可以带走很多东西,却带不走1988年到1991年在县城的美好回忆。我以微弱的差距没能达到中小学的年级线。还好我生气的时候考上了县,因为我曾经听说“进了县中门,就是秀才”。
从施甸向东到挖港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如泰运河水位离河岸越来越近,挖港快到了。
县城大门面向操场,朝东,牌子上写着“如东县高级中学”和“如东县晶体管厂”(一家生产黑白电视机的校办企业,年利润10万元)。学校大门南侧是小商店和理发店(小商店主要卖零食和文具,店主和他的妻子说着一种我听不懂的军人家里的方言),而里面是值班室和接待室。进入校门后,沿着一条砖砌的道路,可以看到一座山墙,斗达的校训上写着“勤奋、纪律、现实、奋进”八个字。
学生宿舍有12张床,有上下铺位,门口有一个下铺放行李。宿舍门中间有一个方孔,是管家用来检查和观察卫生的。通常是用毛巾或者袜子堵着。
伙食费每月18元。高一在平房吃饭,八个人站一桌吃饭。经常有大肥肉,豆腐块,青菜配青虫,营养基本够用。
高二的时候,益仁堂落成,成为全校食堂,大大改善了环境。之后还要排队吃饭。我和张剑锋一起工作。平时他做饭,我做饭。张剑锋家在迪岗附近,妈妈经常带熟鱼来宿舍,比食堂的荤菜好吃多了。
一人堂的餐桌折叠后变成椅子。高一50周年校庆在怡仁堂举行。每个学生都收到了一本厚厚的如东中学50周年纪念手册,了解了如东中学的光荣历史。手册附录里的校歌是“黄海之滨的海滨城市有一所美丽的如东中学...抗战的篝火映着红色的校旗,自卫的炮火促使新生向往自由。”
怡仁堂北侧,有一个月牙形的池塘。河上蜿蜒的走廊通向角落精致的不知疲倦的亭子(亭子周围有带靠背的石凳)。走过庶人桥(县书法家张德斌题字)是一座精致的小花园,园门圆,假山一人多高。草坪很好。它大约是这个县最美丽的地方。
招生那天,穿着黑色运动服的班主任王云给我们做了指导。五班很多人超过了中小学的分数,甚至有几个超过了600分。似乎人们不会高估对县城的任何评价和殷切期望。全县教学条件相当好,实验楼(物理学家关校友题词)可进行物理、化学和微机实验。高二的时候,在五班教室旁边新建了一个图书馆(社会名人褚图南题字)(我们忍着施工时的噪音)。图书馆是县城最现代化的建筑,附近有两座汉白玉雕像(记得基座分别叫勤学苦练)。
县城的老师是县城最好的,很大一部分是从镇中学调过来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大学生,他们大多接受过权威教师的专业培训,学术造诣高深,专业水平高超,教学基本功扎实。三年间,数学老师乔海燕、蔡、,物理老师王芸、、侯、、马伟,化学老师,语文老师,英语老师李凌、陈健,生物老师韩登峰,政治老师吴广庆、陈健(老),历史老师秦霞,体育老师臧慧明等。,都是认真负责的,可以称得上名师了县上的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都是普通话授课。上课害怕提问,因为不会说普通话,发现自己的施甸话好像没有迪岗话好听。
初三的教室集中在一排平房里,从西到东五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在平房的走廊里,指导主任、年级组长、班主任等。经常在巡逻,晚自习(10点结束)和晨读(6点开始)也不例外。平房附近的自行车棚是班主任于建华讲课的重要场所。平房西侧山墙上的白油笔是用正楷写的,公布了上一次高考录取名单。左上角从北大和复旦开始。
我们的选择,选择了我们。最大的选择是填报志愿(高考前),接连发生了几件事,决定了我的选择。学校组织徒步,步行参观全镇部队,观看士兵内务和训练,一个戴眼镜的少校做了演讲。劳动模范王霞芳在怡仁堂演讲。讲座结束后,我有幸参加了小型研讨会。他大约六十岁左右,身材高大,穿着草绿色军装,解放鞋和一顶五角星软布军帽。前毕业生张小曳身着草绿色军装来到县城,向大家介绍了复旦大学南昌陆军学院大一新生的感受。他的演讲水平几乎可以和范志进书记媲美。
天气开始变热的时候,二炮工程学院的一个瘦骨嶙峋的队长来做招生宣传,穿着短袖卡其布军装,从一个巨大的旅行包里拿出宣传资料。在县城组织填志愿的时候,化学老师毕成先生给了我一封空军校的白色推荐信,告诉我填完这张表到了本科线就可以去这所军校了,强调可以免除我所有的学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想用她来寻找光明。多次穿军装的人在眼前晃来晃去,还有毕老师的关键信息,我下定决心,一锤子买卖的抉择——
从此我一辈子都依附于军校。
与其说是在县城读书,不如说是在那里长大。贫穷能激发人的潜能,却不能给人好的品格。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县里的性格培养科目确实很多,除了邀请那些穿制服的来学校。
县里出版的《绿岸报》大多是师生的作品,我记得主编叫姚。
每个班也编自己的报纸。学生用A3格式的纸手写画画。我曾经抄过一期的短文。晶体管厂厂长(大概姓李)去上课请电工,带了仪器和耗材到现场焊接引脚,林也去主席台上做了一些操作。刘亚佳用BASIC语言举办了一个微机编程实验,讲解赋值语句和循环语句(我完全看不懂),指导学生编程和显示函数曲线。
学校组织散步参观通用机械厂,师生坐在地板上。厂长(记得给王大海打电话)介绍了工厂的发展,说有些产品出口到澳洲。县域在国旗下举行的演讲通常都是主旨演讲,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李兴元和范志进,一个是关心稳定,一个是慷慨激昂。
学校大门的东面是一条石街,两边是平房式的门面。晚上同学拿着热水瓶去石头街上的柴火灶(一对老夫妻开的)开水。大勺子把热水瓶灌满开水,挺巧的,挺像初中课文里卖油的。县城也有一个开水间,在校园西北角,但是那里打水的缺点是热水瓶容易破。
石板街,分为南街和北街,我去过很多次。县城附近的北街熙熙攘攘,两边是衣服、鞋子、锁和儿童读物。整个石街区都是平房区,南北小径也铺着石板,纵横交错。
沿着北街向东走,到达觉岗镇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向北是大会堂,一直向南,过桥到觉岗汽车站。学生一个月回家一次,大部分从这里上车。如遇节假日,需提前购票。汽车站候车室是朝东的平房。道路的东侧是一个霸道的小上海店,有一个大工厂(像纺织厂)。
在汽车站的南侧,有一家叫烹饪香屋的高档酒店,然后向南到达城市边缘。有一段时间,我看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长途大巴上挂着横幅。当时不知道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大事,窗外什么都听不到。
我对当时香港的挖掘很熟悉。有一次期中考试结束,晚上和耿一起去香港挖地,走了几个小时,大概半夜才回到宿舍。2018年下半年,我去迪岗做生意。我的学长朋友,那条狗,热情地载着我在迪岗街逛了一圈,竟然走过了很多不熟悉的街道。没有旧汽车站的痕迹。西沟是施甸人,但我很佩服他说的是地道的挖港方言。
一切都不是时间的对手,美好的事情都会过去。2011年,朱明、孙国民和毛郭萍等人及时组织了5班20年毕业晚会,我也参加了活动,县上的老师也接见了同学。变化是唯一不变的东西。县城变了。已经搬到了南方的香格里拉路,这是一个高端大气的名字。新校门气势磅礴,宽度是以前的三倍,校门没有小店,也不会有石头街。
历史不主持正义,只主持辩论。三天修完全部七门课,百度现在知道,91年高考录取率是历年最低的。特别是当时的考前淘汰制,让考前不再是热身和锻炼。我们对高考的政策和规则一无所知,认为“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1991年7月,南方各省多次降雨和洪水。我们离开是为了下一次再见,但我们不擅长说再见。毕业时,面向南的校门刚刚建好(书法家陈大羽写了学校的名字),水泥路面还没干,还铺了芦苇垫。毕业照是很久以前拍摄的。大家都留了家庭地址,以后互相写信,关系比较近的同学也会说一些事情。
一个月后,我去县里检查成绩。不知道怎么进的老师宿舍(他宿舍在学校南边的围墙里面)。1991年的高考单也会用正楷抄在初三平房的山墙上,虽然我没看到。除了给我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县里还给了我一些分数,涵盖了性格刻板印象,待人接物,思维习惯,科学知识,以及毕业生在县里的身份。在我看来,不管你上不上大学,班里所有的学生都留下了这个印记,这是我们赖以联系和信任的纽带。这种标记对于每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都有很大的价值,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我的学习智商平平,很多知识点和问题我都很难理解。为了弥补智商上的不足,我注重学习笔记,整理问题书。后来这几捆东西被一个叫于红(我侄女)的人拿走了,那天我不在家。还好我的毕业证和准考证没有被顺便拿走,至今保存完好。
就过去而言,就未来而言。我家离挖港很远,每次回家的路上都没有车,很少有机会挖港。天空中没有鸟的痕迹空,但我已经飞过。全县已建成五星级高年级名校。八十周年纪念时,赞·郑智发布了他专门在老县城拍摄的照片,让我们觉得过去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尽管我很清楚世界上没有宴会。

笔名:阅读器
征文:散文、随笔、小说、诗歌等。,一般在4000字以内。必须原创,必须入手,有插图和配乐,当然更好。如果20天内没有收到稿件信息,可以转到其他媒体。自负。
1.《如东中学 我的如东县中学记忆(1988-1991)》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如东中学 我的如东县中学记忆(1988-1991)》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shehui/12843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