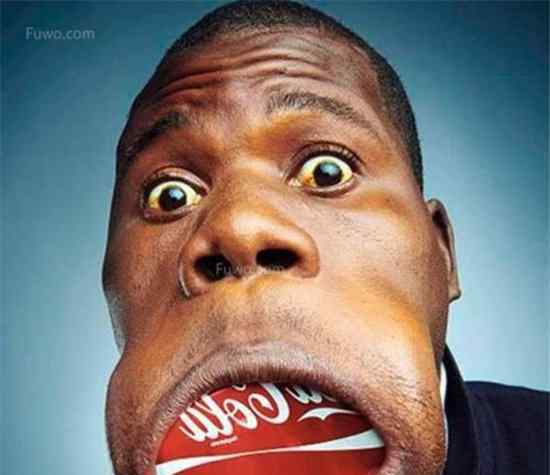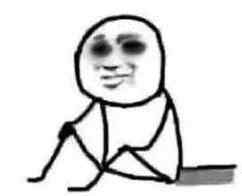爱、性和残疾
本文选自《中午5点:有人送我西兰花》
采访和整理|胡文彦
残疾人也有生理需求。但很多时候,他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在法国,残疾人的性欲仍然是一个私人的少数民族话题。性伴是野领导,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卖淫还是赡养?志愿者活动还是收费服务?你是真的做爱还是只是做爱?很少有人能解释清楚。
促进性住宿协会是法国第一个促进残疾人性陪护的协会。它自己培养性护士,同时为残疾人和性护士匹配爱情需求。通过协会,我们联系了三个性工作者,两个女的,一个男的。下面是他们的故事。
第一,“我想做爱”
口头|吉尔·努斯
女,32岁,住在斯特拉斯堡郊区

1.
2011年,我还是应召女郎。没错,我在普通人眼里就是个妓女。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一上来就告诉我,他是残疾人,四肢瘫痪,坐轮椅。他建议我们最好通过skype见面。提前让我了解情况再回复。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不知道残疾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有其他特别的想法。但是这个人住在格勒诺布尔,我在里昂,一个小时的车程。我非常担心如何去他家。终于,我顺利到达。
他住在郊区的独栋房子里。护士都走了,他一个人在家。他挺独立的。第一,他欢迎我,和我聊了一会儿,互相了解了一下。中间他让我倒水给他喝。后来他让我把他从轮椅上抱到他旁边的沙发上。他不能脱衣服,不能穿衣服,当然也不能手淫。渐渐地,我渐渐意识到,是的,他是残疾人,不时需要帮助。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
我有很多无知和偏见。我以前认为四肢瘫痪的人不可能有知觉。事实上,他的腿瘫痪了,但他的大腿向上一点,他有意识。当然,他每次都做不到,有时会反应,有时不会。但他有性欲,能理解,能让别人开心。
和他做爱是复杂的,不是兴奋、勃起、插入、射精等。马上就好了,所以你要有耐心。后来他来看过我几次,有时候要等很久。我在那里等他,他告诉我有性工作者看到他没有勃起,马上转身离开了。
我认识的很多妓女,看到坐轮椅的人,就好像看到怪物一样,会吓到,喊不不不不,直接拒绝。其他人会在自己的网站上表示不接受黑人、阿拉伯人或者肥胖的人。看到这个我特别震惊,但是怎么说呢?每个人的底线都不一样。大家提前解释一下可能有好处。有时候这么直白不一定是坏事。
即使是普通客人,他们也大不相同,有些小,有些胖,有些金发,有些秃头...反正我无所谓。这些都是细节。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例外,残疾只是其中之一。
但是那天我特别震惊。我陪了他一下午,没多收一分钱。
那次见面后,不知怎么的,我开始在网上打一些关键词,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然后我修改了个人网站,强调我同意接待所有的客人:男的,女的,残疾人,健康的,漂亮的,丑的,我对自己的长相没有任何阻碍和限制。
后来我接触到了——SEPH,一个瑞士的促进残疾人性生活的协会,接受了一些相关的培训。在瑞士,性陪护是法律认可的,是真正的职业。性工作者拒绝接吻,也不会和客人有真正的性交,但这些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我可以做到。
不是我不在乎,只是我喜欢人。所有的身体都很美,裸体或者裹着金衣,残废或者健康,黑或者白,甚至是绿色,哈哈哈,都很美。比如一个人是胖是瘦,但是标准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用胖和瘦这样的形容词来定义一个人吗?即使这是真的,那又如何?
每一个身体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是伴随着生命的故事,传奇的经历。各种喜怒哀乐都藏在他们的皱纹里,藏在他们的瞳孔之间。我知道,面对一个人,不是一张皮。我的判断就这么简单。只要一个人和我一样,没有什么能让我恶心。
第一个客人和我很久没联系了。两年前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有女朋友了,很开心。当他和女朋友睡觉时,他不会感到紧张和害怕,因为他知道如何给予和享受性快感。
2.
就这样,我做了一年半的性陪护,接待了十几个残疾客人。
有些人在事故前有健康的生活,事故后坐轮椅,在脐带和脚趾之间活动,没有任何知觉。性器官突然衰竭,不知所措,失去生活中的性经验,很痛苦。我的工作是和他们一起探索、发现和学习其他感官体验。
性分为多种形式和层次。开放性观念很重要,各种既定模式要打破。健康人做爱的时候会考虑哪个位置会更好。有一天你失去了性功能,你该怎么办?要知道,性生活并不局限于生殖器层面,通过爱抚会有快感。
有一次遇到一个客人,和法国电影《Intouchable》里的残疾英雄很像,他所有的感情都是靠摸脸得来的。他的性快感体验有些错位。我抚摸着他的脸,额头,耳朵,他激动得一下子变得疯狂起来,开心得比一个健康的人经历得强烈得多。如果有人这样摸我,我会觉得挺舒服的,挺好的,但是对他来说,有一种力量可以引起塌方。

在电影《遥不可及》的剧照中,白人富翁菲利普瘫痪在床,黑人Driss是他的专职陪护。
的确,残疾人的性生活和性欲望很差,但其实他们的第一欲望是情感和关怀。
我遇到的这些人,一般早上都会有护士或者按摩师过来,他们是接触最多的医护人员。白大褂、白口罩、橡胶手套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背景。他们赤身裸体,彼此都穿着衣服。当你想到整个画面时,你会觉得相当不平衡。
对他们来说,经历一点温柔和爱是一种奢侈。有的人在医疗的机械环境里呆的太久了,忘记了这些温暖的感情,能有一段平凡的美好时光已经很满足了。我经常收到类似的请求:他们不想发生关系,只想脱下衣服裸睡和我在一起。
瑞士人把这种工作称为性治疗,在法国不流行,我非常喜欢。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对他们表示善意、同情或怜悯,完全不是,我们只是想关心和照顾别人。
我做过妓女和性工作者,我知道他们不一样。妓女的工作就是简单的尝试各种姿势,和你做爱,回应你的性幻想。比如我会和很多客人扮演角色,但是性陪护不会有这些服务。是帮助残疾人重建性生活,在以后的性关系中主动而不是被动。
我当妓女的时候,很多客人都爱上了我,发誓要把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我在做性工作者的时候,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其实我做的这些都是自愿的,并不是被迫的。
和正常人不一样的是,我经历过很多事情,睡在大街上,逛过俱乐部性交或者交换性伴侣,然后自告奋勇去做应召女郎。现在结婚了,投身佛教,注重个人和精神建设,生活特别平静有条理。
3.
2012年的一天,马塞尔·努斯联系我,说巴黎有个绅士想得到性陪护服务,问我能不能过来。
之前在网上搜索过关于性陪护的信息,马塞尔努斯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名字。他从小就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他13岁辍学,开始了自学生涯。现在他已经出版了几本书,包括小说和散文,尤其是他2012年的自传《我爱》,在全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他加入并成立了许多协会,并做了大量工作来促进残疾人获得性权利。
那时候他只是个媒人,我们的关系本可以到此为止。后来我们保持联系,聊了很多,彼此一拍即合,写邮件,通过Skype视频聊天互相交谈。当时我27岁,他57岁。像两个孩子一样,我们畅所欲言。
那年年底,他提出让我去他家,让我住他的客房。很有趣。去过别人家,没在客房睡过。我问能不能和他睡,他没拒绝。后来,我们在一起了。我搬到了他在阿尔萨斯的家。
2013年,我不再做应召女郎和性工作者。
当然也有人说我坏话,说这个女人恶心。她以前是个妓女,现在嫁给了一个比她大30岁的重度残疾人。谣言很多,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了。我32岁,仿佛活了几代人。我总是接受和承认我做过的事,我知道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没事。
我们成立APPAS协会是为了培训性护士,做实事,而不是像一些专家那样多说话少做事。该协会是法国第一个促进残疾人性陪护的协会,它为有需要的残疾人和性工作者提供服务。我是协会的秘书,负责联络工作,建立残疾人和性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也负责筛选性工作者候选人,看他们能否参加培训。
2015年3月,我们举办了首次性工作者培训。六天时间,邀请了德国、瑞士的性学家、律师、整骨医生、性护士进行讲解,让大家从不同角度了解性陪护。在性工作者的培训中,大部分人都是做按摩、医疗、心理咨询的。他们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身体和性欲,让自己在这条路上有所作为。性工作者只是一小部分。
性工作者花钱培训,他们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然后从事这个“职业”。所有的工作都应该有报酬,所以他们收钱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我认为残疾人的性陪护费用不需要社保补偿。很多健康的人性生活很差。你觉得,这不是病,不是缺陷,不应该有什么医疗保险。
一般我们建议一个半小时150欧,另外客人需要为性工作者支付额外的交通费。有些护士会要求更高的价格,客人也给了我们反馈,说这根本不能接受。我们没有坚持,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在瑞士,每小时120瑞士法郎。所以,我们建议的报价是合理的。残疾人的情况非常复杂。你得负责移动它,弄清楚他的身体是怎么工作的。一个半小时肯定不够。其实每次有性工作者陪伴,她都要花一个半小时以上。
除了写信,很多残疾人在Facebook上和我聊天,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账号的。他们和我打字聊天,毫不犹豫的聊起这些性话题。因为性教育不多,他们对性了解很少。他们看成人电影,跟我说他们绝对不会那么演,一直说做不到。
这个时候,我要一遍又一遍的说。事实上,没有人像洛可·希佛帝一样。他演成人电影,不真实,正常的性关系不是那样的。每个人的性欲和性能力都不一样。就算和同一个人发生关系,也不会每次都是这样。
总的来说,要保持开放的性观念,让生活中有更多的可能性。
第二,我的五个女客人
口头| Fabrice Flageul
男,52岁,住在里昂郊区

1.
本人52岁,已婚,有一个三岁半的女儿。他出生在诺曼底,在定居里昂郊区之前,他搬了无数次家。
我做按摩。现在想来,二十五年前我接待的第一位客人,就是一位残疾人。他的胳膊从小就不发达,结婚三十五年,他老婆也没碰过他的胳膊。我轻轻地按摩和拍打,从头到脚,一直到我的胳膊。他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安慰和快感,就像重生一样。当时我就知道,按摩,哪怕是简单的按摩,都能给残疾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舒适感。
平日里,残疾客人不多。但是有时候我被一些公司委托接收残疾员工。
我的工作是密切接触人们的身体。如果你访问我的网站,你还会看到这个,叫做“按摩坦陀罗”,也就是通过按摩,你会带领你的客人踏上一段性感体验的旅程。妻子是性治疗师,她也治疗有性问题的个人或夫妇。
我就在这条路上,希望能走的更远,帮助那些有性需求却得不到的人。况且和我一样,年轻的时候性生活很差,过着悲惨的生活,完全理解性饥渴的痛苦。
2015年,老婆告诉我APPAS举办了第一次性工作者培训,知道我肯定会感兴趣。
在普通人眼里,我一点都不“正常”。我们是夫妻,也是很特别的一对,一直过着放纵开放的婚姻生活。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谁。我决定做一名性工作者。没人大惊小怪。
家人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是最了解我的妈妈是我爸,有点震惊。当然也怪我。之前没跟他提什么,故意想恶搞他。有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我,没看懂,觉得儿子要当鸭子了,接受不了。听了我的解释,他表示理解,说性陪护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在法国,个人卖淫合法但不道德。在普通大众的生活中,道德判断比违法处罚具有更深远的影响。拉皮条是违法的,也就是说APPAS的工作虽然是志愿服务,但是会被贴上拉皮条的标签。该协会梦想有一天被送上法庭,这将引起公众的关注。
可惜没人起诉我们。
2.
培训结束后,几个月没人来找我。这也很正常。与男性相比,提供性陪护的女性要少得多。具体来说,要求性陪伴的人中95%到98%是男性,其余是女性。我们的生活不也是这样吗?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样坦诚,说自己需要性,渴望性。女人谈生理需求,总是遮遮掩掩,甚至讳莫如深。但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
暑假过后,几个客人通过APPAS陆续来找我。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一共接待了五位客人。他们是常客,有的见过一两次,有的见过三五次。有的人天生残疾,没有参考系数,感觉不到一些冲动和刺激。但是,后天残疾的人就不一样了。出事后,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有无体验特别真实,痛苦会相对更大。
一位客人脊柱受损,下身残疾,但她相当独立,可以坐轮椅自由活动。
另一位客人,65岁,三年前在非洲得了疟疾,被迫截肢,失去手脚,非常痛苦。以前的她,风情万种,生活多姿多彩。事故发生后,她没有遇到合适的男人照顾她。一开始她无法接受付钱和男人发生关系,后来她意识到自己没有太多选择。她也试着和一些老人交往,但是她的残疾有时候会把人吓跑,她也不想和一个残疾人发生关系。
残疾人不想和残疾人发生关系。普通人听了会特别惊讶。人们觉得和对方发生关系那么正常,为什么总想着和健康的人发生关系?我们一直聊到后来才知道,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性欲充满了完美的酮体。
一个客人31岁的时候出了车祸。他瘫痪了,经历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我经历过一个健康人的生活,很纠结花钱和一个男人上床。现在她45岁了,无法抗拒失望和孤独,她不得不这样做。后来她很开心,很自信,整个人容光焕发,开始想着吸引别人。她最近谈恋爱了,希望这次能管用。
这样做,也是在帮助她们重拾女性自信,从容向前。本质上,这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性关系。我们关注的是心理重建,这和花钱买性是不一样的。想想我们花在这上面的时间。性陪护赚不了多少钱。我做按摩,客人打电话预约。一个半小时收150欧元。但是性陪护每次见面前后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另一位客人在6个月大的时候被发现患有脑瘫,严重残疾。除此之外,她特别强壮,体重增加了100公斤,这很难操作。她可爱又敏感,可惜我们不能做爱。她的身体损伤如此严重,以至于她的腿总是在颤动。我们试了几次,但都失败了。她只能摸我和我的小弟弟玩。他们之间的交流更感性。在所有的客人中,她离我最近。
但是,当我收到她的短信时,有时我会故意不回,希望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她已经45岁了,但是在那个心理年龄——有时候我觉得她就坐在前面。她的一生是一部与痛苦抗争的历史。知道了这些,你会感叹说:哇,难以想象。10年前的我没有现在的我成熟强大,当然也做不到这一点。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位客人。她天生脊柱裂,性生活非常活跃。她总是在网上找男人,希望一直有性生活。但是我在网上发现的并不是很严重,对她也没有表现出尊重。这些人有些是出于好奇来找她的,但做完就走了。她不喜欢,就通过了协会,希望能找到一个对她好一点,尊重她,关心她的男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欲。有的人比别人厉害,很难满足自己。这其实很痛苦。其实我特别理解她,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不仅仅是坚强,我渴望在生活中得到很多性。现在我老了,好了一点。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不能及时行乐,痛苦的要死。现在还是后悔。
我还答应帮两个同性恋情侣做爱。早些时候,里昂的一个残疾人研究中心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忙。他们身体残疾,不能自己做爱,需要别人的帮助,但不希望有女人在场。我不是同性恋,我不能接受和男人发生关系,但我可以帮助他们做爱。当然我没有直接介入,而是通过按摩辅助。我正在等他们的电话。
3.
在会见客人之前,我们会聊很多。这和卖淫不一样。嫖娼,客人打电话,约好时间地点,不用说太多。但是见面之前要通几次电话。如果可以,我们最好先见面谈谈。
住在里昂的那个,我们提前见过面,足足讨论了一刻钟。她想了想,想了下一步,约了性陪护。如果客人住的太远,就不能这样见面。但在此之前,我们至少要打五六个电话。如果她有什么期待和幻想,一定要跟我说清楚,让我知道自己有没有满足别人的能力。
不像女人,小哥哥随时都不能勃起,这也是风险之一。见面之前要说清楚。APPAS协会也告诉大家,性工作者不必强迫自己。有些人会为此吃药,但我不能。我崇尚自然。如果没有性向,说别的也没用。幸运的是,直到现在,这种担心从未发生。
成本是个大问题。两个小时150欧元。此外,他们还要支付我的往返交通费。我每次陪他们三个小时,总是比预设时间长。这是专业服务,不是个人情感,所以要付出,要自律。否则对方会有不正当的情感期待,一码不归一码,没办法澄清。
在工作日,他们很难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有两位客人,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期待。这时,我和他们聊了几句,打开天窗,然后大家就能明白了。况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所有的情感都值得珍惜。
我喜欢在治疗开始前就结账,做事也不用提钱。他们可以分期付款。比如我会先收到他们的三张支票,但是我隔一个月兑现一张,三个月后就收到了。这样,他们在经济上更容易被接受。普通的卖淫,从来不会这样。
我之前什么都说了。见面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互相联系,聊聊我们的生活。我和我的客人都很想认识一下。性工作者和客人之间应该很少有这样的关系。
但有时候开场白很短。比如我的第一位客人,她渴望的只是性交。她特别不耐烦,不想等。聊了一会儿,她对我说:“我们开始吧。”。整个过程太快了,我很惊讶,觉得太搞笑了,但是回头一看,没错,我们就是这么去做的。这位客人只有一个疗程,并不代表她不想再来找我,但我不能每次都同意她的提议。
我们脱了衣服,在床上裸奔。先按摩,慢慢进化,慢慢推进,但这种事情的速度因人而异,因性欲而异。我无法提前预测进度。每种待遇都不一样。
有时候,他们只是想爱抚,享受我的手或嘴带来的刺激,抚摸我,捏我的小弟弟,不用让我进入他们的身体,他们会特别开心。但在大多数疗程中,他们还是想体验真正的性交,感受男人进入自己的身体,享受这种独特的感觉。他们不仅自得其乐,还特别关注我会不会有快感。挺感人的。
对于一些客人来说,做爱是一种新鲜的体验,而对于另一些客人来说,它可能会唤起他们太久以前的记忆。每次见面,总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刻骨铭心。当然也会有一些尴尬的时刻。有的人身体伤害太严重,不易操作;心理上,你要告诉自己,要超越表面所见。眼前的身体不够性感,会不会激动是个问题。
我不禁担心。有时候,我只能跟着感觉走。
第三,他们渴望性,更渴望关心
口服|纳丁m。
女,50岁左右,住在巴黎郊区

1.
一直以来,我在公共活动中特别活跃。80年代,我在索邦大学读社会学的时候,参加过很多社团活动。我会选择做性伴侣,这是一些女权政治诉求的要求。话又说回来,很多女权主义者反对性陪护,但很少有像我这样自称女权主义者去做性陪护的。
我小时候是女权主义者,我的感情和性,包括不生孩子,不跟伴侣住在一起,都和这个有关。我生长在70年代,是1968年五月风暴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年轻人。那时候性解放如火如荼,我们对性没有顾忌,没有禁忌,结婚了,可以有多个性伴侣。这在当时很流行,社会好像也鼓励大家这样做。后来,世界渐渐变了。现在,和我们年轻的时候相比,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在法国,再谈女权主义有点过时了。我们根本没有成功,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在回头。我是女权主义者,但我不反对男性。相反,我很喜欢他们。
现在的另一半知道我是性工作者,我没意见。当然,我不会因为他不认同我这个性工作者而放弃退让,也不会因为担心他嫉妒而改变主意。
关于我,我只能说这么多。我不想在网上有任何个人资料。信息时代,我想把它藏得尽可能深。
和别人聊天,谈性陪护,都是一个调子。他们非常激动,说:“你们都是伟大的人,富有同情心,喜欢帮助别人。”他们还补充说:“哟,你太勇敢了,我做不到。这样做太特殊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做过心理咨询,对语言表达特别敏感。仔细考虑了一下,觉得这些话背后有着深刻的含义。说白了,每一句话似乎都在提醒你,残疾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太可怜了。对你的认可也是基于这种同情。他们潜意识里是这么想的,没毛病,就是太肤浅了。每次听到这个我都觉得好笑。
之后我告诉他们我要收费。整个气氛完全变了,特别尴尬。他们对性伴侣一无所知,认为我这样做纯粹是“无私奉献”。总之,我的形象一落千丈,突然从“处女”变成了“妓女”。你看,人类是多么矛盾的生物。
在处理金钱和身体的关系时会有一些误解。我也没觉得困扰。如果我在乎别人的眼光,我就不会是性陪护。我会向他们解释的。有的人能理解,有的人固执。没关系,就这样。既然我觉得这是正道,那我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前进。
每个人都有误解。说到底是因为性陪护在法国不是一个职业,不受法律约束,无法与护士、医生、医疗按摩等其他职业相比。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待人接物特别敏感和细心。另外,我有丰富的性生活经验,这是我的优势。但是,如果我上升到专业水平,那是不够的。
所以实际上法国性工作者基本上是为所欲为。比如你能不能实际性交,或者绝对能不能性交,就看你自己了。比如我是不是真的每次都这样,就看我对客人的感觉,还有我此时此刻的状态。
另外,我有两条底线。监护人一定是个男人。再来一个,我就不亲了。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接吻更私密的了。我希望和我的爱人做爱时能保留一些特别的东西。客人打电话给我,我会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们不会期待的。
2.
2009年,我听了一个关于瑞士性伴侣的广播节目。当时法国人对此一无所知,我也没听说过。节目分几个时段,他们采访了很多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残疾人的性陪护问题,比如医护人员、性护士、渴望性的残疾人、性陪护老师,涉及伦理、心理分析等不同维度。
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能说有一点或一个细节让我觉得特别,但整个问题让我明白了。但是看完就这么过去了,不是说我八年前拍了拍脑袋说,好吧,我要去做性陪护,但是没有这回事。它只是一个花蕾,但后来它生根了。
2015年参加了APPAS协会组织的性工作者培训,同时个人生活也有了一些变化,知道自己已经做好了做性陪护的准备。我有很理性的一面。我觉得我的生活是由很多抽屉组成的。打开每一个抽屉,都会看到生活的不同方面,但都包装得很好,层次分明,不乱。
第一次要求从一个轻度残疾的客人开始。他是截瘫患者,大约四十岁,住在巴黎郊区。怎么说呢,我不紧张,你知道,辅导员不是白来的。他很害羞,但他很健谈。我也明白他朋友很少,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生活,最后接触到的是日常生活之外的女人。他有很强的倾诉欲,喜欢聊开心的事。我爱听别人说话,不多问,懂得保持适当的距离。和他发生关系,当然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和我正常的性生活不一样,但不代表有问题。
作为性工作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入来源,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生存。到现在为止,我一共做过十次,大概六七次。记不清了,因为认识了几个人,但是没有陪护。很正常。当你和一些人在一起时,你会感到不舒服。跟他们的残疾无关,跟他们的态度和对待别人的方式有关。
在残疾人中,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人,与健康人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同。不是因为他们残疾,所以特别好,特别温暖,特别聪明。完全不是这样。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傻叉,完全不尊重人,不按游戏规则玩。细节我不能告诉你,但是用“不尊重”这个词就足以说明一切。一聊天就知道自己是喜欢还是讨厌这个人,所以在治疗开始前两者的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电话里,有的人有时候觉得是免费的。他们浏览协会的网站,却不仔细看,以为性工作者都是义务劳动。我必须向他们解释。如果我同意,我会继续谈下去。不同意就挂。
我的收费在150-170欧之间,因为涉及到交通和住宿,比如有的人有房,有的人没有,他要给我交酒店的费用。考虑到这些条件,收费会有所波动。
大多数残疾人的经济状况一般。说来也怪,我接待的这些人中,只有一个人靠残疾人最低保障生活,其他人家庭条件都不错,没有经济问题。我不知道他们的钱是怎么来的,也不在乎。也许他们有经济积蓄,或者继承父母的遗产。
有些人住在医院,有些人住在父母家里,有些人独自生活。他们为什么要性陪护?这是第一次交流中必问的问题。其实大部分答案都是一样的。他们不仅没有性生活,而且缺乏爱和身体接触。他们希望被医护人员以外的人感动,也希望感动别人,得到乐趣。很多时候,他们不开心。
但我不是为了享乐的性陪护。如果他们开心,问我下次还能不能见面,那我会很满足,很开心。
——————
驻法记者胡文彦。
描述:吉尔-努斯和马塞尔-努斯,由让-弗朗索瓦-里克森拍摄。
[相关书籍]

中午5点:有人给了我西兰花
正午故事写作文学|随笔
这本书是《正午》系列的第五本书,选自《界面新闻》的非虚构平台《正午》。
在“特写”专栏里,本期推荐罗的《傻姑娘》,用一个强奸案描述广州一个村庄的生态。《176被告》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荒诞。一个普通的小区,一个普通的建筑,一个普通人被砖头打死。警方调查失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7条,该建筑的所有居民都成为被告。
在“随笔”专栏中,我推荐张莹莹的《植物覆盖上海》,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描述一个城市。本期收录了范的《农民大哥》和几篇风格迥异的散文。
在这次午间采访中,梅峰谈到了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如何打造所谓的“民国”,以及“学院派”的淡与衰,还有他个人的读书史。
其实“个人历史”就是口述历史,挖掘那些被埋没却记忆犹新的记忆。我们请迟迟讲他的脱口秀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幽默的张文。另一篇《爱、性与残疾》,讲的是一个独特的话题,法国为残疾人提供性护送的人。
本期《视觉》是一组非常感人的画面。摄影师高山拍摄他的母亲。
最后,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长故事”。这一期的三个长篇故事一如既往的长而优美。他们是春丽的李旭义决定抢劫运钞车,的西北野孩子和罗的春药内衣骗局。
1.《做性 他们渴望性,更渴望爱 | 给残疾人做性陪护》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做性 他们渴望性,更渴望爱 | 给残疾人做性陪护》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tiyu/8683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