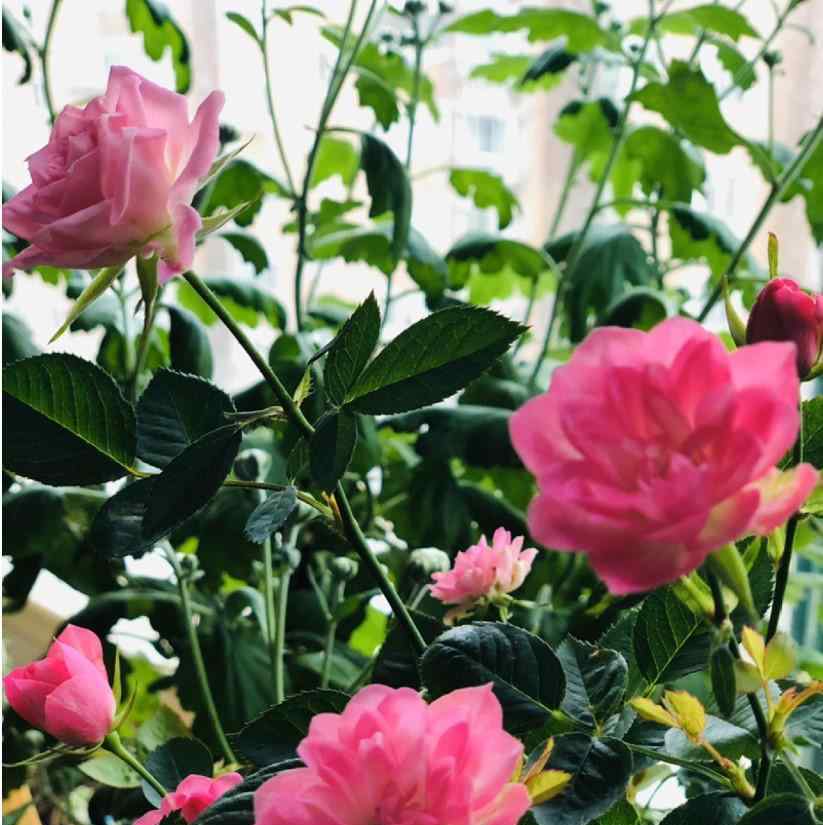上队向西死得早,夜车乱弹好像在找鱼,十有八九十有八九是鱼蜀毒少。
我敢打赌没一个内环线内“原生”的上海人可以听懂这句话,但这句话是正宗的南汇“本地闲话”。
译文
15队最西边那个家伙,昨夜闲聊像吵架似的,痴头怪脑没点正经没点规矩,真是挺讨厌的。
上周末听娄一晨夫妇讲一件趣事:他俩在挪威旅游,有两个中国女孩忍不住追上来问,你们说的是上海话吧……哦,果然不是韩语!而我听到的说法是,因为南汇话有很多浊音,所以它听起来像日语。
事实上即便上海人,特别是“60前”的上海市区人,我相信听宁波话会比听南汇话轻松些。
上海市区人占据经济文化的优势地位,市区上海话自然也是上海话的“标准”。不过有意思的是,据我的观察,只有南汇话和崇明话是市区人开玩笑的对象。我想可能是因为地域的偏远和隔离,让南汇话和崇明话保持了“原汁原味”的乡音。松江、青浦、嘉定、宝山等是文商发达、交通辐辏之地,“土”味不足,而金山、奉贤对市区人来说,心目中的距离又更远一些。
我觉得南汇话的与众不同,可能还来自于南汇人口构成的独特性。南汇是一个依靠盐业发展起来的海滨“新大陆”,据专家考证,古代盐业生产十分艰苦,早期的盐民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从西部临近地区招募来的劳工,二是为躲避战乱迁徙来的难民,三是由官府发配到此的流民和罪犯。元明时期,南汇盐业生产进入高峰,与盐业相关人员大量迁入,并定居下来成为“新南汇人”。如此看来南汇的人口史还挺像像澳大利亚呢。
所以南汇话虽是吴语系,但由于人口构成较松江、青浦、嘉定、宝山等更为复杂,也就更多变化,更难懂了。
如果取笑崇明话“蟹”是一个梗,那么南汇话就是“风(hong)大(du)了邪(xia)啦!”。和一些中年市区人聊天时,讲起我是南汇本地人,经常有人冒出这句“南汇话”,有的人还会加一句“格边边(这边),伊边边(那边)”。大部分人这么说的时候没有恶意,可能是想接近你。他们的发音虽然夸张,但还是标准的。可是南汇人好像从来不说这句话啊!南汇人要说风大,一般就简单说“风邪大”。虽然我觉得南汇话可能是世界上最多语气助词的方言,但在表达风大的时候,真的这么简单。
说到“风(hong)”,还得说南汇话的这个音是相当有古风的,用在古诗里,一些原来以普通话念不合韵的格律诗,立时完美了。如唐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中(zhong)、红(hong)、风(hong),都是东韵。
还有一个乌龙其实是南汇人自己制造的。通常来说,“伲”是标志性的浦东本地人自称,“我们”的意思。报纸电台写农村报道,标题里总要做个“伲”字。但其实稍早一点的南汇人是不称“伲”的,至少我爷爷说“实伲”,说我,就是“实我”,他就是“实伊”。“实”貌似是个无意义的助词,但我听爷爷这么说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一种语言的韵味和质感。从父亲这一辈开始,“实我”“实伲”“实伊”就极少讲了,更无论现在的年轻人。
南汇话是很“啰嗦”的方言。我觉得这其中包含的语言学问题尚未得到科学地归纳和总结。任何一句话,我们不加上一两个甚至三四个语气助词就感觉说得不痛快,或者表达不到位。而这些几乎无规律可循的语气助词,让南汇话成为一门几乎学不会的方言。
比如说“这个女孩真漂亮”,南汇话“迭个姑娘邪趣呃嘛”,“呃嘛”后面还可以加个“嘎”音。再狠点可以说成“邪趣呃嘛嘎索加里!”觉得还不足以表达惊叹,那就在句首再加个语气词“阿妈”(娘哎),还可以加到“阿妈娘啊”,那么“这女孩真漂亮”的顶级南汇话版本就是“阿妈娘啊迭个姑娘邪趣呃嘛嘎索加里”。
所以南汇话听起来真的很乡土,特别是那些夸张的后缀语气助词。然而就是这些看似繁冗无意义的助词,让我觉得南汇话俏皮可爱,充满乡间的泥土气息,又有人间的和谐与温馨。而不同语气助词对语意的微妙改变恐怕只有南汇人自己能体会了。
一方面是语气助词的繁复,另一方面是丰富的词汇和极强的表现力。我认为南汇话是一种发展得非常成熟的方言,虽然较少高雅文艺的表达,但在生活劳动中极其好用。
南汇话成熟的一个表现是虚词的灵活运用,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比如“邪(xia)”这个副词,一般意义相当于“很”。但它可以很灵活地过渡到形容词。比如你看到一个人捕了很多鱼,可以直接说“邪呃嘛!”,一个人描述另一个人力气很大,你表示认可并惊讶,只需附和两个字“邪呃”。再如“咋”这个词,咋?——怎么啦/干什么?,咋啦嘎?——干什么啦?,拉咋?——在干什么?,咋去?——到哪里去?,咋呃?——做什么用的?另外“能”这个虚词很有意思,加在形容词后,类似“地”,如笃笃能、慢慢能、好好能、安安能。
南汇话在词序上可以非常自由地转换,创造出别致的表达形式。比如动词后置:“眼泪出(哭)”“雨落(下雨)”“水没(被水淹)”,还有一种是代词后置,如:“拨只鸡伊”(给他只鸡),“送把伞侬”(送你把伞)。
南汇话的精细最突出的表现是动词。比如骂人,可以说“岁”“产”“呱”,三墩大团地区还会说“闹”,对应不同对象不同程度的“骂”,“50前”南汇人是不用“骂”这个字的,但现在很普遍了。人体的每一个动作南汇话几乎都有对应的动词。比如,人脸部朝前碰一下,谓之“冲”,而额头先磕上,就是“碰”,而不是“冲”了;掐那么一小下,摘那么一点点,南汇话有个专门的词音类“滴”,“滴人”是南汇女人惯用的体罚手段,疼而不伤。
有些在市区话里发音统一的词,在南汇话里是有明确区别的。这可能是让市区人抓狂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比如“笔”≠“壁”,“立”≠“粒”,“齐”≠“旗”,“精”≠“经”,“哭”≠“壳”,“客”≠“掐”,“磕”≠“刻”,等等。
南汇话这么土,但在我看来,又是那么雅。有些表达丰富情感的词,我在“标准上海话”里找不到对应。这是岁月的积淀,也是人际紧密的农耕社会的烙印。
比如上了年纪的人会说“常着牵记侬”,“牵记”就是牵挂想念的意思。而“常着忱侬”,就是说老是惦记你。表达的是真挚而含蓄的情感。
南汇话情绪的表达经常是温和的,似乎总在考虑倾听者的感受。为了不让人担心,老人会把生点小病说成“有眼呒趣”。会笑说疯疯癫癫没半点正经的人“不作派额”,如果这人说话还带点色,我们不说他黄,而是说他“白”:“老白额”“只白早死”。南汇话描述人丑有个专门的字“泡”,但一般老人不大会直接这般品评人,会说“个姑娘勿趣透呃”,这么说无疑是丑了。
而我奶奶的语言我觉得是最优雅的南汇话,她说话不会有太多的语气词,总是适可而止。而她说的一些词,就像田野里曾经生长过的丹顶鹤,消失了。
我记得奶奶说回家,不是说“回来”,而是说“居来”,“哪能还勿能居来”就是怎么还没回家。我以前的印象中,奶奶的不少词汇其实和非常书面的古汉语接近,当时还觉得挺惊讶的,可惜大多记不得了。比如偷鸡摸狗或者男盗女娼的事,奶奶就说他们“犯条款”。吴语是不大说“喝”这个词的,但我奶奶会说“喝(音近哈)口茶”,我奶奶说的茶,不是茶,而是白开水,这也是非常特别的。当她说外面很嘈杂的时候,就说“孰来”。她说男孩是“囡囡”,女孩是“女囡”,说猫的时候,语音居然是上声,有点往上扬的,很好听,可以感觉到一种对动物的友爱在里面。
而当我翻阅南汇方志,感觉对南汇话的研究虽然已有一些语言学上的分析,但对它独特表现力的分析和描述仍显不够,大量独有词汇的收集更只是一鳞半爪。这一点我非常钦敬一位崇明前辈顾此彼先生,潜心十余年成《崇明话大全》,有此贤德之士,实乃地方大幸。前几年听到上海有搞“方言实录”,要65 岁以上、没有读过书、基本不出门等条件,以求其原生态。我不知道他们对南汇方言的记录是怎样进行的。我觉得应该和采集人相处一个月以上,而且要在不同的生活劳作场合,男女也要分别采录,如此才能一窥南汇话的精华,但这似乎是“过分”的要求了。
但多姿多彩的南汇话在真真实实地消失。
南汇这个行政区划本身就在2009年消逝在与浦东新区合并的时代潮流里。而方言的稀释和改变甚至比地域的融合快得多。特别随着城乡边界的日益模糊,人员流动的极大频繁,加上电视广播互联网的渗入,原汁原味的南汇话,已经越来越难听到了。连我70多岁的老母,现在讲话也经常夹杂一些时髦的词,比如“一般性”“了不起”“豪华”“可爱”啥的。那些90后们更是“与时俱进”了,“实我”是不可能讲了,现在连“伲”都不大有人讲了,而“阿拉”讲的人越来越多了。至于那些古雅生僻的词,在他们嘴里通通消失了,代之以标准上海话或普通话的南汇音版。如果听两个90岁的老人用南汇话聊天是一种享受,那么听两个90后的年轻人用南汇话聊天简直要哭。
不过近些年社交网络的发展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新现象。一些南汇年轻人制作了很多南汇话版的“汤姆猫”段子或“元首的愤怒”等配音,因为南汇话独有的“土味”和夸张语感,在网上大受欢迎。这其实是年轻一代南汇人内心对故乡文化的眷恋和守望。对任何一个特定地域的人群来说,乡音包含了不可替代的人文积淀、乡土风物和情感依托。
而我本人又是另一种样本。40年前我奶奶带我的时候,我讲的应该是最标准的南汇话,甚至可能有点我奶奶的古音。因为这扎实的“功底”,即便到县城读高中,我的南汇话还是标准的。但在市区读大学,不到一年,我就全盘“标准上海话”了。虽然哪怕很多年后,仍有正宗的市区上海人能听出我的口音。
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从郊区来的女生很快能讲一口标准的市区上海话,而我们男生则进度不一。有一个川沙来的男生,因为内心对市区人的距离感甚至某种莫名其妙的“歧视”,直到毕业讲的仍是一口两不像的上海话。
而我一直觉得我像一条耐旱的鱼,一旦扔回南汇的水里,又游出最自然的姿态。但我的南汇话能力终究还是退步了,南汇老同学笑话我说怎么家乡话也不会讲了,时不时冒出“上海闲话”。然而我又感觉我的“上海话”也退步了,就像青团里的糯米粉一样,搁一阵就“回生”了。但我也越来越不刻意追求上海话的“标准”了,怎样自然就怎样讲吧。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已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南汇话词汇选录
时间
着沟日(聂)子——大前天
沟日子——前天
上日头——昨天
今朝——今天
明朝——明天
后日底——后天
早千里——一早
壮五头——早上
当日中兴——中午
夜快头——傍晚
迭息能——现在
涨息——过了一会儿、等会儿
方位词
表示远一点的方位(比如乡东乡西)
东嗨(边)——东面
南嗨(边)——南面
西嗨(边)——西面
北嗨(边)——北面
表示近一点的距离(比如田东田西)
东板——东边
南板——南边
西板——西边
北板——北边
浜嗨头——河边
格板——这边
个板——那边
人称代词
我、实我——我
侬——你
伊、实伊——他(她)
实伲、我伲——我们
那——你们
嘎拉——他们
农活农具
斫稻——割稻
斫柴浜——-砍割芦柴、干草
捉花——采棉花
耖地——犁地
塔草——锄草
毛捻头——草绳
横刀——镰刀
铁 搭——锄头
町岸——田埂
名词
妈妈(mámá)——母乳,也指乳房
污纳——婴儿的尿布
御馋——小孩的围兜
节头管——手指
脚奎子——小腿
大脚奎子——大腿
夹着落——腋窝
脚发郎当——裤裆
猪狗臭——狐臭
天落水——积淀的雨水
哈嘛沙——霍乱
雷响——雷声
节肯——节气、节日
阴天势——阴天
叭叭呜、叭叭车——汽车
老芥菜——牛皮哄哄的人
菜花姐——爱哭的女孩
新娘子——新娘
新客人——新郎
善咭老太婆——话很多的人
老实头、好和头——老实人
大花头——特别精明活络的人
鹅头——呆子
道伴——同伴、伙伴
偎灶猫——萎靡的人
捻头——钞票(哩语)
落扫——茄子
油衣——雨披
汤 盅——小碗
蛋抄——勺子、调羹
对日铃——葵花籽
捐捐米——玉米
牛头裤——短裤
妹妹子——谜语
乌龙块——充血肿块
白相干——玩具
摸龙宫——鱼鹰
霍西——闪电
户荡——地方
别场好——别地方
门头——人情开支
动词
白话——聊
蛮白相——玩
发冷(头)——寒潮来临
做人家——节约
业舍——入赘
好好能——乖一点
庄庄较——规矩一点
行 针——针灸
拆泻——腹泻
吃角头——挨批评
奥扫——快一点
触壁脚——挑拨离间
仪思——害羞/不好意思
图死——浑浑噩噩
捉扳头——找茬
叽麻碌瞩——闲话太多
兜着——遭到霉运
回头——向家长告状
惯世——习惯(带贬义)
浪里浪生——因不满而语带愤恨
捉落空——抽空
勒海——在其中
杀枯——对人苛刻
污脱——浪费掉
呒数——没底、不清楚
眼痴假呆(ai)——装聋作哑
打棚一一轻度恶作剧、开玩笑
勿入调一一不学好、走歪路子
熬不得——忌妒
奥麻求告——苦苦求饶
疙嘴——结巴
落瘪——瘦
长肉——胖
捉嗝端——打嗝
打噢——恶心反胃
撒勿住——扛不住、吃不消
咬极口——勉强坚持
过人——传染
绕只脚——算了,不搞了
无讲头——没有共同语言
搭勿够——交情不深
吓邪——吓怕了
坍冲——出丑、出洋相
瞎乱撞——乱来
安安能一一安静
拆神思(伤神思)——伤脑筋
形容词
趣——漂亮
泡——丑
唰腊——形容人帅气精神或活干得漂亮
叮——痒
卡活——活泼、开心/活该
(真的是同一个发音)
走 油——吃力、无可奈何
触毒——看不惯、讨厌
蜡——不明智
孰——嘈杂
好白话——容易心软的
狗皮倒糟——形容小气吝啬
出客——仪表整洁大方/出手大方、
拆天拆地——顽皮
蹩脚无恙——走路无力
神思不收——不象样
呆(ai)不茏葱——迟钝
触死板凳——呆板
驼子八气——心不正焉、没责任心
(驼子形容不靠谱的人)
细脚蟹大——无能、笨拙
乌理蛮理——不讲道理、纠缠不清
胡摇三四——嘻闹、调皮
远七八只脚——相去甚远,差别很大
远天野地——差得很远
一眼不当——一点点
干略——干净
青肆——清洁、干净
面红堂春——气色很好
矮倭扎敦——矮小结实
气吭八倒——上气不接下气
浩水大来——口气很大
航行山似——好多好多
对色——厉害
悬七八只脚————相差很远
老门槛——很精明
有升梢——有出息的
虚词、副词
更转——反而、反倒
能好——如果(表达期待)
哑哑能/偷别自——偷偷地
难末/告牢——因此
大约摸嘎——大概
好末嗒嗒——突然间
1.《【居来】这句“上海话”,恐怕80%的上海人听不懂》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居来】这句“上海话”,恐怕80%的上海人听不懂》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yule/31584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