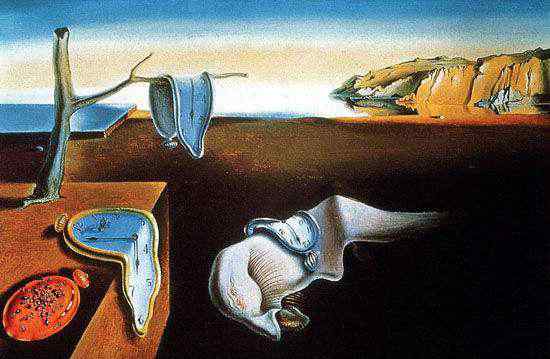那年冬天,我们正要从达那里夫岛搬回来,回到自己在大加那利岛的家。
一年的工作结束了,美丽的人造海滩引进了碧蓝平静的海水。
荷西和我坐在完工的河堤旁,看着看着享受着成绩,累不死。景观工程的快乐是非凡的。
从黄昏开始,我们一直坐在海边,直到午夜。除夕之夜,在漆黑的日子里,盛开的烟花梦幻般地照在我们仰着的脸上空。
滨海大道上挤满了快乐的人。时钟敲了十二下,荷西抱着我说:“赶紧许十二个愿,在心里重复十二句类似的话:”希望人最后,希望人最后,希望人最后,希望人最后,希望人最后——”

去年送走了,新的一年来了。
荷西先从堤上跳下来,伸手挽住我。
我们交叉手指,面对面凝视了一会儿。在烟花缤纷的光影下,我们笑着说:“新年快乐!”然后一个小吻。我突然眼泪有些湿,赖在他怀里不肯迈步。
新年总是让人惆怅,这一年的到来仿佛是真的。我许愿的下一句话,对夫妻来说不是很幸运。说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心慌。
“你许了什么愿?”我温和地问他。
“说不出来,说出来也不行。”
我勾住他的脖子不松手。荷西知道我怕冷,就把我卷进他的大夹克里。我再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亮,映出我的脸。
“没事的!回去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就回家!”
他拍拍我的背,我失声叫道:“我希望这种情况永远持续下去,没有明天!”
“我们当然要永远走下去,但我们必须先回家。加油,不要这样。”
一路回到租来的公寓,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仿佛要把彼此的生命握成永恒。
但是我心里很难过。新年刚来的第一个小时,我害怕难过,因为快乐在溢出。
不肯在租来的地方多待一分钟,收拾了所有杂七杂八的东西,装了一车。早上六点钟的码头上,一辆小白车在等渡船。
大年初一没有旅行者,但是我们急着要回家。
在家关了一年,杂草齐膝,满是灰尘的房间,面对着荒凉,原来是焦虑心痛,没有过年,两人立刻开始收拾。
然而,在家住了两个多月,那天早上我在院子里的花上洒了水。发电报的朋友在木门外大喊:“Echo,给荷西的电报!”
我匆匆忙忙的跑着,心里上蹿下跳。不要像我在马德里的家人一样!电报总是令人不安。
“撕什么!先签吧。”朋友在摩托车上说。我胡乱签了个名,转身在车库里喊荷西。
“你不要害怕!给我看看。”何塞把它抢走了。
原来新工作来了,让他赶紧去拉巴马岛报到。就在几个小时后,我一个人从机场回来,荷西走了。
离离岛不远,螺旋桨飞机需要45分钟。新机场和新港口正在建设中。因为没有人去最外面的荒岛,大渡船不会去那里。
虽然我知道荷西能照顾好自己的衣食,但是看着他每次带着小盒子离开家还是让我很难过。
家里丢了荷西就丢了命,没好处。

等了一个星期,电报到了。
“你不能租房,你先来,我们住酒店。”
刚刚整理好的家又被锁上了。邻居多次向我建议:“你住家里,荷西周末回来住一天半,他在那里住单身宿舍,不经济!”
我怎么可能心甘情愿。我急忙去打听货船的水路,检查了杂物,一笼金丝雀和汽车,推着一个行李箱上了飞机。
当飞机降落在宁静而荒凉的机场时,它看到了沉重的火山,那两座黑色中带着卡兰的山。
喉咙突然卡住,内心压抑,说不出的烦闷淹没了重逢的喜悦和期待。
荷西一只手拎着箱子,另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向机场外面走去。
“这个岛不对!”我说了一个闷闷的。
“上次我们来玩的时候你不是很喜欢吗?”
“不知道,我的心好奇怪,看到就想哭。”我的手握着他腰带上的搭扣。
“别想了,风景好的地方太多了,正好赶上看杏花!”
他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发,安慰地吻了吻我。
小镇上只有两万人租不到房子。我们搬进了一个公寓酒店,有一个房间,一个大厅和一个小厨房。一半以上的收入都付给了这个固执的人。
在新家安顿的第三天,一家人开始请客。结婚几年后,荷西第一次成为小组组长。水里另外四个同事没有带家属,其中两个还是单身。在我们家,食物总是比外面好。对于荷西对朋友真诚的爱,他渴望和朋友分享他温暖的家。我知道内心深处,他也为有我而骄傲,这份感激,当然是对他一心一意家事的回报。
岛上的日子很长,看不到国外的报纸,岛上的是怀旧编的。久而久之,外界传来的消息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只是守护着大海,守护着家,守护着彼此。每次荷西下班回来听到楼上急促的脚步声,我心里都是欢喜的。
六年过去了,他回家的时候,为什么还是不照样跑,慢慢走?六年了,结婚好像是昨天,他们之间多少悲欢离合。
小地方比较暖和,住在那里不久,深山里的农民要一杯水,一定要带家酿的酒,然后送一满盆鲜花。我们也是善良的人。土豆熟了,星期天总有两个人弯腰在田里帮忙收割。做热,跳进水库游泳,趴在荷西的肩膀上喊,却不肯放手。
在过去的日子里,在其他岛屿上,我们有时会发疯,吵架。
有一次,他们约定安静地读英语,晚上的电视不许开。他们被钉在餐桌上一盏孤独的灯前。
只持续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受教者偷看了一下手表,然后看了十分钟。一个音节被发送了二十次,但仍然不正确。荷西又看了看他的手腕。明知自己人教不了自己人,看到他的动作,手里的圆珠笔被扔了,身边的护垫摔了一跤,愤怒的大叫:“你这个傻女人!”
第一次被荷西骂,呆了几分钟,不知道怎么骂。我冲进浴室,拿起剪刀,扭了扭头发。我边剪边哭,长发掉了一地。
荷西追了进来,看到我疯了,但我没有上来抢。我就在门口冷笑道:“你不用这样,我去。”
拿了车钥匙后,门砰的一声关上,离家出走。
我冲到阳台上去看,他凄厉的叫了一声名字,他不肯停下来,车子唰的一下就消失了。
那漫长的一夜,怎么熬下来,自己都迷茫了。只看离家的人没钱,所以暴怒,不能出事。
早上五点,他轻轻地回来了。我躺在床上不说话,哭得脸都肿了。我离开父母家这么多年了,谁也受不了这份委屈。只有荷西,他不能对我刻薄。在他面前,我不设防!
荷西用冰给了我一张冰脸,带我照了照镜子,拿起剪刀给我家狗的短发做了补救。我被小心翼翼地修剪了又修剪,嘴里叹息着:“我只是气得骂了你一顿,还扭了头发。万一有一天我死了呢?”
他说了这样的话,让我很害怕。他转过身抱住他,放声大哭。他们被碎发包裹着,却不肯放手。
到了新的离岛,头发长到了肩并肩,辫子也梳不动了,但是他们再也没有吵过架。

一个依山而建,背靠大海的小镇,宁静得只有两条街的市场就是一切。
我们从不刻意交朋友。待了几个月,我们的朋友滚雪球。他们对我们真诚友好,都是真诚的。周末一定要被朋友占用,爬山,下海,下地帮忙,在森林里采摘野果,或者找个老派,晚上在睡袋里讲巫术和鬼故事,岛上一群疯子在这个天堂里躲着做神仙。有时候,我好开心,总觉得自己和荷西一起死了,掉到这个没有时间的地方空。
当时心又不好了,也厌倦了胸口的压迫,肠绞痛也是。从市场上买的一小袋物资,一口气提不到四楼。
不敢告诉荷西,悄悄跑去看医生,每次回头都是正常的,正常的。
荷西下午四点下班,以后都是我们的时间,所以有段时间没有出去疯狂玩。黄昏的阳台上,面朝大海,半杯红酒,几碟小菜,一盘棋,静静的玩着游戏,直到天上的星星从海上升起。
一天晚上,我们步行去看恐怖电影。旧剧院里只有五个人在楼上楼下数着。铁椅子被漆成铝灰色,冰冷,然后一群群鬼魂飘出来,在雾蒙蒙、凄冷的山城里捕捉路人。
到了晚上,潮水上涨,水花喷到了街上。我们被电影和电影院吓死了。他们手牵着手,在雾中跑回家。我一边跑,一边傻笑,摔坏了荷西,一个人拼命跑。他大喊大叫,像幽灵一样在后面追赶。
还没到家,心绞痛突然发了,冲了几步,抱着杆子不敢动。
荷西惊讶地问我怎么了,我指着左胸无法回答。那一次,他把我抱到了四楼。回来后,心不再痛,两人牵着手静静醒来,直到天明。
然后,困扰了我好几年的噩梦又紧紧的回来了。梦里总是上车,一上车就怕去哪里。梦里,没有荷西我是一个人。
多少个夜晚,我在冷汗中逃离梦魅,发现我的手被睡在我身边的荷西牵着,泪流满面。我知道,我大概知道生死预测。
想着我先走,我悄悄去公证处写了遗嘱。时间不多了,虽然天还是一样笑嘻嘻的洗衣服,这种感觉也感染了荷西。
即使岸上的机器坏了一个螺丝,只花了两个小时就修好了,荷西也不肯在工地等。他脱下潜水服跑回家。妻子不在的时候,他上街找。一家店问:“你看到Echo了吗?”看到Echo了吗?"
我找了个地方,双手环抱,看着老婆,没有避开人家的笑容。然后他们一路牵着手,提着一篮子菜向工地走去,直到又要下水的时候。
总觉得聚在一起的理由不长,尤其是我和朋友来参加周末活动的时候,总是把身体带回去。
周五,公交车上悄悄装上帐篷和睡袋,在海边废弃的地方搭起临时住所,感受黑暗抓螃蟹。在岩石的缝隙里,两磅重的黄光扣在他们的头上,在海浪的声音里只听见两个人的名字。那种大喊大叫的方法已经被天地震动了,我们还在无意识中。
每天早上,我买蔬菜,水果和鲜花,但我总是不愿意回家。我邻居的自行车是给我骑的。篮子里装着水彩的我跑到码头。当骑进码头时,第一个看到我的岸上工人总是微笑着指着方向:“今天在那里,再骑下去——”
车还没骑完巨大的工地,那边岸上的助手就拉了信号。当我的车停下来时,水里的人浮了上来。我跪在堤岸边,向他伸出手。荷西已经跳了起来。
大西洋晴天空下,分享一袋樱桃就好。当你靠在荷西身上时,左袖总是湿的。
几分钟后,荷西的手指轻轻压着我的嘴唇,微笑着沉回海里。

每次看到他沉沦,我总是看着他。
岸上的助手曾经问我:“你结婚多少年了?”“再过一个月就是六年了。”我还在看着水中的隐形人,我慌了。
“太好了,谁看你都不懂!”
我听了一笑就上车了,眼睛湿湿的。最后一秒还在一起,夫妻感情做的很好,不能分手。
我不敢在家里浪费时间。扣除房租,我日子过得很紧。有时候中午到码头,荷西和几个朋友站在一起等我走。“Echo,银行里有多少钱?”荷西在众人面前大声喊道。“两万,为什么?”
“去拿吧,很急,拿出一万二!”
千万不要在朋友面前为难荷西。他一转身就去要钱。他说的金额打了相当大的折扣,他赶紧把它给了还湿着的他。他一转手,就递给了朋友。
回家后,我一个人无聊。有时候,当我得到太多的时候,我会委屈的哭。我哪里知道是荷西对这个世界的兴趣?只过了一小会儿,朋友们就流下了眼泪来回报我?
结婚纪念日那天,荷西没有按时回家。我很担心。我开车去找他。借了辆自行车找人,然后就下楼了。他回来了,脸上有点不舒服。
匆忙给他吃了一顿饭——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我坐下来,向他举起酒杯。我惊讶地看到桌子上有一个红色的天鹅绒盒子。我打开一看,是一只老式的罗马字女表。
“别生气,先问价格,这是加班的外快——”他叫道。
我微微笑了笑,没有气,后悔他神经病,买了块表,多给了我几个小时的水。所以为什么不向朋友要钱呢?结婚六年,终于有了手表。
“你不能在下一分钟忘记我,让它为你计算。”荷西走过来,把手放在我身后。
就是这么不祥的一句话,让人害怕。
那天晚上,荷西睡去了,在潮水的声音里,我不停的想起他少年时的样子,十七岁大树下痴情的女孩,13年后在我枕头上分享气息的亲人。
我一时疯了,把他叫醒,轻轻喊他的名字。他完全醒不过来。我对他说:“荷西,我爱你!”
“你说什么?”他完全醒了,坐了起来。
“我说,我爱你!”为什么黑暗中有些呜咽声。“等了你这么多年,你总是说出来!”
“今晚我告诉过你,我爱你,爱你胜过我自己的生命,何塞——”
在那里,我还没来得及说下去,就像个孩子一样被抓住了。做了六年夫妻,为了这些对话,半夜眼泪打湿了我的脸颊。醒来的荷西已经不见了,没有看到他吃早餐让我忐忑不安,心虚,赶紧跑到厨房看到洗好的牛奶杯里有一朵清晨的花。
我一直坐到中午。这样的半夜悄声细语,海枯石烂,为什么一天天泛滥?我们的命运来了吗?不会发生的事,只有太开心产生的恐惧!
我照例去工地送零食,他们见面就脸红。连看都不敢看一眼,就拿着水果到处扔。
有一天,我看到太阳刚刚好。荷西回来之前,我一个人洗了四张床单。我搬家从来不带洗衣机,再去外面一趟,费用也不太方便自己洗。
当床单挂在屋顶,夹子还在的时候,我的心又闷了,然后熟悉的绞痛又来了。我丢下水桶,下楼了。进了门,感觉左臂发麻。我就知道不是很好。我赶紧喝了口酒,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
荷西没看到我送零食,中午就穿着潜水服开车回去了。“没什么,洗床单累了。”我病恹恹地说。
“谁叫你等我洗?”他跪在我的床边。“没有病,何必急!医生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来,坐过来……”
他靠在我身边,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
“荷西——”我说:“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答应我再结婚。温柔的姑娘就好,听见了吗?”
“你的神经!告诉这些做什么——”
“没有神经,我先跟你说清楚。如果我不再婚,我的灵魂将永远不得安宁。”
“你最近不正常,不跟你说话。你要是死了,我就用火把房子烧了,然后上船飘去老死——”
“放火也可以,只要你再嫁人——”
荷西瞪了我一眼,我看到他快步走出来,低着头,门被轻轻扣上。
我一直以为是我,一直对自己有感觉。我每一分钟都在害怕,不愿意,担心。而噩梦,一天就像一天的纠缠。
普通的夫妻和我们,生死思虑,依旧无边无际。如果再失去一天,会是怎样的一段时间?我不能先走。我要疯了,因为荷西丢了。
完全不懂,只是茫然的等待。
有时候坐在阳台上看渔船和荷西一起钓鱼。晚霞普照,清风徐来。我一摸他的脖子,就无缘无故的哭。
荷西不敢说什么。他只说这个美丽的小岛不适合我。赶紧完成一期工程,不续约,回家吧。
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我没有疯,但是会有很大的痛苦。那一年,我们没有完成秋天。
荷西,我回来了。几个月前我穿着黑色离开,现在我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回来了。开心吗?
和你告别的时候,阳光灿烂,孤独的墓地里只有蝉鸣。
我坐在地上,在你熟睡的身旁,双手环抱着我们的十字架。
我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你的名字——何塞·玛丽亚·奎罗。
我一次又一次的抚摸你,就像每次轻轻抚摸你的头发。
我在心里对你说——荷西,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如果这句话让你等了十三年,让我悄悄告诉你只有一个人!
我吻了你的名字,一次,一次又一次,尽管我的嘴里一直在说“何塞安息吧!荷西安息吧!”但我的手臂不会让你离开。我又对你说:“荷西,你乖乖睡觉。我去中国会回来陪你的。不要难过。你刚睡了!”
结婚前,在塞戈维亚的大雪中,我已经变心了。你带来的那个是我的,我的是你的。
埋葬的是你和我。是我们离开了。
我拿出我缝好的小白布口袋,在黑缎带里,我在你的坟前黄土上系了一个把手。跟我来,亲爱的!跟着我真的是休息吗?
我又一次为你整理了满满一瓶花,血像一朵深红色的玫瑰。对你来说,过几天就要枯萎残废了,但是我要回中国了,荷西。怎么回事?一瞬间,人就死了。何塞,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
该走了。好几次想放开你,好几次想紧紧抱住你的名字。黄土下你寂寞,我寂寞。为什么我不能躺在你身边?
我的父母在山脚下等我。荷西,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有你知道你妻子的心埋在哪里。
苍天,你不说话,对我来说,天地间最大的玄机是荷西,而你,你什么都不说,就放回去,只会让我含泪仰望晴天空。
我最后一次吻你,荷西,给我勇气,让你走,走开!
我背着你跑了,跑了很远。我忍不住停下来回头看。我又跑回你身边,扑到你身上哭。
我爱的人不忍心把你一个人留在黑暗里,在那个地方,然后去那里牵着你的手睡觉?
我趴在地上哭,开始挖。让我用手指把血挖出来,把你挖出来,再抱住你,把你抱到我们的骨头上!当时我被哭着上来的父母带走了。我不敢挣扎,全身颤抖,泪如泉涌。最后一眼,阳光下的十字架被新漆照亮。你,没有一句告别的话给我。
那个十字架是你我的背。我知道我们不会放手,直到我们再次相遇。

荷西,我永远的丈夫,我遵守了我的诺言。钱山回来了。不要为我难过。看着我,我不是穿着你最喜欢的华丽多彩的衣服来看你的吗?
下飞机后,我去镇上买花。店里的人看到我从中国回来都很惊讶。他们握着我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们相视一笑,泪流满面。
我抱着花走过小镇的石头路,街上的车都停了。不知道的人只是淡淡地对我说:“上车!送你去见荷西。”下了车,我点点头,感谢人们。当我看到你去年停下来的小屋时,我的心狂跳起来。在那个房间里,用四根白色的蜡烛,我握着你冰冷苍白的手,静静地度过了我们的最后一夜,今生最后一次相聚。
我鼓起勇气走在通往墓地的煤渣路上,一步一步,穿过一排排熟睡的外人。我上了石阶,又上了石阶,向左拐,看见了你躺的那块地,离得很远。我脚步凌乱,呼吸急促,忍不住向你奔去。荷西,我回来了——我跑开了手里的花束,我就像疯了一样跑向你。
冲到你的坟前,惊讶地看到坟墓已经被拱起,十字架老死不相往来,你的名字弱得看不清是谁。
我丢了花,扑向你吻你。万箭穿心之痛。是我离开的,你的墓地如此荒芜。何塞,我为你感到难过——我不能。我没有坐下来为你哭泣。我先给你种花,把瓶子装满清水,然后下去给你买颜料。
来,让我再抱抱你,即使你已经变成了一根白骨,你依然是春闺梦里相思相思病的亲人!
我走镇上,进五金店要了浅棕色清漆和小刷子,去文具店买了一支黑色粗芯笔。
路上有我熟悉的朋友。我匆忙抱住他们,心都碎了。关于这种情况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银行行长好心想再陪我去墓地。我谢过他,只允许把他的大车送到门口。
这一次只属于我们,谁也不能袖手旁观。荷西,别担心。今天,明天,后天,我坐在你身边,直到天黑,一起睡。
我再次走进墓地,传来了丁字镐的声音。谁在挖墓地管理员的坟墓?
我一步一步走进去。马诺洛看见是我,叫了一声,放下工具向我跑来。
“马诺洛,我回来了!”我向他伸出手,他用双手抓住了我,却又用袖子擦汗。
“好热!”他说木头。
“是的,春天结束了。”我说。
这时,我看到一个坟墓被挖了出来,另一个工人正在用铁棒撬开棺材,一个黑衣女人站在远处的角落里。“你在捡骨头吗?”我问。
马诺洛点点头,朝那边的女人望了一眼。
我慢慢向她走去,她遇见了她。
“五年?”我轻轻问她,她轻轻点头。“你要去哪里?”
“马德里。”
传来一阵劈柴声,又传来一声喊:“夫人,来看看签名,好让我们把小盒子装好!”
中年妇女的脸抽动了一下。
我捏她的手,但她不能动。
“不看行不行?只签。”我忍不住为她大喊。“不,不看怎么交代,怎么给市政府交签字——”那边又喊了一声。
“我给你看看?”我拥抱她,亲吻她的脸颊。她点点头,用手帕遮住眼睛。
我走向已经打开的棺材。躺着的那个人看起来不像骨头,连衣服都是灰色的。
马诺洛和另一个掘墓人拉着那个人的大腿,他身上的东西像灰尘一样飞走了,飞灰和尸骨一天天地暴露在外。我还是一个可怕的跳跃,不知不觉转过头去。
“看到了吗?”那边问。
“我给你读了,这位女士过会儿会签名的。”
太阳太强了,我跑过去扶着肩膀抽搐的孤独女人到树上。
看到的景象让我目瞪口呆,但就是冷得直哆嗦。“你一个人来的吗?”我问她,她点点头。
我抓住她的手。“过一会儿,收拾小箱子。回酒店睡吧。”她又点点头,低声说了声谢谢。
没有那个女人,我的脚步摇摇欲坠,生怕自己晕倒。
我忘不了刚才的场景。我抱着一棵树,靠在矮墙上。我无法恢复恐惧,心灰意冷。
我慢慢的摸了摸水龙头另一边的水槽,浸湿了胳膊,然后往脸上泼凉水。
荷西的坟墓在那边。很难。
我知道你的灵魂不在黄土之下,可是五年后,荷西,我怎么面对刚刚看到的景象,在你身上重演?
我静静地坐了很久,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
又一次,我用尽全力把脸泡在冷水里,然后我拿着颜料罐去了墓地。
太阳底下,我没有再对荷西说,钢笔填满了雕花的木槽——何塞·玛丽亚·克雷罗。安息吧。你妻子纪念你。
把那些字刷成全新的,干了就用小刷子开始刷。
在那个炎热的下午,在花丛和树叶中,一个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女人一遍又一遍地画着十字架和周围的山姆。没有眼泪,她只是在做妻子做的事——照顾丈夫。
不要去想五年后的情况,在我心里,荷西,你永远活着,一次又一次的跑回家,跑回家看望你的妻子。我倚在树下,等油漆干了,再重新涂,等它干了,再涂,再涂一个新的十字架。我们再一起推!我又渴又累又困。荷西,那让我靠在你这边。不再流泪,不再号哭,我只想靠在你身上,就像过去的岁月和岁月。
我抱着你的脖子慢慢睡着了。远处有人在轻声歌唱——
当我们年轻时
你喜欢说话
我喜欢笑
有一次,鸟儿并排坐在桃树上,在树梢唱歌。
我们不知怎么睡着了。
柏杨魏跃军
本期编辑:柏杨
1.《梦里花落知多少下一句 三毛经典散文:梦里花落知多少》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梦里花落知多少下一句 三毛经典散文:梦里花落知多少》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yule/8183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