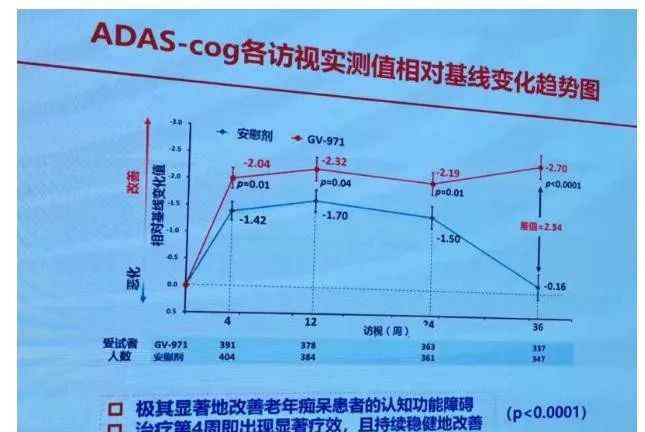2019年12月24日下午,众多作家、评论家齐聚蚌埠“湖升明月”古宅博览园,见证2019收获文学排行榜颁奖典礼。

颁奖仪式由《丰收文学》杂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丰收文学殷放专项基金理事会、蚌埠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由上海湘江实业有限公司承办,上海文艺出版社和雷丁集团为合作伙伴。


、

其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云中实录》获得2019收获文学排行榜小说榜第一名!

获奖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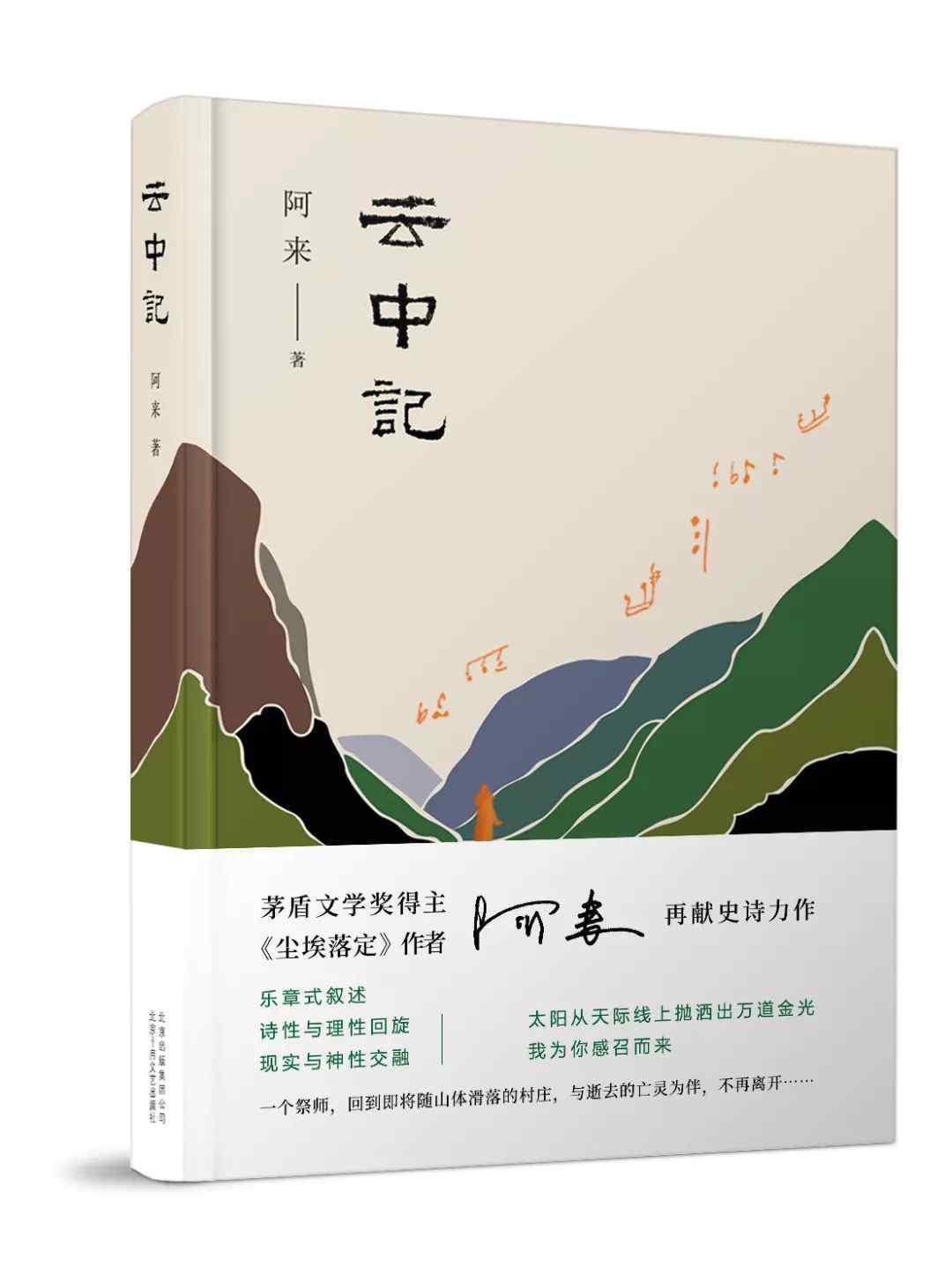
洛伊的《云》
2019年10月1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版
《云的故事》讲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阿坝在汶川地震中以牺牲死者的过程。是超越灾难文学的祭祀诗。作品中交织隐现着生死、历史与现实、自然灾害与生态关怀、传统习俗与现代更新等诸多命题,为消失的村庄布道,唤起逝去的生命,在生死的烛照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反思的方式将灾难变成民族精神重建的独特骨骼,建立健康的灾难书写伦理,唱响一曲苍茫庄严的安魂曲。
《云》获奖,谈语言
阿莱山脉(位于吉尔吉斯斯坦)
我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目睹了最震撼的死亡场景,目睹了最绝望最悲伤的时刻,见证了人类在自救互救时最惨烈的挣扎和无私的爱。所以我经常有写作的冲动,但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我多次压制住了这种冲动。为此,我不得不背负着常常触动我内心的愧疚。
地震后,许多村庄和城镇重新诞生了。也有城镇和村庄,许多人完全从世界上消失了。我想写一下这次失踪。我想写这种消失,不仅仅是沉浸在悲伤的哀悼中,更要写生命的庄严,写人类精神的崇高和伟大。写每一个肉体的毁灭和残害,都要写情感的深度和意志的力量,写灵魂和精神的方向,需要一种颂调。在最黑暗的时刻,让人性之光,由弱变强,照亮世界。即使这束光很难照亮现实世界,至少应该照亮我自己创造的世界。要写出这种光,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语言。必须优雅庄重。情绪一定要充盈丰满,但同时又要克制含蓄。要让语言在呈现事物的同时发出声音,像赞美诗一样歌唱。
这样的语言在神话和宗教歌唱中已经存在。当神话时代已经过去,如何用一种庄严的语言来书写当下的日常生活和灾难,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科学时代,神性之光已经褪去。如果文学坚持赞美奥德赛英雄,自然要和当下流行的审美保持一定的距离。
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史诗》(Epic)一书中说:“史诗中压义的特征——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是英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岳翎式的讽刺。”他还说但丁、弥尔顿和惠特曼都充满了这种精神。如果说但丁和弥尔顿和我有些不同的话,惠特曼是我理解和热爱的东西。布鲁姆说,惠特曼的英雄精神“可以定义为坚持不懈”,“也可以理解为不懈的远见卓识”。在这个视野里,你看到的一切都因为一种精神气质而变得更强大。”。
我所在的族群有一套古老的崇拜制度,是一种前佛教信仰。它的核心本质不是屈服于某个代表终极秩序和神圣力量的神或教皇,而是用人的生命去尊重自然的东西。这种信仰认为,有一个美丽的灵魂,伴随着血肉和欲望。真正的人是同时拥有两者的人。他们的神在部落历史上也有,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有自己的血脉传承。这种信仰和纯宗教的区别在于,后者只需要服从,而前者可以激发凡人潜在的英雄品质。

这与斯宾诺莎倡导的自然神性是一致的。
斯宾诺莎说:“我对上帝的概念是结合深厚的感情,坚信经验世界所展现的高超理性。按照通常的说法,这可以称为‘泛神论’的概念。”
要表达或相信这样的泛神论价值观,我们必须使用诗意的语言。我很熟悉这样的语言系统。当进入《云的故事》的写作时,我可以把全知全知的概念从我的第一种母语贾蓉转移过来——不,说这个概念是全知全知是不正确的。这并不是说复制这个语言系统就足够了。作为一种古老的语言,它不再完全有能力从当前的世俗社会生活中发现诗歌和神性,它的特点很难在一个语言系统中完美呈现。更有甚者,写地震的时候会和一整套科学的地理术语发生碰撞,其中既有可能性的诱惑,也有失败的陷阱。
即便如此,我还是以这种语言,这种语言感知世界的方式为出发点。
随着场景的展开和人物的动作,我总能捕捉到超越现实生活和基本事实的先验的、形而上的东西,并一直呈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可以通过自我导向来产生意义,而不是受到一般经验的约束。它不会因为对现实主义的狭隘理解和对现实再现的执念而被现象淹没。
这种语言调性的建立,文言文给了我很好的帮助。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很多伟大的瞬间,一个人的一生与身边的事物相遇,事物与我交融在一起。
那是一个像“挥之不去的蝴蝶一直在跳舞,迷人的林莺只是安心地哭泣”的瞬间。这是一个像“花瓣像眼泪一样落下,孤独的鸟儿歌唱他们的悲伤”的时刻。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身心都在一个人的身体里,感官得到充分的开启,语言融入了情感和意义。而中国叙事文学中的“且听下回分解”的方法,却从未获得过如此巨大的语言学胜利。
《云中录》这本书在表达人与灵魂、人与大地的关系时,一定要着眼于更为普遍的生命现象,一定要着眼于人们对自身情感和灵魂的自省。这时,中国作品文学中那些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招数就失效了。只有中国诗歌中那些伟大的启发性的召唤经验,才是我所需要的,而在叙述事情的同时,能够很好的表达和控制情绪,才是我所需要的。我发现在中国文学的巅峰时期,诗歌的手段并不复杂:赋、比、兴,还有形、音、隐而不显的多义词。更重要的支撑是对美的信仰。美与善,善与美。至少在这本书里,我不想成为怀疑论者。我想护送我的英雄沿着一条由文字开启的美学之路一路前行。

花儿,高到我的窗前,伤透了一个流浪者的心,因为我从高处看到了到处都是悲伤
"付强语仍在哭泣,而胡尔星又在歌唱."
巨大的灾难,众多的死亡,当然让人落泪,但是灾难的书写不应该仅仅止于绝望,更应该书写“行走、歌唱”的不屈与昂扬。
我觉得语文很好,需要珍惜和发展。《文心雕龙》里说“万物有所触,万物有所触”,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我们对如何完成一部小说有很多讨论,但我们仍然更关注内容。而我一直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语言。有些人写作需要材料和思路,但要等待的是特定语言的出现。在写作过程中,字与字之间有灵光一闪。作家是灵感的捕捉者,他所拥有的只是一张随时可以展开的网,在文字的海洋中捕捉灵感。下网,抓东西,打开,抓事故外面的东西。通感。符号。比喻。或者只是一个确切的词。或者是一个生动的词。似乎没有什么暗示。一瞬间,那个用了无数次的麻木字又活了过来。那句老话,站在那里摇一摇,就会发出新的声音,有了新的音色,有了新的质感。这样,小说文本就逐渐生成了。文字是它的基础,是它的门户,是它的穹顶。
哈罗德·布鲁姆列举了优秀小说的三个标准,第一个是“审美光”。我觉得这个光一定来自语言。
最后,正如我之前所说,贾蓉是我的第一母语。这种语言是我进入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的第一条路。刚开始写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用中文写的。我更喜欢叫很多人中国人。这种语言被称为汉语,因为它也是全中国通用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把汉语称为我的第二母语。对我来说幸运的是,这两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给了我很大的滋养。

作家、四川作家协会主席阿来,曾任《科幻世界》杂志主编、社长。
诗歌创作始于1982年,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18年,他的中篇小说《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成为“双冠”。
主要作品有诗集《莫索河》、小说集《旧年血泊》、《月光下的银匠》、随笔《大地的阶梯》、《草与植物的理想国度:成都物候》、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詹兑”、“三冬虫夏草”、“蘑菇圈”
2019年,最新小说《云中录》出版。
1.《长篇小说排行榜 《云中记》荣获2019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小说榜第一名》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长篇小说排行榜 《云中记》荣获2019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小说榜第一名》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guoji/16242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