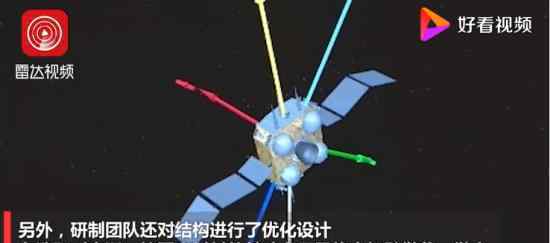扎加耶夫斯基散文选
和郝|翻译
摘自《杨紫茳诗刊》,2014(1)
捍卫形容词
我们经常被告知删除形容词。风格不错,我们听说过,据说不用形容词。名词是实体弓,移动的,无处不在的箭头动词,两者都够用。然而,一个没有形容词的世界,就像周日的外科医院一样悲伤。蓝色的灯光从冰冷的窗户里渗出,荧光灯静静地嗫嚅着。名词和动词对于国家的军人和领导人来说已经足够了。形容词是独立的个体和事物不可缺少的保证者。我看见水果摊上有一堆瓜。形容词的反对者不难表达:“瓜堆在水果摊上。”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个跟塔列朗出席维也纳大会时的脸一样黄的瓜。另一种绿色,未成熟,充满年轻人的骄傲;还有一个瓜子脸凹陷,迷失在悲伤和沉默的底层,仿佛受不了和外省呆在一起。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瓜。有些是椭圆形的,有些是粗壮的。硬还是软。闻起来像乡村或者夕阳,或者被巴黎郊区的道路、雨水、陌生的手、灰暗的日子折磨着空,干燥、顺从、疲惫。形容词对于语言就像颜色对于绘画一样。地铁里站在我旁边的老人是一串形容词。他假装打瞌睡,但通过他半闭的眼睛,他也在观察其他乘客。他的嘴唇因拱形的微笑而发红,有时变成嘲弄的扭曲。我不知道他的心里是藏着一种冰冷的绝望,还是疲惫,还是对时间的一种顽强而耐心的幽默感。军人限定大量形容词。他们只有一个形容词,就是“一样”,从那双没有光泽的眼睛里放射出来。同样的制服,同样的步枪。任何一个从部队回来,换上便服,向平民城镇迈出第一步的人,都会记得充满整个世界的形容词、颜色、音调、形状、不可替代的个体存在的不可思议的爆炸。万岁,形容词!大的,小的,被遗忘的,存在的。我们需要你,附在事物或人身上的灵活狡猾的形容词,让我们看到从未失落的个体的鲜活味道。一座灰暗的城市,街道沉浸在残酷的灰色阳光中。鸽翅色云,黑云满戾气:如果不是你身边流淌着多变的形容词,你会是什么样?道德是另一个没有形容词就活不了一天的领域。善、恶、狡猾、慷慨、报复心强、热情而神圣,这些词像锋利的铡草机一样闪闪发光。要不是形容词,我们就没有记忆了。记忆来源于形容词。一条长长的街道,一个炎热的八月天,一扇通向花园的废弃的门,就在那里,在布满夏日灰尘的红醋栗树中间,是你多变的手指。
狂喜和讽刺
在诗歌中,有两种矛盾的元素:狂喜和讽刺。狂喜的元素与无条件接受世界密切相关,甚至包括残忍和荒谬。相比之下,讽刺是思想、批评和怀疑的艺术表现。狂喜是准备接受全世界;讽刺跟随思想的步伐,质疑一切,挑起争议。它怀疑诗歌的意义,甚至怀疑诗歌本身。反讽知道这个世界是悲剧的,是悲哀的。两种差异如此之大的元素形成的诗歌令人惊叹,甚至相互调和。难怪很少有人读诗。
来自其他世界
诗歌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什么世界?来自内心生活的世界。世界在哪里?我说不出来。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思想、隐喻和情感。他们有时充满了崇高的信任,有时表现出蔑视和嘲笑。他们出现在奇怪的时间,不请自来,也没有通知。但是当他们被叫的时候,他们经常隐藏自己。在巴黎街头,哑剧逗乐了围观者。他们模仿严肃的路人的脚步,手里拿着沉重的公文包,脑子里想着沉重的事情,急匆匆地去上班。哑剧演员完美地模仿他们走路的方式,他的表情、举止、严肃、匆忙和专注,直到路人意识到他被一个活跃的模仿者跟踪,闹剧结束,观众哄堂大笑,笑话的受害者加快脚步消失在街道的另一边,然后演员们鞠躬收钱。精神生活以类似的方式模仿这个严肃世界的政治、历史、经济。它跟着,跟着,悲伤或者快乐。它跟随着现实世界,像一头红发的疯狂守护天使,哭着笑着,拉着小提琴,或者吟诗。当现实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的时候,鬼影向大众鞠躬,然后消失了。诗歌来自另一个世界。从哪里?我不知道。
天真和经验
我们都欠威廉·布莱克著名的《天真与经验之歌》。我们本能地倾向于按照时间顺序来读布莱克的诗:首先是纯真,然后是对苦难和经历的补偿。真的是这样吗?纯真真的是我们失去的东西,就像童年一样,一旦失去,就永远失去了?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失去经验?经验是一种知识。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知识更容易分裂。这也适用于伦理学领域,也就是智慧。有些人从集中营里活了下来,保持了尊严和正直,但也许后来他们变得傲慢和自私,这会伤害一个孩子。如果他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后悔,他会在那天回到真正的王国。这就是为什么在生命的尽头拥有经验并不总是正确的。天真是跟着经验走的,没有别的路。天真变得经验丰富,自负变得贫乏。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只是在某一刻明白了,然后忘记了,或者说我们背叛了自己明白的那一刻。在这一端是天真、无知、苦涩的天真、绝望和惊讶的再现。
历史想象
当我还是一个渴望知识的高中生时,我经常去听著名学者的讲座,他们来我们省会讲课。通常来我们这个小地方的人都是专门领域的专家:一个人讲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一个人讲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下一个人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像往常一样,观众大多是我这样的高中生和一些退休老人。前者观众想知道生活在等着他们,后者观众想试着理解生活给他们留下了什么。即使是最成功的讲座也没能满足我们的愿望。例如,一位来自华沙的高大阴郁的学者做了一个关于中世纪建筑的讲座,他讲得如此热情,以至于我们想知道他是否对城市的未来规划有一套想法——这让我们俩都很失望,他也没有给我们的基本问题带来答案。有一天,一个关于历史想象的讲座将在那里举行。我们这些经常一起来听课的人,问问主办方谁会是下一个演讲者。这一次我们被告知,他不是历史学家或科学家,而是诗人,他很优秀,但不是特别有名。他多年来不受当局欢迎,但他的情况终于有所改善。他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与大众见面。(“为什么”,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叹了口气,“如果大众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请他来。不受当局欢迎的人不会受到听众的欢迎。”)他终于出现了。他和以前在这里发言的人很不一样。他似乎没什么信心,似乎也不相信会有人理解他。其实观众只有五个人。“我们知道的很少,”他重复道。“我们将一切推向历史。我们用历史来解释一切。“上一次战争,”他说,“是一场不幸的灾难,不仅因为数百万无辜的人丧生。更重要的是,在战争中,我们不仅失去了我们人民的尊严,他们在被审判和判刑后被谋杀,而且那些幸存的人也失去了尊严。他们活得像一种非历史的、永久的存在,历史上无望的、混乱的……”各位注意到了吗?“他问了我们五个人:三个高中生和两个年长的女人。其中一个人几分钟后开始打瞌睡,睡得像个沉默的印第安人——“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注意到了吗,现在人们写的诗、小说或剧本都怪历史?你注意到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吗?但我们是意志和思想的心脏,是每个独立命运的透镜?“只有历史,填平、征用、破坏一切的历史,才彻底割断了空我们的历史。而历史想象,你一定知道,在未来发展了,极其发达,像野兽和寄生虫一样,吞噬着其他一切,其他一切丰富的想象和思想,甚至连同它们的自由,不,那一点点尊严的痕迹也被剥夺了。很久以前,我们作为旅行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意外地来到了暴力场面,死亡和战争。有人闭上眼睛,有人试图逃跑,还有人继续受到保护。”我们是别人,我们来自外地,罪让我们惊喜。我们不理解苦难。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已经成为历史。有的斯大林或希特勒踩了我们的摇篮,制服的细条缝在我们的西装上;我们总是要报复一些人或者拯救另一些人,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已经犯下了错误或者罪过。历史想象成了我们的辩护律师。为什么说有罪?这不是我,我们争论这是一个新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在这样做,而历史想象力则站在一边为我们建议用词。“我们已经离历史如此之近,以至于经验和缺乏经验、白天和黑夜、音乐和统计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但是我绝对不会同意这些。我宁愿疯狂也不要属于历史。我宁愿走极端,也不愿意活在平庸中。我宁愿什么都不知道。”他厌倦了说话。他停下来,很快离开了论坛,没有等待任何问题或不同意见。我们也分别离开了,我们,五个不同年龄的听众。我们什么也没说,谁也没有勇气叫醒熟睡的老婆婆。那是一个十一月的夜晚;我们手表上的滴答在静静地走着。
关于神秘的演讲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诗。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苦难。我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秘。
文学的两大缺陷
1.当作者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集中在自己的弱点上,集中在自己的生活上,他就忘记了客观世界,忘记了对现实的探索。2.当作者只专注于追求世界的真相、客观现实、公平正义、评判他人、新时代、社会习俗等。,他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的软弱,忘记了自己的生活。
关注花城杂志
独立精神、人文立场和新理念
《花城》2017年第三期目录
长篇小说
平原客/李
短篇小说
祖先和小丑/雷莫
花城关注专栏主持人:何平
变形/陈思安
采访:“心是战场,一边战斗一边前进。”/何西安
乌拉霍溪/儿童端
采访:“我在找一个重述整体的方法”/何平同
27年俱乐部/杨碧薇
采访:可能是我去拜访了一个假的“卫”/和平
对此问题的评论:制造“85后”:戏仿的文学命名/何平
诗歌
秘密花园或疯人院场景(组诗)/华清
散文随笔
雅凡/罗南
蓝色东欧
另一种美(节选)/[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译李义良
思考永无止境
【讲堂】写作和阅读其实是生活方式/欧阳何江
域外视角
当代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三本杂志一部中篇小说集/[美]罗福林译王
1.《imagine的形容词 听说好的语言风格,都不需要形容词?》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imagine的形容词 听说好的语言风格,都不需要形容词?》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keji/9895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