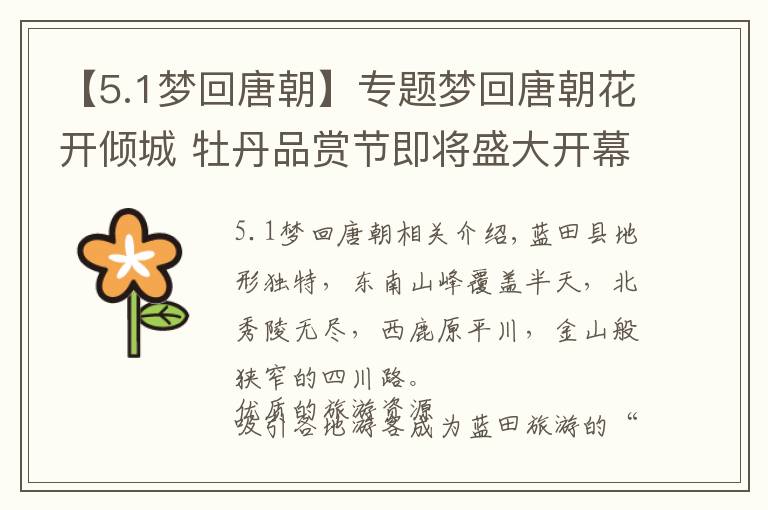这篇文章刊登在《三联生活周刊》 2019年第32期,原文题目《乐队在中国》上
回顾中国乐队的现场,总能看到包含那一代精神表达的时代烙印。
记者/黑麦
1994年,邓讴歌、何勇、欧洋,在香港红磡的演出现场(高原 摄)
80年代,前奏
1978年4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中出现了“乐队”一词,作为“Beatles”词条的解释,此时,英国的披头士乐队已解散数年,这个非常滞后并且有些含糊的解释,似乎并不能让当时的人把乐队和某种从未在中国大陆发出声的音乐形态联系在一起。
一年后,商务印书馆接着出版了一本《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书中所提到的“摇滚”,也是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字眼儿,它看上去并不那么雅观,却在年轻人中营造出一种虚幻、极端的氛围。就在那段时间里,改革开放的同步宣告,似乎昭示着新时代的到来,一些新的事物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打开了某种视野。
80年代中期,人们不再像过去听邓丽君那样偷偷摸摸,磁带伴随着流行的声音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市面上最触手可及的精神食粮,几块钱一盘的磁带,几乎可以让一个年轻人享受数月,这是他们最喜爱的娱乐,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最初方式,尽管还有些模模糊糊的。在磁带文化盛行的岁月里,抒情歌曲占据了主导地位,先是一批台湾校园歌曲,随后而来的是诸如《万里长城永不倒》之类的香港电视剧主题歌,同期的罗大佑、张明敏等人似乎奠定了这一音乐文化形态的最初审美。不过,随后的一曲《黄土高坡》将其颠覆,这种更像北方民歌的喊唱似乎在北方终结了阴柔的演唱风格,让很多人找到了一种情绪出口。
在这片禁锢了已久的广袤土地上,一种新的声音正在浮出水面。1980年的夏天,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北京高校文艺汇演,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电声乐队站在舞台上初试啼声,他们翻唱的大多是披头士乐队的歌曲。此前,摇滚乐和吉他只是一些人的特权,只有少数人在北京海淀的部队大院里,看见过弹着吉他招摇过市的高干子弟,那个形象,无疑充满了对于旧审美和体制的挑衅,也对年轻人充满极大的诱惑。
第二外国语学院舞台上的这支乐队名叫“万里马王”,它的名字由四位成员的姓氏拼凑而成,彼时流行的“千里马”精神也为乐队的名声助了一臂之力,在《昨天》这样流行的曲调中,现场的年轻观众激动不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听到这种音乐,这与他们此前接触到的宏大的、严肃的音符不同。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主持人的吴晓庸也在现场,他将这场演出的录音带到了自己的节目中,没过多久,英国广播公司(BBC)也迅速做出了报道,认定那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摇滚乐演出。
田壮壮曾在80年代拍摄过一部名为《摇滚青年》的电影,在当时,流行和摇滚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摇滚”这个词很模糊,它更像是一种对于不羁与抗争的形容。生于1965年的杜昊,是二炮文工团的演奏员,他在80年代初“下海”成为了一名摇滚歌手,在他的自述《年少轻狂的日子》中,他讲道,当时全北京的演出队伍不过几十个人,这些玩音乐的“散户”大多来自北影、全总、儿艺、广播乐团、文工团、歌舞团等,他们技术优秀,很快将这些来自境外的音乐,转化成本土的声音。这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一支乐队,名为“七合板”,1984年,他们发行了一张翻唱美国民谣歌曲的专辑,随后被相关部门遣散。在专辑的封面上,穿着燕尾服,蹲在最前面的崔健和刘元,在数年后缔造了中国摇滚乐的开端。
1985年初,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内尔·里奇联手美国近百名歌星发起了一场为助非洲灾民录制唱片的活动。感人至深的大合唱《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很快就传入了北京。花果山乐队的侯德健,向歌舞团推荐了当时还未成名的郭峰,由此,一张打着“为世界和平年”而录制的专辑呼之欲出。
1986年5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一位名叫崔健的年轻人和他的乐队登上了舞台,他衣着随意,一只裤腿挽起,露出一截白色的袜子,给人一种玩世不恭的感觉。他在吉他的和弦中发出犹如嘶吼的“我曾经问个不休”,随即迎来台下的一阵喝彩。当鼓声键入,刘元的唢呐声响起时,台下的观众几乎沸腾了,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只是觉得那种带有节奏的张狂刺激着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一种压抑了已久的情绪,在这些音符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于是,这首名为《一无所有》的歌曲,随即成为了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
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的演出现场(高原 摄)
3年后,这张名为《一无所有》的专辑上市了,像是一把刀子,直击了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极为贫瘠的社会处境,这些歌词和音乐如同一种拷问,发人深省。很多人在当年记住了《一块红布》或是《花房姑娘》这样的歌曲,作者用浪漫的爱情比喻革命,书写时代,但是很多年以后,人们更为感叹的是专辑中的另一句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在今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官方网站上,崔健和这首《一无所有》被形容为中国摇滚乐的先人和先曲,文字中甚至提到了曾经被停止销售的专辑《红旗下的蛋》,时过境迁,摇滚乐也不再是敏感的事物,它成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声音,记录着当下发生的种种现实。
80年代末,北京已经出现了几十个乐队,乐手们不断更迭着自己的创作伙伴,试图在种种有限的碰撞中,找到新的火花。在面孔乐队吉他手邓讴歌的回忆里,他们的乐队就是由一批年轻的霹雳舞少年所组成的,由此,“唐朝”“黑豹”“呼吸”“1989”“眼镜蛇”“面孔”,这些在几年后的音乐圈中如雷贯耳的名字,相继成立,成就了中国摇滚最初的光芒。
90年代,散落的记忆
早在80年代末期,台湾与香港的唱片公司已经将目光转移到北京,一方面它们各自经历了瓶颈与过渡期,另一方面,它们在中国大陆看到了一大批即将破茧的音乐人与巨大的市场。李宗盛在《和自己赛跑的人》这首歌中唱到过一个名叫Landy的人,他的中文名字是张培仁,在90年代初,他和贾敏恕成为了北京摇滚圈的第一批探访者。有很长一段时间,滚石唱片的办公地点都设在新大都饭店的客房里,坐在地上不停地打电话是他们的工作日常。有一年冬天,张楚录制的小样《姐姐》通过唐朝当时的经纪人刘杰辗转送到办公室,贾敏恕和张培仁听完后都有点感动,他们冲出酒店,在一个地下室里找到了张楚。
那时候,崇文门西大街上总是停放着一辆银色的甲壳虫汽车,在它的一侧,是一排两层楼高的商铺,其中一个名为“马克西姆餐厅”,是当时摇滚青年开Party的聚集地。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曾经把这里形容为“金字塔的顶端”,不只因为那里汇集了上流社会青年,更重要的是,在北京出现现场俱乐部之前,这家餐厅是唯一的演出场所,它甚至是崔健乐队梦开始的地方。
唐朝乐队是这里的常驻嘉宾,曾经不少人专程来到这里花上100元看他们的演出,这在当时价格不菲。不久,这个乐队便成为了滚石旗下“魔岩唱片”率先签约的乐队,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这支乐队就变成了北京摇滚圈的焦点,无论这四个高个子长头发的青年出现在哪里,都会引起众人的瞩目。他们太显眼了,无论是人还是作品,他们的音乐中都传达出很多当时社会不曾有过的情绪和思考。张培仁从台湾邀请了方无行来这边为他们制作,并为他们带来了乐器和录音设备。在贾敏恕的回忆中,那是一个流露的创作过程,每一首歌似乎都影射着那个年代的情愫。
台湾艺术家谢春德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一号棚拍摄《梦回唐朝》MV的时候,乐队的年轻人赤裸着上身,抱着吉他,甩动长发,给人一种生猛之感。后来,他们陆续来到银川等地,继续拍摄,为当年的音乐人留下了珍贵的录影。当时的台湾唱片工业已经很成熟了,张培仁亲自为乐队写了宣传册上的文字,非常详尽地介绍了我们这片土地的音乐现状,以及摇滚乐文化的发展,并以“中国人的自信”与“新世代的开始”为题,形容他们的音乐。
摄影集《把青春唱完》,留下了这支乐队青涩的模样。这本书的作者是高原,作为中国摇滚的亲历者,和当时为数不多的摄影师,她用镜头记录了很多珍贵的瞬间。在她的书出版后,有读者意外地在唐朝乐队首发签售的相片中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高原曾好奇地问陈羽凡,以求对证,陈羽凡看着相片里稚嫩的脸,自己也惊呆了。在高原的新书中,陈羽凡自述自己当时只是个上职高一年级的乐迷,那些乐队的名字,都是带着光环的,是这些音乐指引着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原一直觉得音乐只是收音机里的声音,她甚至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观看不倒翁乐队的排练,以及第一次去外交人员大酒家看唐朝乐队演出时的情景,在那以后,她了解到乐队存在的意义和他们的生产过程,也目睹了不少因为分歧而解散的乐队。她知道那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真实的音乐形态,尽管那时她不知道如何去形容,只觉得他们很酷。后来,高原去了工艺美校,成为了摄影系的第一个学生。不过那时候,她还从未想过摄影会和音乐产生什么瓜葛,更不知道自己会成为那段岁月几乎唯一的记录者。
张楚(李骁 摄)
那一年,魔岩唱片刚刚签下了三个年轻人,他们是窦唯、张楚、何勇。张楚是他们中话最少的一个,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质朴的歌声中还隐藏着一种对于社会独特的观察视角。导演张扬那会儿刚刚从中戏毕业,他带着还没毕业的王学兵和演员贾宏声来给张楚拍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MV。高原的镜头记录了那个洁白的冰面上,站着的一群理想主义的年轻人。
1994年12月,被称为“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何勇以及作为嘉宾演出的唐朝乐队以特殊渠道抵达香港,他们即将在红磡体育馆表演一场名为“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这场演出距今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是它所留下的烙印以及对之后乐队所产生的影响尚在。演唱会前,何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戏谑地评价了当时红极一时的香港“四大天王”,他说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那场犹如踢馆的演出,在舆论的驱动下,把这些年轻的音乐人推上了风口浪尖。在那天的演出期间,高原记录了异常平静的窦唯,一贯忧郁的张楚,以及一个极其气愤的何勇。两年后,何勇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在北京的“流行音乐十年”现场唱了两首歌,却意外地遭到了当时舆论的抨击。
高原说,何勇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在他身上能看到很多冲突,他习惯用愤怒去表达他的哀伤情绪。在红磡的现场,我拍到的是一个来自北京的朋克男孩,一个人对于年轻的真实呈现。我很怀念这种真实”。那是摇滚乐刚刚浮出水面的一段日子,一些乐队开始被人熟知,似乎每一个声音都能在那个岁月中得到回应。很多人认为,中国摇滚乐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和那个时代、政治、文化背景深深地绑定在了一起。而高原却认为那些标签更像是一个坚硬的外壳,它杂糅着一代人单纯而漫长的青春期。在她的新书中,她试图用新的照片去重新表达这场音乐革命。
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摇滚乐正式告别了金属和硬摇滚,开始向多元的声音靠拢。一大批开始尝试电子设备的音乐人,如王勇、王凡都是在摒弃了传统的吉他演奏后,开始在自己的音乐中使用起midi或合成器,他们相信这些声音所带来的,会是一场摇滚乐的革命。那一年,王勇在他的Keep In Touch酒吧开创了最早的Rave Party。张亚东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最早的时候,他在窦唯的《艳阳天》中尝试使用过电子音色,后来,在他给地下婴儿乐队制作专辑的时候,他把乐队的唱词“都是一个样”重混成drum & bass的风格。
窦唯(1993年)(高原 摄)
在很多人看来,整个90年代是中国文艺发展最为迅猛的一段时间,音乐、艺术和文学,都在那段时间里,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它也是被接纳的一段时间,像所有文化形态一样,它生根于那些氛围之中,并且开始自在生长。高原觉得,那是摇滚乐最为鼎盛的一段时间,她亲历了音乐人与音乐形态的更迭。令她记忆犹新的是,1997年在为麦田守望者乐队拍摄专辑时,她突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阳光,她说,这些男孩的音乐有很强的青春气息,也流露出对于文学作品的自我理解,比如那首根据凯鲁亚克小说命名的《在路上》。
5年前,高原在跟随汪峰拍摄长达3年之后,决定在“鸟巢”的现场结束自己的这个拍摄项目。那3年里,她目睹了汪峰的成名,也看到了娱乐和商业给音乐人所带来的变化,她一直认为,站在熟悉的拍摄点,应该能轻易地拍出不同的气场,然而越来越多的限制却让她无法实现,在一代摇滚音乐人的身上,有些东西消失了。高原很喜欢她在1995年为汪峰拍摄的一张照片,那是林兆华导演的《浮士德》现场,消瘦的汪峰穿着白色的衬衣,带着黑色的粗框眼镜,姿态中表现出一种张狂和无畏。
2000年后,此消彼长
在装帧精美的《北京新声》一书中,扉页印着“献给打口的一代”的字样。但是当时的打口青年们大多是买不起这本在1999年售价超过100元的书的,因为这笔钱可以换回至少三盘乐队的磁带,那是他们的精神口粮。但无论评价如何,这本收录了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鲍家街43号、子曰、张浅潜、清醒、超级市场、新裤子、花儿、秋天的虫子等乐队的书籍,展示了在世纪末诞生的一批乐队,和他们所向往的精神世界。
在乐评人颜峻看来,购买打口的年轻人大多标榜“营养不良”,因为他们的胃口很大。这些年轻人代表了不甘压抑的一代、盲目寻找的一代、打开地下通道的一代、创造边缘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代、顽强生长的一代、抗拒和挣扎的一代,拼命地在同龄人撰写的《通俗歌曲》《我爱摇滚乐》《极端音乐》《重型音乐》等杂志中找到可以证明自己的东西。
《北京新声》似乎为第三代乐队做出一个漫长的铺垫,他们大多成立于摇滚乐较为低潮的时期。90年代末,娱乐工业基本成型,比起乐队,唱片公司更偏好稳定的歌手或组合。那段时间,新裤子乐队刚刚成立不久,庞宽曾经和彭磊商量着开一家小卖部,或者去广州做点服装生意来养活自己。不过在他们随后录制的第一张专辑中,并没有提到太多生活的窘境,雷蒙斯式的朋克音乐是他们曾经的唯一。在工体的愚公移山酒吧,三人乐队的演出曾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上百个年轻人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随意乱撞;以后,他们在星光现场,用一场“功夫派对”完成了音乐上的过渡期。
高原
地下婴儿是这些乐队之中不乏自我觉醒的一支。他们热衷于叛逆的演出,又时常从那些聒噪的声音中抽离出来。高阳、李鹏、沈悦、肖容等来自不同学校的青少年,随意组合,组起了十几个奇特名字的乐队,反光镜便是其中一支。那段时间,五道口的语言学院胡同附近开了嚎叫俱乐部,这个处在违建之间的酒吧,成为了这些年轻人的阵营。在日本NHK电视台的节目和纪录片《北京朋克摇滚乐的故事》中,这些梳着鸡冠头或是刺头的男孩,用极富挑衅的语言形容着他们所生长的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讲,此后出现的一大批乐队,都像是延续着当年的朋克,无论什么风格,这种叛逆似乎一直在主导着他们的音乐。故宫西门的老What酒吧,扩建之前只有十余平方米,屋里站上十几个人已是满满当当,酒吧尽头的那个2平方米见方的水泥舞台,是“80后”新生代的发源地,Carsick Cars、Joyside、后海大鲨鱼等乐队大多诞生在这里,这是他们最初始的舞台。
酒吧的第一任老板是琴姐,酒吧因她的乐队得名,琴姐有点胖,和几个外国朋友组了一支有点融合的乐队,开个酒吧算是自娱自乐。或许是因为这里没有什么门槛,外加上老板豪爽的性格,她总是邀请一些年轻的乐队来这里演出。在2003年前后,这里因为便宜的啤酒和屋外的风景,聚齐了一众玩音乐的年轻人。
记得某个冬天,门口的棉布帘子垂下来,屋里屋外站了几十人,很多人扒着窗户拎着酒瓶站在飘着小雪的屋外。夜晚,南池子大街静得出奇,只有清晰的鼓声和年轻人的嘶吼回响在街上。Carsick Cars的主唱名叫张守望,他涂着黑色的眼圈,像极了the Cure乐队的Robert Smith,很多年前,窦唯刚刚组建他的梦乐队的时候,也在演出前画过类似的妆。当乐队的《中南海》想起时,那些依稀听过这首歌的年轻人狂躁了起来,这一小群享受着秘密快乐的人,陷入了一种原始的躁动。总之,在那段时间里,这些音乐会让你觉得叛逆的青春永远是地下的,是属于边缘的亚文化的。
新裤子乐队在演出现场(李骁 摄)
摄影师马修(Matthew Niederhauser)曾经出过一本名为《首都之音》的影集,其中记录了大量处于地下状态的新乐队,刺猬、新裤子、Click#15的主唱Ricky曾经的乐队Rustic也名列其中。但是几年后,这里的多半乐队和照片中的演出场所,都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2012年后聚集了不同的音乐圈子,老What、D-22、XP、平安大街愚公移山、鼓楼的MAO等演出场所相继消失,“80后”的一代独立音乐人,和小型现场的历史似乎也终告完结。而此时,还没有太多人开始注意到,在互联网上出现了更多的乐队。
2019年3月,新裤子成为了为数不多的登上工体舞台的乐队。那晚,两个小时的演出浓缩了乐队20余年的作品,他们有趣地把自己虚拟成卡通的乐队成员,试图更好地讲述这一代人的故事。当晚,他们第一次演唱了《最后的乐队》,但这并不是他们的离别歌曲,或许彭磊想说的是,那些曾经的乐队已经不再;或许他还想说的是,那些我们曾经固执的审美,也会随着时代消失。在“虽然这音乐还在继续,却和你一样焦虑”的歌声里,乐队漫长的青春期也定格在了这一年的夏天。
(文中部分内容参考、摘录自高原所著的《把青春唱完》以及即将发布的新书。特此鸣谢高原、赵怡文、古逃逃、安帅等,实习生ev、黄晏浩、张佳婧等对本文亦有贡献)
1.《5.1梦回唐朝,干货看这篇!中国乐队的现场,满满都是时代的烙印,它们讲述了几代中国人的故事》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5.1梦回唐朝,干货看这篇!中国乐队的现场,满满都是时代的烙印,它们讲述了几代中国人的故事》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lishi/2058003.html